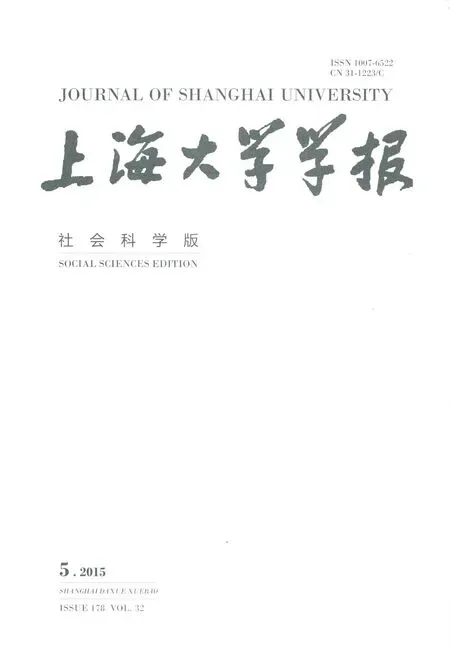苏式美学话语的膨胀及美学研究的偏狭
——“十七年”时期美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
2015-04-02范玉刚
范 玉 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
苏式美学话语的膨胀及美学研究的偏狭
——“十七年”时期美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
范 玉 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北京 100091)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使苏式美学话语拥有了全国性的话语生产机制,成为“美学在中国”的主导性内容,导致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中国获得话语霸权。“十七年”时期的美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是苏式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挤压遮蔽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的过程,因研究视野狭隘和方法陈旧,原本丰富的美学研究被窄化为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反映论美学,简单化为“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贴标签过程,终因学理性缺失造成“中国的美学”研究的偏狭。
“十七年”;苏式美学;美学在中国;中国的美学;研究范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在肃清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思想文化领域的几次大批判,就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询唤。借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逐步取得美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进程中,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研究范式的全面输入,不仅成为这一时期“美学在中国”①“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的美学”是高建平先生最早阐释和界定的概念,本文在此基础上,作为论文的核心概念予以借用,可参阅其《“美学”的起源》《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等论文。的主导性内容,还以其苏式审美话语的霸权式膨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美学”的建构,并以压倒性话语优势构成其底色和时代特色。“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使苏式美学话语具有了全国性的话语生产机制,成为建构“中国的美学”的唯一有效的合法性资源,并在美学研究领域取得话语优势。这一时期的美学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规训下,苏式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逐渐挤压遮蔽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的过程,不仅抑制了西方美学话语在美学学科建构中的合法性,还因研究视野狭隘和方法陈旧,使原本丰富多彩的美学研究被窄化为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反映论美学”,简单化为“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贴标签过程,终因学理性缺失而造成“中国的美学”研究的偏狭。
一、 苏式美学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全面输入
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原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20世纪初美学经由日本传到中国,尽管有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大家的极力倡导和学术实践,但对建国初期的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陌生的。要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立场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进行批判,就必须有一种知识上的积累和研究范式的借鉴。国际风云的变动不居和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需求,使学界把寻求资源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此时的苏联正开展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激辩。国际形势的战略格局迫使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全面倒向苏联。在普遍“向苏联学习”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苏式美学话语体系和研究资料以种种不同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被引进国内,既作为学术资源参与“中国的美学”的知识建构,也作为思想资源参与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致使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占据压倒性的话语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通常被学界称为“十七年”。通过对“十七年”时期美学思想史的审读可以发现,苏式美学话语及其体系是影响中国本土美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就连“美学大讨论”的发生,也有学者认为是“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美学说明”,[1]是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确立苏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主导地位的必然。仔细洞察可以发现,不论是苏联“自然派”美学提出的“美是客观的”思想,还是“社会派”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人化”观提出的“美是客观的”,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关系”中形成的观点,都在中国美学研究和大讨论中有着即刻直观的反应。当时的学人更是有着自觉意识,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我们现在建设美学,必须从马列主义哲学的基础出发;而从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出发,必须以苏联为师”,“边讨论,边学习,边建立,这是我们今后美学工作的道路”。[2]在有意识引进和自觉学习的背景下,国内的报刊都辟有“学术动态”专栏来及时通报苏联美学研究动态。1956年及其后,苏联《真理报》《文学报》《哲学问题》等杂志刊登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讨论文章,都逐渐被介绍进国内。如《学习译丛》1956年10月号刊载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对象的讨论》,《文艺理论译丛》1956年第一辑刊载的特罗非莫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美术》1956年第12期发表的《苏联美术界展开学术讨论》,《学术月刊》在1957年的发刊号中发表的司马舒的《苏联美学问题讨论简况》等文章。除了介绍文章和研究信息,还有大量的国外美学文艺学资料涌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译丛和文选,如创始于1959年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计出版19种)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计出版11种)。创办于1957年的《文艺理论译丛》(到1965年出版17期)和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也在1963和1964年组织专家编写完成。重要的翻译作品,还有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三大卷和宗白华翻译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此外,还有克林兼德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艺术》(未知译,三联书店1951年版)、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鲍桑葵的《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以及贺麟翻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一章《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的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在众多翻译资料中,苏式美学话语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仅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J.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米·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版)、索洛维耶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真译,新潮书店1950年版)和《论托尔斯泰》(林华译,北京中外出版社1952年版;立华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克拉斯诺娃编的《列宁论文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另外,《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和《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第一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赫尔岑的《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等著作都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成为美学和文艺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曹葆华译,东北书店1949年版;《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学书简》,曹葆华、渠建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经过系统的翻译和有意识的推介,均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方面,是大量输入;一方面,是基于国内形势的有意识“挪用”。早在1950年3月由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再版,在选集的序言中,周扬按照中国的标准和本土化要求,重新编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权威的经典谱系:一方面,确立了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到高尔基的国外谱系;一方面,加上了中国的两位代表人物——鲁迅和毛泽东。需要重点提及的是苏联美学家里夫希茨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该书先后于1960年、1963年、1966年分四册翻译出版,是一部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读本,对新中国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册主要包括《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阶级社会中的艺术》《艺术与共产主义》;第二册主要包括《关于艺术史和文学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和文学》;第三册主要包括《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判分析》《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庸俗性和反动思想》《工人阶级政党和文学中的资产阶级风尚》;第四册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诗人们的关系》《英国的社会主义作家》《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摘录)》《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与书信(摘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与文学》。编者采取了文化哲学的视角,目的在于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科学性与合法地位,批驳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谬论,从而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在“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思想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正如里夫希茨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序言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是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新美学”,而此前的任何美学形态(包括德国古典美学)都被归之于“旧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旧美学”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旧的美学或艺术哲学由于历史视野的局限,把旧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归结为无关乎历史的、永恒的“人性之谜”。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基于现实历史的发展来考察社会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敌视艺术和诗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成为艺术繁荣的最大障碍。这些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中影响深远。
审视这一时期“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除偶尔的西方美学翻译资料外,铺天盖地的苏式美学话语作为理论资源,已成为中国学界展开美学争鸣和学科建构的重要外部推手。这一时期的“中国的美学”潜在地体现了西方美学话语体系与苏式美学话语体系的冲突以及两种美学研究范式的较量。在意识形态规训下,苏式美学话语体系不断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甚至直接影响了“美学大讨论”。如“客观派美学”德米特里耶娃的《美的美学范畴》,“客观社会统一派美学”的万斯洛夫的《客观上的美存在吗?》,“主客观统一派美学”的布罗夫的《美学应该是美学》等,论文集如《论苏维埃艺术中的美的问题》(1957)、《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1957)等,在被及时翻译过来后,有些观点和资料就被运用到“美学大讨论”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正是借助苏式美学话语的强势,蔡仪、李泽厚一直占据争论的上风,处于权威的地位。而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高尔泰的“美即美感说”作为上一个历史时段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延伸,在强势的苏式美学话语的挤压下,或处于艰难的守护地位(朱光潜)或被排挤出局(高尔泰)。甚至在“实践美学”的理论缘起上,苏联“社会派”从马克思“自然人化”思想出发,在“社会历史实践”关系上阐释“美”的“社会性”意义的思想,对中国语境中“实践论”美学思想的萌芽与转向都起到了关键的学理支持,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未脱出认识论框架。同时,苏式美学话语的强势,迫使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渐趋完成了对早期西方“直接论”美学思想的根基性替换,这意味着朱先生在批判中基本完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饶有趣味的是,相对于过于强势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朱光潜反倒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的本色。“美学大辩论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促使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根据《费尔巴哈论纲》、《资本论》和《巴黎手稿》以及恩格斯《从猿到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定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要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禁区”。[3]正是朱光潜对《巴黎手稿》的研究而非苏式美学话语的借鉴,使其以哲人的智慧回归了美学之可能的正常轨道。可以说,在几近相似的时段内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既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主观-客观”的认识论框架内展开的一场中苏同步共振的哲学回响,又是一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合法的思想原则的美学批判。不仅蔡仪的“客观典型说”与德米特里耶娃、波斯彼洛夫为代表的“自然派”相近,体现了斯大林时期唯物主义客观反映论的美学主张;而且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说”更与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为代表的“社会派”相似,体现了后斯大林时期美学试图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论的初步美学尝试。当时能脱出苏联美学影响的学人很少,而从背离苏式美学话语的程度,可检验“中国的美学”建构的难度和高度。
从学科建设上看,“美学在中国”的前期主要以西方美学资料翻译和研究范式为主,从20世纪初期的美学拓荒到50年代朱光潜遭到批判为止,主要是对西方美学进行翻译和介绍;此后一直到中苏关系交恶,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研究范式成了“美学在中国”的主导性内容,并以其审美话语的膨胀及其对西方美学话语的压迫和遮蔽,构成了“中国的美学”的底色和主要特色。随着“一边倒”的“全面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俄苏美学大量传入中国,在中国出现了一些以列宁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学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导地位的确立。当时,在美学研究领域,无论是美学课的教学、课程设置、知识建构、教学资料,还是聘请苏联专家讲学,派遣美学专家和学生赴苏交流学习,都是对苏联的借鉴和学习。可以说,“苏联美学经验模式”为“中国的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体制原型”和“理论原型”。[4]从专业设置和教材视角看,50年代可以说是在学术和教育体制上全面借鉴苏联的时代,其时代特征是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高度政治化,受其影响,新中国的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高度政治化意味。不仅马克思主义美学占据学术研究的主导地位,大量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论著,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文艺学研究提供了某种“规范”,尤其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教学与教材建设上具有鲜明的“苏联模式”特征。苏联文艺与政治高度融合的模式契合了当时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全面学习苏联”的思路几乎成为“一边倒”的现实趋势,即使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苏联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还通过“黄皮书”式的“内部参考资料”影响中国的美学研究。当时许多高校的文科教材、教学大纲,甚至院系和学科设置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直接从苏联聘请教师到中国来授课。在教学上基本采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甚至直接用苏联的教科书、教学大纲和教师。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全面输入的苏联理论模式是对中国学界的“殖民”,其后果不仅是毁了那个年代的人文学术,更僵化了在那个年代享有“学术地位”的数代学者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建构,酷似被统一做了“脑外科手术”。
“十七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占据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甚至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是“科学的美学”,才是正确的美学观,才能指导艺术的健康发展,给艺术研究以“科学的理论基础”,给艺术批评以“科学的根据”。但“此马”乃是建立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基础上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有着经过“美学大讨论”平台的意识形态纯洁化的效果,更有着苏式审美话语的全面侵蚀,而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具有理论资源的同构性。在中国美学学科建构中,苏式美学话语已成压倒性优势,强烈影响了“中国的美学”的生成和发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进程中,苏式美学的研究范式“功不可没”。但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也非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作为潜流及其美学史发展的复线结构,成为“中国的美学”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苏式美学话语的膨胀及其对西方美学研究的遮蔽
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苏联被置于“榜样”和“先生”的地位,国内全方位地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运动。翻阅当时的报刊可见,苏联的文艺政策、各种报告、决议、社论、专论等,都及时地在中国得到传播。苏联的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被完整地引入中国。中国的文艺实践和学术研究,不仅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被迫关上大门,而且在对待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方面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尽管中央提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主张,但在实践中却畏首畏尾,成效不大,似乎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苏联一途。在研究中还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甚至在“中国的美学”建构中把“反映论”作为“党性原则”来贯彻,贴标签成了思维惯性。“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语境为维系或赢取‘学术地位’,学界极少有人不想‘活学活用’此(苏联)理论模式。”[5]只要与苏联模式不同,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批评原则相悖,都会被作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予以否定和批判。
“十七年”时期,中国美学界逐渐失去了与欧美学界的联系,单方面地向苏联学习和靠拢,在美学研究上几乎保持了与苏联美学研究同步的话语共振,一些苏联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有堪称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权威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苏联科学院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研究所编)。就教材而言,苏联哲学所、艺术史研究所编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在中国成为一种“范本”,有四个美学关键词:生活、共产主义、艺术实践、审美教育,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美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我们的美学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不断加强同生活、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联系,促进社会主义艺术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繁荣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审美教育。”[6]另外,苏·特罗斐莫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马晶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美学教学体系。可以说,苏式美学研究范式和美学教材,以其权威性和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的美学”建构的重要参照系和主要借鉴目标,全面地影响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发展。
何谓苏式美学研究范式?总体上看,无论是确定美的“自然标准”的自然派美学家,还是明确美的“社会-人的标准”的社会派美学家,都是“以直接的自然科学认识论代替审美地掌握”或干脆“否定自然界事物的审美的客观性”过程中走向两个“极端”。[7]其共同性表现在“对艺术单一的认识论态度”,将美与真相提并论,把美视为认识论范畴,从而把审美感知、审美体验问题纳入到“认识-反映”的单一视角内,并以一种“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始终唯物的、以反映论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得出美客观存在于现实之中。[8]15-16它可以简化为“立场-方法-观点”,是苏联理论模式①所谓苏联理论模式,是指斯大林时代所规定的,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苏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为人格符号的苏共文化政纲。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苏式美学研究范式在“一边倒”的外交环境下,成为“中国的美学”建构的唯一合法性参照系,成为美学研究者竞相借鉴的研究范式。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美学研究基本上陷入“主观-客观”与“唯心-唯物”的论争和贴标签中。凭借深厚的西方美学功底,朱光潜先生意识到把“认识论”硬搬到美学研究中不妥,但由于大气候的意识形态干预和自身思维惯性终究未能超越,其后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鲍威尔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获得新的视域后,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引入自己的美学体系,显现出一种美学研究的新气象,但仍在坚持实践论的同时将反映论摆在首位。
受控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训,这一时期的美学建设呈现出同质化的苏式美学话语霸权的膨胀,在“一边倒”的话语复制与繁殖中,以正宗主流姿态压抑和遮蔽了“西方美学话语”及其研究范式,伴随思想改造的规训背景,在话语和研究范式转换中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形塑与精神改造,进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典范”建构。对苏式美学话语和研究范式的“压倒性”引进,不仅禁锢了中国美学研究者的视野和思维,还使得本土美学研究和讨论在“以苏联为师”的旗帜下,愈发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文艺创作实践,从而陷入概念式的理论思辨和自说自话的境地。因强势苏式美学话语的压迫,西方美学话语基本上失声。朱光潜完全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似乎仅有“主观派”的高尔泰还在坚持,认为美产生于美感,美只有人感受到它才存在,明显脱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模式。他以“人论”为中心的“人化的创造说”在否定“客观的美的存在”基础上所张扬的“美即美感”有其合理性。在高尔泰看来,美之发生,仅有“物象”是不够的,还需另一个重要条件——“审美的人”。[9]如其所说,当年“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都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10]正是高尔泰以其诗性的笔触和对美的现场感的描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认识论的桎梏。这主要源自高尔泰继承了中国美学传统中“情景合一”的思想,虽在美学思维上未脱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但体现出挣脱狭隘认识论窠臼的努力。可以说,高尔泰的美学思想是“苏式美学话语体系”之外的“中国的美学”中的“一枝独秀”,它潜在地接通了此前20世纪美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美学在中国”的传统和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西化文论模式”的余韵回响,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全面“苏化文论模式”的霸权冲击下,“不甘于失败而徘徊不忍离去”。西方美学话语虽声音微弱,但并非完全销声匿迹。这一时期学界还发表了几篇研究康德美学的重要论文,如宗白华的《康德美学原理述评》(《新建设》1960年5月号)、朱光潜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蒋孔阳的《康德美学思想——简评〈判断力批判〉》(《文汇报》1961年7月4日)。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国的美学”研究失去了国际视野,这种既排斥西方话语又否定传统话语的近乎自我封闭的文化态度,除了无产阶级式的空白地基和主观臆造的空中楼阁,就只能追随和模仿苏联美学话语和研究范式了。在与本土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结合中,制造了一系列革命激进的“乌托邦奇观”——抽离人性的丰富性,拔民族文化的根脉,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的杂糅,不食人间烟火的纪念碑式的美学巨制,所有这些形成了美学宏大话语和概念的笼罩。作为结果,在罅隙中建构的“中国的美学”,几乎复制苏式美学话语而打上同一性的底色。朱光潜因深厚的西学功底,成了被批判和清除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蔡仪、黄药眠、吕荧等人都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宣传者,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译介苏联文论。李泽厚、高尔泰是在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这决定了当时大多数美学研究者对“苏式美学话语体系”的情有独钟或心向往之,在对苏式美学话语和苏联文艺的“师承”中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美学”的时代特色。某种程度上,单一性的“话语挪用”和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并没有使“美学在中国”的内涵更丰富,反而因对“西方美学话语体系”的压抑和遮蔽,使“中国的美学”研究愈加偏狭和逼仄。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赓续西方美学、文论研究的传统,“中国的美学”才再度融入世界美学图景,迎来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美学热”。美学也成为思想再启蒙、人性解放、真理大讨论及催生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与舆论资源,从而担负更多的文化使命。
三、 国际视野的缺失与主体性意识的不足
审视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和学科建构,一方面要立足于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动起来的巨大革命激情的美学张扬,一方面要对照世界范围内的美学发展实际,以及两者之间的落差与错位。什么美学观点和美学资料能进入新中国和如何进入新中国,需要从内外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说,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学史,有两个坐标:一是纵向的史的梳理,一是横向的现实对照。两者相互观照可能会对这一时段的美学状况有一个科学的、合理合情的定位。
这一时期的文艺政策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灌输,建构党在文化艺术上的领导权,在文艺上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颓废、落后的倾向,要求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上,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应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规训。在“一边倒”地引进苏式美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日丹诺夫式的批判风格和话语言说方式”一并被中国文艺界和美学研究者“吸纳”了。在“中国的美学”建构中,特别是“美学大讨论”中,从朱光潜先生自我批判的宣言“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开始,到最后大讨论的偃旗息鼓,整个过程中无不充斥着“日丹诺夫式语言”的暴力、粗鲁、专制、嘲讽等词汇。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像“魔杖”一样的令人着迷,激励着每一个参与者都身披“马列”的伪装在充满硝烟味的“战场”上四处追寻“猎物”,在恶狠和痛快的“批斗”与“宰制”中完成政治身份的自我确立与角色认同。尽管其间有贯彻“双百”方针的要求,但在“一体化”话语的规训语境中,它也仅是文化政治化的一个注脚。
美学研究固然不能脱出时代过度政治化的大潮而独善其身,但学者主体性意识的不足愈发加剧了这种不堪,甚至使美学研究现出一种“丑相”。“中国的美学”的这种扭曲跛足的发展,不仅进一步拉大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距,西方国家正经历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讨论,而“中国的美学”虽置身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却在古典式命题“美是什么”中打转转;同时,也把中国的文艺发展逼向单极性维度,人似乎都成了“抽象的人”“真空的人”,从而限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为“文革”期间文艺的极端化发展提供了逻辑。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确实存在“时代的症状”,但更有着研究者主体性意识不足和缺乏担当的精神品格,加之研究者美学修养良莠不齐,美学学科基础薄弱,缺乏多元化的美学资源和理论滋养,导致狭隘化的美学研究基本上遵循列宁所阐明的“认识论-反映论”原理,使“美的本质”问题讨论始终囿于“主观-客观”与“唯物-唯心”的贴标签式的身份认定中。对于这种狭隘化的苏式美学研究范式,苏联美学家有过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把意识反映现实的过程本身理解为机械的、镜子似的复制,而是理解为复杂的、辩证矛盾的过程……人的审美关系历来是价值关系,没有价值论的态度,要认识它原则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可能把认识论态度同价值说态度结合起来,而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不协调。我们有时片面地看待美学同哲学的相互关系,仿佛美学只同认识论相联系。”[8]17,20-21对此,中国美学界也有过诸多反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方法论原则很丰富,认识反映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向度,与美学更为相关的是价值论思想。正是对经典作家丰富思想的理解的匮乏和片面,导致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窄化,加之缺乏必要的美学知识和文艺修养,导致“中国的美学”建构大多套搬马列主义话语,常纠缠于概念,陷入形而上的玄谈。如蒋孔阳批评的:“当前美学讨论的问题还不仅在于兜概念,而是对概念还没有钻进去,争论的双方常常对概念缺乏共同的理解”,“学习美学应该先学哲学史和美学史,摸清了美学发展的线索,才能使学习有了基础和出发点”。[11]可以说,当时处于“移植”和“复制”苏式美学话语的“中国的美学”的研究水平,不仅不及苏联,还处于苏联美学研究的末端(未能突破狭隘的认识论桎梏)。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另外,要深刻反思研究视野的狭隘。“十七年”时期,可以说仅有“苏式美学话语”及其资料成为中国美学建构的合法性资源,一方面,因缺乏高远的国际视野(当然有政治外交的主因)而导致与西方学界交流中断的“隔”。就西方美学的输入而言,经由王国维、朱光潜等大家的研究传播,在国内已有相当基础,不仅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使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逐渐被认可。朱光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把西方流行的现代美学理论,如“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等介绍到国内,并出版了《悲剧心理学》等专著。但在建国后“一边倒”的苏式美学话语体系的压迫下,西方美学被置于“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甚至被视为需要批判和清理的“反动思想”,可以说西方美学研究范式被苏式美学研究范式遮蔽了,一度造成中国美学现代性的中断。另一方面,还因缺乏深邃的历史眼光导致的虚无主义态度而使其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相“隔”。在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被嵌入封建的镜子中,其性质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一样,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加以重新清理和批判。同时,因缺乏宏阔的现实感,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当下生活状态或者文艺实践相“隔”。无论是西方现代美学还是中国古典美学,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下只能被视为“异端”,沦落到被批判和清除的下场。因只见概念和宏大话语,而无视人情冷暖和生活细节,结果经由列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折射”,美学几乎成了一种认识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粗暴地把“美”实体化为客观现实的反映,把美感视为美的反映,从而在美是“主观-客观-主客观统一”的闭环中打转转。以上反思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学术研究视野,不能太狭隘,文化发展和学术进步是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已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拐点,我们不再单纯地和国际接轨,而是已经融入甚至就在世界中。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文化的对外开放水平,这要求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
回到研究现实,当时大多数学者遵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主要基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文本,可谓“惟马是举”而又言“马”非“马”,从而带有明显的“苏式美学话语”的色彩和印记。因着政治教化的外因和主体性意识不足,急于标榜或者囿于“政治正确”而愈加远离审美活动实践,陷于“规定动作”中争吵不休。美学研究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神实质,还在“唯马是举”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中抛弃了原本丰富的民族的和传统的美学资源。正如诸多学者早就指出的在理论阐释上“缺乏原创性”,美学讨论和当时的研究多是“宏大词语”,在远离美学理论和精神品格的概念中兜圈子,而缺少真正的学术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若放在比较视野中,这种认知即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在主义的喧嚣背后是“知识的贫乏、思想的贫乏、学术的贫乏、学科的贫乏”。[12]反观国际美学研究则是硕果累累,即使面临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挑战,依旧有阿多诺、伽达默尔、杜威、巴尔塔萨等美学研究大家的体系性美学大作问世。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基本处于意识形态规训与时而浮出历史地表的“双百”方针的微观松绑间的多向复杂曲折的互动,从而制造了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美学奇观”——“学术外衣政治里子”的精神符号,体现了强势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挤压和话语笼罩。在研究范式的建构上,哲学思维方式的禁锢、美学知识的匮乏、思想的僵化和认识论模式的束缚及其研究视野的狭隘,使得有着丰富人文价值内涵的“美学何为”的本体论追问,下沉为机械性的“美是什么”的认识论追问。学科的错位使得对“美的本质”的哲学运思始终局限在“主观-客观”的古典认识论框架中,难以脱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而其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不仅与国际主流美学研究成果有相当的差距,就是与此前的王国维、鲁迅、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研究相比,也嫌不足,没有形成美学学科坚实的知识论基础,使得“美学在中国”命运多舛,步履蹒跚,导致“中国的美学”学术水准和理论层次不断下沉,出现中西美学思想源泉的断裂以及当代美学的长期空缺。对于这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流弊,不仅要在深刻反思中不断进行“解毒”,还要对其生成的土壤和历史局限,特别是学者主体性意识的不足保持足够的警惕。时刻葆有现代性意识,深刻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建构权力的边界意识和文化空间的自主意识,使美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担负起引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使命。
[ 1 ] 赵士林.对“美学热”的重新审视[J].文艺争鸣,2005(6):91-102.
[ 2 ] 朱光潜.把美学建设得更美![N].文汇报,1959-10-01(7).
[ 3 ]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534,649.
[ 4 ] 史磊,王确.新中国美学课发生进程中的“苏联经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3):113-116.
[ 5 ] 夏中义.“脑外科手术”是如何实施的——追问“苏联理论模式在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33-37.
[ 6 ] 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艺术史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M].陆梅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1:2.
[ 7 ] [苏]亚·伊·布罗夫.美学:问题与争论——美学论争的方法论原则[M].张婕,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9.
[ 8 ] [苏]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9 ] 高尔泰.论美[M]∥文艺报编辑部.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33.
[10] 高尔泰.寻找家园[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94.
[11] 探讨当前美学研究中若干问题 部分美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N].文汇报,1962-05-18(1).
[12] 王建疆.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2(2):22-26.
(责任编辑:魏 琼)
The Expansion of Soviet Aesthetic Discourse and the Bigotry of Aesthetic Studies——One of the Studies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during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FAN Yu-gang
(FacultyofHumanities,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Beijing100091,China)
The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and a host of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fered nationwide discourse generating mechanisms for the Soviet aesthetic discourse which became the dominant content of “aesthetics in China”, leading to the discourse hegemony of Soviet Marxist Aesthetic Studies in China. The aesthetic research during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o some extent a process of the Soviet aesthe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squeezing and overshadowing the Western aesthe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Due to the narro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outdated research methods, the originally diverse aesthetic studies were narrowed down to the “reflective aesthetics” based on philosophical ontology, simplified into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and “materialism-idealism” labeling process, and finally reduced to the bigot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curred by the lack of rationale.
Seventeen-Year period; Soviet aesthetics; aesthetics in China;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 paradigm; bigotry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5.005
2014-08-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11)
范玉刚(1969- ),男,山东临邑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学室副主任、教授。
B832
A
1007-6522(2015)05-00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