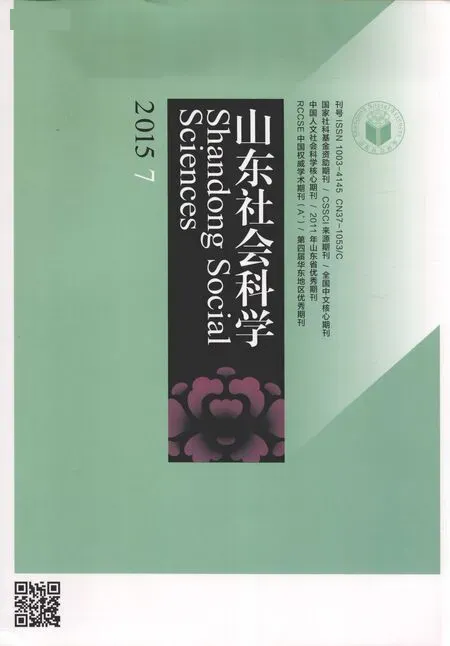论明治末期(1903—1912)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2015-04-02张卓识徐冰
张卓识 徐冰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024)
论明治末期(1903—1912)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张卓识 徐冰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吉林 长春 130024)
明治初期古典中国文化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修养依然被基础教育界重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则冲淡了古典中国在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比重,以宣扬国威、增强民族自豪感为旨归的内容有大幅度增加。对古典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中国的轻蔑相叠加构成了明治日本人之中国认识的特点。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思想界,更作为一种时代印迹呈现在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中,并作为一种根植于幼小心灵中的“思想”塑造了青少年对中日文化价值的认识。小学教科书中对日本两次对外大战的高调宣扬,实际上是向青少年灌输个人英雄主义和军国主义,激扬作为世界强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直接塑造了日本少年的中国观和战争观,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对华步步紧逼、最终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遗毒甚剧。
明治末期;日本小学教科书;中国形象
一
江户时期,日本民众因阶级的差异所受教育也大不相同,武士家的孩子会去藩学学习,主要以汉籍为教课书,而庶民(农、工、商)家的孩子却在寺子屋(假借自家民房为校舍)上课,主要学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1872年,日本学制遵循“推翻旧的封建制度,建立近代市民社会”①唐沢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80年版,第52頁。的精神,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献,其中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书籍占绝大部分。换言之,教育界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自东徂西”的转变。尽管1879年,日本颁发教育令主张教科书回归重视道德教育;但1886年,随着学制改革的推进,教科书开始实施检定制,教育目标也定位为“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成为一等国,富国强兵”②海後宗臣·仲新:『教科書でみる近代日本の教育』,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71頁。。此后,因近代国际体制的重整、中央集权的深化、教育敕语的颁布、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于1902年确立日本教科书国定制,即各学校教师及学生所使用的教科书均为国家指定机构编写,③中村紀久二:『教科書の歴史——明治維新から戦敗まで』,岩波書店1992年版,第128頁。教科书编写松散多元的状况终结,国家成为唯一的权威。明治末期日本改用国定教科书,小学作为基础教育,所有青少年享有四年的义务教育权利,即至少有四年的时间接触教科书,接受其中的知识、思想教育的熏陶,无疑对当时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小学课程设置来看,其科目主要有修身、国语、算数、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体操、手工;而具体到教学计划设计上,又以国语、修身、历史、地理的授课时间为最多。①据教育学術研究会:『改訂国定教科書新教授細目』,同文館1910年版统计得出。可见,这四类课程在形塑青少年世界认识、养成民族精神的意义上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本文对有关明治末期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中国认识之分析也将基于对此四种课程的考察展开。
具体到教育领域,历史上,作为日本的文化母体国,明治时期以前中国一直都是其效仿的对象,所以使用的教科书皆为汉籍。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长期以来,思想领域尊崇中国的取向受到质疑,明治维新以降,从器物到制度诸层面,西方取代中国儒教思想成为其追随、效仿的对象,作为福泽谕吉笔下“半开化国”的中国反倒成为其窥探的对象,“脱亚入欧”论一时间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追求。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因译介西籍而崛起”②陆晓芳:《晚清翻译的实学性——南洋公学译书院外籍汉译考论》,《东岳论丛》2014年第12期。,汉籍被西方书籍所代替,主要有中村正直译的《西国立志编》、箕作麟祥译的《西泰劝善训蒙》、福泽渝吉译的《童蒙教草》、阿部泰藏译的《修身论》等等,由此可见在此期间日本极力学习西方,同时排斥中国古典文化。而1877年以后,日本教育政策根据“教学圣旨”主张回归中国儒教思想教育③中村紀久二:『教科書の歴史——明治維新から戦敗まで』,岩波書店1992年版,第43頁。,所以教科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中国儒教方面的内容又逐渐增加。例如,《礼记》《左传》《中庸》《论语》《小学》《朱子》等汉籍以及陶侃、杨震、范纯仁、王仲舒、张裔、吴奎等中国古典人物均被收录其中。从当时修身教科书所引用的中西方的人物比例来看,中国人物有45.9%、西洋人物占54.1%。④唐沢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80年版,第108頁。由此可见,作为儿童基本的文化修养,中国古典教育(尤其是儒学经典教学)在日本基础教育阶段是不可或缺的。但随着检定制的开始,有关中国内容的记述明显逐渐减少,到明治末期,教科书中出现的中国古典人物一共9人、分别为廉颇与蔺相如、张良与韩信、勾践与范蠡、诸葛亮、孔子与孟子。而仅“修身”一科教科书中,西洋人物就提到了13人⑤唐沢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80年版,第237頁。,中国人物只有廉颇与蔺相如在一篇《度量》⑥海後宗臣:『日本教科书大系·近代篇·第三卷·修身三』,講談社1978年版,第51頁。的课文中有相应的描述,可见相差悬殊。其原因从《教育公报》1904年9月刊登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我之前看过一本教科书,其中有夸大自傲之嫌的报道,作为读者不禁让人回忆起那些支那人鄙视外国人。然而这本书(此时期的教科书)所叙述的合乎义理,日本作为小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及欧洲强国,所以孩子们要以此为目标全力以赴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⑦唐沢富太郎:『教科書の歴史——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創文社1980年版,第237頁。。而对中国古典的排斥则是中日甲午战争以降之事,有评论认为“支那故事很多都夸大其词,而且还是我们的敌国,不应采取”⑧载『教育時論』1894年7月25日号。转引自金山泰志:『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民衆の中国観』,芙蓉書房2014年版,第39頁。。
另外,尽管篇幅不大,但这一时期的日本小学教科书对现实中国的风土、物产、人情之常识还是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介绍。例如,第一期国定国语教科书《高等小学读本·卷二》第六课《海之话》中,简单地介绍了中国黄海;第二期国定国语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卷九》第十五课《冠物》中,对中国的帽子有所描写;第二十五课《货币》中提及了中国古代的货币。《寻常小学读本·卷十》第二十三课《家畜》介绍了中国人喜欢吃猪肉。
二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关于此战的开战缘由,日本学者伊藤痴游在《被隐藏事实的明治内幕史》中作出了中允的论述:“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警备舰从蔚岛出发,看到四艘支那军舰从渤海方面出动,警备舰队司令官立即乘入高千穗。海军唯一的奇才坪井少将批准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向敌军开炮,战争开始。”⑨伊藤痴遊:『隠れたる事実明治裏面史続編』,大同出版社1939年版,第389頁。据此,是非正义立判。作为日本近代史上首次对世界大国之战的胜利,小学教育界也作出了迅捷、热情的回应。课文《明治二十七八年战争》称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清国背弃与我国的约定”,并“在韩国丰岛,向我军军舰开炮。我国军舰轻而易举击败了敌军的军舰,但由于清国太蛮不讲理,最终我国派出很多军队,与清国打起仗来”①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六巻·国語三』,講談社1978年版,第477頁。本文中的课本引文均由笔者自译,不另注。,而发动战争意在保护日本的独立②泉哲:『国定教科書の国際解説』,南光社1924年版,第118頁。。开战后,丰岛海战、成欢战役、平壤之战、黄海海战、旅顺战役、辽东半岛之战,威海卫战役等战役均以中国失败告终。文中提到:“旅顺口攻难易守,但我军只用了一天就攻下来了,大挫敌军的士气。”教科书中并没有详细地介绍战争进程,只是宣扬在世界强国日本面前,向素的“老大国”中国不堪一击,此战使日本“在世界中名声大震”。《小学日本历史·二》(1903年)第十七课《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中,日本虽要“与中国共同实现东洋和平,但中国并没有兑现”,并以“被清舰伏击”为导火索,由此展开海战。其结果是日本“国威大振,西洋诸国终于知道其真正的价值”。以世界大帝国为对手的胜利,高扬起一种使人骄傲、激昂、舍我其谁的民族主义情绪。
此外,还有很多课文提及了中日甲午战争。例如,《国定国语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五》的第十八课《黄海之战》、《国定国语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七》的第十六课《开港场》、《国定国语教科书寻常小学读本·八》的第十九课《地球(一)》、《国定国语教科书高等小学读本·一》的第四课《靖国神社》、第五课《钦佩的母亲(一)》,其意旨与前述内容大同小异,兹不赘述。战争结束后,爱知县对于小学生的游戏项目设置进行了调查。在当时青少年的游戏中,角色扮演的游戏颇受孩子们喜爱。其中有关战争的模仿更为突出:“两组分别模仿日本军与清国,双方的强弱毋庸置疑日本军必然胜利,所以谁被分为清军都会感到厌恶。”③井口和起:『日清·日露戦争』,吉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183頁。由此可见,中国作为不堪一击的“无理弱国”形象已经深植于日本青少年思想意识中。
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及其胜利深刻地影响了小学课本的内容构成和政治导向性,教科书的编者也与政界开展责任的推诿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小学教科书中收录的很多战争题材的课文,目的都在于“论证与宣传日本军队及军事行为的正当性及永久性,即美谈化”④中内敏夫:『軍国美談と教科書』,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20頁。。这一倾向甚至影响到了对此前侵华历史事件的论述倾向。在第一期教科书中,课文《征伐台湾与西南战争》对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作出了如下评述:
当时,台湾是清国的领地,但清国视蕃人为化外民,完全不顾虑。佐贺之乱平定后,日本政府委任西乡从道征伐台湾的蕃人。然而,清国马上提出异议,最终,经过谈判后,清国赔款,日本收兵。《小学日本历史》(二)第十五课⑤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一九巻·歴史二』,講談社1978年版,第489頁。
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后,日本与中国的地位平等化,与此同时也企图对其进行侵略。日本以台湾原住民杀害了琉球住民为借口,向台湾出兵,并谎称这次行动是义举,自此开始了“大陆政策”。台湾事件是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首次碰触,以中国失败、日本胜利告终,“清国给予日本绥靖的态度,使日本有了优越意识”⑥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共同印刷工業株式会社1994年版,第112頁。。而在文章题目中使用“征伐”一词,也有着特殊用意。“征伐”一词一般用于文明国惩罚野蛮人种的不法行为,平等国之间是不能使用该词的。但在古代,除自己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被视作劣等国,战争时更是常用“讨伐”或“征讨”等词。⑦泉哲:『国定教科書の国際解説』,南光社1924年版,第96頁。将这一词汇套用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论述中,在侵略/被侵略、加害/受害等二元框架之外,隐含的是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梳理出的“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王升远在考察日本文化人北京天桥体验的文章中指出,日本文化人在贬损中国、“使其形象具有显而易见的漫画化特征的同时,通过自我反视的确认,赋予自身以优越性,将自身的价值正向化,使之以美好幻想的形式凸现出来”⑧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将这一论述置换在本文的论述脉络中,依然成立。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担心中国领土被其他列强瓜分,所以做好准备随时等待有利时机。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日本分割中国的机会随之而来。因此日本教科书中不会错过向青少年灌输国家意识形态的良机,所以有课文详细地介绍了义和团运动。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的本意只是一场驱逐宣教士、“扶清灭洋”的运动。但文中提到:“我国公使馆除了馆员,还有留学生、技师、新闻记者、照相师等等一共三十三人组成义勇队,与最先攻入京的水兵二十四人一同尽力防御。”最后,“我军已经攻破城门,涌入城内。”⑨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第六巻·国語三』,講談社1978年版,第609頁。从当时各国列强的兵力数据统计表可以看出,日本军的人数最多。①井口和起:『日清?日露戦争』,吉川弘文館1994年版,第14頁。可见日本对于这次战争并非没有准备,而是随时等待机会从中国获得利益,换句话说,“日本政府表面是保护日本国民,而实际上是应付列强派出的陆军,企图与强国保持势均力敌。②山口一之:『陸羯南の外政論:義和団事変と善後策』,《駒沢史学》1986年05期,第4頁。而且,几乎每篇课文的结尾都会出现“我大日本帝国威名世界”、“我军超越了其他国军队,总是勇往直前,因此大家都称‘日本军真是神勇’。从此威名世界”等类似的字样。宣称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已从“强国”沦为“老弱国”,日本看到“老弱国”的惨状不禁心生怜悯,为了保全人民不惜派出最多的士兵,却在最后向中国索取最少的利益。③石井国次:『国民の覚悟:戦時教育』,富山房1904年版,第24頁。实际上,日本在最后没有索取更多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保全中国,而是日本没有与列强对抗的实力,被迫撤兵。为了能在日后取得更大利益,他们希望“中国这块肥肉完整地留在自己身边”④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中国此时已是不堪一击,教科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无非是一种日本可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并可从历史上的“先生”——中国这里得到利益的傲慢表现。与此同时,教育管理部门要求在讲授这些知识时教师应注意“我国教育者向学生简单地讲述排外思想是多么不合时宜,他们的顽固党如何消极面对时势、耽误国政。决不能过分地只讲拳匪的粗暴、北京政府的蛮横与清兵的残暴”⑤金山泰志:『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民衆の中国観』,芙蓉書房2014年版,第48頁。。由此可见,教育界已经料想到教师在讲述此次事件时的侧重点,因此不失时机地适时提醒,保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一表现是将侵略战争作“合理化”论述的表征。此外,《寻常小学读本·六》(明治三十六年)的第十九课《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二)》、《小学日本历史·二》(明治三十六年)的第十七课《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的课文中也对此次事件简单进行了记述。
三
明治末期,日本一共经历了两期国定教科书的使用,从形成背景来看,之所以修订第二期除了一些社会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与沙俄帝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领土上为争夺中国的领土而进行的战争,大批中国人民遭受屠杀抢掠;而此时日本却无视于中国的立场和利益,告诫清政府要保持中立态度,以保证国内治安。为了宣扬日本的国家主义,斋藤斐章主张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东洋史⑥这里的东洋历史指的就是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亚洲历史。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日本史和世界史就足够了。⑦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1895—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因此,第二期国定教科书中记述的中国形象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修订版寻常小学日本历史·卷二》中,虽然有《征伐台湾》与《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的描述,但对中日交涉的部分都一笔带过,反而是对日俄战争大篇幅地加以叙述。这其中的原因通过陆军少佐寺家村朔月的一席话可以得出答案:“日清战争中旅顺只用了仅仅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来了,这无疑说明支那军队的不堪一击,无论支那军队如何不堪一击,俄国的军队如何强大,日清战争中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来的,现在却五六个月没有拿下来真是不可思议。”⑧转引自金山泰志:『明治期日本における民衆の中国観』,芙蓉書房2014年版,第115頁。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在日本的视野中,中国已经以沙俄帝国为参照,进一步弱化。例如在《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中讲述了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战争胜利后,中国已从原来的“先生”沦落为现在的“弟子”。日本更是以保护“弟子”为由与英国同盟,却以俄国无视其存在为由,与俄国开战,最终成为战胜国。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大战”。另一方面,日本以保全东洋和平为名,侵略亚洲,尤其是中国,并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视此次战争是因为俄国在朝鲜及南满洲势力的扩大威胁到了日本的独立,所以才要驱逐俄国。⑨泉哲:『国定教科書の国際解説』,南光社1924年版,第118頁。换言之,认可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日本都是出于自卫而被迫开展的。借蔡元培在《中日外交史》中的表述:“在名义上,为日本代俄国悉有辽东租借地与东清铁路所获之一切利益;然试阅附约内所载,则日本于无形中已大扩张其利权于朴资茅斯和约范围之外,而侵占我国主权颇巨。”(10)吴敬恒、蔡元培、王岫庐:《新时代史地丛书——中日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0页。
此外,教材中收录了较长篇幅的《橘中佐》(《寻常小学读本·卷八》)。这篇课文主要描写了日俄战争中牺牲的“军神”——陆军中佐橘周太,即使“敌人的弹如雨下般。中佐的右手有一处受伤,但丝毫不畏惧,左手持军刀激励自己的士兵,最终赶走山上的敌人,八月三十一日凌晨插上日本的国旗。”之所以称其为“军神”,是一种古代个人主义的英雄崇拜的体现。①中内敏夫:『軍国美談と教科書』,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42頁。在这一历史、思想脉络下,为日本、为天皇尽忠是极其崇高的。教授明细中写道:“本文重点:要介绍日俄战争与两大军神;橘中佐的生平;首山堡的攻击与占领;橘中佐的英勇。教授上注意:要简要说明日俄战争的原因;培养学生忠勇的心”②教育学術研究会:『改訂国定教科書新教授細目』,同文館1910年版,第83頁。。另外进入教材的著名人物是乃木希典,出现在《水师营的会见》(《寻常小学读本·卷十》)中。之所以使用这篇课文意在“体现皇军的正义,使读者领悟真实的面目,培养一种大国民的胸襟”③教育学術研究会:『改訂国定教科書新教授細目』,同文館1910年版,第21頁。。社会主义思想诗人秋田雨雀在自传中写道:他在年少时,军国主义编造的诸多爱国英雄形象对他具有极大影响,所以他也曾是一个可怕的军国主义者。④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页。由此不难窥知,此文并未直接描写对中国的印象,但以“最终赶走山上的敌人,八月三十一日凌晨插上日本的国旗”为标志,日本赢得了战争。而这场发生在第三国领土上赤裸裸的践踏和侵略却被美化成“保全清国国土”。
以上通过对日本英雄人物的介绍来间接地描写日俄战争,宣扬日本的国威。另外也有课文讲述从中国取得的利益,例如课文《南满洲铁路》(《寻常小学读本·卷八》),主要描写了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南满铁路的权益。其中,特意提到了“街道起名大山通、儿玉町、乃木町等等,主要是为了纪念明治三十七八年战争”、“旅顺线从大连的下一站臭水子分支,可以到达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非常有名的旅顺口。日俄战争中,俄军把此处作为海军根据地死守,我军苦战十一个月终于将其攻下。其后方的群山洒满我国同胞的鲜血。”课文虽然看似没有涉及日俄战争,但教师讲授注意事项中规定须讲述取得南满洲铁路的原因;南满洲铁路的便利及对此身为日本人应有的觉悟。⑤教育学術研究会:『改訂国定教科書新教授細目』,同文館1910年版,第123頁。而且从课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无非是抢夺中国的土地,两国侵占中国领土,却因一方从另一方手里抢赢而拿来炫耀。另外,文中提到“清国政府在此安置总督,监督整个满洲,我国也安置总督领事。在这附近有很多我国在留居民”,对“总督领事”这一外交机构的设置之强调,事实上是向小学生们提示:通过侵略战争而获取的在他国的权益已经稳固化,以此增强日本人作为世界强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激扬民族主义情绪。
从以上军事题材的课文不难看出,第二期教科书的涉华部分主要与日俄战争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前就赶往中国的司督阁在自传《奉天三十年》中说道:“打败了一个大国的日本是最优秀的,支那是可以无视的。这种脸色表明他们不是救世主,而是以胜利者而来的,他们将支那人视为被征服者,对之持有轻侮之念”⑥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1895—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四
通过本文的考察,不难看出,如果说明治初期古典中国文化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修养依然被基础教育界重视;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则彻底冲淡了古典中国在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比重,以宣扬国威、增强民族自豪感为旨归的内容有大幅度增加。著名学者安藤彦太郎指出:“对古典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中国的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并批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旧称“支那学研究”)存在着古典中国与现实中国分裂的“非连续性”倾向。⑦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卞立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思想界,更作为一种时代印迹呈现在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中,并作为一种根植于幼小心灵中的思想影响着青少年的中国观和战争观。历史学家江口圭一将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总结为“对英美协调主义”与“亚洲门罗主义”对决、后者最终赢得胜利的历史。⑧江口圭一:《1931-1945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小学教科书中对日本两次对外大战的高调宣扬所培植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军国主义倾向所影响的绝非秋田雨雀一人,而是几代人,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对华步步紧逼、最终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遗毒甚剧。
(责任编辑:陆晓芳)
I0-03
A
1003-4145[2015]07-0094-05
2015-04-20
张卓识,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徐冰,男,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日教科书冲突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0BGJ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项目编号:12CWW01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文化人在华北沦陷区的侵略活动及其涉华创作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ZX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项目)一等资助“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近代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项目编号:2014M560285)、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项目“文学、学术视域中侵华时期日本对华思想战、宣传战”(项目编号:140904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