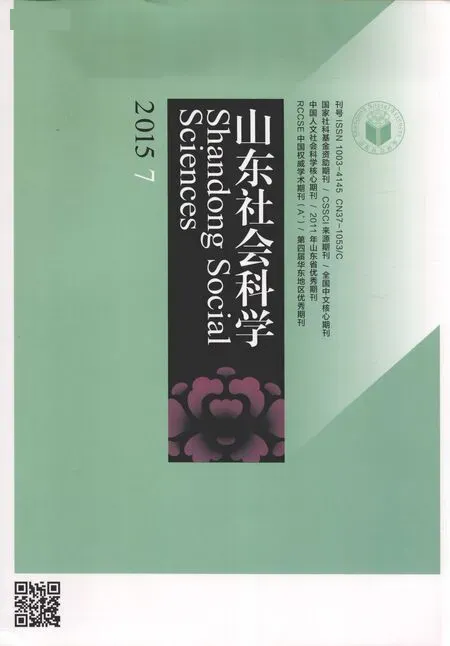通往近代白话文之路: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之考察评价
2015-04-02段怀清
段怀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通往近代白话文之路: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之考察评价
段怀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的语言实践或语言策略,实际上是对他们宣教策略的一种体现与落实。他们对于官话或白话及白话文的“发现”与借用,并不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就地取材”,而是与他们基督教化中国与现代化中国的终极目标相一致的整体策略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侧面。而美国传教士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率先明确提出以官话作为基督教中文文献的语言工具的主张,不仅促成了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更为集中且大规模地讨论这种“新语言”,而且也促成了《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与出版。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在思想心灵层面及现实日常生活层面双重关注并致力于不断改进提升的新语言,不仅成为晚清中国话语结构及语言结构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亦关联着后来传播五四新文化的现代语言并为其提供了近代语境和资源借鉴。
富善;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官话;白话文;语言策略
语言问题(尤其是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几乎是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术语问题”之外所遭遇到的另一巨大挑战。这一挑战同样关涉到基督教的本地化问题,甚至还关联着一种独特的语言政治——基督教到底是一种仅仅面向知识阶级或权贵阶层的宗教,还是一种亲近更为广泛的普通大众之福音?
如果说语言问题早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时代就已经引起这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们的关注,鉴于他们当时多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教,尚未深入到广大的内陆地区,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生成足够数量的面向中国普通读者听众的书面文献之迫切需要,譬如各种形式的宣教小册子、赞美诗以及《圣经》中文节译本或选译本等,尤其是他们还没有与中国的知识阶级展开足够必要的接触,对于这个阶级或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以及语言状况,还缺乏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了解,推而广之,对于中国的整个语言状况同样缺乏基本认知,语言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亦就尚未真正全面展开。因此,我们在这些传教士的中英文著作,尤其是中文著作中获得的语言信息或者语言观点,其实是充满矛盾的。这一点从《圣经》“委办本”的生成过程及最后文本中亦可见一斑。在某种意义上,以方言白话为日常工作口语,以文言文为主要文本翻译及书写语言,基本上为1870年代之前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尚能接受的语言组合选择,甚至于一种语言策略。①有关新教来华传教士在汉语语言尤其是各种方言研究方面的进展状况,其实从《教务杂志》上面的相关报道信息中亦可知一斑。譬如1872年1月开始,《教务杂志》上明显增多了来华传教士们研究汉语、中文以及各种地方方言的成果。其中1月份内封中就广告介绍了鲍德温的《福州方言指南》和湛约翰的《英语—广东话字典》。不仅如此,在该期最后一页的“出版信息”一栏中,更是介绍了一系列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有关汉语语言及汉语方言的著述,其中包括卢公明两卷本的《汉语词汇手册》、威廉臣的《英华词汇》、麦都思的《英华词典》、马礼逊的《汉语词典》、合信的《医学词汇》、艾约瑟的《汉语语法及进级课程》、麦都思的《汉语对话》(修订版)、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等。这些著述表明,语言问题尤其是方言问题早已经引起传教士们的关注,但如何因应中国的语言现实,尤其是如何确立传教士们更为清晰且具有前瞻性、通用性及可操作性的语言策略,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召开之前,似乎还没有最终成形。
但这种混合式的过渡性语言策略,在1877年5月中下旬召开的第一次来华传教士上海大会①第一次新教来华传教士上海大会,于1877年5月10日—24日在上海召开。上遭遇到了尖锐的批评,一种更为清晰、更为明确且更为单一的语言策略被揭示了出来,这种语言策略的核心内涵,就是一种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白话以及以这种白话为基础所形成的书面语言——白话文。而最为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语言或语文主张者,就是美国传教士富善(Rev.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当然在此次大会上尚有丁韪良(Rev.W.A.P.Martin,1827—1916)、鲍德温(Rev.S.L.Baldwin,1835—1902)两人,亦从不同侧面回应了富善的报告②鲍德温的报告为《基督教文本,已做了的以及还需要去做的》(Christian Literature,What has been done and what is need),丁韪良的报告为《俗文学》(Secular Literature)。比较之下,丁韪良的报告对富善的正面回应甚至赞同更为明显。鲍德温的报告时间为1877年5月16日上午,也就是大会开始后第三日,而富善和丁韪良的报告紧随其后。这似乎亦表明,直至1877年上海大会,语言文学尽管已经颇受关注,但依然不是传教士们当时最为关注的话题,混合式的过渡性语言策略仍然广为使用。,共同推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圣经》“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成立及“和合本”《圣经》的翻译。③对于富善在推动《圣经》“和合本”翻译及过程中的贡献,有论者给予极高评价:“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译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的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一样。”(转引自林振时:《富善·序》,刘翼凌,香港:宣道出版社1987年11月版。)而“和合本”《圣经》,亦被公认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范本。④胡适和周作人都对《圣经》“和合本”给予过正面评价,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一
明显不同于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白话以及《圣经》翻译语言之报告的是,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所有报告中,关于中文基督教文献或文学的报告只有三篇,即来自于福州的传教士鲍德温的报告《基督教文本:已做了的以及还需要去做的》、来自于北京的丁韪良的《俗文学》,以及来自于北京通州的富善⑤富善在《圣经》北方官话译本尤其是“和合本”中的贡献与作用,在《译经论丛》(刘翼凌编著,福音文宣社翻译丛书第二种,1979年5月)中,专门刊登“富善相片”“官话和合本译者五人合影”及“官话和合本修订委员会及其中国顾问合影”照片三祯,其中富善的地位显而易见。的《一种特别参照北京官话的白话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ndarin)。
这篇在《圣经》“和合本”翻译史上极具历史意义和重要性的报告,实际上其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圣经》及近代传教史领域。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篇文献事实上亦掀开了晚清由传教士所主导的白话文运动的序幕——这一方向的白话文运动,与由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们所主导的白话及白话文运动彼此呼应亦彼此参照借鉴,而在发现、改进并推动这种新语言的态度、方式与结果上,传教士们的实验与尝试,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事实上亦成为晚清新语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来到华北通州地区传教的富善,在宣教十年之后,最终对于当时中国的语言现状有了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知判断,并在此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因为方言之不同而呈现出来的“区域”差异之大,远不是一般传教士所能想象的!“如果考虑到那些差异,难道在太阳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不成?仅就方言这单一内容而言,这让人怎不会联想到巴比塔!”⑥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10-24,1877,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p.214.出自本书的引文下不一一注释,只随正文夹注页码。富善这里拿来作为案例的,是在基督教世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词语”或通用语的“阿门”这一词语,但在中国各种地方方言中,这个词语的发音差异却很大。在富善看来,表面上统一的中国,实际上因为语言或让人难以应对的地方方言而陷入一种“语言隔阂”或“语言分裂”之中,缺乏一种通用语以及更能够兼顾底层普通大众的公共语文,是中国社会不能实现真正统一的最迫切需要铲除的障碍之一。这种障碍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之间,亦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因为语言隔膜而不能真正意义上沟通交流对话的“冷漠”社会。⑦其实,鲁迅的《祝福》和《孔乙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上述状况的文学形象化表现。即便有所交流,这种交流也是缺乏一个共同认同的基础的。而通常中国的知识阶级所谓的共同的历史与儒家信仰,在富善这些传教士们眼里,很多时候恐怕不过是一种有些想当然的民族共性。因为似乎有更多的区域性、地方性甚至民间性,在分解或者选择性地转化上述所谓的共同性。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分解或转化工具,就是令人眼花缭乱、数量众多的地方方言乃至部分社会方言。
注意到方言与官话(北京官话)之间的差别,是富善这篇报告的起点,当然也是一种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所不同的是,富善的这种意识直接关涉到福音的传播,并非一开始即就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处境而言的。而传教之困难,其中最为迫切的一点,就在于每一位传教士都必须学习宣教所在地的方言白话,而这也就为基督教文本的中文生成形态带来了困难,“这样的话,我们那些基督教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究竟应该用文言呢,还是翻译成为各种不同的地域方言白话呢?”(p.214)或者使用一些口语体文来满足部分实际需要呢?
对此,富善报告中直接提出了一个设想,那就是使用这种不被重视甚至遭到鄙视的语体文,是否可以大部分解决上述因方言之不同而造成的语言不通的问题?而尤其让人关注的是,富善开宗明义地提出:“本报告就是希望通过对文言文献与语体文献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与北京官话文献的比较,来为上述问题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解决途径。”(p.214)换言之,富善这里实际上已经昭示出一个思考的向度,那就是语体文,尤其是北京官话文本形态在以后具体的宣教实践中得以推广的现实可能性,并由此使之成为一种通行之语言规则,“从而那些印刷制成的基督教文献之力量,能够最广泛、深入和持久地被感受到”(p.214)。
富善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各种地方方言中北京官话的地位与推广可能性;其二是语体文替代文言文之可能。最终希望实现的目标,当然是一种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包含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内涵的新语体文,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文言文而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这样在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两个层面,困扰传教士们的语言问题亦就彻底得以解决。
有意思的是,富善有关《圣经》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语言问题的讨论,并非拘囿于中国,而是建立在一个可供参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圣经》最初的各个民族译本,都是供那些知识精英阶层阅读的,之后才出现供那些大众阶层使用传播的译本。(p.214)这种有所参照借鉴的讨论,还拓展到1380年由Wickliffes完成翻译的英语《圣经》译本。在当时,上帝和《圣经》被视为教会和特种阶层才能享有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值得承受上帝如此伟大的护佑”(p.214)。而到了19世纪,在新教教会这里,上帝不再是一个专属概念,而是一个自由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阶层或组织。“他并不因为人们地位之低微而放弃向他们传递他的福音。”(p.215)由此,富善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那些普通民众该有多么需要白话版的《圣经》啊,这样他们就能够接近那被封闭的福音宝藏了。”(p.215)这种《圣经》面前的平等与自由,或者教堂里面的平等与自由,无论与现实中的真实具有怎样的反差,至少在一种宗教理想中,还是可以暂时存在的,这是富善式的《圣经》平等思想延伸到语言层面的平等的一种自然结果。
在上述讨论中,富善不仅将《圣经》翻译的语言选择问题,置于一个《圣经》翻译史的世界性历史语境之中,来作为对于那些预料之中的为中国的特殊性进行辩护的声音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应。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富善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翻译政治或翻译的意识形态命题,那就是《圣经》翻译史上,总是伴随着各翻译国家一种更通用(“更活泼、更普遍的语言”)的国语之诞生,使得圣经可以在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只手上得以传递阅读。这一目标的达成,基于《圣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中使用一种白话语言,或者一种一般大众都能够懂得的语言。“上帝之意在于,《圣经》之光,亦将照彻深谷,就如同它照亮山巅一样。”(p.215)富善坚信这样一个在新教传教士中的普遍信念,那就是即便是在中国,人民也必须拥有用他们自己的白话语言翻译而成的《圣经》中译本。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也必须拥有一部通用语的中文《圣经》。(p.215)换言之,新教传教士们所期待的这样一部中文《圣经》,不仅是白话(可能是各地不同方言),而且还必须是一种通用的白话。而在富善看来,这种具有地域上的更大广泛性与语言上的阶层、地域适用性的白话,也就只有北京官话最为合适,可以作为一种“通用白话”之语言平台。
显而易见,富善的上述提议,还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因此报告中例举了若干技术性的操作尝试命题,譬如他谈到了赞美诗。颂诗赞美诗究竟该用怎样的语言来翻译或者创作呢?富善认为,应该是用一种“进到教堂里面的大多数人都容易懂的语言”(p.215)。这种语言,在他看来,当然就是一种简易的语体文,至少具有一种所有人都基本能懂的语言风格。
在颂诗赞美诗之外,还有主日(礼拜日)学校所用文的文本材料的语言问题。对此,富善更是明确提出需要使用白话,“这些书面文本材料改用白话语体文之后,马上变得老少咸宜,并成为这样一个新的、广阔而重要领域中的积极存在”(p.215)。富善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需要这种礼拜日学校,而对于礼拜日学校来说,所用书面文献材料必须是白话文,或者一种不超过它的语言,譬如北京官话。
尽管上面的分析中,其实已经涉及使用白话来作为基督教文献的中文语言平台的原因,但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富善进一步就这种语体文提出了两条理由。
首先,富善认为这种普通大众所广泛使用的语体文具有简明的风格。对此,富善在报告中从语言风格或文风的角度展开过粗略分析。富善认为,或许有人会就风格上究竟哪一点最为重要这样的问题发问,而在他看来,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答案都是“简明”(perspicuity)。在富善这里,“简明”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或文体风格,而且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文本的重要基础。这种将读者尤其是普通大众读者的阅读理解需求置于重要地位,并将文本作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对话沟通之中介的观点,无疑是一种颇为近代的观点,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文本通常只是作为知识阶级的文字语言特权的习惯认识。在富善看来,文言即便是对于那些能够认识汉字的中国人来说,其中大部分也是难以读懂或理解的。(p.216)而这一事实,不仅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事实,甚至连有些来华传教士也渐渐适应了这种语言现实。而宣教布道的目的,首先是通过让听者听懂然后启信最后入信并持之以恒。“无论我们用手中的笔还是用嘴巴来宣教布道,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别人是否能懂得我们的宣教。”(p.216)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作为中介的工作语言,就必须是一种大众的而非小众的、日常生活化的而非特殊语境的、简洁明了的而非过分追求典雅难懂的新语言,一种首先强调其人际之间对话交流功能的工具语言。
对于这种新语言的语言风格,富善认为也是一种宣教布道的语言策略——为了让普通民众亦能享受到“上帝真理之光”。“西方人享受到了白话《圣经》的便利,而那些基督教文本,都是《圣经》之衍生,自当亦为白话。”(p.216)富善甚至认为,一部简易朴素明白的《圣经》,乃今日世界范围内的福音运动之首要。而且,“正是这种简明的品质,使得基督教真理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酵母力量,能够在社会上下各阶层均产生渐进的推动力量,并提升整个社会大众。”“正是这种简明的品质,成就了西方社会读者与思想者共有的国家。”(p.217)
换言之,富善已经将白话《圣经》从基督教传教之现实需要,上升到宗教信仰之自由平等,上升到一种宗教传播的语言选择战略或语言政治,同时亦上升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打破社会僵化隔膜、实现社会各阶层和解的思想政治高度来认识。所以,他进一步分析道,“具有这种简明风格品质的白话著述,已经开始在中国产生类似效果。”这种效果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呢?富善说,“基督教真理,以及人们渴望阅读《圣经》真理的心愿,可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p.217)如果说这种联结感真实存在的话,它也一定不是基于中国人形成其社会关系基础的血缘、宗族等,而是基于一种新语言——一种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新语言。这种新语言,成为中国社会再次真正统一的基础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民族共同语,在富善的报告中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如果说上述观点还只是就白话及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差别”而展开的论述的话,接下来富善对于这种新语言与生活和经验之间关系的阐述,也就是对于这种新语言的本质属性的阐述,更加值得引起注意。在他看来,这种白话语体文是一种强调个人感受性的语言(vernacular is the language of feeling),而不是一种教条化的僵化空洞的书面语言。它强调作为个体生活者的人与他的生活体验之间真实的、现实的、即时的感受关系,强调其个人性、当下性和即时生成性或鲜活性,不像文言文那样更多体现出一种历史语言和他者语言的现象。
在富善看来,这种新语言是“清晰明白”的,也就是说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已经足够清楚了。“感受依赖于心灵中已经清晰且容易理解的东西,而任何一个难懂的词语或表述则倾向于拘禁或突破时下的流行语汇。”(p.217)而且,“白话之所以是一种感受的语言,还因为它是一种日常生活语言(language of daily life),一种心的语言,它还有一个清晰的应用的边际或方向”(p.217)。换言之,富善已经注意到白话相对于文言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当然是在与文言相对而言的语境中被凸显出来的。当然,富善当时所注意到的这些语言差异,主要还是基于一种生活应用层面的观察,还没有对白话语言的历史与内在的差异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阐述。而且,当时富善所提到的白话,还主要限于一种日常生活白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白话(一些白话文学作品中的白话)以及宗教文献中的白话等,还没有也不可能予以足够重视和充分说明,也没有直接清晰地涉及这种被改造的新白话的新的应用领域与扩大范围,而还是在强调突出白话现有的“边际或方向”。这些边际或方向,固然曾是白话区别于文言并获得其相对独立性的前提和基础,但这是否就是白话不可超越的边界,或者这种新白话究竟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运动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富善的报告有所涉及,但看上去显然还没有充分透彻的认识思考。而对于这种新语言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直到十余年之后,也就是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才更为集中和明晰地表达出来。
“总而言之,真理必须通过一种冲击性的力量、以唤起感受的回应的方式来突入到心灵之中。在精神世界之中,就跟在自然界一样,我们必须就像拥有智慧一样拥有热力,以安顿情感心灵的驱动力。”(p.217)而在富善看来,“文言产生情感的力量要远远逊色于白话”;“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文言给人所产生的印象,就跟透过阴云的阳光一样。而且,由于高高在上,又被视为经典,这种语言就跟冰一样冷”。(p.217)
很难说富善上述对于文言作为一种语言的观察性与感受性的描述正确还是错误,因为这种描述有一个预设的价值立场,也已经生成了一个情感朝向。也因此,富善会如此坚定地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白话绝对是圣灵用来转换普通百姓,并将他们造就成为富有精神内涵的生命的最佳语言。”(p.217)富善这里一再提及“民众”,以及主要针对民众而应有的《圣经》中译本之语言风格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并不关注对于本土知识阶层的福音传播。“不要以为我低估了对于更高阶层读者的更高风格的文学的重要性的认识。那种语言,通常被称为文言(书面语)。”只是,如果要选择一种语言,既能带来光明之智慧,亦有鼓舞情感之热力,既简洁明了又富有感染力,而且这种语言还要适应于一般民众,结合中国当时的语言现状,亦就非白话莫属了。
二
富善对于中国古典语言或文言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观点或发现呢?他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古典语言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呢?对于这一点,回答似乎也是肯定的。富善认为,“在东方,古典语言研究的主要及适当目标,其实与西方世界并无多大差异。其中有些目标在于获得精神秩序或纪律、一种优雅的风格、历史信息、一种更广博的哲学,再就是传承一些前人创造的典故箴言。正如在西方,人们会阅读恺撒、塔西佗和贺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p.217)富善认为,相对于那种历史语言、古典语言,在未来中国,白话之应用势必将成为主流,“首先应该在中国的基督教会里——这里也应该是圣经扎根之所在”。也就是说,《圣经》传播及传教士,应该成为这种现代语言或民族共同语的积极推动力量,甚至一种领先的实验者。富善作出如此判断,基于两个原因,而这两个原因可能又是彼此对立的:“一是精神活动的加速,这可能导致一种差异性更大、更深刻的学术;另一原因是,随着白话越来越渗透到原本由古典语言所占据的地域,白话不仅将成为基督教文学的语言,而且还将成为哲学和诗的语言,它也将比文言在语言风格上更为简洁。”(p.218)
对于这种语言使用及精神与审美版图的改变,富善的解释还有,“文学上的这种语言改变,从文言到白话,肇始于一种将真理传播到所有人的渴望,并通过接受基督教真理的方式,来让人们获得救赎。”(p.218)有意思的是,富善再次将在中国传播《圣经》福音所涉及的语言问题,不仅与西方世界中的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之间的替换现象相提并论,而且还与13和14世纪天主教会与新教教会之间的论战与分野相提并论。“那些深受基督精神影响者,将像他一样说话,而且所用的写作语言,也将是一种明显平实的语言。那些期待着去拯救心灵的人,将永远不会放弃白话。”(p.218)
不过,对于白话在中国应用的现实,富善在报告中也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观察力和现实感。他说,“我并非对白话在中国的应用可能不被热心接受的现实毫无意识。原因在于,(1)是认为白话是一种坊间乡野之语言,不足以表达超越于一般普通之思想,而且也不足以作为一种永恒文学之语言;(2)那些已经用白话印刷出版的书籍,许多并没有得到应有之关注,对于这种语言,也缺乏应有足够之了解,或者得到适宜之帮助;(3)中国知识阶级对于那些白话著述人所共知的轻视,关于这一点,那些南方的读书人们要比北方或西部的读书人更甚,因为在北部和西部,人们讲北京话或官话,而且也已有一些著述是用白话写的,尽管其中夹杂着文理或文言。”(p.218)
此外,对于倡导白话著述及白话布道可能在传教士中引发的“误解”,富善也早有自觉:“我这里还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倡导使用白话,并不是在倡导一种易动感情的风格。”(p.218)原因很简单,已经有听过富善布道的传教士告诉他,他所用来布道的语言,是那种街坊店铺里的语言。对此,富善的回应是,“我也假设,中国的每一种白话方言,其纯粹性、清楚性以及力量,依赖于讲这种语言的人的修养。很显然,在北方,街上的劳动者们讲官话,书斋里的学者们也讲官话,但这两种语言是彼此分隔甚远的,而那些用官话宣教和写作的学者,致力于一种纯粹明晰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与那些文盲日常生活对话中所使用的官话相比,当然就是‘古典’的(文言)。这种语言风格,其文理深点还是浅点,取决于那些著述的读者们的地位之高低。”“近来北京地区所完成的《圣经》译本,几乎完全是用官话翻译完成的,许多圣诗也是官话翻译的(尽管有时是用一种混合的风格成文的,而且偶尔还是用一种纯粹的古典风格成文的),包括一些礼拜日宣教布道的文本,这些著述尽管并没有非常广博的词汇和成语,依然证明官话著述足以在中国的基督教文献中占据主要地位。”(p.218)
富善的论述,似乎在不断证明一个他所期待同时亦坚信不疑的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的到来或许还需要长期而艰辛之努力,即“官话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种通用语”(p.219)。对此,富善尽管基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和语言现实多少有所保留,但他还是认为将来是有可能的(p.219)。原因之一是富善注意到,当时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能够讲官话,“它足以达到文言的雅致;它与文言方言之间因为那些借用的词汇而带来的亲缘关系,以及它的大量词汇与成语……而且总体上朝向统一的趋势,尤其是在基督教意义上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官话方言的增长与扩展”(p.219)。
对于这种将被作为民族共同语言的白话语言的书写形式,富善亦有所思考。他说,“这一话题曾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被提及过,而且此次会议上也有些代表希望讨论这个话题。我并不反对使用罗马字母的拼音系统,不过这主要是为了那些不会认写汉字的妇女们,而不是为了那些在学校里的女孩子们。我对广泛地放弃使用汉字并不表示乐观,亦不积极推动放弃汉字。……词的衍生,乃为一种语言之财富的一大部分,将会因为这种拼写方式的改变而全部丧失。”(p.219)富善对于白话拼音方式的有所保留的意见,换言之他对汉字学习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对于汉字这种文字学习困难程度的理性与科学认知上。在他看来,“汉字学习的难度,时常被人们高估。一个孩子学习书写阅读官话方言的难度,并不比一个孩子学习英语阅读书写的难度更大。”
富善注意到了汉字如果因为罗马拼音系统的引进使用而可能遭遇到的“损失”,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因为这样一种拼音方式的改变,而可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断裂”性的破坏。“古典文学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p.219)而所有这些话题讨论,几乎在四五十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又被本土知识分子们重新检讨了一遍。这一事实,亦从一个角度说明富善当时这一报告的“前驱性”或“先锋性”。而无论是他对于白话与文言的比较阐述,还是对于白话及白话文将替代文言及文言文而成为中国未来的一种民族共同语的判断,包括他对用罗马拼音字母替代汉字主张所变现出来的谨慎态度甚至反对意见,都已为后来中国的语言现实所证明是准确的。
三
对于富善在第一次传教士上海大会上就白话、白话文及白话文学所发出的积极呼吁,以及在此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这种语言的认知解读,包括之后对于《圣经》白话翻译的积极不遗余力的推动,还应该将其纳入富善后来对《圣经》“和合本”长达20余年的翻译实践之中来综合考察,同时亦应该将其纳入他有关官话的语言研究结构之中予以考察①参阅富善1891年初版之《富善词典》(A Pocket Dictionary[Chinese-English]and Pekingese Syllabary)以及1898年初版的《官话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值得注意的是,富善这两部著述均成书于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确定成立《圣经》三个翻译委员会(包括官话翻译委员会)之后,并完成于《圣经》“和合本”完成之前。由此亦可以说是富善《圣经》翻译过程中对于白话汉语的词汇及语言特性研究的集中体现。——富善在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的倡议以及背后所依托的思想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缺乏连续性的,而是他从1860年代开始用北京话或官话开始布道之后的系统思考的一次集中体现。②据记载,富善第一次用北京话公开布道,时间为1866年11月(参阅林振时:《富善》,香港:宣道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62页)。
将富善的白话语言思想想当然地与所谓的语言民主意识等联系起来,看上去多少有些牵强。不过在费正清就“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这一命题进行阐述时,他提到了传教士在晚清中西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与贡献,并指出:“只有传教士们努力与置身两种文明中的普通民众进行直接接触”,“他们是中国乡村和美国小城镇之间基本的甚至惟一的纽带。”③[美]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吴莉苇译,《国际汉学》2003年第2期。如果说这种关系还只是催生富善等来华传教士关注中国的语言现实和民间底层语言现状的因素之一的话,借用这种语言来实现什么目标,应该才是让富善这些传教士们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的真正原因。对此,费正清亦曾有过一段文字涉及这个问题:“只有他们(指传教士——作者)力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最大程度地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①[美]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吴莉苇译,《国际汉学》2003年第2期。
上述论断揭示出讨论新教传教士的在华语文策略时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最根本的目的。对此,几乎所有传教士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基督教化中国,推而广之,乃西方化中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对象都是“中国”或“中国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中国人或某一特定群体,譬如知识阶级。
“力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这里所谓的“中国人”,显然已经不是《圣经》“委办本”时期的读者对象,至少不是以那些能够阅读使用文言文《圣经》译本为主的对象。也就是说,宣教目的与宗旨,促使传教士们在中国寻找一种更具有广泛性的“通用语文”。当这种意识与诉求逐渐明晰——这一过程与传教士们对于中国的语言状况和结构的认识了解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委办本”时期的翻译策略,尤其是语言策略,即通过使用本土知识阶级的语言来影响这一特定读者群体,并通过他们来间接影响教化更大范围的本土民众的思路,开始遭遇到一种直接面对本土普通民众意识的挑战。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途径之一,就是将普通大众的语言确定为传教士与普通大众之间关系的工作语言。这实际上成为白话及白话文进入传教士视野范围的最初主因。
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直至第一次传教士大会,英国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伦敦会传教士在《圣经》翻译、各种宣教文本的生成出版等方面占据了相当话语权,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圣经》“委办本”。而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之后,直至《圣经》“和合本”的正式出版,也就是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初,美国来华传教士在宣教布道、教育、卫生、新闻出版以及《圣经》翻译等方面,逐渐明显超越英国来华传教士,而《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出版,足以见证上述过程。
比较而言,英国来华传教士大多以更偏于学术与文化兴趣的方式,一方面宣教布道、教化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文学、民俗等等,亦往往容易产生出一种更具有学术与调查研究意味的兴趣和行为——亚洲文会之类的机构以及《中国评论》之类的期刊,足以见证这一点。而美国传教士则大多以更具有宗教意味与现实诉求的行为,扩展与宣教布道相关的社会慈善事业,譬如教育、卫生等事业,而这些又往往带有面向社会普通大众、改进生活方式、直接改变提升现实生活水准等特点,与他们力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宏大理想相呼应,成为一种带有美国思想文化印记的宣教布道方式。
这种方式渗透到语言策略方面,自然会关注民间的、底层的、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语言。但这种语言关注又并非直接的、简单的、不作任何改变的语言借用;相反,这种语言直接朝向美国来华传教士们在思想心灵层面及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的双重关注,这种语言遂亦深深打上上述两个层面的烙印——这是一种新语言,既关涉思想心灵,亦不回避日常现实生活。而这种日常现实生活,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日常现实,而是渗透着一种积极改变现实的意图和努力于其中。这种新语言具有内在精神与外部物质及日常现实生活兼顾并举的特点,且在这两个方面或层面均表现出一种朝向内部的改变和朝向外部的改变的“双重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亦可以从基督教化中国与现代化中国(亦有人将其归结为西方化)这两个朝向上得以诠释。而这种新语言,遂亦由此确定并在随后的社会实践层面不断得以生成发展,成为晚清中国颇为清晰且具有相当话语力量的一种新语言。
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语言提案,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上述特点。更确切地说,它是对上述特点在时间上的较早回应,也是一种在内容上清晰而明确的回应。
(责任编辑:陆晓芳)
I0-03
A
1003-4145[2015]07-0087-07
2014-09-04
段怀清(1966—),湖北随州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
本文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