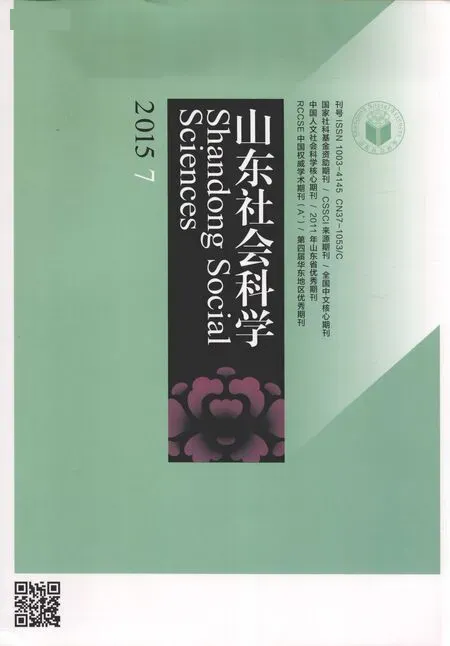对日本文艺诸概念的反思与再认识
——概念编制与评价史的视角
2015-04-02铃木贞美撰黄彩霞译
[日]铃木贞美撰 黄彩霞译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610119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学术主持人:王升远)·
对日本文艺诸概念的反思与再认识
——概念编制与评价史的视角
[日]铃木贞美撰 黄彩霞译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6101192;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无论随笔或小说,都有在不同地域、规范及价值观的作用下相应发展的历史。以往因为国际视野的缺失,人们一般不关注平时使用的术语、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颠倒错乱的“日本文学”观被说得煞有介事。“私小说”常被当作日本独特的类型,或被称作平安时代以来“日记文学”的传统。实际上被称为日本独特类型的是随笔形式的“心境小说”,且所谓“平安女流日记文学”类别是在1920年代才开始出现、属个人记录的各种文章的总称。即使在明治末期狭义“文学”确立后,女流日记、纪行文及随笔类仍未明确分类。日本三大随笔观有可能是在二战后随着国语教科书的辅助教材或考试参考书的普及才得以传播的。此类问题既是类别概念的问题,也是评价史的问题。
日本文学;概念编制;日记;随笔;日记文学;私小说;心境小说
一、概念编制与评价史因何重要
“日本文学”这一概念至明治中期才开始出现。前近代的“文学”意味着以儒学为中心的汉诗世界,和歌与物语都未被称为“文学”,无论从何种意义看都不存在与近代“文学”相对应的概念。在此,笔者将谈一谈“日记”“随笔”“日记文学”“私小说”“心境小说”等“日本文学”的下位类别概念。
“日本文学”最初是参照欧洲各国整个19世纪逐步形成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这一概念被提出的,是指那些与基督教神学(关于神的语言领域)相对、用母语进行创作的从属人类优美语言领域的人文学(the humanities)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曾被当作人们读写的范本和知识阶层应当背诵并掌握的东西。但是,新提出的“日本文学”是基于日本文化传统的作用,包括宗教书籍、用汉语(汉文)书写的书籍,还包括近松门左卫门的戏曲及曲亭马琴的读本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之后,至1910年前后,欧洲19世纪末形成的以诗歌、小说、戏曲为主要类别、用文字来书写的语言艺术(literary art)的“纯文学”[尤其是德语中与“Wissenschaft Literature”(知性文学或“科文学”)相对的“shōne Literature”(美文学)]传入日本,狭义的“文学”(literature)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扎根。在前近代泛指所有技艺的“艺术”(广义)一词,在日本明治初期成为作为英语“fine art”的译词而出现的“美术”一词的同义词①北澤憲昭:『眼の神殿―「美術」受容史ノート』,ブリュッケ2010年版。,用来指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中义)整体,而特指绘画与雕刻的狭义的“艺术”则是1910年由文部省使用的,同时用文字来表现的狭义“文学”概念也作为平行概念被固定下来。但广义的“文学”概念直至二战结束前一直都在使用。②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1998年版;鈴木貞美:『「日本文学」の成立』,2009年版。
向20世纪过渡时期,在欧洲兴起的象征主义艺术——浪漫主义中积极运用发达的象征技巧的流派——因吸收了被基督教视为异教、邪教的民族宗教等信仰,染上了一种宗教色彩,而未被日本接受。因此,已渗入日本古典中的神道、儒学、佛教、道家思想等要素未被排除,而且“能乐”等宗教艺能的词章也作为狭义的“文学”,没有任何违和感地被研究或教授。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芸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
为什么要谈这五种类别或范畴呢?那是因为它们之间关联密切,如果仅考察其中的一种类型,有些地方会解释不明白。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作家亲身体验的“私小说”是国际上20世纪小说的主流,其代表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弗朗茨·卡夫卡、威廉·福克纳、亨利·米勒、罗伯特·穆齐尔……不胜枚举。这与艺术领域中印象主义向象征主义的转变有关,也与向20世纪过渡时期兴盛的“意识哲学”的变化有关。日本的一位作家曾预言全世界各国小说最终都将会变成此类形态,此人即是岩野泡鸣。②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芸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
但是,“私小说”常常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的类型,甚至被认为是平安时代以来“日记文学”的传统。实际上被称为日本独特类型的是指在中国及欧美未被列入小说范畴的随笔形式的“心境小说”。而且,“平安女流日记文学”这种类别其实是在“私小说”“心境小说”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在此之前并无此分类。
以往因为国际视野的缺失,人们一般不关注自己平时使用的术语、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概念结构或编制),因此一直以来颠倒错乱的“日本文学(史)”观被说得煞有介事。今天,《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被称为日本三大随笔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至今连此种结论究竟是在何时、依据何种价值观作出的都尚未弄清楚(好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此,关于“日记”“随笔”“日记文学”“私小说”“心境小说”这五个概念要相互关联着考虑。关于各个类别的作品,我们有必要追溯前近代的概念与评价在近现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概念编制的改编与评价的变迁。此时,我们要注意“文学”的近代概念带来的关于古典的性质方面的各种偏见。例如,“历史物语”这一概念是在向20世纪过渡时期出现的。让我们以此为例来看一下评价古典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太平记》(编纂时间推定为14世纪中期—1370年前后)描写的是天皇家南北朝分裂、中世战乱时期的内容,其读本被称为“太平記読み”,至江户时代仍被广大民众所喜读。着眼于“读物”这一特征,兵藤裕己出版了《太平记〈阅读〉的可能性》(1995),另外,着眼于《太平记》在民众的政治观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进行。《太平记》将楠正成等土豪以“忠臣”形象来书写有着作者的意图,直至二战结束前都给日本人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当今的历史学上将其视为历史叙述。
在今天的某部文学事典中这样评价《太平记》:“通过战乱悲剧强调了人类道义,表达了与始终贯穿政权争夺的政治相抗争的民族的哀叹,作为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有着空前的价值。”此评论虽亦映射了日本战败的影子,但评论者从《太平记》表达了向往“太平”的“民族的哀叹”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感情表达,或作为一种以文字记述的语言艺术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釜田喜三郎“太平记”,见《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1968)和《新潮日本文学辞典》(1988)]。
在“国文学”领域将《太平记》等中世的战记称为“军记物语”并视其为狭义的“文学”形式之一,始于19世纪末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史十讲》(1899)。读其序可知,在此之前的“日本文学史”是“以全体学问为对象”的(实际上这是日本的人文学的范围——引者),但芳贺矢一认为“文学就是被制作的美术品”,可称为“美文学”。之所以称为“美术品”,是因为在19世纪末以前诗歌、小说、绘画、音乐、舞蹈等都被统称为“艺术”或“美术”。根据这一思想,故事性亦即艺术性,于是出现了一种用近代文学的基准来评价古典的姿态。
历史叙述主张将直面历史事件的人们的心理或感情融入作品,如《源氏物语》“萤之卷”,既可比正史更加详细地记载历史事实,还可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里的“物语”指的是从中国传入的“章回小说”的形式,每一章回都有标题,故事情节也具有连续性。正因物语具有这样的特点,随着藤原政权的发展,继《荣华物语》(11世纪)之后诞生的《大镜》(平安后期)、《今镜》(平安末期)、《水镜》(镰仓时代)、《增镜》(南北朝时期)等“四镜”也采用了这种形式,不仅运用了对话,还加入了围绕史实评价的论述。相对于用汉文记载的皇家“正史”,“四镜”可谓是用日语书写的另一部“正史”。《荣华物语》“鹤之林”章中有将藤原道长的死比作光源氏的记述。历史叙述中可用虚构的故事事件作比喻,这在中国的“史”书中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的“正史”是由下一朝代的史官整理前代王朝的历史记录。而在日本,没有王朝的更迭,用汉文记载的皇家“正史”(六国史)的记载中断后,在藤原政权时出现了用物语形式书写的“史”。从此,历史叙述开始呈现多样性。平安时代中期开始,日本在向中国寻求范本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向日本独特性发展的倾向。在二战期间此种倾向被称为“国风文化”,历史上曾提出停派遣唐使的菅原道真也得到赞赏。但今天我们认为当时之所以停派遣唐使,其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已经可以与中国进行各种物资贸易,因而已没有特意派遣国使的必要。而且,现在菅原道真以及作为当时“国风”文化担当者的纪贯之等人的高深的汉诗素养也正在被我们重新认识。原本“国风”的原意即是地方特色的意思。
兵藤裕己还指出了《太平记》中作者有意模仿《平家物语》而增加了作品趣味的地方,如交战场面等。在引经据典中体会其变化的乐趣,这大概与和歌的“本歌取”(一种引用古和歌的词句或趣向来创作和歌的方法)的创作方法相类似。物语形式会唤起人们脱离史实的自在感吧。
尽管《荣华物语》与《太平记》中包含感情表达或愉悦读者的各种要素,但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作为芳贺矢一所说的“美术”或“艺术”被创作的。关于对中国“史”的概念的受容应另当别论①鈴木貞美:「历史的历史」,『「日本文学」の成立』,2009年版。,但以近代的“艺术”观来评价处于历史叙述与感情表达未分化状态的古典显然不合适。要想避免用近代的评价标准对古典进行判断及其带来的误解,必须要了解各个概念的成立情况。概念是当时的知识阶层都了解的意思或用法。
首先谈一谈“日记文学”,它是1920年代新出现的一种概念,然后按照“日记”“随笔”“私小说”“心境小说”的顺序对各概念史进行略述。关于各概念相互间的关联,即概念间的结构或编制,首先从大致上进行把握比较重要,之后再逐渐对细微处进行修正。在此先声明,尤其关于“随笔”部分目前尚处于研究之中。另外,在前近代,文章的分类概念,除了参考中国的“经、史、诗、集”,还参考了类书的分类。13世纪前叶根据事实编写的故事集《古今著闻集》中使用了“神祇”(神道)、“释教”(佛教)、“文学”(汉诗文)等带有日本特性的概念编制,虽然这些概念编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发生过各种变化,但一直延续到了幕末。作为明治政府的国家事业进行编纂的古籍《古事类苑》就是在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又参考了西洋的分类概念。
二、“日记文学”的形成
首先,关于“日记文学”这一类别,主要以所谓的“平安女流日记文学”为对象来谈。例如,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一般被认为假托女性口吻而写,还有平安时代中期的《蜻蛉日记》(975年前后)、《紫式部日记》(1010年前后)、《和泉式部日记》(推定为1004年)、菅原孝标女的《更级日记》(1059年以后)、《赞岐典侍日记》(推定为1109年)等。
《土佐日记》是纪贯之结束在土佐的任期返京途中写的记录,将本来应该用汉文来书写的每天的记录(即日次记)假托女性的口吻并使用多为平假名的和文来书写。内有和歌57首,包括和歌在内,所记内容并不会使人认为作者是女性,任何人一读便知,其实只是一种设定的假托而已。此种假托在汉诗中早就存在。《文华秀丽集》(818)中巨势识人与嵯峨天皇的“长门怨”相呼应,以女性的口吻慨叹独宿的孤独。另外,慈圆《早率露胆百首》(1188)的题词中写道,此诗为常诵俱舍论的比叡山的幼儿所做。另外,《土佐日记》起首的“男もすなる日記といふものを女もしてみむとて”可以理解为“男子写的日记,作为女子的我也不妨一试”,但这句话中并不带有“我是女子中第一个尝试写日记的”这种强烈的含义。
《源氏物语》的注释书《河海抄》成书于室町时代初期,其中引用了醍醐天皇皇后稳子的日记。稳子为关白藤原基经之女,入宫之后的日记都是用平假名记述,但在朱雀天皇即位其本人当上皇太后之后的日记都改用汉文记述。稳子的这两种日记都早于《土佐日记》的执笔时间。大致可以推测为,稳子本人对宫廷的各项活动做的记录用平假名,而当上皇太后之后即由专门负责记录的人用汉文来记录了。
《土佐日记》出现之前也有一些带有日期的宫廷仪式或祭典当天的记录,以及斗诗会、和歌会的记录。比如,阳明文库所藏《类聚歌合》卷17的“和歌合抄目录”中有“延喜13年(913)3月13日亭子院歌合”一项,下面写着“参照伊势日记”。另外,尊经阁文库所藏《歌合》卷1的和歌会记录一般认为也是取自《伊势日记》。这些“和歌会日记”都是关于和歌的记录,所以都用平假名书写,但不一定都是女官所记。此类情况下的“日记”很可能只是当天的记录的意思。还有和歌诗人藤原隆房记录后白河法皇50寿诞庆祝仪式的《安元御贺日记》亦是如此。
藤原道纲的母亲写的《蜻蛉日记》共包含261首和歌,前半部分描写的是对丈夫的怨恨,后半部分则采用游记的形式描写了参拜寺院的内容。起首有这样一句话:“我拥有普通人没有的经历,将我的经历写成日记,应该会有人对它感兴趣吧”①『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0』,岩波書店1957年版,第109頁。。从“日记”就是将某一时期的事情记录下来这个意义上来看,“日记”一词的意义已被挪用,即使非日次记,记录人亦非公职人员,也都可称之为“日记”。安和2年(969)的一段日记中,在写完西宫左大臣的事情之后附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不应该在原本只记录我自己生活的日记中写入这样的事情”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0』,岩波書店1957年版,第175頁。。对此,玉井幸助在《日记文学概说》中作如是评论:“相对于一般的日记,‘只记录我自己生活的日记’是极其特殊的日记”③玉井幸助:『日記文学概説』,国書刊行会1983年復刻版,第245頁。。确实如此,远离公文的女性记录超出规范的“日记”并普及开来,应属后来所说的“平安女流日记”。
《紫式部日记》又叫《紫式记》,并非日次记,是一些和歌的记录或某种情况的随手记录之类,可能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阅读而写的,一般认为其中使用了比书信更接近于口语的书写方式。
直至江户时代,《和泉式部日记》又叫《和泉式部物语》,以带有章回题目的物语形式记录了某“女子”对恋爱经历的回忆以及新恋情成功的经过。《更级日记》的前半部分主要记录了从上总(现千叶县)到京都的游记,后半部分则主要是对遁入佛门之前的经历的回忆,其中对梦境的大量记述很有特色。
镰仓初期藤原为家的侧室阿佛尼写的《十六夜日记》(成立于1283年左右)记录了阿佛尼为领地纠纷诉讼而从京都去镰仓途中的旅行纪实和在镰仓滞留期间的生活。另外还有记录藤原经子13年宫廷生活回忆的《中务内侍日记》。
今天,包括《土佐日记》在内的这些作品被冠以“日记文学”的名称,被视为日本文学中一种独特的类型,但是这样一来,对于这一形式和内容都各不相同的作品群,无论进行怎样的细致分析与深刻研究都不可能了解其特质了。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拥有除了私人记录以外的其他的共同规范意识。
江户时代后期,塙保己一编纂的《群书类从》是对本朝古书的整理,分为神祇部、帝王部、补任部、系谱部、传部、官职部、律令部、公事部、装束部、文笔部、消息部、和歌部、连歌部、物语部、日记部、纪行部、管弦部、蹴鞠部、鹰部、游戏部、饮食部、合战部、武家部、释字部、杂部,属于“国学”系统,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近乎正式的分类意识。将汉诗列入“文笔”部,在“物语”部与“管弦”部之间设立“日记”部,内收《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宗长手记》等八篇,“纪行”部中以《土佐日记》开头,下列《海道记》《东关纪行》等十四篇。《土佐日记》虽是日次记,但被归为纪行类。纪行文开始是由遣唐使等人作为公务报告而写的,可能早就有了将其视为一种类型的意识。在中国古代,为与上表文等正式公文相区别而称私记类,在这里亦可将“日记”看作是对中国古代用法的一种沿袭吧。
实际上,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史”中并没有提及“日记文学”这一范畴。堪称“日本文学史”嚆矢的三上参次、高津锹次郎编的《日本文学史》(1890)虽然在编写时参考了欧洲近代的文学类别概念,但如前所述,此书编写的是日本的“人文学”、广义“文学”的历史(其态度也出现过些许动摇。《日本文学史》总序中写道:“汉文全部未采用。但与国文学相关之处自然要使之明确”④三上参次、高津鍬次郎合著:『日本文学史』上巻,金港堂1890年版,第11-12頁。。实际上,上卷率先登载了《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用万叶假名书写的歌谣之类,显示出对语言艺术的尊重,但《出云国风土记》中的国引神话一节(原文汉文)却使用了和汉混同体,而下卷(镰仓时代以后)则重视儒学,又引用了新井白石的汉文。上卷和下卷在结构与文体上稍有不同。据推测,此书是由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历史学科的三上参次教授进行整体构思,当时在读硕士研究生的高津锹次郎执笔上卷,三上执笔下卷),编者在第三篇“平安朝的文学”的第四章“日记及纪行文”中写道,日记、纪行、随笔“这三者之间很难界定明显的界限”⑤三上参次、高津鍬次郎合著:『日本文学史』上巻,金港堂1890年版,第298頁。。因此,关于“随笔”我们也需要多加注意。
综上所述,无论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对于时政新闻来说,优质的新闻主体内容仍旧是新媒体时代的核心。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广播新闻采编人员要创新模式,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综合素质。只有掌握较强的新闻采编技巧,融合新媒体元素,创新采编形式,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推进广播事业快速发展。
在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史十讲》的第五讲、中古文学之二“假名文字散文”中同时写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蜻蛉日记》的内容,其内部并未细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广泛阅读的简明文学史——藤冈作太郎编写的《国文学史讲话》(1901),显示出一种纵观美术动向的文化史的姿态,其中谈道:“枕草子为清少纳言之作,尽管当时也出现了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等很多类似作品,但都得给此书让步”,之后便进入与《源氏物语》的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即使在明治末期狭义“文学”确立之后,女流日记、纪行及随笔类仍未进行明确分类。
哥伦比亚大学的铃木登美已在研究中指出①鈴木登美:「ジャンル·ジェンダー·文学史記述―『女流日記文学』の構築を中心に」,载ハルオ·シラネ、鈴木登美編『創造された古典―カノン形成·国民国家·日本文学』,新曜社1999年版,第104頁。,今天,“日记文学”一词最初出现在书名中是池田龟鉴的《宫廷女流日记文学》(1928),首次出现应是池田龟鉴《自省文学的历史性展开》(《国文教育》1926年11月号)中的“围绕‘日记’与‘日记文学’概念的笔记”,“日记文学”的目的在于“作者心境的漂白”。池田龟鉴在《自省文学的历史性展开》中写道:今天的“自省文学的全盛时代”“带来了可以通过新视角去解释国文学的时机”,可将这些作品列入“直接讲述自己真实经历的忏悔、告白与祈祷文学系列”,与“陶醉、沉迷于现在”的抒情诗不同,它们是“对过去的思索与反省”,并“伴有一种叫作‘乡愁’的寂寥”。②池田龟鑑:『日記·和歌文学』,至文堂1969年版,第56頁。今天所谓的“自省文学的全盛时代”,应该是指“私小说”与“心境小说”盛行的时代。但实际上,与主要面向文学青年的“文坛小说”相对,当时携手歌颂勤劳大众的、被称作“时代もの”或“髷物”的“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大众文学”(取材于当代风俗的“通俗小说”曾被当作“文坛小说”,1930—1935年也被纳入“大众文学”)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私小说”“心境小说”则隐形遁世。因此,毋宁说当时是一个围绕“私小说”“心境小说”激烈争论的时期。关于那些争论如何姑且不论,下面仅谈一谈有关“日记”概念变迁的基本情况。
三、日本的“日记”概念
首先,我们今天使用的“日记”概念未见于前近代的汉语,据说现在中国使用的“日记”概念是20世纪通过日本的教科书之类传到中国去的。虽然中国古代也有“日记”一词,但与今天的“日记”概念相差甚远。据玉井幸助的《日记文学概说》(1944)第一章“概观”可知,在中国“日记”一词最早可见于东汉王充《论衡》第13卷“效力篇”,论及“文儒之力”示于文章时指出“上书日记”并立可见,王充认为优于“上书”者如效力于汉成帝的谷子云,优于“日记”者如孔子。换言之,《春秋》等五经即被视为古代“日记”。相对于上奏给皇帝的奏本,个人每天书写或收集、编集的文章等都可称为“日记”。总之,“日记”就是用来指在每天的生活中所做的所有与写文章相关的事情。玉井还写道,到后来一般通用的也还是此意义上的“日记”,“日录”“日钞”“日抄”“日疏”等词可看作“日记”的同义词,即古汉语中的“日记”仅仅是“私人记述”,不属文学类别。
北村季吟等人论及纪贯之的《土佐日记》时将“日记”定义为“记录每日事”,同时又把非“记录每日事”的《篁日记》等与其列为同类。对此,玉井幸助在《日记文学概说》第二篇“我国的日记”中进行了质疑。也就是说,日语中的“日记”在江户时代“记录每日事”这一词义已基本固定下来,但仍有传统意义的残留,从而导致了使用上的波动。但是,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日记”也仍与古汉语中的“日记”有所差别。玉井幸助谈道:现存文献中“日记”一词最早见于《类聚符宣抄》中的弘仁12年宣(821)。内有“自今以后、令载其外记于日记”一文,意思是“自今以后,律令要由外记载入日记中”。“外记”就是位于记录宫廷仪式的少纳言之下的史官及其所做的记录。因此,在日本,史官所作的带日期的公家记录(可能是按日记录)也被叫作“日记”。
作为今天所说的“日记”的起源,经常会提到中国皇帝的言行记录“起居注”。由史官记录,后作为“实录”修撰,其中有大家熟知的汉武帝的“禁中起居注”。史官名从周代开始有“左史”“右史”,但据说汉代作为官职名的“起居注”尚未得到确认。从晋朝起设置“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专门官职,此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③受清华大学王中枕教授的启发。另外,众所周知,《日本书记》神功皇后摄政第66年的部分有对《晋起居注》的引用。
现存最早的“起居注”为中国唐代的编年体史书《大唐创业起居注》,但之后留存下来的较少。据说是因为下一朝代对前朝的“正史”进行编纂时被扔掉了。清朝的“起居注册”目前保存在台湾的国立故宮博物馆。无论哪一朝的“起居注”都是经史官之手记录的。
在日本,内记负责相当于起居注的皇宫记录,外记则负责宫廷仪式记录。记录中使用了“日記す”“日記せしむ”这样的动词。此外,还有一些贵族或官吏记的个人记录。在中国一直没有发现有关宫廷仪式的个人记录,可能宫廷仪式的个人记录是被禁止的吧。
天皇的日记有“三代御记”,即现存最早的《宇多天皇御记》(宽平御记)以及《醍醐天皇御记》、《村上天皇御记》。皇族日记有醍醐天皇第四皇子重明亲王的《吏部王记》等,高级贵族的日记有藤原忠平的《贞信公记》、藤原实赖的《清慎公记》、藤原师辅的《九历》(九条殿御记)等。取名“历”是因为此记录是使用具注历记录的。另外,正仓院文书中发现了天平年间以来的国司业务记录以及一些使用了具注历余白、纸背的记录。
具注历最初是古代日本为了支配或统治国家的时间而由朝廷向地方行政机构颁布的。据平安末期的《本朝世纪》可知,由于新抄纸及重抄纸不足等原因,10世纪时此制度遭到了破坏。另外,有学者认为,10世纪时贵族及寺院依靠历博士或历生来制作、书写具注历已成惯例。或者也可以说具注历的一半用途是用来书写日记的吧。据说最初是藤原摄关家接受了具注历的进献,但具体时间不详。现存最古的亲笔历记中有藤原道长的《御堂关白记》,其大部分都是按照日语的语序书写并适当使用了汉字词。可能连汉文读写水平很高的藤原道长都觉得使用正规的汉文记述太麻烦了吧。
也就是说,日本前近代的“日记”有两种:①是指正式“公文”以外的个人记录的所有文章,②鈴木貞美:「日々の暮らしを庶民が書くこと―『ホトヽギス』募集日記をめぐって」,佐藤バーバラ編『日常生活の誕生―戦間期日本の文化変容』,柏書房2007年版。是指宫廷史官所做的带日期的记录。①中又混合了三种用法,即用具注历记录的文章、个人记录的日次记,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江户时代,属于旧中间层的理发店或商家,出于写各种报告的需要,形成了以上述①中的第二种形态即以日次记的形式做记录的习惯,但其书写样式各不相同。在第一章中曾谈到的自平安中期开始至镰仓、室町时代由女性创作,被冠以“日记”之名,并于1930年代前半期被归类为“平安女流日记文学”的作品群,应属①中第三种用法,即为个人记录的各式各样文章的总称,这一点再次得到了确认。
四、“日记”概念的近代化
在欧洲相当于“日记”的概念有“journal”和“diary”两种,前者是指所有附有日期的记录类文章,后者是指记录预定计划或备忘录的带有印刷的年、月、日的笔记类。但日本的“日记”概念并未受到此概念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明治后期,正冈子规创办的俳句杂志《杜鹃》曾于1900年10月至1903年9月(4卷1号—12号、5卷2、4、8、10、12号)征集、选拔并刊登过“每周日记”和“每日日记”。众所周知,正冈子规致力于短歌、俳句及“叙事文”的近代化革新,此征集活动正是“叙事文”(所谓的“写实文”)改良的一次尝试。俳谐本是作为百姓的一种游戏而普及、固定下来的,因此应征者多是平民阶层。看其所录用的日记就会发现,“每周日记”的投稿首先是各种业务的记录,由此可以看出此种习惯在民间早已深深扎根。在日记的空白处写一点感想,这与古代朝臣个人记录的日次记差不多。文体基本也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在百姓中流行的名词结尾、“コト”结尾、用言终止形结尾、表过去或完了的“た”形结尾的口语文体。
一般认为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文体改良运动是将文语体改成口语体,但这只是对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对平民阶层而言仅仅是将上述口语体(“する、した”体)的句子结尾处统一改成“だ、である”而已。在小学教育阶段只要经过训练很容易就能转变过来。通过《杜鹃》征集的日记明显能看出这种转变。②
1895年创刊的引领社会舆论潮流的博文馆的综合杂志《太阳》,接受各界读者投稿,不限制执笔者文体使用的自由。比较该杂志的文体变化情况就会发现,在对“だ、である”体的使用方面,平民百姓比善用文语的知识分子更容易习惯。在《太阳》的署名投稿中,政治类文章的文语体残留现象较多,大部分文章都使用“だ、である”体是在1905年前后。另外,正冈子规在《杜鹃》中引导人们重点描写印象深刻的事情,其效果在“每日日记”中尤为可见。①鈴木貞美:『日本語の常識を問う』,平凡社新書2012年版,第3章。
日次记形式的“日记”发生的大变化在于,记载的内容不再仅仅以事件记述为中心,也可围绕自己的思考内容、感想来记述。比如,记录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生前思考点滴的日记(journals)在其死后被分为2册出版。有可能受此影响,国木田独步于1893—1897年间围绕恋爱心情而写的心理记录《欺かざるの記》在其死后也被出版了(前部1908年,后部1909年),净土真宗改革派的清泽满之晚年的内省记录《腊扇记》等被读者当作“修养书”一样去读,这些都为日记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之后,阿部次郎以新文艺的方法提倡“精神生活的如实描写”,出版了非回忆的、记录彷徨内心的《三太郎的日记》(1914年,第二1915年,合本1918年),本间久雄在《日记文的写法》(新文章速达丛书,止善堂,1918)中作为范本刊载了尾崎红叶的记录式日记以及樋口一叶的感想日记,并收录了新潮社系新进作家们的随笔风格的日记。这些改变大概也刺激了中学生或女学生、高中生们的日记写作,学生中间也逐渐形成了作为内省记录的日记习惯。1920年代,尊重儿童自发感情表达的情操教育风潮(以大正生命主义的北原白秋的《童谣》理念为代表)在小学教师中间席卷开来,于是作为作文教育的一环记录每天生活的日记形式固定了下来。
前章介绍的池田龟鉴在《自省文学的历史性展开》中始创“日记文学”一词并提出“日记文学”的目的在于“作者心境的漂白”,如果说这一学说的提出是以随笔形式的“心境小说”的兴盛为文学史背景的,那么我们就要了解这里指的应该是更广义的文化史的背景。
五、关于“随笔”的概念
下面,我想简单追溯一下“随笔”一词的历史变迁。《新潮世界文学小辞典》(1966;增补改编版为《新潮世界文学辞典》,1990)中担当“随笔”一词解说的福原麟太郎这样解释:“纵观中西文化,汉语中‘随笔’一词的出现始于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1180年公开发行,之后还著有《容斋续笔》乃至未完成的《容斋五笔》)。在日本,第一部以‘随笔’冠名的书籍是室町中期一条兼良编撰的说话集《东斋随笔》。与东方的起源相对,英语中‘随笔’的概念是由英国作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受法国随笔开山鼻祖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的《随笔集》(Essais,1580,1588)的影响,将古罗马时期新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小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e,公元前3—公元65)的书简也包括在内,将‘随笔’的范畴扩大,使其变成一种既包括理智又包括情感、书写形式自由的文学形式。”该辞典中还规定“随笔”是“内容多样的小品散文样式”,并顺便提到“我国的私小说类作品在英国被算作散文的一种”。
蒙田的《随笔集》描写了在旧教和新教的宗教战争面前,人类对自身伦理道德的怀疑和反省。读了此书的培根,会想起塞涅卡的书简及文章一点都不奇怪。一度随心所欲生活的塞涅卡一边随时等待着皇帝派来的死亡使者登门,一边在日常琐事中对人性进行观察,在文章中直抒胸臆地吐露自己对道德根本进行的思考。
在19世纪的英国,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常被称为随笔文学的巅峰。其含义是感受富含人类机智和洞察力的文章带来的快乐。虽然设定了伊利亚这个叙述者,但其中也含有很多自传性元素。福原麟太郎之所以提到“我国的私小说类作品在英国被算作散文的一种”肯定是受到《伊利亚随笔》的影响吧。另外,“我国的私小说”中特别限定为“我国的”,大概是为了与欧洲的“自叙体小说”相区别,是指作家的形象不直接表现在作品中而以随笔形式陈述自己心境的、被称为“心境小说”的那种“私小说”而言的。
总之,不是以一般人信奉的宗教世界为对象,而主要以人性为对象对伦理进行考察的态度及其文章的妙趣构成了欧洲随笔的根本。可以说,由此人们才会喜欢上像讽刺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被认为“说得妙”的奇特构思和新颖的表达。“随笔”正是在这种人文学的基本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扩大到“内容多样的小品散文样式”与报业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无视上述历史变迁,直接将“随笔”定义为“内容多样的小品散文样式”,并强加在中国及日本古典文学上的态度是有些危险的。虽说一条兼良编著的说话集取名为《东斋随笔》,但当时在日本“随笔”一词是否被理解为“内容多样的小品散文样式”还有待考究。而且,“我国的私小说类作品”不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中国都不被算作小说的情况也没有被考虑在内。无论随笔类还是小说,都有在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规范及价值观的作用下相应发展的历史。正因如此,才有必要追究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即概念构成或编制的历史变迁。
《容斋随笔》的自序中说明了“随笔”的含义,即“意之所至,随即记录”。此书汇集了各种内容的笔记,从题材来看,以经史为首,诸子百家、诗文、方术,甚至民间信仰,资料丰富,涉及范围广泛,确是“内容多样的小品散文样式”。此书对史料记载的评议或典据的考察都非常确切,向来以对“文字”的考证精确而著名。①大西陽子:「『容斎随筆』に見る表現形式―読者との係わりの中で」,『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1987年第6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其为南宋说部之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将各种内容的笔记编纂成册的书籍早在11世纪就已出现,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等。可将二者视为同一类型。究其成书背景,在唐代,不拘泥于规范的文章的自由写法(肆笔)就已十分盛行,②高橋文治:「〈肆筆〉の文学―陸龟蒙の散文をめぐって」,荒木浩編『中世の随筆―成立·展開と文体』竹林舎2014年版。出版物在民间大量流传,其中尤以经书、史书类注疏(注释书)为盛。长期担任史官的洪迈,博览群书,经世致用,对尘世的“浅妄”多予以嘲笑。洪迈的考证范围极其广泛,自“经、史、子、集”到佛教批判、人物评、地志等无不有所涉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议官”出身的“杂家者流”。意思是说洪迈不是“稗官”“小说家”。洪迈评价过主张三教一致论的白居易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容斋随笔》是以写“经、史、子、集”的内容为根本规范,虽然也有超出此规范的内容,如当时的街头轶事、人物传闻等,但作者并非要去写故事,毕竟洪迈不属于以著有《吕氏春秋》的吕不韦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那样的流派吧。
有一类文章,不像《容斋随笔》这类书籍是关于史实考证或评论的,也不是写社会事件或传说的,其开创者应该是明代的作家袁弘道。袁弘道非常擅长花道技艺,同时也对饮酒的方式颇有心得。他曾经写过关于花道的《瓶史》和指导人们如何愉快地饮酒的《觞证》。说袁弘道的文章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也不为过吧,在中国,各类体裁的“史”书都习惯在“正史”中编写,“花道史”却是一个例外。但袁弘道能够创作出与“经”“史”都无关的著作,大概可以归结为他年轻时与其弟一起师从1930年代被称为“阳明学左派”的李贽(李卓吾)的缘故吧。在李贽那里,袁弘道学到了“解放欲望,达到‘圣人’境界”的思想,养成了自由发挥思想的风格。袁弘道与其兄弟一起反对拟古、复古的诗风而推崇清新的诗风,由于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世称“公安派”。清代袁枚等学者继承了袁弘道的文风,提倡文章要自由表现个人性情,开创了“性灵派”的诗风。袁枚还著有关于烹饪技巧的书《随园食单》,并效仿李贽提倡妇女文学,甚至公开刊行了《随园女弟子诗选》一书,因此遭到了朱子学派的非难和抨击。
中国的杂文在不断地发展,自明代的“古文辞派”开始,至清代则流行对事物的由来等进行考证的形式。而且,这些“杂文”都是正式的文言文体,不是讲义、讲话、问答时用的“白话文”。
相对于中国的“杂文”,日本最早以“随笔”冠名的书籍是《东斋随笔》。此书为一条兼良从已有文献中摘录了78则民间故事和传说编撰而成的,内容分为音乐、草木、鸟兽、人物事件、诗歌、政治、佛法、神道、礼仪、好色、游玩等11个部分。室町时代后期又出现了“连歌师”荒木田守武编著的《守武随笔》,此书大概是效仿《东斋随笔》而命名的。
虽然《东斋随笔》被命名为“随笔”,但不像中国宋代的杂文集那样,多选择一些诗文对其进行论述、整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斋随笔》命名为“东斋漫录”应该更合适。那么为何取名为“随笔”呢?现在还不能确定“随笔”一词是否被赋予了特定的意思。与中国宋代的杂文集相比,《东斋随笔》的显著特色在于其内容选取的对象并非“经、史、子、集”,而是日本前代的故事和传说。当然,在此书之前已有著述前代传说的先例,但在此没有必要追溯到平安初期的《日本现报善恶灵异记》。12世纪的《今昔物语集》的编纂动机也不详。
从《东斋随笔》中分类的情况来推测,此书有可能受到13世纪前期镰仓时代由橘成季编著的《古今著闻集》的影响。有关《古今著闻集》的编写目的,如其序文中所说,是为了补充“实录”。所谓“说话”一般都基于事实,而且很多都涉及朝廷的规章典制或者当时那个年代的事件。因此,橘成季的为了补充《实录》的说法亦可理解。在此之前,13世纪初,精通典章制度的源显兼编著的《古事谈》共有王道后宫、臣节、僧行、勇士、神社佛寺,亭宅诸道等六卷,被称为皇族、贵族、僧人的奇谈或秘闻集,此书在编写时可能也带有辅助《实录》的目的性。但是,在此之前的说话集中是否也伴有类似的意识?而且《古事谈》的书名中使用“谈”字是否是因其内容为传说?这些我都不能判断。在中国,“语”和“语录”倾向于用于白话文,但在记录讲说的内容时也有使用“笔谈”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测,《古事谈》中的“谈”也可能是一种比喻用法。这一点姑且不论,将以民间故事为主要材料编纂的《古今著闻集》作为《实录》编纂的补充这一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且书中根据中国的类书进行分类的做法,都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处于中世这样一个价值规范混乱的时期。当时,公家政权的官僚阶层欲用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仅形式上符合中国式规范的东西,来支撑勉强延续下来的王朝。
《古今著闻集》分为神祇、释教、政道忠臣、公事、文学、和歌、管弦歌舞、能书、术道、孝行恩爱、好色、武勇、弓箭、马艺、相扑强力、图书、蹴鞠、博弈、偷盗、祝言、哀伤、游览、宿执、争斗、兴言利口、怪异、变化、饮食、草木、虫鱼鸟兽等30篇。显然,此种分类仿照了中国的类书,但也有不符合类书的地方。现参照初唐时期欧阳询编纂的较有代表性的类书《艺文类聚》(624)来加以对照。卷头有“天”2卷、“岁时”3卷,接着是“地”“州”各1卷、“山”2卷、“水”2卷。至此处相当于“天文”“地文”,以下为“人文”。接下来是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符命”1卷、“帝王”4卷、“后妃”1卷、“储宫”1卷、“人”20卷、“礼”3卷、“乐”4卷、“职官”5卷、“封爵”1卷、“治政”2卷、“杂文”3卷、“武”1卷、“军器”1卷、“居所”4卷、“产业”2卷、“衣冠”1卷。另外,“鸟”“兽”“鱼贝”,甚至“灵异”等也都收入其中,最后一卷是“灾异”,共46部727个子目。徐坚编撰的规模较小的类书《初学记》(727)共23部313个子目,其基本构成与《艺文类聚》大致相同。可以说,这些类书,尤其在平安前期的汉诗文繁盛时期,作为诗文的文典被广泛使用。
虽说《古今著闻集》借用了类书的分类,却没有“天、地、人”的大分类,将“神祇”“释教”置于开头,这是与中国类书不同的显著特征。这可以看作是《日本书纪》以来日本正史中所体现出的日本式意识的表现。汉文被归于“文学”部。此外,出于对世事的关心进行了诸如“孝行恩爱”“好色”“博弈”“偷盗”等非常精细的分类,这一点也值得关注。
但是,《东斋随笔》与《古今著闻集》的顺序显著不同。大概《东斋随笔》没有补充《实录》的意识吧。而且,《东斋随笔》的编写方法与鸭长明的《发心集》中基于特定主题编写佛教传说的做法也不同。有人推测《东斋随笔》将“音乐”置于开头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儒家古流派的“乐”的尊重,但“草木”紧接其后的理由却不得而知。因此,《东斋随笔》编纂的动机不详。
与此相对,《守武随笔》可以看作是连歌师收集的滑稽故事集。与概念或分类意识不同,在研究中世的所谓随笔类的评价史时,俳谐连歌所起的作用非常大。
进入江户时期,汉诗文与和汉混同体盛行,比如山鹿素行的著作中没有以“随笔”来命名的,而是用“论”或“纪”来命名。但是,荻生徂徕学习中国明代的古文辞派,强烈批判朱子学,并把通过对伊藤仁斋古义学的批判而独自开创古文辞学的他的著作题名为《萱园随笔》。萱园即为徂徕的号。
众所周知,参加中国明代遗臣活动后流亡日本的朱舜水以水户藩德川光国的修史事业(后命名为《大日本史》)为开端,相继辅助其完成了各种事业,并为日本古代的考证(称和学或本朝学,明治前期统称为“国学”)创造了契机。在此潮流中涌现了诸如本居宜长《玉胜间》那样收录了各种笔记的书籍,内容涉及诸多领域。是否有意所为不得而知,或许是在模仿先前谈过的《容斋随笔》等“杂家流派”的形式。
在中国清代,各地都在编纂地志。受其影响,日本民间也进行了地志编纂。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江户时代的风俗或传承方面的考证随笔大量刊行。19世纪初,仅就文化而言,出现了大量著名的广搜文献并配有插图的考证书籍,如曲亭马琴的《燕石杂志》、柳亭种彦的《还魂纸料》、山东京传的《古董集》等。都是大开本,比读本、剧作类高级,可能当时已意识到这些作品属于一个类别吧。之后,纪行类、中国清朝时期盛行的地志也大量编纂,其中有完全属于民间爱好者的铃木牧之模仿别人编写的《北越雪谱》。编纂过程中,与山东京传、曲亭马琴商量过,但因未能具体化,最终由山东京传的弟弟山东京山制作出版,受到民间的好评。原本计划按季节出续编,最终因铃木牧之逝去而未能完结。以前我曾提到过,关于雪这一气象的考察明显有参考寺岛了庵《和汉三才图绘》(1712)的痕迹,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区分法。①鈴木貞美:『生命観の探究―重層する危機のなかで』,作品社2003年版,第4章11節6。
另外,江户后期曾频繁使用“随笔”一词。在兰学学术圈的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条要求提交“随笔”(考证的报告)②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日蘭関係史をよみとく―蘭学を中心に」(2012年12月8-9日)”研讨会上,从上野晶子(北九州市立自然史·历史博物馆学艺员)的报告中得到的启示。。由此可看出,清朝考证学已经影响到了民间。
明治时期,各种散文也开始进行改良。前面已经谈到过,由德富苏峰主编的《国民之友》有一段时期采取以《史论》为“文学”核心的方针,但是这里的“文学”相当于欧洲人文学(但日本的“文学”包括宗教教义书、汉文这类异语言作品、民众文艺,这一点与欧洲不同)范畴的“文学”,此“文学”概念直至明治末期一直都是主流。1895年博文馆创刊的商业综合杂志《太阳》,在目录中引入了“史传”与“随想”。“史传”就是“史”与“传”的意思。“随想”应该是“エッセイ”的翻译,是指与“评论”相对而不明确发表见解的文章。
向20世纪过渡时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比如,曾于19世纪中叶游历法国的俄罗斯贵族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所著的《猎人日记》(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1852)中使用英译题目A Sportsman's Sketches;德富芦花受到由外光派转向印象派的绘画的影响,对“写生”的兴趣大增,在韵律和声调等方面下足功夫,写出了充满散文艺术气息的作品《自然与人生》;国木田独步参考二叶亭四迷翻译的《猎人日记》中的“幽会”(《国民之友》1888年初出版;《かた恋》,春阳堂,1896年收录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芸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第88、152頁。)出版了《武藏野》(1901)并引起关注;正冈子规提倡以“描写世间存在的事物(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写出有趣文章之法”来写“叙事文”,倡导“将事物按照其客观存在的状态或看到的状态进行临摹”(报纸《日本》附录周报,1900年1月29日),并在《杜鹃》杂志上向读者征集日记,指导大家以印象深刻的地方为焦点来写日记,对地方城市中那些对俳句感兴趣的人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鈴木貞美:「日々の暮らしを庶民が書くこと―『ホトヽギス』募集日記をめぐって」,佐藤バーバラ編『日常生活の誕生―戦間期日本の文化変容』(柏書房2007年版)及『日本語の「常識」を問う』(平凡社新書2012年版)。。
人们在论及此事时常常与“言文一致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就是文言文体,这与文体的问题无关,也与作品类别无关。总之,非考察性的、情景描写或印象再现、以兴趣为中心的文章流行了起来。例如,一种被称为“写生文”的短小散文,还有一种被叫作“小品”体裁的文章,如夏目漱石的《永日小品》(1990),它从江户时代的汉文世界扩展开来,并容许加入虚构成分,也被用于杂志投稿。
在日本,“随笔”作为一种文学类别名称被广泛使用,是在1920年前后综合杂志、女性杂志大量涌现,“杂文”类作为一种不同于评论、可轻松阅读的文章被广泛接受之后的事情。自此,“小品”的名称基本被驱逐。1923年菊池宽创刊的《文艺春秋》的成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芥川龙之介连载的警句《侏儒の言葉》以及直木三十五的文坛闲话等在当时都很畅销。菊池宽则未使用“随笔”,一直使用“杂文”一词。③鈴木貞美:『「文藝春秋」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講談社2011年版,第2章第1節。同年12月、中户川吉二在水守龟之助以及牧野信一等人的协助下,以追求强烈艺术性的“随笔文学”为目标而创刊的《随笔》杂志并未持续多长时间。而1930年代内田百间(后改为“閒”)掺杂对夏目漱石的回忆,包括关于朋友关系、对金钱的信念之类的文章,以轻妙洒脱的文风写就的《百鬼园随笔》(1933)等却再版发行。我们今天所说的不问材料与形式、能让人轻松阅读的杂文意义上的“随笔”的用法,应该是1920—1930年代固定下来的。
六、“私小说”与“心境小说”
最后,谈谈“私小说”与“心境小说”的问题。“私小说”受到德语“Ich Roman”(I novel)的启发,并受到欧洲浪漫主义小说形式的影响,通常是指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题材,以第一人称(有时也用第三人称)来讲述的小说。以歌德自身的恋爱经历为题材而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被公认为“私小说”的开端。虽然小说的主人公维特因失恋而自杀,但歌德却活了下来且写了这部小说,因此仅凭这一点即可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虚构的。在法国19世纪初叶,夏多布里昂以在美国与当地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经历为原型,用流丽的文笔写了小说《勒内》(1802),描写了回到巴黎的青年的忧愁,开拓了“近代忧愁”的表现手法。自由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贡斯当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中,《阿道尔夫》(Adolf,1816)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倦怠以及被女人吸引时的心理,被誉为心理分析小说的杰作。
但是,在以野史小说、传奇小说为发端的东方小说传统中,不会将自身体验虚构化,即使在江户时代发行的大量戏剧作品中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作品。明治时期,用各种口语体来书写一般文章的习惯早已在江户时代的平民百姓中得以普及,小说类多以“なり、たり”结句的文语体来书写,在这些所谓的“言文一致体”小说的尝试中,虽然有几部作品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的,但并非以作家的自身经历为题材写就的。
因此,田山花袋将其与女弟子之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为题材而写的《棉被》(1907)被看作日本最早的“私小说”。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我”对女弟子抱有的情欲,被称作“自然主义”。然而,这部小说用一种让世间作家感到滑稽的方式描述了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达到一种自我嘲讽的效果。
田山花袋在创作时应该意识到了约翰内斯·弗尔凯特(Johannes Volkelt)在《美学上的时事问题》(Asthetisce Zeitfrangen,1895)中所说的“揭露深奥、神秘内心世界的‘后自然主义’”。弗尔凯特看到原本呈现“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家们开始倾向于神秘童话等象征主义时说道:虽然大家都说“自然主义结束了”,但自然的“揭露深奥、神秘内心世界的‘后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且近代人“神经质”的特质使人们比起“现实的感觉”越来越注重“空想的感觉”。森鸥外把这个翻译成《审美新说》并作了介绍(《栅草子》1898—1899年连载,1900年出版发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田山花袋在《小说中的象征诸派》(《早稻田文学》1906年2月号)中指出:梅特林克、于伊斯芒斯、易卜生们“欲在自然主义的核心下创出新意”,因此可以断定田山花袋应该读过《审美新说》,而且他一定也想创造出自己的新意。但是,随着片上伸的“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早稻田文学》1907年12月号)的提出,“自然主义”被当作性欲的代名词,这也成为“自然主义”在1910年衰退的原因。
实际上,随着“私小说”的方法传播开来,在德田秋声一派,即在所谓的“自然主义”作家中间流行起来,他们还写出了类似于身边杂记的一些作品。因向往法国浪漫主义而立志成为作家的宇野浩二也写了与诹访市艺人之间的爱情为题材的“私小说”,但在小说《甘き世の話》(1917)中写道:“近来小说界的一部分作品”,不介绍容貌、职业、性格等情况,“突然冒出来一个不知所以的‘我’”,“尽写一些奇奇怪怪的感想”。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使人们误认为“‘私’小说”的创作就是把作家自身的经历原封不动地写下来,这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麻烦。这里所说的没有小说样的小说,指的是以志贺直哉的《在城崎》(1917)为代表的随笔形式的作品,是从它与起源于欧洲自叙体小说的“私小说”不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志贺直哉年轻时写过以描述自己内心活动为主的《某个早晨》,有一天写稿时在笔记本上注上了“非小说”字样。1920年前后在《新潮》等刊物上,包括小说讲述者是否使用“我”来讲述等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话题。担任过《新潮》编辑的作家中村武罗夫在“写实小说与心境小说”(《新小说》1924年1月号)中,将“心境小说”与俄罗斯的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1865—1869)等欧洲的长篇大作相比较,并进行了批判。尽管是对宇野浩二提出问题的误解,但文中对“心境小说”作出了说明,即“作者直接出现在作品中的小说”,“专门讲述作者心理的小说”,这明显是在指随笔的形式。
我们知道,前面提到的池田龟鉴在《自省文学的历史性展开》中提出的“最直接地讲述自己真实的内心”的说法也是基于此说。即“心境小说”是指无需客观地介绍作家情况,以讲述自己内心世界为主的作品。
久米正雄在《‘私’小说与‘心境’小说》(《文艺讲座》1925年1、2月)中主张:不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都只不过是“伟大的通俗小说”,“真正的‘私小说’同样必须是‘心境小说’”。这其中包含了俳句中所说的“腰のすわり”以及一种东方的求道的思想。“通俗小说”是相对于“历史小说”而言的,指当代风俗小说,但在这里有着强烈的面向大众的意味。后来,久米正雄认为写“心境小说”的作家生活会难以为继,因此又倡导了“纯文学余技说”(1935年4月)。
另外,宇野浩二在《‘私小说’之我见》(《新潮》1925年10月号)中,在讲述了自己曾经关注过“白桦”派的“自我”哲学的问题后,对葛西善藏的《柯树叶》《湖畔手记》(1924)用随笔形式记述面临落魄、毁灭的心境以及接触大自然后得以慰藉的心境的价值给予了肯定,承认了“心境小说”虽然“在形式上超乎寻常”,但确是一种“私小说”。同时宇野浩二还谈道:“我们不能期望日本人写出巴尔扎克式的正规小说,同样也不能期待西方人创作出芭蕉或善藏那样的艺术。”宇野浩二也开始考虑所谓符合日本人的小说的写法了。久米与宇野两人的学说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时代的产物。
佐藤春夫则不同。他在“关于自叙体小说”(1926)中谈到了真实告白的困难及反社会性,在“‘心境小说’与‘正规小说’”(1927)中,将“私小说”比作建立在作家自身基础上的浮雕,将“心境小说”说成是散文叙事诗一样的“变态”小说,是生活在狭小文坛中的“早老者的诗”。这里的“变态”与宇野浩二所说的“超乎寻常”应属同义,因为随笔形式在欧洲并不被承认是小说。
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1919)是一部“心境小说”,作品描写了在城市受伤的神经对田园生活的兴致以及由于神经患病而感受到的美,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掀起了一股热潮。不过,由于故事讲述者的生活状况也被写在内,之后这也成为了“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在形式上的区别变得含混不清的原因。
佐藤春夫在将《病了的蔷薇》(1918)改写成定本《田园的忧郁》的过程中,把故事讲述者(主人公)只知道作一些平庸的俳谐来消遣改写成了沉浸在松尾芭蕉的世界里。但作者在小说的结构上并未做改动,仍将自身境遇比作亲手精心培育的、被虫蚕食了的蔷薇,最后以一句“你是患了蔷薇病了吧”的感叹来结尾。明治末期,蒲原有明在象征诗集《春鸟集》的序言中介绍欧洲象征主义时,以松尾芭蕉的世界为范本,展示了日本人如何用简单的语言展现高深的意境,在象征诗人中掀起了再评价之风。
佐藤春夫在“《〈风流〉论》(《中央公论》1924年4月号)中写道:在天地自然间感受“悲愁”和“喜悦”融为一体的感动以及“宇宙与永恒似乎相连的那种真实的闪光的瞬间”,“渴望能设法将其变成永恒”,并想把此愿望留在作品中,此乃艺术的根本要求,而且,人的意志从中世的“物哀”即“无常观”中脱离出来,完全与宇宙融为一体,达到心神合一,将那种瞬间的感觉表达出来的正是松尾芭蕉的艺术,松尾芭蕉的艺术与波德莱尔等的颓废美学有共通之处。同时,佐藤春夫还主张将其视为判断一部作品能否从极度关注人类思想矛盾与冲突并构成审美艺术的近代小说(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近代小说)中脱颖而出的标准。这也表明了一种文艺上的“近代的超克”的意识。
1935年,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出身的作家舟桥圣一,大概受到池田龟鉴命名的自省文学作品群的影响,借横光利一的《纯粹小说论》和小林秀雄的《私小说论》的对战,在《关于私小说和主题小说》(《新潮》10月号)中提出了“私小说传统”的观点。舟桥圣一说:“今天的私小说”是平安时代女流日记文学“残留的尾巴”,而“随笔文学”的渊源是鸭长明的《方丈记》(1212)①根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石川肇氏提供的材料。。
正是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分不清小说和随笔的区别了。志贺直哉很早就开始写《某个早晨》(1908)、《到网走去》(1910)等短篇小说,从内心世界挖掘自我意识的细节变化。前面谈到过,志贺直哉在撰写《某个早晨》的底稿时在笔记本上留下了“非小说”的字样。但是,比如他曾把刊登在杂志的随笔栏中的《偶感》(1924)编入创作集《雨蛙》(1925)中,1927年又把接到芥川龙之介自杀的讣告后写成的回忆文章《沓掛にて——芥川君の事》(后改为《沓掛にて——芥川君のこと》)编入了短篇小说集。关于这一点,他在《续创作余谈》(1928)中明确指出:也许应将追悼文编入追悼文集,但是,用心写的文章或明确表达自己心情的文章也可视为一种“创作”,对此不作明确区分。志贺直哉不区分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別,可谓之思想犯。
志贺直哉随笔形式的作品《在城崎》,描述了作者经历交通事故后前去城崎温泉疗养,在那里目击了三个昆虫或小动物的死而深切感受到了生死无常的一种心境。志贺直哉在《创作余谈》中写道,《在城崎》是按照实际经历写的“描述事实的小说”,“即便所谓心境小说,也是由余裕中诞生,并非心境”②『志賀直哉全集6』,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208頁。。这里的“所谓心境小说”是在当时人们纷纷议论俳句、议论余裕有无的语境下而言的。
另一方面,新潮作家崛辰雄也在随笔《嘉村先生》(1934)等作品中谈道:“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实际发生的,抑或是自己想象的,都是自己意识内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如此一来,随笔与心境小说的区别愈发模糊了。
此外,在1920年代的“随笔”全盛期,冈田三郎把由法国的民间传说、寓言之类发展而来的“幽默小故事”介绍到了日本。比如沙尔·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Charles Baudelaire.Le Spleen de Paris.1869年死后刊行)中即含有类似幽默小故事的成分。法国象征诗巨匠斯特芳·马拉美不仅研究希腊神话,还研究了印度民间故事,他将收集到的印度民间故事都整理在《印第安人·幽默故事》(Contes Hindienne)中。在打破定型韵律诗规范的散文诗这一新类别的形成时期,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类相互交叉,“幽默小故事”与之结合在一起传入日本后,就与讽刺幽默、轻巧的“小噺”(小笑话)掺杂在一起,获得了强劲的发展。众所周知,川端康成将其命名为“掌篇小说”并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但是其中很多作品都没有与“随笔”相区别。因此可以说,自由书写自己所思所想的“随笔”与将作者意识里的东西进行再创作的20世纪小说的创作方法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被人们所在意,一直模棱两可地发展至今。
安德烈·纪德写过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或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1905)。其中,《伪币制造者》采取了作品中小说家艾杜瓦的日记与故事情节同时展开的方式,艾杜瓦的日记中记录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来讲述的,读者可以通过艾杜瓦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得知《伪币制造者》小说情节发展的情况。纪德在作品中把唯一的“浪漫”称作“纯粹小说”。受到纪德作品的启发,1935年,横光利一在《纯粹小说论》中指出:要想将以复杂的现代社会为舞台的风俗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私小说”的形式来创作,有必要充分利用偶然性来引起读者的兴趣,抑或使用除主人公=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之外的“第四人称”(即作家统率小说世界的思想)。对此,小林秀雄在“私小说论”中谈道:不能只模仿外国作品的形式,“私小说”之所以能在日本盛行是因为实证主义没有在日本扎根,并且“多余的旧肥料太多了”。“多余的旧肥料”指的是俳句。这是小林秀雄出于知识分子应该对满洲事变后的社会积极关心的态度而提出的。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芸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第3章第3節。
此次争论中,久米正雄提出了“纯文学余技说”,菊池宽在“日本的现代小说”中也提出:“私小说或者身边小说”就是描述“与俳句所表现的达观相似的平静心情和在非社交性的自我本位世界中的生活的作品”,是“日本文学的特色”②鈴木貞美:「菊池寛『日本の現代小説』―近代文学史観を狂わせた元凶」,『Japan To-day研究―戦時期「文藝春秋」の海外発信』,作品社2011年版。。此次争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有舟桥圣一的《关于私小说和主题小说》(《新潮》10月号)。舟桥圣一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在学期间接受过藤村作的指导,可能受到池田龟鉴命名的自省文学作品的影响,提出了“私小说传统”。舟桥圣一认为:“今天的私小说”是平安女流日记文学“残留的尾巴”,而“随笔文学”的渊源是鸭长明的《方丈记》(1212)③根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石川肇氏提供的材料。。另外,“主题小说”受到了菊池宽的影响,他主张小说的主题即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东西”④鈴木貞美:『「文藝春秋」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講談社2011年版,12第2章。。
江户时代,虽然各种通俗文学盛行,可没有人把自己的内心活动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也没有出现任何与“私小说”类似的作品,随笔也倾向于考证。如果没有来自西洋的刺激,无论是“私小说”还是随笔都不会诞生。正是由于对这一点的忽略,人们才会去谈论平安时代以来的“私小说”传统的问题。战后,在说法上也有人称为“私小说的风土”。
七、研究仍将继续
舟桥圣一的意见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随笔文学”的渊源是镰仓时代鸭长明的《方丈记》。很明显,他不承认平安时代中期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是随笔。自江户时代起《枕草子》即因其题名被称为放在枕边的随手笔记,而不被视为“随笔文学”应该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科的主流意见吧。
今天,《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被称为日本的三大随笔。《枕草子》是随笔形式的作品,却明显表现出了对文体的关心。可能正因如此,《枕草子》得到了藤原定家的高度评价,后被北村季吟继承,而且即使按照西欧的随笔标准来看也会得到好评。
那么,镰仓时代末期的兼好法师的《徒然草》又如何呢?此作品发行后约百年未引起世人的关注。后来,在连歌师中得到好评,至江户时代成名。这也是作品的风格或作家的姿态让我们觉得有趣的地方吧。《徒然草》是从《枕草子》中得到启发创作的,作品中出现了名字,在江户时代已有相关论述,据说在江户时代就已出现将《徒然草》称为“随笔”的文章。但是,塙保己一的《群书类聚》却连“杂”部都未将其收录其中。
明治时期,在三上参次的《日本文学史》下卷中,对《方丈记》有如下评价:“说是随笔又像日记,说是日记又像随笔”,居于《枕草子》之下,基本可与《徒然草》并列。从此评价来看,三大随笔说的出现好像也较为合理。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史十讲》中将《枕草子》和《方丈记》称为“随笔”,但藤冈作太郎的《国文学史讲话》中却未将《枕草子》视为“随笔”。似乎三上参次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及。而且,《方丈记》的风格与其他两部截然不同。
那么,《枕草子》《方丈记》《徒然草》被作为日本三大随笔的观点是何时形成、又如何得以广为流传的呢?我推测可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语教科书的辅助教材以及考试参考书的普及得以广泛传播的。此类问题既是类别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评价史的问题。研究仍将继续。
(责任编辑:陆晓芳)
I0-03
A
1003-4145[2015]07-0074-13
2015-04-12
铃木贞美(1947—),男,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国际知名学者,曾获日本大众文学研究奖,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
译者简介:黄彩霞(1978—),女,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文学、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