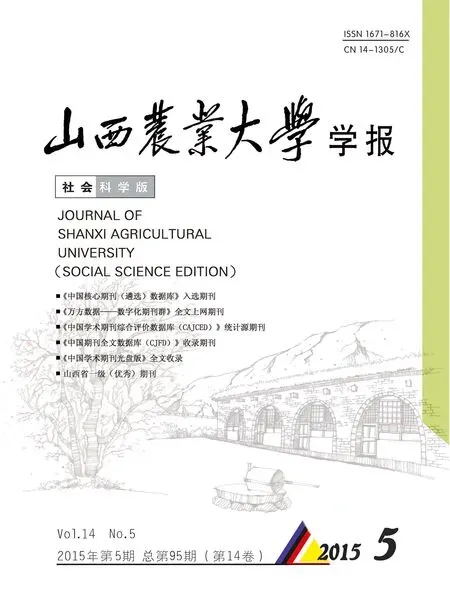论钱大昕的天道思想
2015-04-02刘湘平
刘湘平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钱大昕是我国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乾嘉学术”的开创者之一。学界以往关于钱大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方面;对于他的思想,特别是其独特性方面,则较少有人关注。事实上,钱大昕不仅是一位在史学、经学、天算、舆地、音韵、金石等传统学科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的 “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而且也是一位在思想领域的很多问题上都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本文仅以钱大昕的天道思想为例,通过回顾和分析他关于 “天道”问题的致思历程,揭示他对 “天道”的独特认识和见解,彰显他有别于一般学者的思想家品格。
一、质疑理学式的天道话语
具有哲学形上学意味的 “性与天道”问题曾是宋、明时期理学家反复辩难、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但到了乾嘉时期,随着实证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学术观念的转变,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宋明理学家关于天道的论述。纪昀 《滦阳消夏录》曾记载:
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屡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即康节最通数学,亦仅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故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先圣有言: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1]
钱大昕也曾作诗批评邵雍:
更历三万年,人缩如鸡狗。我欲问安乐:此语谁所受?太空了无言,纪述自谁某?谁从混沌前,亲见混沌后?瞿昙谭劫数,谬悠本无取。奈何拾余唾,欲与羲文耦。[2]
可以看出,对有着实证精神和深厚天算学素养的钱大昕等乾嘉学者而言,理学家关于 “天道”等问题的哲学思辨式的讨论虽然高妙宏远,但其实是没有文本依据和经不起实证科学检验的臆想。
正因如此,钱大昕在解释 《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语时,一方面针对宋明以来人人侈谈性天的流弊,强调 “天道”问题幽深玄奥,并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 (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3]并进一步指出: “子贡 ‘亿则屡中’,而犹谓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则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与此,此子产讥裨灶‘焉知天道’,而梓慎之见屈于叔孙昭子也。”[2]另一方面,他从儒学的根本精神出发,认为宋明以来盛行的关于 “性与天道”的讨论近似空谈,已经偏离了儒学的正轨,需要加以纠正和救治。因此他说:
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 《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2]
钱大昕并不否认孔子学说中包含有 “性与天道”的内容,只是认为 “天道”既然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又不是 “儒者之学”的主要内容,因此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多的主观性发挥,作悬空之谈。他将 “性与天道”问题抬升到非“圣人”不能了解的高度,目的是为了在学者已经普遍搁置 “成圣成贤”人生理想的乾嘉时期,消解宋明理学家关于 “天道”论述的合法性;他将 “儒者之学”的核心精神重新界定为 “明体以致用”,也含有纠正理学家过分关注哲学形上学问题而忽视儒家 “经世致用”精神的意图。
钱大昕的这一态度也体现在他对戴震学术的评价上面。戴震是一位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考据学者,对宋明理学家反复辩难的 “性与天道”等哲学形上学问题始终抱有浓厚兴趣,而且在 《原善》、《孟子私淑录》和 《绪言》中都有大量讨论“性与天道”的文字,在 《孟子字义疏证》中更是专门列出一卷来阐发他关于 “性”与 “天道”的思想。但据章学诚 《答邵二云书》记载:“当时中朝荐绅负重望者,大兴朱氏,嘉定钱氏,实为一时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训诂名物,六书九数,用功深细而已,及见 《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4]戴震殁后,洪榜在 《行状》中载入 《与彭进士尺木书》,朱筠对此提出异议:“《状》中所载 《答彭进士书》,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5]而钱大昕在 《戴先生震传》中对戴震 《原善》和 《孟子字义疏证》等书的内容不置一词,可知他与朱筠正持同一观点,认为 “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
二、“还原”先秦天道观
当然,对理学家 “天道”话语的批评与贬斥,并不意味着钱大昕放弃和回避对 “天道”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反对理学家的向壁虚造和任情发挥,主张通过历史语言与情境的还原去发掘儒家经典的 “原意”,是乾嘉朴学的基本观念之一。钱大昕对于 “天道”问题的思考也是如此。他没有像理学家那样,将对 “天道”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个体的领悟和体验上面,而是坚持从文本出发,主张通过对先秦典籍中 “天道”一词的归纳和分析,来 “还原”和理解 “天道”的真实含义。
具体而言,钱大昕首先举出先秦典籍中有关“天道”一词的典型文句,如:(1)《易传》:“天道亏盈而益谦。”(2)《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3)《古文尚书》:“天道福善而祸淫。”(4)《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5)《春秋传》: “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6)《春秋传》:“天道不謟。”(7)《国语》:“天道赏善而罚淫。”(8)《国语》:“我非瞽史,焉知天道?”(9)《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此基础上,他归纳出 “天道”一词的一般含义:“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3]在《〈淮南天文训补注〉序》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经典文本中 “天道”一词的理解:“尝考天之言文,始于宣尼赞 《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有变动曰物,物相杂曰文,天文即天道也。经传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2]为了证成自己的论断,他又引用郑玄 《论语注》对 “性与天道”的解释:“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3]又以此验证 《孟子》中的 “天道”概念:“《孟子》‘圣人之于天道也’,正谓虞舜井廪、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类,故曰 ‘命也’。”[3]
可以看出,钱大昕通过文本归纳和分析而得出的 “天道”概念,其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天文即天道”。这个意义上的 “天道”,指的是自然世界特别是水、火、木、金、土、日、月等天体 (即他所说的 “七政”)的运行规律。他在 《与戴东原书》中评价江永的天文历算之学时说:“天道至大,非一时一人之术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缩,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2]这里的 “天道”,正是作为自然现象的 “天文”的意思。其二,“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钱大昕根据古籍中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天道福善而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说法,认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理解的 “天道”,很多时候是与人的吉凶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意义上的 “天道”,似乎已经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指的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并且能够主宰人们吉凶祸福的超越性力量或法则。
三、阐发 “敬天修身”说
正因为钱大昕对 “天道”的 “还原”是双重的 (既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宗教的成分),因此他对 “天道”的态度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 “天道”只是日月五星等自然天体的运行,从而主张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他的 《三统术衍》、《三统术钤》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摆脱先秦天道观的影响,反而有意识地保留了 “天道”的宗教含义,并进一步发挥出了一套 “敬天修身”的理论。他的 “敬天修身”理论之要点大致包括:
(一)重建对 “天道”的信仰
在钱大昕看来,经典文本中的 “天道”指称的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超越性力量,而且“虽大贤不得与闻”;但他同时指出,古人之于天道,主要采取的是一种 “以天道证人事”的态度。所谓 “以天道证人事”的态度,就是说人们对天道的关注,不是因为生性好奇而产生 “天道是什么”之类的追问,而主要是立足于人事,反思 “天道对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他说:
古者祝宗、卜史亚于太宰,冯相、保章官以世氏,习其业者皆传授有本,非矫诬疑众。五纪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纪,天道不謟,文亦在兹。是以名卿学士,就而咨访,以察时变,睹火流而知失闰,望鸟帑而识弃次,八会之占,验于吴楚;玉门之策,习于种、蠡,虽小道有可观,而夫子焉不学。[2]
这些都是古人 “观乎天文,以查时变”,即通过观测天象来预占人事吉凶的例子。但钱大昕引用这些事例并不是真的想要复活古代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 “占星术”,而在于论证 “天道”与“人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唤起人们对“天道”的敬畏之心和重建关于天道 “亏盈而益谦”、“福善而祸淫”的信仰。他强调:“幽明之理固不可测,而行道有福,其常也。”[2]又说:“天道福善而祸淫,行道有福,违天不祥。”[2]在他看来,“天道”这种超越性的力量之于人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为人们行善得福或德福一致提供终极性的保证。
(二)发掘儒家的 “报应”说
为了强调这一保证的可靠性,钱大昕进一步发掘出了儒家的 “报应”说。他首先针对当时流行的 “儒家以褒贬劝人行善,佛教以报应劝人行善”的说法,指出 “报应”并不是佛教的专利,儒家也有报应观念。他说:
说者疑 ‘报应’两字出于释氏书,且责报于天,似非圣贤勉人修德之旨。予案 《诗》云 ‘报以介福’,《书》云 ‘报虐以威’,《礼记》曰 ‘大报天’,曰 ‘大报本’,古圣之言报者多矣!‘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报德报怨,虽施于侪辈之称,然史公传伯夷即有 ‘天之报施善人’之语,后汉鲁恭上疏言:‘爱人者,必有天报。’其时佛法未入中国,儒家不讳言报也。[2]
在此基础上,钱大昕指出儒家的报应观念是:“以天道证人事,治乱兴亡荣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恶之报如响斯应。”[2]他强调这种善恶之报“验诸 《三传》、 《太史公书》,历历不诬矣”[2],并举出 《左传》记载的具体史实来加以证明:“齐商人、蔡般皆弒君之贼……然商人终被弒,亡后,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惨死,天道果可畏哉!”[2]又在为他的学生李文藻之父李远所作的墓表中写道:“观君之行善如此,文藻之欲传其亲如此,天之报作善者,果有爽哉!果有爽哉!”[2]针对他人提出 “报应不验”的质疑,他解释说:“夫天道远,人道迩,休咎之不尽验者,其验在后,非终于不验也。”[2]并强调:“因一时之未验,置人事而不讲, 《五行志》累牍连篇,悉视为断烂朝报,此与鲧之汩陈何异?”[2]
可以看出,钱大昕之所以要竭力论证 “报应”的有效性,其目的正是要为人们信仰 “亏盈而益谦”、“福善而祸淫”的天道提供经验事实的支持,而其落脚点则是 “人事”,是为了劝人行善。
他在 《重刊太上感应篇笺注序》一文中将这层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他说:
古圣贤之学,莫先于明善。宣尼赞 《易》,于 《坤》之初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于 《复》之初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善与不善,其分别只在几希之间,而舜跖判焉。圣人不忍斯人之陷于恶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动之,不遽言恶,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犹可以善也。成汤大圣,而言 ‘改过不吝’;颜子大贤,而言 ‘不贰过’。过者,一时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过则喜,后之人告以过则愠,由是自欺以欺人,恶积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祸淫,行道有福,违天不祥,谓感应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获罪于天而无所祷乎![2]
这段文字的主旨在于阐发儒家的 “明善寡过”之学,但在行文时却以 《易》传的 “余庆余殃”说立论,而以 “天道福善祸淫”说作结;在这种今人看来似乎有些跳跃的论述结构中,正好可以看出钱大昕的真正用心:他对 “天道”、“报应”等 “幽明之理”的思考是为他的 “明善寡过”的儒家教化主张服务的;他将 “天道”这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超越性力量 “纯化”或限定为能够提供 “福善祸淫”、“亏盈益谦”的终极性保证的力量,其实是在尝试着用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德福一致”问题,从而为儒家 “劝人为善”的教化主张提供理论支持。
(三)提出儒家的 “敬天”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钱大昕进一步在与佛、道二教的比较中提出了儒家的 “敬天”说。在《重建集仙宫玉皇殿记》一文中,他从 “劝人为善”的角度肯定佛、道二教在 “教化”层面与儒家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指出:“二氏之教,其宗旨与吾儒异,其欲人迁善而远罪则同。”[2]并认为儒家与佛、道二教相对应的教化理论就是 “敬天说”。他在文中写道:“圣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处高而听卑,福善祸淫,亏盈益谦,皆视其人之自取。圣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复于善,其自处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鉴在兹,故能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而为内省不疚之君子。 《诗》云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2]在 《募修圆元道院疏引》中,他再次指出:“予惟圣贤立教,以敬天为先,孟子云: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善事天者,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极之一出王一游衍,常若昊天之在其上,在其左右,是以日迁善改过而不自知也。”[6]
从钱大昕对 “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 “天”似乎具有一种宗教的意味,但 “常若高高者之日鉴在兹”、“常若昊天之在其上,在其左右”中的 “常若”二字,又可以说明他的 “敬天”,其实是一种 “祭神如神在”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强调或突出 “天”的存在感,能够“使人知天之可敬而从事于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预远于不善,则上之可以入圣,下之可以保身,而广之可以善俗”;[2]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天”的可敬可畏只在于它有而且仅有规范人类活动的 “福善祸淫”的力量和法则,并不具有赏善罚恶的意志,因此 “求福于天不若求福于己”,因为 “作善者不求福而福来,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2]可见,钱大昕所说的 “天”虽然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 “天道”的形象化,而不是可以主宰人间一切事物的人格神;他所说的 “敬天”,实际上是希望借鉴佛教与道教的经验,将 “天道”划入信仰的范围,更好地为儒家的教化理论服务。
总之,钱大昕依托先秦儒家天道观而发展出来的 “敬天修身”说,是一套以建立对天道 “福善祸淫,亏盈益谦”的信仰为中心,以解决人类“德福一致”问题为目的,而以对个人的 “从事于善,预远于不善”的劝戒为归宿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钱大昕在批判宋明理学家天道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经典文本中 “天道”一词的考释,“还原”出了 “天道”的科学含义和宗教含义。科学意义上的 “天道”,主要指的是自然天体的运行规律;而宗教意义上的 “天道”,则是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并且能够主宰人们吉凶祸福的超越性力量。对于科学意义上的 “天道”,钱大昕主张采取实证的办法来加以研究;对于宗教意义上的 “天道”,钱大昕基于 “经世致用”的考虑,将其视为解决人类 “德福一致”问题的终极性保证,划入信仰的范围,并阐发出一套适应时代需要的有宗教意味的 “敬天修身”学说,从而在与佛、道二教的竞争中,为儒家 “明善寡过”的教化理论提供了新的基础和依据。他的天道思想也许不像戴震的道论思想那样深刻和系统,但也涉及到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体现出一位学者在思想领域的不懈追求。
有的学者举钱大昕的 “报应”说为证,认为“为了与反佛特别是批判轮回说的立场相呼应,钱大昕在利用儒家经义这一理论武器时,对其中的天人感应、灾异符瑞等另一种形式的神秘主义有时也不惜加以推崇和发挥”,因而对钱大昕的这些思想评价很低。[7]钱大昕的确没有简单地否定古代的天人感应、灾异符瑞思想,但如果据此而推论他对古代 “神秘主义”思想有 “推崇和发挥”,而且这种 “推崇和发挥”是为了 “与反佛特别是批判轮回说的立场相呼应”,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说法。
首先,钱大昕对所谓的 “天人感应”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与古代的 “天人感应”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古代的 “天人感应”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些思想如 “天象见于上而人事应于下”等等也确实存在将人事活动与自然现象进行盲目比附的神秘主义倾向,而且在士大夫中还很有市场。例如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就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而且对这些内容津津乐道、笃信不疑。[8]但钱大昕则不同,在他的著作中很少有这种直接将自然天象与人事活动联系起来的论述。上文已经指出,钱大昕对 “天”或 “天道”的理解有科学含义与宗教含义之分。他所说的“天人感应”中的 “天”,实际上主要是就其宗教含义而言的,并不指称自然天体及其运行规律;他的这种宗教意义上的 “天”,与原始儒家存而不论的 “命”有一定关系,但不像 “命”那样充满了偶然性,而是被限定为一种具有 “福善祸淫”功能,因而只是一种能够为人类行为的 “德福一致”提供终极保证的超越性力量或法则。可见,钱大昕并没有对古代的神秘主义 “加以推崇和发挥”;恰恰相反,他的天道思想正是对古代的神秘主义思想加以理性化的一种表现。
其次,钱大昕提出的 “报应”说等理论,其出发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佛。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由于政治条件以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明清时期的儒学发展有一种 “下行”的趋势,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便是王阳明在传统儒家 “得君行道”的理想破灭之后,开启了 “觉民行道”的新方向。[9]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那么钱大昕的这套包括 “报应”说在内的 “敬天修身”的理论,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儒学的 “下行”和“觉民行道”的新趋向在乾嘉时期的流衍。他在《星命说》中明确指出:“圣贤知命而又能立命,故不为祸福所动。”[2]可见他对儒家的 “俟命论”是非常了解的。只不过这种 “俟命论”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德福一致”问题,因此以之 “教天下之君子”则可,以之 “教天下之小人”则不足,在教化层面不像佛教的轮回报应说那样具有 “震怖人心”的力量。而钱大昕的 “敬天修身”说正是在借鉴佛、道二教经验的基础上,对儒家 “俟命论”的一种补充。他的 “敬天修身”说也许隐含了与佛、道二教相对抗的意图,但其重点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儒家宗教性思想资源的发掘,完善儒家的道德学说,更好地 “觉民行道”,而不仅仅是为了反佛。
此外,从哲学的角度看,钱大昕的 “敬天修身”说所要解决的 “德福一致”或 “德福相配”问题也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许多哲学家如康德、牟宗三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仅就致思方式而言,钱大昕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康德较为接近。他将指称自然天体运行的 “天道”归为科学问题,主张采取实证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而将指称 “主吉凶祸福而言”的“天道”归为宗教问题,并倾向于用信仰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种将 “天道”一分为二的思路,似乎也含有为科学与宗教划界的意味。我们并不因为康德在其道德学说中设定了 “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而认为他的思想是西方中世纪宗教思想的复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钱大昕的天道理论中有 “报应”说等内容而断定他的这些主张就是古代神秘主义思想的复活。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了解一位思想家说了什么固然重要,但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可能更为关键。钱大昕的天道观念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 “敬天修身”说自然有其理论缺陷,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他对 “德福一致”这个问题是有过认真思考的,他的思考是乾嘉时期思想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借鉴价值。
[1]纪晓岚.纪晓岚文集 (第2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79-80.
[2]钱大昕.潜研堂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82,419,422,419,596,419-420,860,423,388,387,387,98,859,388,388,422-423,329,329,330-331,330,50.
[3]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 (第7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7,57,57,57.
[4]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683.
[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3:98.
[6]陈鸿森.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 [A].林庆彰.经学研究论丛 (第6辑)[C].台北:学生书局,1999:197.
[7]张涛,邓声国.钱大昕评传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2-474.
[8]许苏民.顾炎武评传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82-691.
[9]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3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