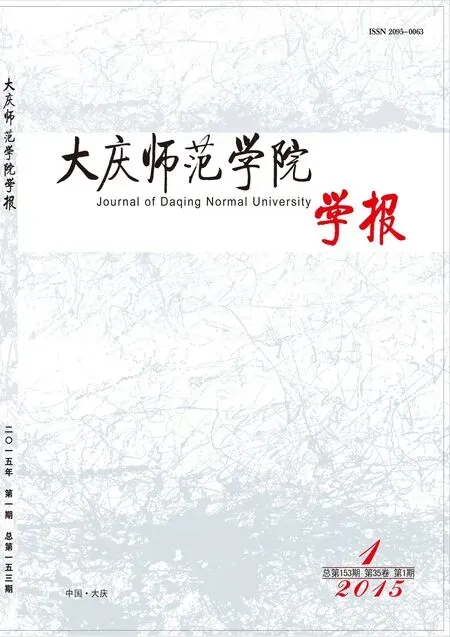20世纪后期国外再洗礼派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及新路径探析
2015-03-30王建
作者简介:王建(1983-),男,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欧中古史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24
1962年,乔治·威廉姆斯名著《激进宗教改革》 ①正式奠定了激进宗教改革研究分支的地位。此后,国外史学界围绕再洗礼派的起源、思想渊源和本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再洗礼派的起源问题上,学者们按照起源地的数量可分别划归一元发生说和多元发生说,与起源问题密切相联的是再洗礼派教义的思想渊源问题。按照追溯到的源头所在的时代,各种观点大致归类为中古渊源论和同期渊源论,两类论断之下又各自可以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观点。再洗礼派的本质问题是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得出了许多大相径庭的结论。上述这些争论一方面体现了本领域史学工作者不懈追求历史真相的精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许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因素。在这些争论中,史学界兴起的社会史潮流为激进宗教改革和再洗礼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社会史的方法对排除再洗礼派研究中主观因素的干扰,达到史学研究“求真”之目的大有裨益。随着研究的深入,截止到20世纪末,以社会史的方法解析再洗礼派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试图在考察国外自威廉姆斯《激进宗教改革》一书发表到20世纪末整个再洗礼派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因素和在争论中新辟出的社会史研究路径进行初步解析,以期为学界提供些许参考。
一、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因素
与史学观点相比,史学工作者自身的立场更具根本性。再洗礼派研究中的史学工作者有的明确意识到并毫不讳言自己的根本立场,有的则声称自己在努力摆脱主观立场的影响。但在后一种情况中,无论怎样努力地保持学术上的客观性,都无法摆脱一些甚至是作者自己都无法觉察的因素的影响。在上述争论中,许多史学家的观点明显受到其教派立场、政治观念等的影响,从许多论述中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地区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子。
(一)教派立场
几乎所有有关宗教的历史研究都受到研究者宗教或教派立场的困扰,有关激进宗教改革的研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早期,不同派别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的功利性应用,使其客观性受到严重影响,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为教派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名的工具。从新教史学和门诺派史学的对立中,可以明显窥见这种倾向。早期新教史学对待再洗礼派的态度由主流改教家们奠定。除布林格尔外,主流改教家们都对再洗礼派持排斥态度。马丁·路德不遗余力地攻击所有激进派别,不加区分地将他们统统称作是“狂热者”。 [1]加尔文同样敌视再洗礼派。 [2]此后几百年,占主导地位的新教史学对再洗礼派的论述更多的像是对路德等人论调的注释,以至于后世的门诺派史学家声称他们之前的史学都偏见地将再洗礼派称作是“革命分子和狂徒” [3]。
当代新教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原有的敌视态度,转而试图从更加客观的立场上研究激进宗教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罗兰德·班顿。其他当代新教史学家也同样试图通过对原始史料的研究来解读激进宗教改革,如罗林·阿摩尔试图通过典型性地分析来考察再洗礼派对洗礼问题的看法。 [4]不过,仍有新教史学家坚持传统立场,如杰弗里·埃尔顿认为再洗礼派的吸引力是“仰仗着给穷人、弱者和充满愤恨的人带来权力和荣誉的主张”,不仅如此,还指责再洗礼派的主张极易导致恐怖。 [5]
对于对立的另一方即再洗礼派的史学家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门诺派史学家寻找自身历史源头的努力推动了激进宗教改革史学研究中门诺学派的崛起。不同的学者给这个学派冠之以不同的名称,有的称其为“本德学派”,有的称其为“戈申学派”。 ①这时的门诺派史学与新教史学针锋相对,有着强烈地为再洗礼派辩护和正名的意味。1960年以后门诺学派在对再洗礼派的认识上有了一些调整,有学者称其为“新门诺学派”, [6]189笔者认为上述调整只是具体史学观点的变化而非根本立场的改变,故仍将其划归门诺学派。这个时期,门诺派史学的派别意味同样开始变淡,但也有例外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霍华德·尤德。 ②
新教史学和门诺派史学纠缠不休的争论引起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烦感,史学求真的精神也始终激励着许多努力追求公允立场的史学家。作为对上述两种史学在方法论上的回应,激进宗教改革研究中的世俗学派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发力。这一学派的学者虽然并非都是门诺派信徒,却也多信奉基督教,之所以称其为“世俗学派”是因为这一派着重强调在“方法论上的无神论”, [7]而其出现的背景则正是上述“会内”史学家各自的教派偏见造成的研究困境。世俗学派的学者包括维尔纳·帕库、汉斯-尤根·格尔茨和戈特弗里德·塞巴斯等,他们的研究极大地开阔了激进宗教改革史学的视界。有的学者称他们为“调和论者” [8],笔者更倾向于称他们为“多重本质论者”。
(二)意识形态
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除受教派立场的影响外,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的对立上。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影响尤为显著。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激进宗教改革研究主要通过闵采尔及其领导的农民战争连接起来。另外,胡特尔派等实行财产公有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关注激进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最早关注农民战争和再洗礼派的是恩格斯 [9],受其影响,考茨基曾专门对再洗礼派及其财产公有制做过考察 [10]。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继续对农民战争给予关注,由此延伸出对再洗礼派的考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学者是东德的格哈德·切比茨。切比茨一方面批判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对部分再洗礼派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在对再洗礼派性质的界定上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比有所差异。 [11]33切比茨的解释对西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世俗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习惯用阶级的观点解释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比如亚历山大·斯奇特斯沃诺。 [12]不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中的贡献已经得到公认,特别是一些从社会史角度考察再洗礼派的学者,在很多问题上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启发。正如阿瑟·迪肯斯等人所说:“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以来,他的历史观催生了一个持久且极富影响力的史学传统,而非仅仅是一种‘时髦’,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 [11]234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对再洗礼派研究也同样适用。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反,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习惯于贬低闵采尔及激进宗教改革中偏好“革命”或“暴力”的一翼,而推崇主张和平主义的另一翼。在当时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许多实际对抗中,这种观点都有了用武之地。一些学者,如富兰克林·里特尔、汉斯·希尔布兰德等,将自由教会传统的源头追溯至再洗礼派。这种观点自被提出以来,始终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如约翰·欧耶尔指出,现在一般都认为再洗礼派至少应被认为是自由教会运动的先驱。 [13]有的学者盛赞再洗礼派对人类历史和现代文明的重要影响:再洗礼派的遗产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中每一个先进文明的宝贵财富”。 [14]但笔者认为不宜不加限定地过高评价再洗礼派在自由教会运动中的作用,虽然再洗礼派中有个别领导人,如胡伯迈尔,确实明确地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张 [15],但从总体上看,再洗礼派的自由主张更多的只是其神学思想的推论,而非一套明确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三)地区性、民族性问题
虽然尚不能直接以国别或地区为标准划分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中的史学流派,但也不能忽视各地区或国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对其史学工作者的影响。“民族对不同基督教模式的决定性影响的问题”早为罗伯特·弗里德曼所觉察 [16],现在这些不同模式又反过来影响学者们的认知模式。例如,美国的历史学家在考察激进宗教改革时,特别热衷于从自由教会的角度阐释问题。美国门诺学派在认定再洗礼派正统新教的性质时,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美国福音派教义作为标准来衡量问题。 [6]189与此相对的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则对社会史的方法情有独钟。在对具体问题的考察上,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影响,例如在许多学者确认荷兰门诺派起源于瑞士时,荷兰的许多学者则坚持门诺派本土性起源;东德的学者在论证闵采尔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地位时,捷克的史学家则强调约翰·胡斯对闵采尔的影响。 [11]203涉足本领域的史学工作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不能不意识到这些或多或少存在的地区性和民族性问题。另外,在研究部分激进宗教改革和再洗礼派问题时,也应意识到我国学者天然具有的能更好地保持中立性和超脱性的优势。
二、新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径
二战以来,各种学术潮流不断兴起,极大地影响了宗教改革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新兴社会史的影响。社会史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领域,自被提出后不久,就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学术潮流,横溢于史学研究中近乎所有的领域,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激进宗教改革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领域,也同样受到了波及。在再洗礼派研究受到诸多主观因素干扰而日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社会史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为再洗礼派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史潮流的影响日趋明显,各种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再洗礼派的学术著作不断出现。总的来说,这种新的路径在再洗礼派研究中有较好的适用性,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在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再洗礼派的著作中,取得成就最大的应属克劳斯-皮特·柯莱森。在《再洗礼派社会史: 1525—1618》一书中,他运用从政府和教会官方等处获得的大量原始史料,详细分析其中的数据,通过对各种数量对比关系的考察,试图从中确定再洗礼派的组成成分、内在动机和社会影响等。通过这些分析,柯莱森最终得出结论:再洗礼派成员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重很小,影响有限。 [17]柯莱森的著作因为在再洗礼派数量、影响、与政府关系等方面所做出的大胆结论而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学术著作,其中对德意志南部和瑞士等地的再洗礼派的考察,直至今天也是最详细的。除专门研究再洗礼派的社会史著作外,更多的是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包括再洗礼派在内的宗教改革的著作,比如吉诺·马奈弗的关于安特卫普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状况的著作就有部分涉及再洗礼派。他指出,虽然当时再洗礼派在安特卫普的组织状况甚为糟糕,但他们仍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并积极利用安特卫普的地域优势传播其思想。 [18]
再洗礼派历史中的一些特殊领域,比如经济、妇女等问题,也开始受到社会史学家们的注意。彼得·卡拉森的《再洗礼派的经济: 1525—1560》也是一部关于再洗礼派的重要社会史著作。 [19]在这部专注于再洗礼派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卡拉森也同样通过筛选、整理大量的史料,得出了许多关于再洗礼派主要领导人的经济观点、胡特尔派的财产公有制实践等问题的重要结论。卡拉森的考察表明,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财产占有上,再洗礼派确实试图重建使徒时代的模式,但卡尔·考茨基的解释,即再洗礼派的经济观代表了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观点,遭到了卡拉森的否定。卡拉森认为,再洗礼派的经济观是效仿门徒身份的一个推论,他们在互助中所展现的神学理性是建立在救赎而非创世的推论之上。这些有力的论证使这部著作成为一部系统研究再洗礼派经济理论及其在再洗礼派神学中地位的重要著作,并对关于当时基督教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重要帮助。除这本专著外,由加尔文·雷德克普、维克多·A.克兰和塞缪尔·J.斯坦纳编订的《再洗礼/门诺派的信仰与经济》是一本集中讨论再洗礼派经济问题的论文集。 [20]在16世纪,基督教通常将信仰、经济和社会正义问题分割开来,再洗礼/门诺派的实践挑战了当时基督教中的这一通行的做法,认为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经济问题按其本源来说实际上就是信仰问题。雷德克普等编订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试图全面考察再洗礼/门诺派的经济主张和实践从早期到当代的变化。书中共收录了19篇相关论文,所有的作者都是研究再洗礼派问题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再洗礼/门诺派信众在时间长河中忠于自身经济理想的程度。
还有的学者致力于考察再洗礼派妇女。罗兰德施·班顿最早开始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妇女问题 ①。受班顿启发以及社会史潮流的影响,研究再洗礼派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在班顿发表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妇女史研究之后,C.阿诺德·施耐德和琳达·A.赫克特编纂了关于再洗礼派妇女问题的专题论文集,集中考察了分别来自瑞士、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地三十多位妇女。 [21]从对再洗礼派妇女的个案考察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的再洗礼派妇女不会读写,所以反映在个人著作中的直接的思想流露基本无从可考。绝大多数关于她们的信息来自当时的宗教或世俗法庭的审讯。这些研究还表明,再洗礼派妇女与她们同时代的姐妹们相比更多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活动。这些妇女也同样面对着更多的危险,其中一些饱受折磨甚至殉道而死。此外,直接记录再洗礼派妇女心声的史料虽然很少,再洗礼派的理论家们对妇女还是有相当的论述的。不过这些论述相对散乱,任何专门的研究都必须首先以系统的史料整理为前提。乔伊斯·L.欧文完成了这些分散史料的整理工作,由他编订的《激进新教中的女性: 1525—1675》史料集为再洗礼派妇女研究提供了许多极富意义的史料。一般来说,那个时期讨论妇女的部分大都夹杂在那些处理其他问题的综合性著作中,没有欧文细致的整理、汇编工作,这些论述就很容易为史学家所忽略。因此,这本史料集对包括再洗礼派在内的激进派妇女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史学家在特殊的社会史领域里的耕耘,往往能从一些通常为人所忽略的问题上得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对认识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乃至整个宗教改革和当时的时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尽管有上述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很显然,对再洗礼派社会史中许多特殊领域的考察还有待完成。
还应该注意的是,西方史学界已经有人在尝试提出一整套解释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的理论框架。美国东部门诺会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尼斯在其论文中提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所揭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与运作机制和兰德尔·柯林斯的关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意识形态的变迁。他指出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直接作用于社会变迁。通过使用上述理论,可以构建起一套关于意识形态变迁的全新理论。如果将其运用到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中,就可以从理论的高度更加深刻解释相关的问题。 [22]虽然尼斯提出的只是个理论框架,国外目前也尚无完整的关于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的宏观理论出现,仍然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一种专门为这种历史现象提供有力解释的系统的社会史理论。
总的来说,社会史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对再洗礼派起源多元化、性质多样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为再洗礼派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其性质与再洗礼派显著的“平民”性共同决定了它能够有效地运用于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罗伯特·W.斯克莱布诺的“大众信仰”对上述研究的有益启示就是一个例证。 ②
此外,柯莱森在《再洗礼派社会史: 1525—1618》一书序言中的论述也体现了对这种联系的独到体悟:“再洗礼派信徒并非全然是像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一样的宗教思想家,他们展望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他们也不像人文主义学者那样孤立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是一个由成千上万普通农民和工匠汇成的社会运动。因此,我选择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再洗礼派。” [17]15正因为如此,再洗礼派研究与社会史的观念和路径一经结合便显示出极大的活力,这种活力由两者的性质决定,并不断地推动着再洗礼派研究向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自1962年威廉姆斯发表《激进宗教改革》一书到20世纪末,国外再洗礼派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无论是在再洗礼派的起源、思想渊源还是本质问题上,都出现了争鸣的局面。在这种史学论争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影响研究客观性的因素,教派立场、意识形态等干扰因素都侵扰其中。这些因素与史学研究“求真”的目的明显相背,严重妨碍了揭示历史真实面貌的努力。在这种纷乱的背景下,社会史观念和方法的引入无异于一股清流,为再洗礼派和激进宗教改革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排除各种主客观因素滋扰,努力达于历史本真。这一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认识的规律,即史学认知在不断地争鸣和努力地祛除干扰因素的影响中交替,螺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