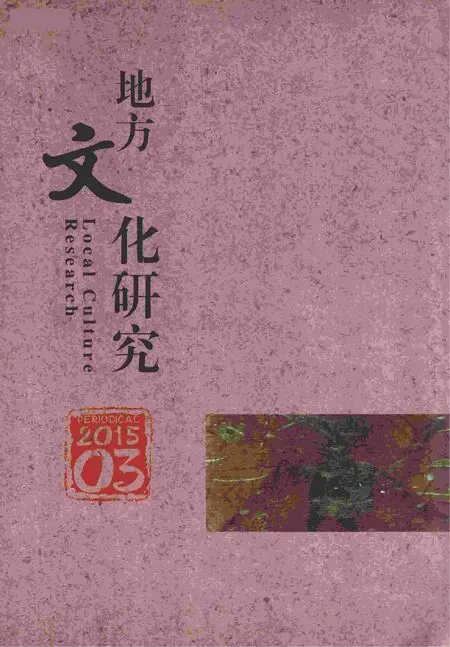浅议黔中王门李渭的思想
2015-03-30张小明
张小明
(中共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贵州 贵阳,550081)
王阳明龙场悟道和贵州传道是“黔中王门”形成的契机。阳明居黔时开创并初步构建了心学思想体系,同时影响了贵州阳明学派以后的思想、组织进程。黔中弟子们传承、发展了阳明学说,形成了“黔中王学”学术思想。其中,李渭取得的成就较大,他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黔中王学的学术水平与面貌。本文对黔中王门重要人物李渭的思想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学思历程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贵州思南府人,生于正德九年癸酉(1513)十二月,卒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四月,为王阳明在黔再传弟子。于嘉靖甲午年(1534)乡试以《易》中举,出仕华阳县知县、和州知州、高州府同知、应天府中南户部郎、工部郞中、韶州知府、广东副使、云南省左参政等职。晚年卸职回乡讲学。
李渭之学从小受于庭训,十五岁生病时,父亲以“毋不敬”、“思无邪”勉励之:“居小楼……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于是专求本心。”①(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嘉靖癸卯(1539)楚中王门巨子蒋信提学贵州,李渭前往问学,蒋信破其“楼上楼下光景”。嘉靖己未(1559)任高州府同知时,拜谒湛甘泉于小嵎峒中。嘉靖癸亥(1563)过麻城访泰州王学耿定向、耿定理兄弟,定向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缺一不可。”②(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任韶州知府时,为王阳明大修祠宇,并与诸亲炙弟子证道论学:“九月,门人陈大伦建明经书院于韶,祀先生。……是月,洪谒甘泉湛先生于庾岭……与邓鲁、胡直等共阐师说。至隆庆巳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诸生与黄城等身证道要,师教复振。”③(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37 页。与南中王门徐阶书信来往,存斋《复李同野太守》。泰州王学大师罗近溪“与太守李同野渭游南岳,……即发明良知实践之学,切切肫肫,务求真实。”④(明)李安仁:《石鼓书院志》上部,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后擢升云南左参政时,又与近溪同在滇做官,学问益进:“本体原无间断,学者不可在起灭上做工夫。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自是欲罢不能。”①(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江右王门邹元标被贬都匀期间,与同野往来论学,对之极其称道“首访清平孙淮海、思南李同野,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②(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为其《先行录》作序。此外,其他王门学者跟其也有论学书信来往,并加以论赞。如邹守益弟子李材《答李同野》,刘宗周之师许孚远《与李同野》,江右王学胡庐山为《大儒治规》题:“四儒治规”,并称:“黔中之学李湜之为彻。”③(明)郭子章:《黔记》卷45,明万历刻本。其弟子郭子章担任贵州巡抚时,将李渭列入《黔记》的理学传等等。李渭与黔中王门其他人物孙应鳌、马廷锡等多次切磋学问,互相砥砺。他为马廷锡《鱼矶别集》作序。孙应鳌为他赋诗云:“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④(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并来思南作诗《题孝友堂》。逝时,耿定向《祭李同野》悲呼:“前年丧胡正甫(庐山),去年丧罗惟德(近溪),同志落落如晨星,而湜之又继之长逝,斯道将何?”⑤(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2,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明神宗按其学问品行亲题:“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明臣。”⑥(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他归纳自己为学之变说:“吾于此学,入白下⑦注:张明认为“白下”应该指拜访湛若水(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阳明学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迁高州府同知,至则谒甘泉湛先生”,那么为学之变,指拜访湛若水与耿定向兄弟的不同。而通过笔者考证,“白下”一词,出现在焦竑为李渭作传中:“公自言于学,入白下见耿师,与居和、高时不同;过楚登天台又觉与白下不同;与近溪游月岩,复觉有不同者。如登九级浮屠,随步而异,所谓未见其止者。”(明)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32页。)故而,“白下”指首访定向,而非拜访湛若水。(首访耿天台)时,觉与官和州时不同;登天台(二访耿天台)时,又觉与白下时不同;与近溪(罗汝芳)游月岩,又觉与前不同。”耿定力《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也论其为学之变:“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且远哉!道林先生(蒋信)破其拘挛,余伯兄(耿天台)谓之有耻,仲兄(耿定理)直指本心,近溪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⑧(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郡后人张清理《谒李同野先生祠》追述了他的思想:“绝徼儒宗阐治规,名臣正学总堪师。功争一介机原密,梦绕三蛇觉未迟。山盗不离心盗外,下楼仍记上楼时。黔州道脉由公肇,俎豆千年系我思。”⑨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府续志》卷10,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他的著作虽大都佚失,但根据地方史志与其他学者相关论说等等,能窥其思想概貌。
二、心性思想
我们知道,阳明学本身即以心性论为根基、特色。李渭虽然对阳明心性思想也有所认识,但更重“仁”的讨论,直接以仁为体。这是由于当时阳明后学中有股思潮,出于对“现成良知”论过于提及心体,导致可能消解道德功夫的忧虑,提倡直接跳过宋明,以传统“仁”为宗,表现一种回归先秦孔孟之根本精神的倾向。故而,李渭心性思想主要谈论的是“仁”,而非阳明学通常之心体、性体、良知。也就是说,阳明学的心、性、心体、良知等基本范畴与命题只具有理论背景价值,被其“仁体”说所统摄、消融。
李渭对“仁”这一儒家传统观念重新进行了一定的解读、发挥,并且逐步确立起了以“仁”为体的理论视域。他说:“孔子学,学仁也。”⑩(清)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旗帜鲜明地说孔学为“仁”学,学孔是学“仁”的精神。他主要是把孔孟的“仁”做了心学时代的解读,明确说“仁”为“体”,“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⑪(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7,明陈氏居敬堂抄本。李渭认为“道”如果被遮蔽不明,仁本体就会被撕裂,如同天地闭塞,其全体大用就不能呈现。他在本体论层面上说明了“仁”的合法、合理性。使得其“仁体”说既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又具备很强的实践可行性。
同时,李渭对仁体的理解、论说,离不开身处时代思潮的阳明学“良知”说。他是把仁体与良知结合起来给予说明,也只有如此,其“仁体”说才能更加合理地得以建构。对李渭这一独特的心性思想,门人萧重望在《同野先生年谱·序》中有精辟的归纳:
加诚敬于仁体,因防检废兢业,认知识为良知,以致知为剩事者,遑遑皆是先师有忧之。亹亹斐斐破本末之二见,谓动静非两途。说择种、说保任、说立民命、说求友亲。人知见则以为不同修,悟则见谓无二论。圣体有果种在地之喻,论理欲有常清常明,不增不減之说。以无不知爱,无不知敬为天地灵窍。以不学不虑为不勉不思种子。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为无纤毫人力功夫。辟异端,黜浮摩。启先行孔道,止毋意奥阃,任仁宗孔,继绝开来,心独苦矣。先师卒之,明年同门中州罗公国贤不倍,熊君时宪仰之,安君岱惧型范远而征言,绝洙泗之宗,复悔支离之痛复起也。①(明)郭子章:《黔记》卷14,明万历刻本。
萧重望旗帜鲜明的揭示李渭学说宗旨,是遵循且统合了孔子“仁”学与阳明“良知”说。同为黔中王门的孙应鳌明确指出:“良知者,仁体也。”②(明)孙应鳌:《贺姜泉南公寿序》,《孙山甫督学文集》卷3,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出版,2005年。可以判定,很多阳明后学把仁体与良知等同起来,李渭也是如此,其“仁体”实质是阳明的“良知”。“仁”一直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与精神,而阳明学“良知”是“仁”在中晚明的时代新形式。当“仁”明确为“仁体”之后,“仁体”与“良知”之间实质一致,完全是可以通用的。当然,二者还是有所差别的。我们发现,李渭心性本体思想更加推重“仁体”而非“良知”,这有着他的良苦用心,是为了解决阳明后学“良知现成论”带来的空疏流弊。他首先在具体求仁之方法上反对“认知识为良知,以致知为剩事”。这主要是学习且遵奉了阳明的相关理念,“心学视野中的‘仁体’或‘良知’都是指主体确有其实性实理,具有道德形而上的本体意义。这样的‘体’决不能用知识分解的路向解释,不能向外求取,须用心、用生命当体体证。”③(明)张小明、王晓昕:《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思想初探》,《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 期。所以,萧重望说李渭担忧把外在的知识等同于主体内在良知德性。同时,既然区分知识与良知,那么应该把致良知放在第一位。李渭认为:“以孔子遗书比偶为文词,是枝叶耳。国家课士以枝叶,因以观士中藏,非教人逐逐外鹜也。”④(明)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那么,李渭也反对不以致良知为第一要务,而为次要的“剩事”。他反对追逐名物知识的支离之学,忧心朱子学支离毛病再起来断绝了儒家真正的学旨、精神,而直接以简明自得的“仁体”为宗旨。既然李渭宗于阳明学的运思理路,在功夫上自然就反对“加诚敬于仁体,因防检废兢业”。阳明学内在性的理路直接在“心体上用功”就用不着画蛇添足的“诚敬”功夫,此即李渭认为的“程子不着纤毫人力,皆非从安排得来。”⑤(明)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31 页。他自然主张无需艰苦地“诚敬”功夫,反对“加诚敬于仁体”,直接在仁体上用功,是无须防检的。
李渭对孔孟仁学的理解,整体上做了心学的诠释、发挥,成了他心性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对于其构建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价值。但以“仁体”为主旨的思想与阳明“良知”宗旨略有不同,可以看做是对阳明思想新的开发。不仅如此,他有最根本的用心,从其整个思想体系上看,是为了针对良知现成论的弊端。所以,李渭认为:“万间新学甚盛,士子競务讲席以为名高。其言既不皆于正,而其行又绝无以副之,则狂妄之病中之深也。”⑥(清)万斯同:《列传一百五十九》,《明史》卷308,清抄本。明万历年间阳明学盛行天下,但有的阳明后学过于凸显心体、自信良知,如王畿等人就造成狂妄空疏诸多弊病。正如杨国荣所说:“王畿现成良知易导向以本然之情、意为良知。在泰州学派那里,以本然之知为现成之知与注重情、意相融合,逐渐导致了理性规范的架空。”⑦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76、266 页。因此,李渭明确以“仁体”而不是“良知”、“心体”的名称,应该具有深意。仁体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本质,是性体,更加具有理性。而“良知”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导向心体,王畿、泰州诸人往往就有只强调良知心体一面,轻视其性体的向度,这样容易消解道德理性规范,从而出现弊端。如果说,“泰州学派与李贽从不同侧面对心体内含的个体之维作了引申,那么,刘蕺山则更多地注目于心体的普遍性向度,并由此表现出某种回归性体的趋向。”⑧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76、266 页。确实,在阳明学流变过程中,晚明有股补偏救弊的思潮。他们要求凸显性体,压制心体,以性体监控、主导心体。出于对现实社会中阳明后学流弊的不满,李渭“仁体”说的提出也是其努力之一,表现了某种回归朱熹理学,甚至孔孟原始儒学的潜在期望。
三、“毋意”论
李渭对阳明心学之“意”话题,作了特别的反应,曾著有《毋意篇》,并在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以“毋意”为学说主旨。耿定力以此归纳了他的学思历程:“公之学……卒契毋意之宗。”①(明)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表明他的学说,是在蒋信、耿定向、耿定理、罗近溪等人的指导与影响下,建立和完成了“毋意”论。弟子萧重望用一语概括到:“先生之学,毋意也。”②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府续志》卷11,贵阳: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贵州后学俞汝本也说:“(李渭)其学以毋意为主”。③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府续志》卷11,贵阳: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当时人们都指出他的思想特色是以“毋意”为宗旨,并以此而知名于晚明思想界。
李渭在阳明学背景下,把源于孔子的“毋意”与孟子、程颢的观点结合起来,对“毋意”说做了心学的诠释、发挥。他说:“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着纤毫人力’,皆非从安排得来。知毋意,即千思万虑皆毋意也;知无纤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实无纤毫人力也。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而已。”④(明)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31 页。“毋意”出自《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的原意一般理解为不要主观臆断,不要刚愎自用、绝对肯定,不要固执拘泥,不要自以为是。孔子之“毋意”只是常识性的学习、生活方法,而他把孔子的“毋意”、孟子的“不学不虑”、程子的“不着纤毫人力”等同起来,显然李渭的“毋意”打上了宋明理学时代的烙印。朱熹曾解释道:“毋,《史记》作无,是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辞。圣人绝此四者,何用禁止?’意,私意也。”⑤(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 页。毋为无,那么从字面上“毋意”等同于“无意”,而意为私意,毋意即没有私心意念。这一与道德修养联系的解释对宋明理学家非常有影响。李渭之“意”也是当私意、意念看,从而提出“毋意”这一与道德修养关联的功夫论。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李渭在阳明学背景下建构了此论。李渭说孟子“不学不虑”,即孟子讲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⑥《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有不学不虑的先天良知良能,阳明主要就以此观点论证了良知学,他在体系中多次提及了孟子的渊源,如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⑦(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9 页。阳明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学、不需要虑而本有的先天德性。程子论“不着纤毫人力”,思想背景是《定性书》。程颢认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⑧(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 页。定指动亦是定、静亦是定,没有绝对的动,也不存在绝对的静,即动静一体、不能分割对立。“无将迎、无内外”是情感没有私心,自然而然的顺适万事万物之理,不要有任何的拘执、滞著,从而保持主体内心的安宁和满足。从而,使“性”该动则动,该静则静,达到动静皆定的廓然大公境界。“定性”的意义就是不能以外物为累,但不是说不要外物,不与外物相接触,断绝人生来就有的思虑情感。程颢的此一思维模式、理念对宋明理学家影响颇大,李渭自然也很受感触,他多次讨论了程颢的相关观点。李渭把“良知”、“定性”与他的“毋意”说结合起来,说:“知毋意即千思万虑,皆毋意也。知无纤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实无纤毫人力也。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而已。”“毋意”并非是断绝意念而绝对的不去思不作为,反而是主张千思万虑都是毋意。“毋意”无纤毫人力是强调化而不有、化而不执著,也是已百已千到极至而有的化境。其实,“千思万虑”、“已百已千”是有、敬畏,“毋意”、“无纤毫人力”是无、洒脱,李渭此说有着有无、敬畏洒脱有机结合的特点。此说是为了如何有效的把握“不学不虑”之仁体或良知,即“毋意”说的提出是为了实现、推致此仁体。那么,毋意为功夫,仁体是本体,李渭把“毋意”与其心性本体关联起来了。李渭进一步对门人说:“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与言学矣。”①(明)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他以天上常清常明,流水不增不減形容良知心体的本体特质,而以浮云人间作雨,狂风江中作浪说明功夫的艰难。所以,他探寻了多种功夫,现在以“毋意”作为功夫要旨。
总之,“毋意”道德修养功夫不是消除、泯灭念虑,而是使念虑为仁体的自然发用流行。这是典型的内向性心学运思理路,阳明后学中有相当多学者的观点与李渭“毋意”相近。我们知道,心学的路子主要认为“心之发动处谓之意”②(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1 页。,而心发动之意有善恶之分,故功夫的关键在“意”上。“意”论为阳明及后学的主要特色,受其极力重视。李渭非常重视“意”的讨论,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以“毋意”为宗。李渭的“毋意”论,顺从于阳明反对程朱外在路线转向内心,即“毋意”随顺主体所固有的仁体、良知,本心自然流行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孙应鳌在此问题上的解说正好表明李渭的运思:“圣人之心,其始也,任理而发,何‘意’之有;其继也,顺理而行,何‘必’之有;其既也,与理俱化,何‘固’之有;其终也,与理俱止,何‘我’之有;蓋未感,只是一寂然之体;既感,只是一顺应之常。故无是四者之累。”③(明)孙应鳌:《孙应鳌文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1 页。只要顺着主体人心所固有的道德本体,从始至终纯任天理而发而行,自然顺应、无滞无著。这就是李渭说的“以不学不虑,为不勉不思种子”,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意”与仁体、良知自然而然的契合。根据阳明学良知自能实现自身的思路,“不学不虑”之良知仁体的呈现、落实,自然用“毋意”的道德功夫论。如此,将本体与功夫贯通起来,达到一致。这样,一切行为自然都出于道德本体,从而只能纯善没有恶产生的可能。
四、“先行”说
在阳明“知行合一”观风行天下的时代思潮中,许多阳明后学全面地、系统地承接了此论。而李渭却剑走偏锋,他没有像其他后学那样系统的梳理阳明“知行合一”说,而是直接以“先行”取代“知行合一”。而且,李渭用“毋意”的道德修养功夫论,是为了直接切入心性仁体,走的是“极高明”一路。同理,“先行”说也是求仁之方,是为了实现“仁体”,走的是“道中庸”一路。如此,虽然都将本体与方法融通起来而达到一致,都能自我诠释、自圆其说。但“毋意”说带有的“良知现成”味道,在阳明后学中近于龙溪、近溪等“良知见在”重本体的特点;而在他晚年时提出了极重实践功夫的“先行”说,这近于钱德洪、邹守益等的重功夫特点。所以,他改“毋意”为“先行”论。
李渭著《先行录》鲜明的提出“先行”,其说来源于孔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④《论语·为政》。的君子观。在邹元标为此作的序中,可以集中看到“先行”说的思想意蕴:
予(邹元标)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譊譊为哉?躬行足矣!”曰:“子知适燕者乎?先诇道里寥廓、山川纡回,然后可以适燕;不然,其不至于摘植塞途者几希!学之不讲,徒曰躬行,亦奚异于是?”。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者非耶?”曰:“此夫子告子贡问君子意也。子贡堕在闻识,故药其病而告之。且圣人与君子有辨,曰圣人,吾不得而见。欲得见君子者,此可以见矣。”他日又告之曰:“予一以贯之,此希圣极功也。”未几,同野先生以《先行录》命余弁卷端。余叹曰:“伟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学者,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夫妇昆弟朋友焉。言理便是实理,言事便是实事。近学者谈杳渺之论,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蹩。其为不学子讪笑而讥议者甚矣!呜呼!其是天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吾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彼讪笑而讥议者,亦吾之躬行之未至。与先生论学而以躬行名录,诚末世之瞑也。”友曰:“子今左,躬行何居?”曰:“知行一体,识得语知而行在其中;语行而知在其中;语先而后在其中。”先生(李渭)昔尝以毋意为宗,观其言曰:“学贵修行,若不知德,与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见;以手扶壁,有足不前。”子可以观矣。子知先生(李渭)之学,则余昔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万里圣途,即之则是。凡我同盟,请绎斯语,庶几为适燕之指南也夫。①(明)莫友芝:《黔诗记略》卷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邹元标说他在没有看见李渭《先行录》之前,对知行关系的看法存在毛病。在往日(为李渭《先行录》作序之前)讨论时,朋友说为学不在于整天空谈,而在于躬行,在亲自实践中才能足够知理,而元标当时的回应非常接近于程朱的观点。朱熹认为知在行先,先知才能行,“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②(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元标说如果要去一个地方,必须先要知道、探问去这个地方的道路方向、远近、状况等“知”的问题,有了“知”然后才可以“行”,去要去的地方。否则会迷茫找不到方向,是不可能到达的。所以元标主张“学之不讲,徒曰躬行,亦奚异于是?”如果不先讲“学”,不先把“知”搞清晰明白,仅仅说“行”就缺乏知的指导,只能徒劳无果。其实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就是针对朱熹等宋儒这样“先知后行”的知行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③(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 页。在阳明眼中元标主张“学之不讲,徒曰躬行”就是朱熹理路,认为必先知了然后才能行,其实就已经将知行看成两个事了,分割了知行。元标作为江右王学后期的主要代表,说明他在贵州时期未见李渭《先行录》之前,至少在知行关系上的看法是不符合阳明学理念的。用阳明的话说这种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积习已经很久了。如果按照元标的看法,要去一个地方,“先诇道里寥廓、山川纡回,然后可以适燕。”就是阳明所说的先做“知”的讲习讨论功夫,等到知得真了,完全了解了,然后再做“行”的功夫。这样就把知、行对立起来,当成两回事,如果终身不行,那么终身也就不知,所以阳明表示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就是针对这种毛病。
接着元标又与友人讨论了《论语》中子贡问君子的话题,因为是在儒家道德哲学范围中,所以其讨论中规中矩,符合传统以来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是李渭“先行”说的题中之义。元标认为这是孔子针对子贡堕落、滞著于闻识中,以多闻多见、巧言善辩自得,这对德性的培养、提升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往往成为障碍,所以“药其病而告之”。他还认为儒家圣人与君子虽然有差别,圣人高于君子,只能为人们所仰视,不能轻易得见。但君子人格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品格。他在与友人讨论完之后,不断回味,后来坚定的表示此品格就应该是他一以贯之的要求,是他仰视、学习圣人的最佳功夫。我们就可以看到,李渭的“先行”说是把阳明学“知行合一”论与孔子以来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道德要求结合起来。二者的完美结合,就是李渭著《先行录》的动机。
当然,如果仅局限于此,那么也只能说李渭具有阳明学道德哲学家的普遍特征,而没有独特之处。李渭此论的提出最根本的目的是针对当时阳明后学的流弊。所以这就是元标在读了《先行录》后的赞叹,“伟哉,先生之心乎!”他深深地理解“先行”说的精神,李渭提倡“仁体”而很少谈论阳明“良知”,在心性思想上就已经不自觉的表现出了一种越过阳明学人,回归孔孟原始儒家的理路。同样在功夫论上的“先行”说还是有种回归孔孟味道。由此,元标赞美李渭“先行”论符合“古”之精神。认为其说理便是实理,说事便是实事,不空谈虚玄。而“近学者”即指有的阳明后学“谈杳渺之论,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蹩。”阳明后学末流喜好空谈“良知”,是渺茫之论,故作玄虚的高远清谈,忽视了儒家君臣、父子等具体的、基本的日常伦理规范,只能成为“跛蹩”之弊,为人所讥笑讽刺。元标觉得自己未能重视躬行功夫,也属于被讥笑讽刺的对象,虽然有谦虚的因素,但其由衷的佩服、赞美,我们是完全能感受到的。故而,元标认为在研读了《先行录》之后,他要以躬行、先行为重,而且李渭“先行”精神有着对阳明后学末流补偏救弊的努力。元标了解“先行”论之后,则反省昔日没能以躬行为准。他说现在受到了此论的影响,今后完全以李渭的“躬行为正”,“先行”学符合儒家正理不能有任何的细微间隔。这是“万里圣途,即之则是”,他号召“凡我同盟”阳明学的同好、同志应该寻求李渭“先行”,并遵奉他讲的事理,这才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最佳路径,“适燕之指南”。一定程度上,元标受此影响,“是江右王门从高谈空寂转变为面向人生的思潮中,最后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①参见胡迎建:《论江右王学的“致良知”》,《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 期。
李渭“先行”更多关注知行功夫问题,其知行思想主要解决功夫向度。这不是说李渭不懂得阳明“知行合一”,用元标理解李渭的说法:“知行一体,识得语知而行在其中;语行而知在其中;语先而后在其中。”李渭也知晓知行为一体、本然合一,说知必然有行,说行本身就内含了知,说“先行其言”,那么“而后从之”自然包括其中。李渭《先行录》说到:“学贵修行,若不知德,与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见;以手扶壁,有足不前。”为学可贵的在于修行知德,此“行”偏向道德精神修养功夫,这也是阳明“行”内含的一个层面。如果不知道、理解道德(知),等于没有进行道德修养(行),就好像进入黑暗的地方,有眼睛却看不见,用手扶墙壁,有脚却不向前走。即“知”出现毛病,“行”自然也会出现问题,故而知行一定要合一,其实李渭逻辑上内含了知行合一主张,虽然更重视“行”。由此可知,李渭剑走偏锋只重“行”的目的,是为反对“良知现成”论带来的空疏流弊。
五、结 语
从李渭整个学说来看,他对阳明本人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命题,有传承、发展,也有不足与偏离。他以“仁体”重于“良知”,“先行”取代“毋意”,甚至“知行合一”,有着良苦的用心,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与理论价值。李渭的思想特点是总关注某些问题,表现出片面的深刻。在一定意义上,他发展了阳明学说,在某些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当然,也发现他对阳明一些重要观点有把握不到位的地方,有谨守矩矱而无大发明的缺陷。然而,不能以此就抹杀他在阳明学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横向参照其他阳明后学流派,也有理解出现偏离,甚至谬误之处,这正是阳明后学发展的历史本来情景。可以说,包括李渭在内的黔中学者不仅仅是对阳明个人魅力的尊崇,他们主要还是通过对阳明基本问题的承接、拓展,才能成为众多阳明后学流派的一部分,构成阳明学史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晚明宗于阳明学的学者为了维护阳明及其思想,针对某些阳明后学的流弊不断地进行补偏救弊的思考,李渭对此也做了应有贡献,说他是这一思想史的一个环节有所夸大,但至少对这一论题有所思考,有所价值。他提出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众多路径之一,一定程度上能对治阳明后学的某些弊端,值得称道。由此可以认为,李渭不仅是黔中王门,也是整个阳明后学群体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