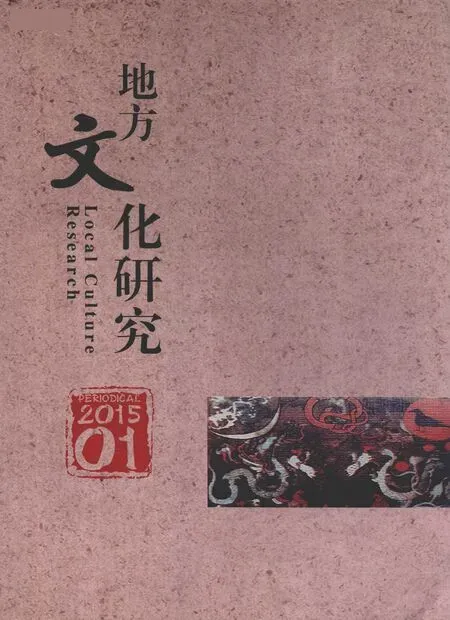贵州“喇叭苗”家族史调查与相关问题探析——以晴隆县长流乡为个案
2015-03-30叶成勇
叶成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贵州“喇叭苗”家族史调查与相关问题探析
——以晴隆县长流乡为个案
叶成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文章以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喇叭苗”家族史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喇叭苗”名称的演变,以及在明代的来源、构成及其参与的战事活动和与土著融合发展的复杂性。指出分布于今晴隆、六枝、盘县、普安一带的“喇叭苗”组成相当复杂,有明初洪武时期前后进入的湖广土军和官军,更有弘治年间平定“米鲁之乱”后留下来的湖广土兵或官军,还有明中期自湖湘雇佣来黔的卫所卫戍军士中的游离者;籍贯有湘西、湘西南、湘中南的不同地域之分。“喇叭苗”群体及其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异源合流”。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是内地汉人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要在“先湖广人”与“后湖广人”之间、汉移民与土著之间、“汉化”与“夷化”之间、地域化与国家化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互动关系。在当地多民族杂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湖湘之人与不同的民族有融合,但融合程度不一。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史志将“喇叭苗”或归入汉,或归入苗,或归入仡佬,或称为“民家子”,这些看似混乱矛盾的称谓或归属,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入黔的湖广军人来源的复杂性及其与不同土著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喇叭苗”;家族史;源流;民族融合
长流乡位于晴隆县最北端,距县城101公里,地处黔西南州北大门,北与水城县猴场乡相连,东与六枝特区中寨乡隔江相望,西与普安县龙吟镇毗邻,素有“一鸣惊四县”之称。2013年8月3日—16日,在晴隆县文体广播电视局李宠局长和张六瑜副局长的亲自安排和指导下,贵州民族大学调查组一行7人(叶成勇、袁本海、贺鑫鑫、杨培飞、潘春、韩基凤、杨莹)深入长流乡开展实地调查访谈摄录工作。笔者与杨莹、贺鑫鑫调查了长流乡“喇叭苗”主要家族的历史源流,以下先按家族分别进行介绍,然后对相关历史问题作一些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一、晴隆县长流乡“喇叭苗”家族史调查
(一)鲁打龙氏家族史
“鲁打”之名,含义不明。1988年鲁打乡属中营区,乡政府设于鲁打。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过程中,长流乡、鲁打乡合并为长流乡。政府所在地移至长流,鲁打政治地位下降,分设凤凰村和虎场村。但当地人仍按传统的意识,称这一片区为“鲁打”,中心地带包括虎场村横山组、白家组、中田组和凤凰村城子组、凹子组、鲁打组。这一地区人口密集,田畴广阔,成片分布,水源较充足;文教也较发达,有小学两所和中学一所,素有整个长流乡“历史文化中心”之称。
龙氏家族成片密集地分布在鲁打片区核心地带的凹子组和城子组,达600户,约3000人,是鲁打最多的姓氏。其次是李氏,稍少于龙氏。此外,最近十余年来,有极少数附近村寨的外姓人迁入。
关于龙氏家族的历史,我们主要访谈了凤凰村城子组的龙洪周先生(68岁),拍摄了其抄存的龙氏家谱《派衍湖广宝庆》,并在他的带领和介绍下,全面地踏查了龙氏家族历史文化遗迹。①长流李定斌提供原谱之复印件。
龙氏祖籍湖南宝庆府州城武冈,据说是明代“调北征南”时迁入,至今已传23代。字辈为:公—必—科—猷—筑—腾—景—启—现—光—兆—泽—应—玉—荣—昌—洪—如—治—化—显—庭—芳。而鲁打龙氏始祖龙筑松,为龙氏入黔第五世孙,传至今已19代。龙筑松弟兄三人,其排行第二,先住晴隆马场。居住一段时间后,老二、老三一起再次外迁,以求生计。老三年幼,走路时落后,老二托行人捎信给老三,说:“你见到有背包包的小伙子,叫他走快点。”老三听到此话,很不服气,离开老二,走向六枝一带。从龙筑松重孙龙启贵墓(在虎场村鲁打小学旁边的虎场包包)前有乾隆十一年(1746)墓碑看,龙筑松直接迁入今鲁打凹子的时间,估计在明末清初。当时此地荒芜,龙氏以开荒种植求生计,与战争无关。
关于鲁打龙氏源流,谱牒也有所记述。龙洪周传抄之龙氏家谱名《派衍湖广宝庆》,为龙洪周之曾祖龙玉田于光绪时期主持修撰。谱书以韵文体形式叙述明代龙氏入黔的情景,史实较详实,可作以上口述史的补充和参照,现摘录其文如下,以作比较。“洪武调北征荒,三丁抽一剿蛮方。大帅兵权执掌……轰轰烈烈上阳关……分防五营四哨,驻扎镇远溪阳……扫平开州立县,先立南龙府官,次取安南立都堂……”
(二)长流李氏家族史
1.源流
长流(原名长牛)李氏,追其入黔始祖为李昶,但不知经过多少代。至李升、李昂兄弟时,始入长流。现当地李氏族人都说不清楚李昶与李升、李昂兄弟是什么关系。李氏最早的祖茔墓碑纪年为康熙年间。与李氏同入长流的还有刘氏,刘姓始祖刘聪、刘靖,与李升、李昂或说是表亲关系,或说是同母异父,但都有血缘关系。又据虎场村横山组李文才讲:李升留在长流,李昂回湖广原籍。李升最先住晴隆老营头,后至江西坡,为兵丁。来长流平“红仡佬”后,即定居于此。李文才这支至李升第五代后裔时才移居于横山、白家。
六枝中寨李昌学家藏光绪十年(1884)《李氏家谱》详细记载有李氏入黔和历次征战情况①长流李定斌提供原谱之复印件。:
洪武十二年,贵州之南洪猫革老叛逆,李昶奉命调北征南,始业普安龙场。二十四年,攻打普纳山等地,平红苗仡佬反叛。其有三子,长子李庚哥,回湖广原籍,仕哥出战云南交趾国,原籍云南。任哥自安南移居江西坡,于来茨勒头建石牌坊,新开龙场,次落皮古,打坝,浪石魁,巽水头上居住,移民楼底下,后居老屋里,流传数代。李昶罢职为民,暂息为农,各守本分、本业者凡几,或移居他乡,不知凡几。
李昶祖籍湖广衡州府類阳县车马村易都十里穿心十字街。蒙封黄迁仕,郭晚云焦为两路先锋,从京远以上,攻打黑阳大箐,杀尽洪[红]猫革老,上安平、安顺,剿上镇永宁,复征过黄河凉水营,立哨扎屯,观看安南好点地形,才将半城关改关立位,请梓开工,修造安南城,修成三千七百朵口,安定三千七百朵口军。洪武二十四年,又剿毛口、六堕、□□、□店、洪寨、半坡、阿朗、木龙、鲁打、长牛,追过皮古、打坝,剿上罗寨,排勒头,四处安营立哨,攻打普纳山,代剿雨谷、海寨。二十五年,复征猴昌河,二十六年迁立龙土官,得职。管理四十八目头人,夷蛮尽归投降,贵州四处平安,李昶又领兵剿战上云南交枝[趾]国。
转命奉昌安民,调北征南,议定:先命五旗,征剿设法,五瓚统军,具分五旗、五所;先将四大军门,占立四十八屯、七十二堡(谱),概是三千七百御林军,三千七百朵口军,三千七百马草军,其有甲分人民田亩夫役粮草、花蔴、水口、丁银,具注册薄之上。系是我昶公子孙永远经收,乃为家谱。
自洪武调北征南,吾始祖昶公寓□安南卫,以为总督,系皆军伍,俱分五旗五所。第一旗:于祖云,李秀山;第二旗:黄思恭、刘荣宗;第三旗:彭武仲,王金凤;第四旗:廖思付、李明五;第五旗:郭晚雲焦、张才富、叶天才。总旗:□□□叟,罗□。小旗:邓藏。百户之首是王文。领兵创立安南卫□公战道,瞒文兴,除了北关几名军,三千居屯,五百在城。
康熙三年,打郎岱。四年,攻水西。一十八年,陇土官匪叛龙场,攻打普纳山,□□为堖笆子,康熙二十一年……”
2.字辈
①李定斌提供了一张家传的长流李氏分房世系图,毛笔绘制、抄写,当地人称为“路记”。原文未标明年代,估计为光绪时期所记,与前述《李氏家谱》同时撰成。但世系图不以李昶为始祖,而以李升为始祖。所载字辈:升—春—景(有六兄弟,即:景仙、景华、景贵、景衡、景荣、景秀),景字辈起分房如下:
长房:景仙—仲—应—阳(胜、阿)—仕—君—奇—国
二房:景华—(章、何、可)—仲—应—(太、顺)—仕—(君、朝)—开—洪
三房:景贵—(滔、唐、□)—仲—(应、运、震、云)—(太、朝)—仕—朝—开
六房实传三房下来。景仙无子,景衡填房;景秀分江西岭;景荣无后。
②李氏家神所记字辈:(升、昂)—(春、登)—景(恒、荣、贵、秀、华、先)—仲(全、显)—运(富、贵、福)—(顺虎、仕学)—朝(松、柏、贵、栋)—开(科、举)—洪(驰、浩、章、光)—荣(先、笔、显)—杨(胜、朝)—胜全—元(会、章)—凤(良、才、明)—昌—(玉、佐),共16代。
③溪流村营盘组李定宾所抄录李氏字辈:景—仲—应—顺—仕—朝—开—洪—荣—杨—耀—芳—室—明—定—安—帮—兴—镗—君—大—选。现此房已传至兴字辈,共18代。
由于李氏三房没有统一的字辈,各房自有字辈,但不甚严格执行,显得很混乱,故无法确定李氏至今世系代数。但据李定斌先生讲,长流李氏各房世系传承代数多少不一,最多的房族已传22代。
(三)刘氏家族史
关于刘氏家族史,受访人为长流村白杨组刘佐进(72岁)、虎场村上百家刘凡通(70岁)、长流街上刘胜候(80岁)、长流村长流组刘凡毛(51岁)、溪流村下湾组刘衍海(63岁),各人所述皆有不同,字辈上则大同小异,不超过22代。
①刘佐进所述字辈:聪—凤—大—国—天—启—世—如—朝—廷—家—佐—凡—远—胜—安—邦—定—册—益—友—万—载—兴。刘佐进还说,长流白杨组刘氏已传至“安”字辈,共16代,而溪流村传至“定”字辈,共18代。
②刘凡海所述字辈:聪—奉—大—国—正—德—天—启—世—如—朝—廷—家—祚—凡—衍—胜—安—邦(传至此辈)。较刘佐进所述多出“正、德”两代。
③刘胜候所述字辈:聪—凤—大—国—正—德—家—作—凡—远—胜—安—邦—定—国(传至此辈)。此字辈当有遗漏,已被当场同时受访的刘凡毛指出错漏之处。又据刘胜候介绍,民国时期土匪多,刘、李氏修建长流营盘(位于今长流村营盘组背后),土匪来时,寨人跑上营盘,连猪、牛也要赶上去。现营盘仅有残恒半墙,石门也无存。
④刘凡毛所述字辈:聪—奉—大—国—正—德—天—启—世—如—朝—庭—佐—凡—远—胜—安—邦—定—国—万—载—兴。已传至国字辈,共20代。他追述时记忆很清楚,不假思索,说明对刘氏字辈很熟悉,当可信。
⑤刘衍海所述字辈:聪—凤—大—国—正—德—天—启—世—如—绍—庭—家—佐—凡—衍—胜—安—邦—定—国。已传至国字辈,共21代。刘衍海对刘氏字辈也比较熟悉,不假思索便写出来了,当可信。刘衍海所述字辈与刘凡毛所述仅多出“家”字辈,而此字辈是4人都提到的,而且是现在健在的“佐”字辈的父辈,时间距离很近,应有这个字辈。
总之,长流刘氏世系代数最多21代,距今500年左右,早不过明代中期。另外,我们在长流乡虎场村坡上组调查当地“武教”传承历史时,“武教”先生刘凡福言其所习“武教”为家传,祖籍湖广宝庆府,其坛名“宝山坛”,来贵州已传21代。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氏字辈较可信。刘氏世系代数与李氏传承22代的情况接近,说明当地人盛传的刘、李二氏同时入长流故事可信。各人所述字辈中之“奉”与“凤”,“朝”与“绍”,“祚”与“佐”,“衍”与“远”皆因音近而异,实属同一辈分。可见,刘氏虽然有统一的字辈,但主要靠口传,故误漏歧义难免。
另外,据六枝中寨乡上寨村刘衍达所抄录的约修订于清道光、咸丰时期的《刘氏宗枝谱书》,字辈与长流刘衍海所述字辈相同。笔者有学生刘竟辉君,为中寨刘氏之后。据其口述,中寨与长流两地刘氏本同宗,传说有一个老祖宗死在当地,在抬回家途中的一个晚上,一夜之间,棺材被蚂蚁起土埋起来。当时被认为是吉象,遂留了一支刘氏守这个老祖宗,遂演变为今日的中寨刘氏。《刘氏宗枝谱书》中恰好记载了在大字辈时有刘大举死于郎岱之事,刘大举“由安顺告案转郎岱属,路途病故。葬于双夕塘,跟前左侧,立有碑记。”文献记载和口述比较吻合,当属实。中寨与长流虽然字辈相同,但是在《刘氏宗枝谱书》中,聪字辈前却多出了五代人,即怀玉—(忠、信)—(金、全)—源—(纲、纪)。这涉及到刘氏入黔及其早期世系传承,特录《刘氏宗枝谱书》原文如下:
厥后落籍江西吉安府,世系难稽,后又肆籍三楚,遂家居宝庆府新化县,历有年所。适至大明洪武祖设立调北征南,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而我怀玉祖亦在十二名军中之列焉。我祖原名刘怀玉,与李怀宝二人属内亲,又极为友善,共顶军名。因年久,后辈之人讹传为刘亥玉,怀宝辈相与讹传,土俗呼字不认真,将怀字呼为亥字。此由近县处之人闻得真原名,故敢录真而易其谬耳。
刘怀玉起后6代世系为:怀玉—(忠、信)—(金、全)—源—(纲、纪)—(聪、俊)—奉(明、朝)。其间,刘全习道教,凑名法全,已转回湖广。刘金生刘源,刘源亦习道教,凑名法旺。刘聪与刘俊生于长流,刘俊亦习道教,凑名法俊。刘聪葬于长流瓦厂坳,大概就是长流以刘聪为始祖之故。由于年代久远,刘聪之前世系多被遗忘,正如谱序所言:“但只知以聪为始祖,而不知上有刘李怀宝几辈可也。”
“我始祖于平复之后,即落檐于安南江西坡,后过长流十二寨人。”
(四)邓氏家族史
1.源流
据邓召灿(58岁,杨寨村烂田组,在鲁打小学从教38年)介绍,邓氏始祖邓荣宗,祖籍湖广邵阳,带领罗、戴二氏进入普安龙吟,管理从江西坡至龙吟皮古的九冲九凹,至今已传25代,500余年,是本地最早的汉移民。邓荣宗是调北征南时,朝廷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从内地派兵入黔征讨,当时邓氏有五兄弟,故来了两兄弟。先到黑洋大箐,后到晴隆,时有人跟踪他,为了避免跟踪,在晴隆莲花山宰了一匹马,把他的坟包好,又过往江西坡,再至龙吟一带,死后葬于此(今龙吟岭干脚)。1997年清明节,邓氏合族于此扫墓。邓荣宗来贵州的目的是镇压“夷苗仡佬”,扫除残余,安宁地方,并非正式参战打仗,进攻冲锋。
这支邓氏现在居于盘县、六枝、水城、长流、鲁打、中营(田寨邓家槽),以水城和盘县最多。晴隆之地主要分布在长流、鲁打、中营,普安之地主要分布在龙吟。与邓氏同来的还有罗氏和戴氏。罗氏以长流杨寨村居多,集中在兴昌组、杨家组、光荣组;此外,则主要居住普安江西坡。戴氏主要居住在晴隆碧浪、箐口一带,长流、中营一带无。长流其他姓氏,龙、李、刘等都晚于邓、罗、戴三姓人。
2.字辈
邓召灿老师口述并书写邓氏字辈为:荣—仲—胜—祖—兴—友—思—万—秀—景—宗—尚—良—克—历—朝—庭—心—吉—连—召—瑞—仁—能—品(现传至此辈),共25代。后来到邓召灿老师家中,见其家神所载邓氏世系为:荣—仲—(铭、钦。单名,下同)—(盛、训)—(剑、华)—(钦、起)—友—思—万—秀—景—宗—尚—良—克—想—朝—廷—星—吉—连,共21代。口述中缺失较多,故当以家神牌位为准。加上在世的,邓氏至今传25代,当可信。可惜我们在长流未见到邓氏谱牒。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鲁打街上有一胡氏家神所述其祖先牌位,已有14代。传承世系为:迂(道、迁)—芝忠—金(环、权)—仲富—登(甲、明、秀)—连(贡、先、达、榜、魁)—兴(德、邦)—正(禄、文)—仕(顺、才、显、朝)—永(万、寿、清、章)—国(彪、明、昌、玉)—盛(龙、炳、堂、才、金)—伯考九良—堂兄州喜。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对这一姓氏了解甚少,容将来再做调查。当然,长流乡不止上述家族,对于其他家族我们未作调查。本文以下认识主要是以笔者调查获取的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而提出,这对于认识“喇叭苗”家族史及其相关问题还略微显得有些欠缺。不足之处,希望学界批评指教。
二、“喇叭苗”名称的来历与演变
关于“喇叭”族名来历,当地人有两种说法:
1.与女性服饰有关。结婚时女性头发结成“喇叭”状,故名“喇叭人”。妇女穿大袖口服装,用花带修饰,与头饰辉映成趣,构成“喇叭苗”极鲜明的外在标志。
2.与“壁笆”有关。“壁笆”又称为“朗笆”或“攩笆”,又由此衍伸出“朗笆子”或“攩笆子”。“朗”和“攩”,都是当地方言词,有推和挡之义。光绪十年(1884)《李氏家谱》记载:“康熙十八年,陇土官匪叛龙场,攻打普纳山,□□为堖笆子。”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卷28《普安县》下云:“兴让里有老巴子,亦苗类,由湖南移居于此,其服饰与汉民同,语音稍异。”堖笆子,老巴子,即指“朗笆子”,音稍异,可见此名出现不晚于清中叶,且写入其家谱中。
邓召灿老师解释了“壁笆”的来历:居住时,为防土著或外人侵略村寨,用“壁笆”安装在房壁上作抵挡,从屋里看外面很清楚,相反从外面看屋里则不清楚。当有人来侵犯时,屋里人双手扶住“壁笆”,推倒压向敌人,敌人不防,则被压倒成一片。这当是“壁笆”又称为“朗笆”的原因。“壁笆”以芦竹编制而成,根据房壁需要,有三角形和长方形状,不用抹泥,平时作房屋墙体,战时作防御性武器,可以撤下来,临战时当盾牌使用,故有抵挡之义。长流和中营一带流传一首《战场歌》:“前头陡陡岩,后头大路来。听得山上有号叫,朗起笆折打上来。”正是此意。现在当地较有年代的一些木房外均围以石墙,且左右侧石墙上部多有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小孔洞,当地人称为“炮洞”。这种长方形、三角形、圆形的孔洞(“炮洞”)以石墙为防御主体,是原先木房墙壁上实体“壁笆”的转化形式,也应为防御性设施,与“壁笆”功能类似,这可能是石墙与土枪炮普及后较进步的形态,同时兼有通风的作用。从“壁笆”到石墙及其上部的小“炮洞”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房屋居住形态的变化,同时其防御性特征也表明“喇叭苗”与土著长期混住互有争斗和征战的史实,实属于汉移民垦殖中的自我防御设施。今当地居民修造新房几乎不用木材作房架,而是以石块为基本材料,建成钢筋水泥结构式楼房,在外石墙壁上仍保留有“炮洞”,当是传统习惯使然。但其形态很不规整,排列位置也比较随意,功能进一步退化,很多人说只是起通风之用,有的则为穿孔架木棒其间,铺上木板以隔别室内空间,构成楼之上、下部分。
3.“壁笆”、“朗笆”、“攩笆”、“朗笆子”、“攩笆子”、“堖笆子”、“老巴子”、“喇叭人”与“喇叭苗”之关系。前三种说法都出自本地,本由居住房屋之建筑特色“壁笆”而起,“壁笆”从居住房屋建筑角度而言,“朗笆”、“攩笆”从防御性角度而言,所指实为一物。因其早期特殊的防御性功能而成为一种族群的外在性标志物,故有“朗笆子”、“攩笆子”、“堖笆子”、“老巴子”之称,所指皆同,音稍异而已。但皆为外人对此人群之他称,而非当地人自称,正如民国《普安县志》卷15《苗蛮》“老巴子”条所言:“考老巴子之名,实由前明苗蛮窃据让里补南山,屡攻不克,调湖广兵来攻。山高而险,悬崖壁立,兵欲登山,山上之贼以石滚击,围攻年余,无术抵御,乃扎竹为笆,攀藤附葛,直捣贼巢,贼呼曰‘攩笆贼’。土人误呼曰‘老巴子’。”当地人认为这些称呼均有贬义,并不认可。“喇叭人”则是这个族群体已不太清楚此物(“朗笆”)之根源何在,而从妇女头饰之形态产生联想,音变讹传所致,特别是把“子”变成“人”,明显是为了摆脱被歧视的心态。
三、“喇叭苗”与普纳山之关系
普纳山,文献中有八纳山(明清时期《普安州志》)、普纳大山(民国《普安县志》卷五)、补南山(民国《普安县志》卷15之“老巴子”条)、查剌山(《明孝宗弘治实录》卷154)等写法,实指同一地点同一山名,即今之普纳山。目前,所见最早的记录是明嘉靖三十年(1551)之《普安州志》之《山川》部分。“八纳山:在州治东北七十里,高二十里,上有平顶,旁连小石百余顶,有瀍水……泉声、树色常与烟岚掩映,人迹罕到。土俗相传以为土酋益智藏其祖宗鬼筒于岩穴间,子孙十年一次登山祭之。每登必椎牛羊,持刀弩鼓噪而往焉。”之后,乾隆《普安州志》卷5《山水》还说:“前明上有夷寨,今无。”至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3《山水》则言:“今已建寺,游人络绎矣。”
以上记载并未言及此地有过战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地理条件奇险而有土著居住,但长期人迹罕至;二是为土酋之祖茔地,很神圣,从其葬俗看土酋当属于彝族先民。由此可知,普纳山附近一带当是土著彝族先民统治的核心区域。土酋益智,万历《黔记》卷58有载,元延祐四年(1317)归款,授怀远大将军,掌普安路总管府事,其孙那邦袭职。至明洪武十六年(1383)那邦妻适恭为普安军民府知府,卒,其子普旦嗣知府。二十二年(1389),普旦与越州阿资、本府马乃等反,陷普安府。二十三年(1390),讨平之,罢普安府,归属普安卫军民指挥使司。其后,据《明史》之《地理志七》:建文时复置贡宁安抚司,永乐元年(1403)改普安安抚司,十三年(1415)改设普安州,直隶贵州布政司,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州自卫北来同治。”治所约在今盘县东部、普安北部一带,与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之普安卫一北一南,万历十四年与普安卫同城而治。从元之普安路总管至明洪武时期之普安府知府,再至永乐时期之普安州同知,皆益智一族所袭替,其传袭世系为:益智—那邦(益智之孙)—适恭(那邦之妻,普安军民府知府)—普旦(普安军民府知府)—者昌(普旦之弟,贡宁安抚使,普安安抚使)—慈长 (普安安抚使)—隆木 (普安州同知)—隆寿—隆畅—隆礼—适擦—阿铎—龙文治—龙祖烈—龙天佑—龙元敬—龙炳汉。隆氏(后改为龙氏)为土同知袭职至康熙年间。龙天佑墓在今盘县保基苗族彝族乡垤腊村天桥组,正在今盘县东与普安北之交接地带,与普纳山很近。其墓前有碑,碑文记载:“其始祖元授怀远将军,以开其先,二世祖授宣慰司,以守其土。明授贡宁安抚司,管普安州同知,世皆弗替。越数百余代,暨公之身。”这充分说明隆氏乃益智之后,普安土酋一脉贯通。据《明实录》记载,明代普安土司大的反叛有两次,一次为洪武二十一、二十二年“普旦、阿资之乱”,前后仅月余,很快被傅友德平定;一次为弘治十一年至十五年“米鲁、福佑之乱”,前后近四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军事斗争方才平定。洪武二十一、二十二年“普旦、阿资之乱”,官军与之在普纳山有过战争。据光绪十年(1884)《李氏家谱》:“洪武二十四年,又剿毛口、六堕、□□、□店、洪寨、半坡、阿朗、木龙、鲁打、长牛,追过皮古、打坝,剿上罗寨,排勒头,四处安营立哨,攻打普纳山,代剿雨谷、海寨。二十五年,复征猴昌河(今水城猴场一带之补那河),二十六年迁立龙土官,得职。”据此可知,李氏参与的“迁立龙土官”,即指罢普安府,归属普安卫军民指挥使司,改设贡宁安抚司,以普旦弟者昌为安抚使。
“米鲁、福佑之乱”,《明孝宗实录》所载原委最详,分见卷154、176、180、181、182、189、198,现概述如下。约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因普安州同知隆畅老、阿保与畅妾等争世袭权,遂起叛隆畅,产生兵乱。后双方会盟息兵,归途中畅被其妾米鲁毒死,阿保、米鲁为乱,数攻寨堡,杀伤官军,屡抚不听。阿保于普安城外、安南城外、北盘江东岸和北盘江外筑四大营寨,四寨相距三百余里,派兵据守。号猴场寨(今水城猴场乡,位于北盘江北岸,与长流相对)为承天寨,出入僭用黄旗,自称“无敌大王”。贵州官军往捕,为其众所拒,遂益肆猖獗,劫掠军民,焚烧屯堡,声言欲攻普安、安南二城。后拨十卫官军及诸长官司土兵一万三千七百余人,追斩阿保于查剌山箐,而米鲁亡走其娘家云南沾益州,受其侄安民(时任沾益州土官)庇佑。战事告一段落,贵州官方提出善后方案,其中有一条为:“贼所遗田土除给至赏功外,悉分给邻近屯堡官军,从轻起科。”兵部复议中又提出一条:“俘获妇女,给配有功营长及附近所抚村寨无妻者。上从之。”
以上记载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地点上,战事中心为猴场和查剌山,即位于今“喇叭苗”聚居地附近。阿保被追斩于查剌山,即普纳山;二是时间上,距今500余年,与长流几大姓氏22—25代的世系比较吻合(按22岁一代计);三是处置方案中,分田土给屯堡官军及给配俘获妇女与民国《普安县志》卷15《苗蛮》“老巴子”条谓“湖广兵不思还乡,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的记载有某种关联;四是由贵州十卫官军及诸长官司土兵一万三千七百余人平定,没有言及有湖广兵参与平定。
但至弘治十四年(1501),在沾益州土官安民暗中支持下,米鲁与福佑再起兵反叛,因贵州镇守太监杨友、总兵曹恺、巡抚钱钺等指挥失当,贵州官军失利,普安州几陷落,遂请邻省之兵助剿。此年七月,兵部议定:“调播州土兵五千,酉阳及湖广两江口长官司土兵各三千,与贵州宣慰司土兵二万讨之。”说明在贵州官军无法平定战乱的形势下,始有湖广土兵及其他土兵入黔助剿。两江口长官司,明时属保靖宣慰司,辖地在今湖南龙山县西南,与酉阳临近。又据同治《龙山县志》记载:此时长官司长官为彭世英,“弘治十四年征调贵州普安,破大小盘江、陆卜、毛口等处,救出被掳杨太监。”①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210页。此载较《明实录》更为详实。弘治十四年十月,又有湖广参将赵晟领湖广戍兵并镇远等四卫官军三千往援,犄角讨贼。十一月,又有永顺宣慰司和保靖宣慰司各领土兵三千赴贵州,听贵州提督军务王轼节制。十二月,湖广参将赵晟领兵营于盘江东岸。十五年(1502)二、三月间,王轼调集官军、土兵分八道进攻,其中湖广参将赵晟为左哨,自大盘江入,与其他路军合围,米鲁、福佑被杀,余党悉平。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复擒米鲁余党阿方古等四人及其妾阿弄、子女阿宰等六人。因阿弄、阿宰等弱小,贵州巡抚“请免解京,就彼给配。”皇帝未同意。
由上可知,自弘治十四年七月至十六年四月,确有湖广兵参与平定“米鲁、福佑之乱”,共有三次,达12000人之多,有来自湖广的两江口长官司土兵3000人,湖广戍兵并镇远等四卫官军3000人、永顺宣慰司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各3000千人。其成份有土兵,也有官军,以土兵为多,原籍也不同,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今湖南湘西地区。官军由赵晟率领,自盘东入;土兵则由王轼亲自节制和调度,主要战于“大小盘江、陆卜、毛口等处”。而且,从弘治十六年四月贵州巡抚处置米鲁余党阿方古等人之妾阿弄、子女阿宰等时,因其弱小,“请免解京,就彼给配”的情况看,整个战争中都可能沿袭了第一次的处置办法,即分田土给屯堡官军及将俘获妇女配给有功者的做法,以鼓励士兵冲锋陷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广土兵才会有留下来的生存空间。留下来的本属于湖广土司的部分土兵遂构成今日“喇叭苗”之重要组成部分。②据《明孝宗实录》卷182记载,弘治十四年十二月,还有广西泗城州土舍岑接领土兵二万营于砦布河,后与其他路兵听王轼节制。(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详细介绍:泗城土官岑辉、广南土官侬泰率巨富王、陆、周三姓,各统兵五千余人,计分三路进兵,合于鲁土营。年余始擒米鲁,斩首献京师。朝廷以五姓有功,裂龙氏属地封为土司五姓。各令兵插草为标,自行开辟管业。而贞丰原系奶子所居,其男子悉逐出境外,五姓即以奶子之妇女配给所带兵丁。奶子性强悍,穿短裙,赤足奔走如男子,俗称曰“老户”,非土司不能制之。被称为“奶子”的人,即徕人,是仡佬族的一个支系。今广西隆林县的徕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贵州册亨迁徙而去的。(黄建福:《册亨徕人逃亡录》,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暨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委员会编:《仡佬族百年实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60-61页。)这里明确提及泗城五姓即以奶子之妇女配给所带兵丁之事,与湖广土司兵情况极为一致;而且占领的地盘乃原龙氏土司辖地,也与湖广土司兵进入龙氏核心区普纳山周围很一致。说明当时龙氏土司管辖内有仡佬族不同支系,这跟长流乡民间关于征“苗夷仡佬”的说法也很一致。他们征战的地点主要在盘东,未直接进入普纳山,攻打普纳山之战在此前由本地官军完成(这时本地官军中即有不少明初湖广垛集军后裔,容下文详述)。故弘治年间调入的湖广土兵在平定“米鲁、福佑之乱”中,可能与普纳山关系不大。
明确记载普纳山上有过战争的地方文献出现很晚,目前所见,最早为光绪《李氏家谱》:始祖李昶“洪武二十四年,又剿毛口、六堕、□□、□店、洪寨、半坡、阿朗、木龙、鲁打、长牛,追过皮古、打坝,剿上罗寨,排勒头,四处安营立哨,攻打普纳山,代剿雨谷、海寨。……康熙十八年陇土官匪叛龙场,攻打普纳山,□□为堖笆子……”此载虽为追述,但时间地点很详实,当有其根据。看来普纳山一带的战事不止一次,最早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晚的在康熙十八年(1679)。民国十七年(1928)《普安县志》卷5“普纳大山”条云:“明时苗民叛,筑营于山腰,据险负固,调湖广兵攻之,三年乃破。”同时还极力描述了其山之宽平与险峻,“山高十余里,纵横互五六十里,成冲霄凤口,为北区群山之望,四面嵯崖,仅一小径可通,步不能容骑,山顶宽平,可容万余人。”普纳山上确实是据险负固反叛之绝好地方。而反叛者被说成是“前明苗民”,当时泛指明代之土著,而非今日之苗族,具体年代也不明确,但有三年乃平之艰难,联系前文论述,当是普安州同知一族在弘治年间之反叛,即“米鲁、福佑之乱”。该书卷十五《苗蛮》“老巴子”条:“《识略》云:‘普安县兴让里有老巴子,亦苗类,由湖南移民居于此,其服饰与汉民同,语言稍异。’”此条还详加考证:“考老巴子之名,实由前明苗蛮窃据让里补南山,屡攻不克,调湖广兵来攻。山高而险,悬崖壁立,兵欲登山,山上之贼以石滚击,围攻年余,无术抵御,乃扎竹为笆,攀藤附葛,直捣贼巢,贼呼曰‘攩笆贼’。土人误呼曰‘老巴子’。”讲得如此详实,当源于民间口传,其基本史实正如前文所论,不可否认。
四、“喇叭苗”之源流与构成
“喇叭苗”这个群体盛传他们的祖先曾在洪武年间攻打过普纳山,战胜后定居其四周,亦兵亦农,“戍边屯田”,维护地方安宁。但是这与长流各姓氏之源流及其入长流后之世系及年代有诸多乖舛,这就需要对史志中相关记载作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不否认今“喇叭苗”中有一部分是洪武年间由湖广迁入,但也要承认其中有弘治年间从湖广被派遣来助战且“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的土兵。
民国十七年(1928)《普安县志》卷3有洪武四年至六年(1371-1373)间征普纳山之事,云:“洪武四年,命武德将军黄迁仕剿县属让里叛苗,平之。按:迁仕武冈人,元年由斜阳镇总兵调征贵州黑羊大箐叛苗,三年征曲靖,四年剿让里,其地苗匪据普纳山磴,负固三载,至六年平之。”又说“洪武二年命指挥胡源平夷寨,设军屯。按:是年,命源督同普安州土判官剿平夷落四十八,每寨设立一军屯。”若按前说,洪武四年有土著据普纳山反叛,且战事延续达三年之久,但如此重大战事,《明实录》、《明史》及明清地方志都未言及,当属误记。洪武四、五年间,四川刚平定,朱元璋即着手征伐云南的准备,让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宁、雅、播等处,修治城郭、关梁”,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6;卷185、187。始在黔中地区建立贵州卫以属四川行省,王朝军事力量遂进入贵州腹地。但此时贵州并未出现大的土著反叛势力,也未发生大的战争,贵州几大土司都向心朝廷,频繁朝觐。对于黔中地区,虽“群蛮叛服不常”,但很快平定,不过是“因兵威降金筑、普定诸山寨”而已。②参见《明史·傅友德传》;《明史·顾成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70。故洪武二、三年间(1369-1370),朝廷军队远未进入贵州,更没有进驻云南之曲靖一带。至于贵州西部一线设立军屯,当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左右,因云南平定之故。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同时置普安、尾洒(洪武二十三年改为安南卫)、普定卫。③《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6;卷185、187。故此时方有军屯之设。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命左军都督佥事冯诚往谕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置安南卫。初,官军征云南,指挥使张麟统宝庆土军立栅江西坡屯守。至是,以其地炎瘴,乃徙于尾洒,筑城置卫守之。”④《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6;卷185、187。
以上记载表明,洪武年间大致有两批湖广士兵入黔普安、安南一带屯守,第一批是最初于洪武十五年由张麟统帅的宝庆土军,人数不清楚;第二批则是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来自靖州、五开、辰州、沅州等卫,皆从新军中选出之精锐,总人数在四万五千人(不全在普安,而是遍及普定、安南、普安一线)。⑤《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6;卷185、187。龙氏谱书《派衍湖广宝庆》以韵文体形式叙述明洪武时期龙氏入黔的情景,史实较详实,可作参照:“洪武调北征荒,三丁抽一剿蛮方。大帅兵权执掌……轰轰烈烈上阳关……分防五营四哨,驻扎镇远溪阳……扫平开州立县,先立南龙府官,次取安南立都堂……”屯军的到来,不免会对土著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此时方有土著直接与屯军对抗。如《明太祖实录》卷203“洪武二十三年八月壬午”条记载:“百夫长密即叛,杀屯田官军刘海,尾洒驿丞余成及试百户杨世杰,劫夺驿马,焚馆舍。”民国十七年(1928)《普安县志》卷3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指挥胡源分拨安南卫
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 6;卷185、187。④《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61;卷141;卷206;卷185、187。军屯界址,引《胡氏军民屯册》介绍了东南西北四至和戍守军官之姓名,其中“北至长牛(即今之长流)、阿志(六枝阿志河一带)、墜足(今六枝堕却)、龙场(水城龙场)、毛口(六枝毛口)以袁天定戍守。”安南卫之北界正是今以晴隆县之长流、中营为中心的“喇叭苗”分布的核心地区,包括晴隆、六枝、普安、水城四地之交邻地带。光绪《李氏家谱》所记甚详:“李昶祖籍湖广衡州府类阳县(疑为耒阳县)车马村易都十里穿心十字街。蒙封黄迁仕,郭晚云焦为两路先锋,从京远以上,攻打黑阳大箐,杀尽洪猫革老,上安平安顺,剿上镇永宁,复征过黄河凉水营,立哨扎屯,观看安南好点地形,才将半城关改关立位,请梓开工,修造安南城,修成三千七百朵口,安定三千七百朵口军。”这里的朵口军,即“垛口军”。明代实行卫所屯军制度,兵员除早期参加征战的起义军和归附者外,主要是战事平定后在民户中抽取,称为“垛集”。其办法是:在每三户中垛一人丁多的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出一名兵丁,称为“正军”,正军死,由贴户补充,故称为“三户垛”。①参见《万历大明会典》154,《兵部三七·军政一·勾补》;《明太宗实录》卷15,“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壬申”条;《贵州通史》第2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86页。就安南卫而言,据孟凡松研究,其总旗及以下“充役”者主体来源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从宝庆府垛集而来的民丁,他们绝大多数是底层军人,其中以武冈州最多,此外还有邵阳县、新化县等地。至隆庆三年(1569),中上层武职官员以南直隶地区最多,占40%,湖广地区占33%,以此推定洪武时期湖广籍安南卫武职军官比例要低得多。②孟凡松:《明代安南卫初步研究》,载李建军主编:《屯堡文化研究》(20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龙氏家谱《派衍湖广宝庆》所谓“洪武调北征荒,三丁抽一剿蛮方。”以及民间流传“三丁抽一、五丁抽二”都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以上龙氏、胡氏、李氏当是前述洪武二十年(1387)至二十三年(1390)来自湖广分屯普安、安南一带的精锐之师中的成员,也就是云南战事平定后新垛集的士兵。故今水城、六枝、盘县、晴隆交邻地带10多万“喇叭苗”中定有不少源于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三年由湖广宝庆府及靖州、五开、辰州、沅州等卫垛集的士兵,但也有洪武十五年(1382)左右来自宝庆一带的土军。
据我们对长流“喇叭苗”的调查,家族传承世系最长的邓氏只有25代,刘、李、龙氏不超过22代,若按22岁一代计算,距今约550—484年,约在弘治年间前后,与明初差距100多年。故“喇叭苗”皆明初入黔征战之说,并不可信,民国《普安县志》甚至径直抄录地方谱牒之书,未加辩驳,误以为洪武初年即入黔。当然,这也正反映了民间一些家族对其族源和事迹之记忆与认同有一定的史影,但与史实出入颇大,不可为据。关键就是时代问题,真正的时间当在洪武十五年至二十年间与弘治十一年至十五年间(1498-1502),但民间往往说成是洪武时期,甚至是洪武初年入黔,且往往与普纳山战争联系起来,何故?我们注意到,早在明初即有湖广湘中南一带军事移民涉足长流之地,即从靖州、五开、辰州、沅州卫之新垛集而来的士兵,已有所进入,在明洪武年间和弘治十一、二年间确实也攻打过普纳山,弘治十四年(1501)来自湖广湘西一带的土兵,不过是“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不得不与早先到来的这些汉移民(屯军)保持特定的关系。这些后至的处于边缘化的湖广土兵及其后裔为了提高在当地的地位和获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间,主动与明初来的占主导地位的湖广军事移民靠拢,被迫改写自己的历史,与之合流,并不断流传下来。故都坚持各自的祖先为洪武时期入黔,祖籍集中于湖广湘中南宝庆府、衡州府一带。另外,嘉靖《贵州通志》卷3据旧志所载,谓兴隆卫和威清卫卫戍军士皆湖湘人,“宗族交代从戎,故役无定籍而居无恒产”,又“诈而好讼”。这种自湖湘来黔卫戍之军士,人数实在不少,可能是明中期贵州卫所军士大量逃逸之后,从湖湘之地重新招募垛集而来,属于雇佣军性质,往往是以家族为单位,“交代从戎”,无定籍,无恒产,故诈而好讼。这些新到的湖湘之人自然就是卫所中的底层了,他们很可能会游离到土著社会的边缘,也当是构成“喇叭苗”的一部分。我们在长流调查时,当地人说他们与安顺地区屯堡人服饰和习俗有很多相似,且老辈人有一些往来。这似乎说明黔中的“湖湘人”与“喇叭苗”之间在历史上有某种联系。具体细节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总之,分布于晴隆、六枝、盘县、普安一带的“喇叭苗”之组成很复杂,有明初洪武前后进入的湖广土军和官军,更有弘治年间平定“米鲁之乱”后留下来的湖广土兵或官军,所谓“湖广兵不思还乡,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还有明中期自湖湘雇佣来黔的卫所、卫戍军士中的游离者;并非仅出于一地,籍贯有湘西、湘西南、湘中南的不同地域之分。“喇叭苗”群体及其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是“异源合流”。刘、李、龙、邓、胡等各大姓氏迁入长流的原因各异,时代有别,祖籍也不完全一致,强烈地受制于王朝历史的运转轨迹。他们带着特别的文化血统,肩负着王朝使命,加入军事移民开发浪潮中,不断开拓、控制贵州土著社会,是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植入的先锋队,也是在土著社会之包围中、恶劣环境的挑战下,自求生计的落魄者和拓荒者。因此,后至的任何一个家族能够生存和发展,既要对先前“调北征南”而来的属于“自己人”中各家族的依赖,又要吸收久居于此的土著社会的生计技能和智慧,缓和与土著(主要为仡佬、彝族、布依族先民)的矛盾,并有效地防御土著社会的侵扰;既要适应新的、恶劣的地域地理局限,又要努力顺应王朝国家的政治赓替。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是内地汉人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要在“先湖广人”与“后湖广人”之间、汉移民与土著之间、“汉化”与“夷化”之间、地域化与国家化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互动关系,其历史进程的艰难性可想而知。这个社会比纯粹的汉人社会要复杂,显示出较多的变异性;又因其处于多民族交汇地带的北盘江流域,地势险峻,山高谷深坡陡,历史进程比安顺一带屯堡社会也要复杂,吸收的土著文化较多,经济生活与居住形态的地缘色彩更为突出。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的龙氏反叛“仲家”、李氏反叛“仡佬”、“挡笆”与“壁笆”的传说、当地妇女“放药—下药”、以神树为载体的山神信仰、全能式的家神信仰体系、浓重的立碑祭祖过程仪式(催龙)、“文教”与“武教”之异同、宗教神职人员活动的寺庙场所极少而半神职业人员(“先生”)从事世俗化仪式性活动极强、对山歌的形式、认可“喇叭人”而不认可“喇叭苗”、聚族而居并聚族而葬等现象,都可以从上述视角加以理解。
五、文献所载“喇叭苗”族属问题
民国十七年(1928)《普安县志》卷15《苗蛮》“老巴子”条记载:明代湖广兵平定普纳山战役后,“湖广兵不思还乡,赘苗妇以为室,遂家焉。数百年来男子服饰与汉人同,妇女仍守祖风,服饰衣物饮食犹然苗□,实则汉种也。”也就是说男系为湖广兵,女系为土著,“喇叭苗”为汉苗通婚之产物。至于说“妇女仍守祖风,服饰、衣物、饮食犹然苗□”,则未必如此。我们在长流发现了与现在当地妇女服饰迥异、距今却有约200年的墓碑上的人物服饰。该墓位于长流乡溪流村大穴场组,乃刘世祖及妻合葬墓,墓碑为三碑两柱的组合形式,嘉庆二十年(1819)立。两侧夹柱上各有一幅人物雕像,刘世祖碑一侧的为男性,其妻杨氏碑一侧的为女性,人物的服饰为当时服饰之真实反映,头发挽成圆髻,无耳环,窄长衣袖,前胸有一幅长腰肚兜,由此可以看出当地妇女未必是仍守祖风,也不能认定此墓碑上的人物服饰就是明代土著妇女之服饰。
关于“喇叭苗”祖先是何族属,清代文献记载很不一致。或归入汉,或归入苗,或归入仡佬,或称为“民家子”,未有定准。前引乾隆年间爱必达所著《黔南识略》卷28《普安县》条说得很明确,谓普安县“兴让里有老巴子,亦苗类,由湖南移居于此,其服饰与汉民同,语音稍异。”但在同书卷29《普安直隶厅》条则云:“又僰人俗呼为民家子,自滇迁来,其族多赵、何等姓;又仡佬俗呼为老巴子,自楚流入,其族多邓、杨等姓。二种服色土俗与汉同。”这似乎说明老巴子为仡佬之属,但又与汉人文化更接近。同样类似的矛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贵州布政使罗绕典所撰《黔南职方纪略》中有所反映。该书卷3《大定府》之水城厅条提及夷人有九种,不包括“老巴子”,特别强调“别有里民子即县民,老巴子即民家子,二种本非苗类,其朴野几与苗人相等。”这里明言老巴子和里民子皆非苗人,但朴野几与苗人同。老巴子即民家子,这又跟前述“僰人俗呼为民家子”的记载有交集。该书卷9《苗蛮》专列“喇巴苗”,为水城厅八种苗中之一种,“水城有之,花苗别种也,服食与花苗同。”这里明言“喇巴苗”即花苗别种。还应该注意到,前述文献提到的“喇巴苗”在水城有“花苗别种”与“老巴子即民家子”之别,在普安则有“仡佬俗呼为‘老巴子’”,这些不同地域内不同称呼则表明“老巴子”与仡佬族和民家子有融合关系,并非只是与苗人有融合,且融合的形式和程度不同。前述晴隆县长流乡一带民间传说征“红苗仡佬”后,与仡佬族定居在一起,现在“喇叭苗”聚居区还有仡佬冲、仡佬坝等地名,都印证了老巴子与仡佬族有密切关系。
从历史上看,长流及其附近一带长期属于彝族土司龙氏管辖,实苗、汉杂处之地。据罗绕典所撰《黔南职方纪略》卷2《兴义府》安南县条记述:“外有长牛六甲地方,昔属普安州土司龙天佑管辖。自设县以来(笔者按:康熙二十六年设县),地当新驿之冲,借甲内之阿都田站以为办差之所。乾隆二十七年,因借地设驿未便,酌割长牛、斗郎、鸡场等二十三寨,共计六甲地方,拨县管辖,其地实苗汉杂处。”新驿,即雍正时期鄂尔泰改设贵州至云南官道,由镇宁黄果树至普安蒿子卡,长流、中营、花贡正是新驿所经之地。在这样的多民族杂居地区,湖湘之人自然会与不同的民族有融合,但融合程度不一,加之“喇叭苗”之源也有官军与土兵之别,土兵中又有洪武十五年(1382)左右的湖广宝庆土军和弘治年间湘西地区的彭氏土司土兵,因此“喇叭苗”或归入汉,或归入苗,或归入仡佬,或称为“民家子”,都是十分正常的。正是这些看似混乱矛盾的称谓或归属,才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入黔的湖广军人来源的复杂性及其与不同土著融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喇叭苗”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这个族群体中之部分上层精英分子,顺应国家落实民族政策之需要,而主动归属于苗族系统,成为苗族的一个分支,故有“喇叭苗”之说。不过现在当地民众比较乐意接受的是“喇叭人”这个称呼,而不是“喇叭苗”,这也是历史和现实、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统一。笔者想强调的是,民族之间的融合向来复杂多样,每一个群体族属认同都在各自历史文化传统、祖源记忆和其所处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权衡与选择,都有合理性,尊重历史并复原真实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并服务于现实,而不是否定当下。
(责任编辑:吴启琳)
An investigation on“L aba M iao”(喇叭苗)Fam ily History and Exp lore Some Related Questions
——Taking Changliu Town in Q inglong County as A Case
Ye Chengyong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stitute of Guizhou National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550025)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s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of"Naba Miao"family history in Guizhou province Qinglong county Changliu Xiang as the foundation,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Naba Miao"name,the source,constitution and war activities in the Ming Dynasty,and the comp lex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sion with indigenous.And the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Naba Miao" distributed in Qinglong,Liuzhi,Panxian,Pu'an is very complicated,includes the Huguang local forces and government troops came in before and after the early Hongwu era in the Ming dynasty,and left in pacification"Milu chaos"in Hongzhiera,aswell as the free sergeant persons hired from Hunan in themid-Ming;with differentnative regions ofwest Hunan,Southwest Hunan,and South Hunan."Naba Miao"group and their culture was never amonolithic whole,which is a"heterologous confluence".In this process,it can not be simply transplanted themainland Chinese society,but the reestablishment of equilibrium between the"earlier Huguang peop le"and the"later Huguang people",between Han m igrants and native,"Chinese localization"and"Yi localization",betwee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local multiraci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Hunan people have fused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bu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s different.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Naba Miao"was placed or in the Han,or in the Miao,or in Gelao,or in"Min Jia Zi"in local history,these appellation or ascription seemingly chaotic contradictory,but truely ref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urces of Huguangmilitary into Guizhou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history 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fusion with different indigenous.
"Naba Miao";Family history;Origin;Ethnic integration
G03
A
1008-7354(2015)01-0026-11
叶成勇(1977-),男,贵州思南人,贵州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地区民族史、民族考古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