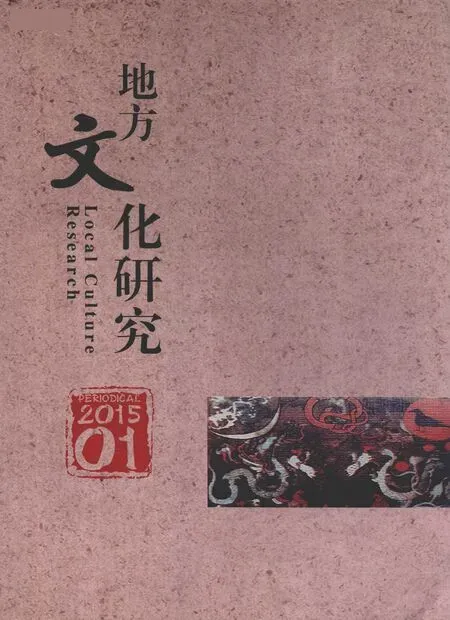张载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思想
2015-03-30林乐昌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 西安710062)
张载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思想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 西安710062)
本文认为,吕大临《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所谓受《中庸》而读之、访诸释老、反求之六经等三次转折都属于张载的早期学术活动,并按早、中、晚三个阶段逐一考察了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张载的关学思想体系成熟于晚年,其理论纲领是以“天”为核心概念,以“天”、“道”、“性”、“心”为概念序列的。
张载;北宋理学;关学学派;关学思想;《张子全书》;《张载集》
张载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以下分别绍述张载的学术历程与关学学派的形成,张载的关学思想体系。
一、学术历程与关学学派
学者叙述张载的学术历程,通常仅依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的寥寥数语,将其划分为受《中庸》而读之、访诸释老、反求之六经等三次转折。其实这三次转折都属于张载早期学术活动的范围,无法全面展现张载学术的阶段性演变脉络。笔者认为,可以将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关学学派的创立和发展,大约在张载学术演进的中期和晚期。
第一,张载治学的前期,大约自其二十一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间,这是他奠定学术基础,进行思想探索的时期。这一时期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为起点,张载当时约二十一岁。吕大临《行状》记载,张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这里“累年尽究其说”的“累年”是多少年?朱熹在述及张载治学经历时说:“夫子蚤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馀年。”①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六《鞠歌第五十一》,《朱子全书》第十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据此推算,张载出入佛老“十有馀年”至“反求之六经”,约在张载二十一岁至三十多岁。张载总结自己读书经历说:“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经学理窟·义理》)这表明,张载三十多岁从佛老“反而求之六经”,又用六七年之功对六经做过一番系统研究,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年龄约在三十七八岁。张载与程颢(1032-11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兄弟京师论学,就发生在此时。由于这一事件关乎张载之学的来源和形成问题,故需略加考察。据《宋史·道学传》张载本传记载:
(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焕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这是他们表叔侄之间第一次晤面。据《行状》记载,这次会晤的时间在宋仁宗嘉祐初(1056),当时张载三十七岁,二程兄弟二十四五岁。后来二程的高足杨时、游酢等人据此认为,张载之学源于二程。①杨时:《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杨时集》卷二十六,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游酢的相同看法见其《书行状后》,《河南程氏遗书·附录》,《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4页。南宋朱熹虽然肯定“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仍坚持张载学说“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②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卷六,《朱子全书》第12册,第1002页,朱熹案语。然而程颐作为当事人则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③《时氏本拾遗》,《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二程集》,第414-415页。显然,程颐的看法是符合史实的。京师论学时,无论张载还是二程都未形成独立的学说,思想远未成熟,各自也没有形成学派。张载与二程对《周易》及“道学之要”的讨论,只是几位有志于复兴儒学的青年学者之间的切磋;在双方学说都尚未形成的情况下,遽然判定张载之学发源于二程,不是门户之见,就是夸诞之词。
程颐晚年曾回顾自己一生的为学经历,他说:“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④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邹德久本)》,《二程集》,第314页。程颐的自述,可以与张载思想演进的时间坐标互为参照。嘉祐初与张载京师论学时,程颐才二十五岁,其为学正处于“读诵”阶段。尽管他在读诵过程中时有独到见解产生,但从总体上看,其思想毕竟尚未成熟。
第二,张载之学演进的中期,亦即其思想形成期,大约从其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十年间。作为始学之书,《中庸》对张载具有特殊意义。张载自述研读《中庸》的经验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经学理窟·义理》)“已长得一格”,是说张载在二十年当中对《中庸》反复研读,对其精义的解读终于达到自成“一格”的境地。从二十一岁始读《中庸》算起,经过二十年,此时张载四十岁出头,似可视作其思想进入中期的开始。据此可以认为,四十岁以前的大约二十年,是张载为学的前期阶段,其思想在探索中趋于形成;从四十岁开始,张载思想在形成中趋于成熟。
与张载之学的演进有关,这里还涉及他所开创的关学学派及其发展过程问题。据《关学编》记载:“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及闻学,遂执弟子礼。”⑤冯从吾:《关学编》卷一《和叔吕先生》,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又据《宋元学案》记载:“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⑥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教授吕和叔先生大钧》,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7页。吕大钧(1031-1082,字和叔)与张载同于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他是最早拜张载为师的关中学者。吕大钧对张载“执弟子礼”,可能在两人同年登进士第之后,大钧对张载的人品和学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时可能在张载约四十岁前后,或约在张载之学形成的早期与中期之间。虽然此时张载的思想尚未进入成熟期,但其谦虚善让的人格魅力和勇于造道的学术精神对关中学子是有强烈感召力的。吕氏乃关中名门望族,在当地有巨大的影响。在吕大钧的带动下,不久后便有更多的学者投于张载门下,包括吕氏兄弟吕大忠、吕大临,以及苏昞、范育等,从而推动了关学学派的形成。
第三,张载之学演进的后期,亦即其思想成熟期,大约从其五十岁前后至去世的七八年间。张载认为,成学自有其规律,“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经学理窟·学大原上》)他晚年回顾说:“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比岁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经学理窟·自道》)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作为张载向学之始,“某学来三十年”,刚好步入五十岁。“入至其中”,可理解为张载之学已登堂入室,思想进入了成熟期。这里张载所谓“亿则屡中”,出自《论语·先进篇》,原意是形容料事准确,而这里张载引申用来说他对义理的思考已经达到运思精深的境地。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向朝廷举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吕大临《行状》)此时张载刚好五十岁。“四方之学者皆宗之”这一局面的形成,说明张载关学学派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与此类似,程颐也描述过张载居乡讲学,学者远道而至的盛况:“(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①程颐:《回礼部取问状》,《河南程氏文集》卷七,《二程集》,第564-565页。
二、关学思想体系
张载关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在其五十岁以后的思想成熟期。张载自述道:“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子语录下》)所谓“成一次第”,就是使自己所创建的学说形成体系或系统。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所指出的,张载是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的大师。②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49页。张载在其《正蒙》首篇《太和》中指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四句话,是张载晚年精心构撰的关学思想纲领,可称为“四句纲领”。这“四句纲领”每一句都以“名”字结句。古人所谓“名”,语意相当于现在之“概念”。“四句纲领”分别界定了“天”、“道”、“性”、“心”四个基本概念,是张载关学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四大概念序列。这“四句纲领”,具有表述严整,排列有序,界定清晰的特点,是考察张载概念序列和关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依据。张载关学体系的天道论和心性论两大层面,完全与其“天”、“道”、“性”、“心”四大概念序列相吻合。构成张载关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元素,除上述基本概念系列外,还有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原理。就其关学思想的基本命题看,主要包括“太虚即气”命题,“性其总,合两”命题,“大其心体天下之物”命题,等等;就其理学思想的基本原理看,则主要包括“太虚”亦即“天”和“气化”的天道论原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原理,“德性之知”、“闻见之知”的知识论原理,“变化气质”和“知礼成性”的工夫论原理,“以礼为教”的教育哲学原理,等等。
张载关学的体系结构,可划分为形上和形下两大部分。关学“四句纲领”前两句说的是“太虚”、“气化”宇宙论哲学,这正是以“天”、“道”范畴为核心的,故也可以称为“天道论”。张载认为,“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正蒙·天道》)可见,张载是把天道论归结为形上学的。关学“四句纲领”后两句所说,属于心性论,就其性质看,也可以归结为形上学。上述关学“四句纲领”,其实是张载学说中形上学部分的纲领,其内容包括天道论和心性论两个层次;而其形下部分,则主要指张载面向现世社会、范导个体行为、社群关系和国家政治秩序的的礼学,具体内容为张载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③林乐昌《张载礼学论纲》,《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第48-51页。礼学,除其根源问题属于形上学外,其基本内容则属于张载关学思想体系的形下部分。
张载的关学思想体系结构,还可以从天与人及其关系的角度归结为“天人之学”。张载门人吕大临和张舜民曾分别以“一天人”、“学际天人”概括乃师的学问特征。在张载的“天人之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基本的面向。在“天”这一方面,以“天”、“道”范畴为基础,构成张载关学的天道论,同时还包括“天性”(“天地之性”)、“天心”等观念。在“人”这一方面,则以“性”、“心”范畴为基础,构成张载关学的人道论。此外,工夫论也属于人道论的内容。张载指出:“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正蒙·诚明》)这是张载为天人之学提出的基本要求,即在知与行两个方面都强调天与人的统一。与天人之学密切相关,张载的著名短论《西铭》,则是其伦理学的纲领。
(一)天、道、性、心的关学思想体系
张载批评“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乃“知人而不知天”④《宋史·张载传》,《张载集·附录》,第386页。,欲回归周孔思孟的“畏天”、“知天”、“事天”传统,把“天”、“天道”作为重建道统和经典诠释的根本方向。在此基础上,张载确立了以“天”为核心概念,以“天”、“道”、“性”、“心”为概念序列的关学纲领。就张载关学而言,无论是“天”,还是“天”、“道”、“性”、“心”序列,无不显示出独特的关学色彩。
下面我们以《正蒙·太和篇》的“四句纲领”作为主线,讨论张载关学思想体系中的形上学内容,即他的宇宙论哲学和心性论哲学。
1.“由太虚,有天之名”。张载“四句纲领”之首句说:“由太虚,有天之名。”儒家经典中本没有“太虚”概念,“太虚”概念出于《庄子·知北游》:“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汉晋以降,“太虚”概念被广泛使用,如《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谓“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这里,“太虚”已被理解为“肇基化元,万物资始”的世界本原概念。晋韩康伯注《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歘尔而自造矣。”①韩康伯:《周易注·附》,收入《王弼集校释》下册,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版,第543页。“太虚”概念遂被引入儒家经典《周易》的解释中。张载的太虚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下提出的。张载接受了韩康伯引入的“太虚”概念,并且也把它当作世界本原来理解和运用。“太虚”既然被作为世界本原的概念来理解和运用,那么它与儒家原有的“天”的概念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传统儒学以超越之“天”作为世界本原的概念,但后来的儒者往往把“天”视作自然之天或经验之天。对此,张载批评说:“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体,姑指日月星辰处,视以为天。”(《横渠易说·系辞上》)又说:“‘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苍苍之形也。”(《正蒙·参两》)强调天不是有形的苍苍之天,而是作为自然界的形上根据之天。他告诫人们:“气之苍苍,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当以心求天之虚。”(《张子语录中》)张载有感于当时已少有人能“以心求”超越的本体之天了,更多的情形是借耳目感官所了解的由气构成的“苍苍”之天亦即经验之天。有鉴于此,张载认为道家的“太虚”概念具有无限性、绝对性、超越性等优点,故借助道家的“太虚”概念对儒家愈益被经验化的天加以改造,以提升儒家之天的超越性。张载所谓“天”,是指超越之“天”,不是指自然之天或经验之天。
经历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洗礼,北宋时期的儒家哲学形态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本体理论。这意味着此一时期的儒者要建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必须对世界终极根源和世界统一性作出哲学的概括,从而提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亦即所谓世界本体范畴,而这个范畴必然是形上的和无限的。因此,作为北宋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或本体范畴,便不应以一种形下的、有限的事物作为建构的根据。张载哲学的本体概念“太虚”或“天”是对经验性苍苍之天的超越,强调的是其本身的纯粹性、无规定性和最高实在性,它既是宇宙自然的本原,同时也是社会价值的本原。
首先,“太虚”或“天”是宇宙自然的本原。张载提出:“虚者天地之祖”,“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张子语录中》)张载认为,天是创生万物的主导力量,他说:“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还把作为创生万物的主导力量称作“神”,他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神。”“神则主乎动,故天下之动,皆神之为也。”(同上)又说:“神者,太虚妙神之目。”(《正蒙·太和》)可见,“神”与“太虚”指称的是同一个本体,只是在动、静不同侧面上才有所区别,“神”偏就动态而言。
其次,“太虚”或“天”是社会价值的本原。张载所谓“天”或“太虚”作为整体观念,其自然、物质涵义与伦理、价值涵义之间并没有被割裂,“天”或“太虚”既是自然世界的终极根源,同时也是价值世界的终极根源。张载指出:“虚者,仁之原”。“虚则生仁,仁在理以成之。”(《张子语录中》)他还指出:“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同上)在张载的道德价值系统中,其核心部分是“天”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之“仁”、“天秩”之“礼”,和以“乾称父、坤称母”为宇宙根源的“孝”。为人的道德价值确定宇宙根源,是张载价值论和伦理原则的突出特点。
总之,张载所谓“太虚”或“天”,是涵盖了精神性实在和物质性实体的最高本体,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性;“太虚”或“天”既是自然本体(万物化生的本原),又是价值本体(道德性命的本原),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物的终极根源。张载以道释儒,不是学术立场倒向道家,而是借道家的“太虚”概念提升儒家之“天”的超越性。因此,应当把张载关学准确地称之为“天道心性之学”,或更简括地称之为“天学”。
2.“由气化,有道之名”。在张载“四句纲领”中,首句“由太虚,有天之名”与第二句“由气化,有道之名”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由宇宙本体向宇宙生成过渡的关系。张载所谓“太虚即气”,是把宇宙本体与宇宙生成连接起来的基本命题。如果说“由太虚,有天之名”强调的是宇宙本体,作为宇宙本体意义的“太虚”或“天”具有超越一切阴与阳、动与静、聚与散、虚与实、一与多、有形与无形等相对层面的特性;而“由气化,有道之名”强调的则是宇宙生成,经由阴阳之气的互动,构成宇宙万物生成的动力、过程及其秩序。作为宇宙本体论的太虚或天,是下贯、参与到现实的气化生成过程之中的。可以认为,“气化”之道,其实也就是“太虚即气”之道。可见,在张载宇宙论哲学中,“太虚”与气之间的关系是其基本关系。但分析地看,“太虚”与气之间的关系既有分又有合,“太虚”与气分则有先后,合则无先后。正是“太虚”与气之间的这种分合或先后关系,决定了张载哲学中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两个层次的划分。
“太虚”与气之间的相分关系,强调的是“太虚”本体的超越性和逻辑的先在性,这便构成宇宙本体论层次。所谓宇宙本体论,是面对宇宙万物和道德价值“发源立本”(《张子语录下》),探究其终极本原和超越源头的理论建构。张载的宇宙本体论突出的是“太虚”本体与气及经验物的区分,突出的是“太虚”本体超越时空、超越气及一切经验层面、相对层面的的“至一”、“至静无感”的独立性。宇宙本体论层次的基本概念是“太虚”亦即“天”。
“太虚”与气之间的相合关系,强调的是“太虚”与气的关连性和无分先后的共在性,这便构成宇宙生成论层次。所谓宇宙生成论,是关于天地万物的生命成长条件、构成、根源、动力、变化过程及其秩序的学说,其内容也包括人性论在内。为了批判佛教以世界为“幻化”的观点,基于充分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这一目的,在宇宙生成论的这一层次张载强调虚与气之间的关连性和不可分割性,主张“太虚即气”,“太虚不能无气”(《正蒙·太和》)。这里,张载突出的不是“太虚”本体的独立性,而是其“合”的作用的发挥,亦即在宇宙创生过程中“太虚”本体经由感应机制与阴阳之气整合为统一的宇宙创生力量。宇宙生成论层次的基本概念是“道”和“性”。
张载建构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有其经典依据,这就是《易传·系辞》所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正与宇宙论哲学的两层结构相对应:“寂然不动”,是宇宙的本体状态,在张载哲学中指“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正蒙·太和》)的“太虚”本体;“感而遂通”,是宇宙生成论的机制,强调的是“太虚”本体经由感应作用下贯现实世界,并作为主导力量参与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的情形。张载指出:“《易》言‘感而遂通’者,盖语神也。”(《横渠易说·系辞上》)这里的“神”,是指“虚”与气相感相合所形成的创生能量和神妙机制。
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命题,是为了批判佛教以世界为“幻化”的观点,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构成、万物的生成根源及运行动力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如果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强调的是“太虚”对气的超越,属于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命题;那么,“太虚即气”强调的则是“太虚”与气的相感相合,属于张载的宇宙生成论命题。就“太虚即气”命题的理论性质和层次定位看,不应当视为涵括宇宙论哲学两个层次共有的命题,而应当视为特指宇宙生成论单一层次的命题。
3.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四句纲领”之第三句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这里应注意张载所谓“合”的意义,“合异”与“非有异则无合”(《正蒙·乾称》),是张载论“合”的原则。这意味着相合的二者必然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否则,“合虚与气”,便不过是同语反复,毫无意义。上述“太虚即气”命题,与这里“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意涵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太虚与气二者在宇宙生成过程中必然要连接在一起。张载宇宙生成论的要义,是揭示万物生成的动力和根源,而“太虚即气”便正是能够体现宇宙万物生成的动力性和根源性的重要命题。尽管道与性的基本结构相同,都是“合虚与气”而构成的,但二者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则各有侧重:道,主要作为万物运行的动力,展现万物的变化过程及其秩序;而性,则主要作为万物生成的根源,赋予万物不同的秉性或本质。张载以“合虚与气”来界定“性”,批评了佛老单纯以虚言性,以及“陋儒”(指汉儒)单纯以气言性的两偏之失。①参见林乐昌:《张载对儒家人性论的重构》,刊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张载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成的共同根源,提出:“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他还说:“性其总,合两也。”(《正蒙·诚明》)此诚如明儒徐必达所解:“性者万物之一源,故曰其总。”②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正蒙释》卷二《发明》,清康熙无锡刻本。由于张载是从世界总体的角度揭示世界万物及人的共同生成根源的,因而此性便具有了“其总”的特征。性不仅具有生成万物的共同根源的意义,而且还有其内在结构层次,此仍如徐必达所解:“然有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者,故曰合两。”③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正蒙释》卷二《发明》,清康熙无锡刻本。内在结构分为两个层面的“合两”之性,与“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中的“虚”与“气”,可以视为一种对应的关系。
在张载看来,包括物性与人性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既有天地之性,又有气质之性,故“合两”之性是为“人、物所同得”的。④江永注:《近思录集注》第一之卷一,“性者万物之一源”句下朱熹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22页。在张载的语汇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有时被简称为天性与气性,或径直称为性与气。
值得注意的是,为“人、物所同得”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并非平列的,而是有本有末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或性与气这两方面究竟何本何末,张载的态度是很明朗的,他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正蒙·诚明》)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正蒙·乾称》)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
由于受佛道及玄学精于形而上思辨的的影响,包括张载在内的宋代理学家开始运用体用、本末、有无等成对范畴来思考哲学问题。张载对于性与气究竟何本何末的定位,所采用的正是本末、体用思维方式。在以张载为代表的宋儒看来,体与用、本与末相比较,体、本占据着优先和主导的地位,是形而上者;而用、末则处于次要和被动的地位,是形而下者。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衡定性与气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性为本,气为末,而不是相反。
在张载看来,人性的本原不是气质之性,而是天地之性。作为天地之性根源的太虚是“至善”的。张载在人性论上特别强调“发源立本”的价值本原意义,他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张子语录中》)“性之本原,莫非至善。”⑤林乐昌:《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刊于《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第124页,第51条。“太虚”乃至善,故根源于“太虚”的“天地之性”在价值论上也是指向至善的。于是,“天地之性”便不仅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而且它作为“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经学理窟·义理》),因而还具有永恒性。
另一方面,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张载说:“有天生性美,则或能孝友廉节者,不美者纵恶而已,性元不曾识磨砺。”(《经学理窟·礼乐》)“天生性美”,指后天之性善;“不美”,指后天之性恶,都属气质之性。由于“天资美不足为功”(《经学理窟·气质》),故气质之善虽与超越之善相通,但它仍然不能作为道德的超越根据;又由于气质之善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殊异,故它也不能作为道德的普遍根据。由以上两点所决定,应当把超越的普遍的永恒的本体之善或天地之性作为人性的本原和根据,而后天的、殊异的、有限的气质之善,则不能作为道德何以可能的超越和普遍根据。这是张载人性论和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前提。
张载以天性为气质之本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张载无视气质之性存在的合理性。他说:“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正蒙·乾称》)按照张载的理解,各人生来所禀受的气不同,自幼养成的习性也不同。张载说:“大凡宽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习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张子语录下》)“宽褊”,指人气量的宽广或狭小。他还说:“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就是说,气(气质)是每个人“形而后”才有的,由于各人所禀受的气不同,由此造成了人在性格、才情等方面的差异。气质不仅影响人的性格、才情,而且气质之恶者还会对人性造成危害,此如张载所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张子语录下》)
张载提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概念,还不仅仅是为了建构起完备的人性理论,而是强调人应通过“变化气质”的实践工夫,以返求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张载曾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这是说人的气质是可以变化的,人通过道德修养的学问之功,便可以体现出完美的德性。由此出发,张载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这里所谓“学”,主要指“变化气质”等道德实践工夫。张载指出:“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经学理窟·义理》)他还指出:“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经学理窟·气质》)突出为学工夫在成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强学以胜其气习”(《张子语录下》),克服自然和生理因素对人的限制,以达致“德胜其气”(《正蒙·诚明》)的道德目标,实现天地之性在个体生命中的呈现。
张载二重化的人性论学说影响了二程。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①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第81页。朱熹对张载、二程的人性论学说大加表彰。据《朱子语类》记载,
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如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那里有三品来!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页。
4.“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张载“四句纲领”之第四句说:“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可以视作张载论“心”定义。与当时流行的认识不同,张载并不孤立地以知觉论心,而是强调人性对知觉的制约和范导作用。张载论“心”定义的突出特色是,为人的感知思维能力确定德性根据,并为后来的学者从多角度理解人的感知思维类型提供了可能性。
张载非常重视“心所从来”的问题,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论“心”定义。张载说:“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正蒙·大心》)又说:“有无一,内外合(自注:庸圣同)。此人心之所自来也。”(《正蒙·乾称》)“心所从来”与“心之所自来”的意思一样,前一段话强调的是“知心所从来”对于“尽其心”的必要性,后一段话则是对何谓“心之所自来”做出正面的解释。按张载解释,“心之所自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谓“有无一”,指向的正是张载所界定的“性”范畴。张载说:“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同上)二是所谓“内外合”,指向的正是张载所谓“知觉”概念。张载这里所谓的“内”,是指人的知觉器官及其能力,“外”是指一切外在的对象物和存在者。“内外合”,指的是“内”在的知觉器官及其能力与“外”在的世界及其事物两方面的结合,由此而有“知觉”的发生。张载论“心”,不只从“内外合”的“知觉”着眼,而还要特别从“有无一”的宇宙万物共有之“性”着眼,这正是张载心论异于诸儒之处。
这里有必要对张载所说的“知觉”作进一步的解析。在张载著述中,“知觉”仅一见,而且他并未对“知觉”做过任何界定。近现代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所谓“知觉”,一般特指外在对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整体映象。而包括张载在内的宋儒所使用的“知觉”一词则不同,它是泛指人的身心感官的一切活动,其涵义包括精神的不同作用形式,是相当于现代的感觉、认知、思维、意志、直觉等概念所能够体现的精神活动及其能力。对我们分析张载的“知觉”涵义有帮助的是,张载认同孟子以“心之官”为“大体”、“耳目之官”为“小体”,并经常使用“大体”和“小体”这两个术语。同时,考虑到在张载论“心”定义所涉及的“性”是有“合两”结构的,故我们可以对应地把张载所谓“知觉”解析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在“耳目之官”(小体)基础上形成的“感官知觉”或“见闻知觉”,二是在“心之官”(大体)基础上形成的“心官知觉”或“虚明知觉”。对于前者所谓“感官知觉”或“见闻知觉”应不难理解,它的对象是一切“形下之物”,它的功能是产生声色臭味之欲(情欲)和见闻之知(感知);而对于后者所谓心官知觉或虚明知觉,则需要略作解释。张载说:“虚明照鉴,神之明也。”(《正蒙·神化》)此外,张载在其佚书《礼记说》中解释《大学》的“格物”涵义时,把“格”训解为“去”,指出:“格去物,则心始虚明。”(《礼记说》卷一四九)在张载看来,格物之“物”是主体耳目感官知觉的感知对象,只有去除一切外在经验物的消极影响,“虚明知觉”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是一种超越见闻之知的“神明”之知,其对象是“形上之道”,它属于主体超越耳目见闻等感觉能力的更高层次的直觉能力和体认能力,按张载本人的说法这便是“大其心”、“虚心”的精神能力。
与此相对应,前述“合内外”便有两种情况。张载说:“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正蒙·大心》)“内外合”的第一种情况是:人的耳目之官“有受”,亦即人的耳目感官接受外在对象的作用,二者发生关连,形成闻见之知。这是在耳目之内的“合内外”。“内外合”的第二种情况是:人的知觉能力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会发生“合内外于耳目之外”,这是指超越于耳目感官知觉及其所产生的见闻之知之外,运用心之官的虚明知觉能力所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合内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经由张载论“心”定义中性与知觉的固有含义,做出如下推导:一方面,如果人的感官知觉与气质之性结合在一起的话,便构成所谓“见闻之知”;另一方面,如果人的心官知觉与天地之性结合在一起的话,便构成所谓“德性之知”。换言之,心官知觉以天地之性亦即“至善”的本原之性为根据,才能够形成德性之知。
在张载哲学的脉络中,所谓知识分为“德性”与“见闻”两类。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见闻之知”,是人以耳目感官对外在具体对象认知的结果,亦即“因物为心”的结果。张载对“见闻之知”的局限性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张子语录下》)因而,这里见闻之知的局限只有靠“尽性”和“尽心”才能克服。张载说:“今所言尽物,盖欲尽心耳。”(同上)“尽心”,不是试图从数量上去穷尽天下所有之物,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尽心”是要从宇宙整体,从造化之道去体悟“德性”的根源,以确立宏阔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在于,二者的来源不同:“见闻之知”,来源于耳目感官知觉对外物的把握;“德性所知”,则来源于心官知觉或虚明知觉对宇宙造化及其根源的直觉。张载关于两种“知”的划分,体现了宋代新儒学的思考重心,凸显了道德知识对于一般感性知识的优先性。
张载虽然强调“德性所知”对于“见闻之知”的优先性,但并不完全否认见闻之知的作用。他说:“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正蒙·大心》)值得注意的是,张载对耳目闻见作用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必须属于“闻见之善者”,才能够发挥积极的“启之之要”的作用。例如,要“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经学理窟·义理》),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经学理窟·气质》),等等;若不属于“闻见之善者”,则“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志。”(同上)
(二)礼学思想
北宋是礼学盛行的时期。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的礼学更是名重一时,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可惜以上诸书均已散佚;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宋史·道学传》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二程称张载之学“以礼立教”,①《论学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195页。都注意到张载学说重视礼学的鲜明特点。
1.礼之多重根源。礼之根源是关乎礼学本质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张载综合秦汉以来儒者的成果,并创发新意,认为礼具有三重根源:一是根源于天(太虚),二是根源于理,三是根源于心或情。
其一,礼源于天(太虚)。张载不认同时贤“专以礼出于人”的观点,强调“礼本天之自然”,以此突显礼的神圣性。张载的观点是有经典依据的,《礼记·礼运》篇便有“礼必本于大(太)一”之语。张载在其佚书《礼记说》中将其哲学的“太虚”概念与“大一”概念联系起来,提出:“大虚(太虚),即礼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礼非出于人,虽无人,礼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人?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礼记说》卷五八)
其二,礼源于理。张载指出,“礼出于理之后”,“知理则能制礼”。(《张子语录下》)就是说,在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礼时,要由更具抽象性的理作为其根据;只有先“穷理”,才能够做到“知礼”、“制礼”和“尽礼”。在此意义上,也可以把“理”视作礼的根源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理”是居于“天”之下的次级范畴,“理”和“天”并未如二程洛学那样同一化为一个整体观念;虽然“理”具有根源涵义,但“理”毕竟还不是终极根源。①林乐昌:《张载理观探微》,刊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第27~28页。
其三,礼源于心或情。虽然张载肯定“天”是礼的终极根源,但他却不能不看到社会生活是以万物之灵的人为主体的,因而张载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心和情也是礼的根源之一。张载说:“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经学理窟·礼乐》)又说:“人情所安即礼也。”(《礼记说》卷五八)心和情,可以视作个体行礼实践的内在精神-情感结构。张载引《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孔子语“无体之礼”,其涵义便指“敬”。②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7页。张载秉承孔子关于礼内在于敬的思想,认为,作为“礼之原”的“心”亦即精神-情感结构,其主要价值内涵便是敬、诚等。
2.礼学的三个层面。张载礼学,大体涉及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以礼成德”。(《礼记说》卷五九)这一层面的礼,主要是就个体而言的。在张载看来,提升和成就自己道德人格的有效方法便是学礼、知礼,并依礼而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礼的要求。他说:“进人之速无如礼。”(《经学理窟·礼乐》)在他看来,人性的提升和成长需要礼仪规则的约束,而“行礼”实践即是人性提升和完成的过程。
如前所述,张载很重视“变化气质”的工夫。在他看来,“变化气质”是必须通过“行礼”实践来实现的。张载说:“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经学理窟·气质》)张载甚至认为,无论圣贤和凡庸,进德修业都不能离开修“礼”一途,他说:“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皆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是透上透下之事也。”(《礼记说》卷二)
在“行礼”实践中,张载强调从“洒扫应对”等基本环节做起,他认为,“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实际上,这也是儒家所谓“下学上达”过程的一部分。张载说:“克己,下学也,下学上达,交相培养,盖不行则成何德行哉!”(同上)
在个体“行礼”实践中,张载不只是要学者熟习“礼”的外在规范要求,更要人重视主体所应当具备的“敬”、“诚”、“仁”等内在的虔敬态度、道德情感和精神品格。如他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正蒙·至当》)又说:“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经学理窟·气质》)但另一方面,敬、诚只有在“行礼”实践中才能够得以彰显。这正如张载所说:“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同上)
第二个层面:用礼成俗。此一层面的礼,其主要内容为乡村生活尤其是家族生活中的常行礼仪,如冠礼、昏礼、丧礼、祭礼等。清儒朱轼在说明张载礼学的内容及其特征时指出,“其家冠、昏、丧、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③朱轼:《史传三编》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于丧、祭等礼仪能够发挥维系和调节宗法关系的作用,故深受张载及其门人的重视。司马光准确地将张载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古礼的作法概括为“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①司马光:《又哀横渠诗》,《张载集·附录》,第388页。由于张载竭力倡导和推行古礼,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②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第664页。,取得了“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的成就③《张子语录·后录上·遗事》,《张载集》,第337页。。后来,张门弟子吕大钧兄弟撰写《乡约》、《乡仪》,并推行于其乡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正是对张载重视在地方上整顿伦理秩序、以礼化俗事业的延续。
第三个层面:养民治国之礼。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吕大临《行状》)。所谓“三代之治”的基础,便是礼乐制度,故张载主张治理国事要“以礼乐为急”(《张子语录中》)。张载认为,礼乐制度应当发挥养民和治民的功能,此即他所说:“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经学理窟·礼乐》)他还说:“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吕大临《行状》)张载提出,开明的社会状况应当是:“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横渠易说·系辞下》)在此基础上,张载提出了以礼“致乎大同”(《礼记说》五四)的社会理想。
3.“以礼为教”。完整地看,张载的礼学不仅是以学理形态呈现的,而且还包含有一套教学实践系统。无论是从事讲学授徒等教育活动,还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都在张载的礼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张载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经学理窟·义理》)可见,张载把讲学传道、培养学者视作“功及天下”的头等大事。
张载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赵宋王朝重教兴学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北宋政治具有明显的“文治”取向特征,这恰恰为北宋历次重教兴学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环境。然而当时理学家与政治家对于兴学立教的初衷和着眼点是有所区别的。如领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和作为理学主要派别之一的洛学,对于政治变法与兴教运动的关系,看法便有所不同。如钱穆所准确指出的:“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味重于教育”,而“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味重过政治。”④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96页。
儒家学者历来关心“为学之方”,而作为人师则必强调“教人之法”。儒学的这一传统特征,至宋代尤著。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卷二题为“为学大要”,卷十一题为“教学之道”,恰好是儒学这一传统的反映。考察宋明理学各派的教学活动则可以发现,其“教人之法”各有不同特征,例如宋代程朱学重视“格物穷理”、“涵养居敬”,陆学重视“先立其大”、“发明本心”,而明代王学则重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
张载逝世两年后(1079),程颐在总结张载关学的教学方法时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⑤《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23页。作为与张载往来密切的洛学代表人物,程颐的就近观察是相当真切的。程颐曾经将自己的这一总结语浓缩为“以礼立教”四字,此四字又在南宋、元、明、清历代学者的广泛征引中被表述为“以礼为教”四字,这就以更明确的意涵彰显了张载教学实践和和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⑥宋代学者吕本中、吕祖谦、朱熹、真德秀,元代学者胡炳文,明代学者吕柟,清代学者顾炎武、颜元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张载“以礼立教”或“以礼为教”的教学实践和教育哲学宗旨。在北宋理学家及其他儒者中,重视教育和通晓礼学者不乏其人,但作为教育家明确标示“以礼为教”,把“以礼教学者”作为自己教学实践宗旨和教育哲学主题的,则惟张载一人而已。
张载“以礼立教”或“以礼为教”的主旨谓何?在学术界对此课题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或者将其归结为“修持工夫”层面,或者将其归结为“学风”和“致思方式”层面,这种理解略嫌不够准确。本文认为,“以礼为教”是张载教学实践和教育哲学的共同主题。张载作为教育家深感“教人至难”(《礼记说》卷八九),其一生于如何达致“善教”之境多所用心,在施教过程中总结出系统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其要点有二。
其一,将“先学礼”(《张子语录下》)及“强礼然后可与立”(《正蒙·中正》)作为以“礼”为中心的教学实践支点。所谓“立”,其目标是主体道德人格的确立,而“立”的根基则在于“礼”。因而,张载反复强调:“人必礼以立”(《横渠易说·系辞上》),“立本既正,然后修持”(《经学理窟·气质》)。故在张载看来,立于礼是“继志”、“入德”的有效方法。张载认为:“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捷径,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经学理窟·礼乐》)张载的这一思想,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30论断的进一步发挥。
其二,突出强调“礼”对于实现仁的积极作用。张载继承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践仁精神,突出地强调了“礼”对于实现仁的积极作用。张载说,仁“不得礼则不立”。(《经学理窟·义理》)就是说,要真正确立仁这一核心价值,就不能不依赖于礼。张载说:“‘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仁之至也,爱道之极也。”(《正蒙·至当》)将礼在实践中的彰显,视作实现仁、爱的极致。张载有诗云:“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31这是以比喻的方式说明礼在实现仁的过程中的优先作用。张载还将“学礼”视为“守仁”的有效途径,他说:“仁守之者,在学礼也。”(《经学理窟·礼乐》)这种通过礼来自我控制(“克己”)从而实现仁的方法,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张载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还形成了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张载的教育哲学思想,其远源于周、孔之学,其近源则在乎《礼记》。《礼记》之《曲礼》篇云:“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32而《礼记》之《学记》篇与张载教育哲学思想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学记》是全面论述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纲领性论著。司马光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诸篇,为《礼记》之精要,且以《学记》在《大学》之前。33在北宋理学诸派中,二程教弟子重《礼记》之《大学》篇,张载则较少言及《大学》篇,而是更重《学记》篇。张载有关《学记》的系统解说,今可集中见于其佚书《礼记说》辑本中。从《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对《学记》诸篇的解说中可知,“以礼为教”四字大体可以涵盖张载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另外,由于礼能够为儒家的公共活动和政治制度提供原则,这样礼就把教育与政治结合了起来。在此意义上,张载礼学便既是教育哲学,又是政治哲学。
(三)《西铭》:伦理学纲领
虽然张载所撰《西铭》全文仅253字,却堪称千古名篇。同为北宋理学家的二程兄弟对《西铭》评价极高,认为此文所说“扩前圣所未发”,并使《西铭》获得了在程门与《大学》并列的经典地位。朱熹曾以《西铭》的前三句为全文的“纲要”,这对我们诠解《西铭》很有启发。朱熹所谓《西铭》前三句是:“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里略做调整,以《西铭》前三句作:“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一文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仁”“孝”伦理原则。《西铭》说“仁”“孝”,与早期儒家有所不同,是基于宇宙根源的解说,其新意表现为“两个扩大”,“一个突破”。34
先看“两个扩大”。一是扩大了“仁”的实践范围。《西铭》首次明确提出“民胞物与”的理念,把自然万物都视作人类的朋友。这种善待自然万物的情怀,是儒家从限于人类说仁爱到不限于人类说仁爱转变的结果,是张载对仁爱观的发展。二是扩大了“孝”的实践范围。孝亲是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西铭》也充分肯定孝顺生身父母是孝子应尽的伦理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西铭》首句“乾称父,坤称母”,显示作者把“乾坤”或下文所谓“天地”视作人类的“父母”。《西铭》还依据《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的诗意,把人子的孝行扩大为人类对天地父母行孝,也就是尊崇和敬畏天地父母,从而为“孝”注入了神圣性,使“孝”成为信仰的一个重要维度。
①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六《季氏第十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522页。
②转引自吕本中:《童蒙训》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一《曲礼上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231页。
④司马光:《书仪》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详见林乐昌:《张载〈西铭〉新诠》,刊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林乐昌:《品读〈西铭〉》,刊于《光明日报》2014年4月21日“学者随笔”专栏。
⑥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再看“一个突破”。早期儒家强调仁爱的血缘根据,主张爱有差等;而张载则重视仁爱的宇宙根据,以谋求平等之爱。《西铭》所谓“民胞物与”,与张载在《正蒙》中提出的“爱必兼爱”完全一致。张岱年先生指出,张载的仁爱观“综合了孔子的仁与墨子的兼爱”,他所谓“兼爱”是有进步意义的。“民胞物与”和“爱必兼爱”理念,对早期儒学而言真可谓石破天惊,是对传统仁爱观的突破。《西铭》把宇宙视作一个大家庭,一切人或物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张载倡导平等之爱,但并不排斥差等之爱。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爱,可为区分社会公德与个人及家庭私德提供传统资源。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最后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反复重申人类是“大地母亲”的孩子,若不能善待“母亲”,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敬畏自然,是一种境界,也是善待自然的前提。《西铭》的理念与汤因比的告诫一样,对今天都极具警醒意义。
(组稿:李承贵;责任编辑:刘丽)
Zhang Zai’s Academ ic Course and H is Guan School Ideology
Lin Lechang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 hanxi Xian,710062)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hree transition called reading the“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visiting Buddhist and Taoist and reversing the Six Classics in Lv Dalin’s“Xingzhuang”and Zhang Zai biography in “Song”all belong Zhang Zai’s early academic activities,and then according to early,middle and late stages,the author investigates Zhang Zai’s nearly four decades of academic career;Zhang Zai’s Guan School ideology matured in his old age,in his theoretical program,“Heaven”was the core concept,“Heaven”,“Taoism”,“Nature”and“Heart”formed the concept sequence.
Zhang Zai;Song Science;Guan School;Guan School ideology;“Zhang book”;“Zhang ZaiWorks”
B21
A
1008-7354(2015)01-0014-12
林乐昌(1949-),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