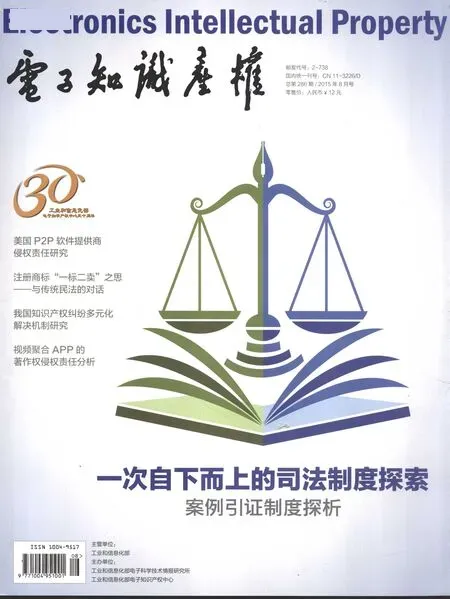案例引证制度之观察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规定为对象
2015-03-29孙艳洪碧蓉
文 / 孙艳 洪碧蓉
案例引证制度之观察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规定为对象
文 / 孙艳 洪碧蓉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推行的案例引证制度,系颇具特色的一项案例运用制度。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案例引证制度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以及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在性质、引述案例范围、提出主体以及如何适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该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对案例引证报告进行定性,其关系到如何在判决书中评价或引用在先案例的裁判规则的问题。从案例引证制度运行的情况来看,其将案例引证报告以类似于证据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进一步探讨。
案例引证;案例指导;判例法
法谚云: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凝聚了解释法律、适用法律乃至创造法律的智慧。在先判决蕴含着法官的说理、智慧和对法律的阐释,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经常会引用类似案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也常常将类似案例中的观点转化为判决书的说理。案例在我国虽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有些特殊的案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公报或一些书籍上公布的案例,实际上已经具有类似于判例的作用。
知识产权案件中,系列案、新类型案、疑难复杂案件较多,参考在先判决成为司法实务中的普遍做法。为进一步规范在先案例在实践中的运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率先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推行案例引证制度。该制度的试行,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对该制度进行介绍,将其与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并指出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以资共同学习和探讨。
一、案例引证制度的功能及特色
根据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台的《案例引证指南(试行)》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将案例引证定义为:当事人或者独立的第三方对过往类似案件进行类型化梳理,根据具体需要提供不同形式的案例引证报告,由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以判决理由的方式加以利用,以确保更大说服力和司法一致性。
(一)功能
1.追求司法规则的一致性。依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案例引证指南(试行)》的规定,案例引证并不拘泥于“类似案件”和“同案同判”的判断上,引证案例与在审案件的关涉性来自司法规则的一致性。案例引证制度是在对海量案例如何运用法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炼出可以普遍适用的司法规则。这样的司法规则并非只有类似案情可以适用,只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同或相类似即可适用。也就是说,案例引证不仅仅追求同案同判,其更多的价值在于如何从分散的案例中提炼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以此达到更具有司法公正内涵的“对同一裁判规则统一理解和适用”的目的。
2.增强判决的说服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新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知识产权纠纷中的新型疑难案件层出不穷。知识产权立法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法官在解决新类型纠纷时,只能运用兜底性条款或法律原则等模糊性规定。在无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也就是运用知识、经验、智慧解释法律的过程,其中凝聚了法官个人的智慧和理性。因此,在先案例对于法官解决新型疑难案件,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对其引证,可以有效提升判决的说服力。
(二)特色
1.案例范围。案例引证制度中,对所引证的案例并没有审级限制或必须是指导性案例,其范围包括全国各地法院的所有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文书。这种无任何范围限制的案例引证方式,体现出对每一位法官司法裁判技艺的尊重。司法裁判本是一种法律技艺,经验的积累是“技艺理性”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1.韩伟:《新时期须加强法官的技艺理性》,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7月17日第2版。,因此,无论文书最终的审级如何,若裁判文书的说理体现法律适用的智慧和理性,都可以作为案件裁判的参考。但正是这种无限制的案例引证范畴给该制度的适用带来了问题,下文会详细阐述。
2.提出主体。除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外,该制度引入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者专家辅助人提出案例引证报告。与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不同,该制度中的专家辅助人,职责是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引证报告,为法官最终形成裁判意见提供参考;而通常的专家辅助人,职责是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说明。法律适用属于法官的职责,第三方机构或专家辅助人能否突破这一界限为法官适用法律提供专门性意见,是存在争议的。
3.提交内容。案例引证不是简单地提交一份类似裁判文书,而是要求当事人、律师或专家辅助人提交引证报告或其他形式的案例引证意见书,将其引证的类型案件梳理出支持己方的裁判规则,还要对此展开辩论,而且在判决书的书写上将引证的案例作为事实写入查明的事实部分,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引用哪一方提交的案例及其理由进行分析,并依其总结出的裁判规则进行裁判。
4.效力。在效力规范的设计上,该制度以指导性案例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对指导性案例和其他案例的效力进行了区分:即指导性案例在类似案件的审理中是“应当参照”,其他案例则是“可以参考”。无论是“应当参照”还是“可以参照”,法官在引述引证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规则时,均应在裁判理由中作出分析和回应。
5.引证规则。首先,在引证案例与在审案例的比较上,案例引证制度并不要求在审案与引证案例为“类似案例”,只要求二者具有司法规则的一致性,这是该制度的特色之一。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新类型案件或合同案件,经常会运用到普通民事案件的裁判规则,如果将引证案例限制在“类似案例”上,会限制知识产权法官的视野,不利于公正判决的作出。案例引证制度在“类似案例”上的突破,充分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类型的特殊性,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的特点。其次,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中对引证案例充分地分析,并注重提炼裁判规则,同时对是否参照该裁判规则说明理由。再次,与案例指导制度相同,引证案例中提取的裁判规则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只能在判决理由部分评价和引述。
二、案例引证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区别
如上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创建的案例引证制度特点显著,且有其现实意义,实系司法审判实践的一大创新举措,与最高人民法院如火如荼大力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及判例法国家的判例制度有明显区别。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的重要特征。所谓判例法,就是以判例而不是成文的制定法、法典等为法律体现形式或渊源的法律体系。从制定或发布的主体来看,判例法是法官在判决中对相关法律规则的表述,是司法过程的产物。判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运行的主要特色如下:1.判例法的运行必须遵守遵循先例的原则。所谓遵循先例,就是对过去判决的依循,对先例中判决理由的依循。2.在判例法体制下,对判例效力影响最大的是作出判决的法院之等级,法院的等级越高,其作出的判决就越有权威。2.陈兴良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0页。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同级法院的判决对其他本级法院具有说服力,但不具有拘束力,各级法院的判决对本法院具有拘束力。3.主要由当事人或律师提出或援引。在英美法系,因奉行当事人主义的抗辩诉讼模式,判例主要是由当事人或其律师提出或主张或援引,法官居中裁判,只在形成判决的过程中因支持或反驳辩方的判例时才需要主动去发现并引用判例。3.沈德咏主编:《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案例引证报告是作为查明的事实写入判决书中,且需对双方提出的裁判规则是否适用于本案事实分别进行分析说理,说明其并非一种法源,但其性质为何,却难以下定论。
而我国正在实施的案例指导制度其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我国的指导性案例是从各级法院通过层层遴选推荐到最高人民法院,案例一般产生于各级法院,但是否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决定及发布权均由最高人民法院掌握,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编纂下发至各级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必须提炼出裁判要旨,也就是法律适用规则。这种规则事实上成为明确的法律规范,可直接适用于与当前案例相似的案件,对于个案纠纷的解决具有直接的、实际的效力,是判决的根据。虽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不同,但实际上已经与司法解释具有相同的功能,是独立于司法解释之外的一种规则载体。
将这两种制度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实行的案例引证制度相比较,可发现其区别如下:
1.性质不同。判例法是一种法源,由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进行造法,而其判决理由就是一规范,对以后同类型案件具有约束力。指导性案例实际也是一种法律规则,在同类型案件审判时应当参照,而所谓参照,就是“参考、遵照的意思,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要遵照、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4.蒋安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载《法制资讯》,2011年第1期。从案例引证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案例引证报告是作为查明的事实写入判决书中,且需对双方提出的裁判规则是否适用于本案事实分别进行分析说理,说明其并非一种法源,但其性质为何,却难以下定论。
2.所引用的案例范围不同。如上述,在判例法体制下,法院的等级越高,其作出的判决就越有权威。克里斯和哈里斯将此归纳如下:一是高级法院的判决应得到尊重;二是即使就其上级法院而言,高级法院的判决也具有说服力;三是无论高级法院的判决多荒谬,都对其下级法院有约束力。所以,在判例法国家中,法官所引用的先例一般是高级法院或同级法院或自身法院所作出的生效判决。指导性案例中所引用的案例也必须是生效判决,且是各级法院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的案例。而案例引证制度中,《案例引证指南(试行)》规定“引证案例不局限于生效判决,也不局限于本院作出的判决”,也就意味着引证的案例可以是未生效的判决,且不限制作出判决的法院级别。
3.提出主体有所不同。在判例法国家,援引的判例一般由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提出。目前的指导性案例一般由法官自行适用,只是鼓励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提出主张。而案例引证报告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提出,也可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或相关专家提出。
4.如何适用有所不同。在判例法国家,所遵循先例的判决理由就是一个法律规范,法官在判决时,无需在查明的事实中对先例进行陈述,也无需论证本案与先例是同类型案件,只需在判决时引用先例的判决理由。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作为一种裁判规则,亦无需写入查明的事实,而是在判决书说理部分直接引用。而案例引证制度中的案例引证报告,是作为查明的事实写入判决书,并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双方提出的裁判规则是否适用于本案事实分别进行分析说理,并做出判决。
三、案例引证制度尚存的疑惑
经过与判例法及案例指导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案例引证制度的性质、运行方式均与上述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别,而性质又是其运行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因案例引证制度的性质不明,导致其运行仍存在一些应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1.案例引证报告难以定性。如上所述,判例法与指导性案例其实都是一种法律规范,是一种法源,而从案例引证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其将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案例引证报告作为查明的事实写入判决书,其实是将案例引证报告以类似于证据的方法在使用,那它是一种证据吗?笔者认为:首先,证据犹如磐石般岿然不动的属性就是用以证明案件客观事实,即关联性。虽然我国学者对证据的定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如事实说认为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而根据说认为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材料说认为证据指可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但是不管怎么定义,均说明证据必须是用来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物质,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其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各种载体表现出来。然而,由于案例引证的功能系“用更强理由服务于法律的正确适用”,可以看出,案例引证报告是对大量判决中所适用的裁判规则的总结概括,是对法律适用规则的提炼,而非案件事实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即并非用于证明案件事实,也就是说案例引证报告并不具有证据属性。其次,案例引证报告无法归入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从案例引证报告的表现形式来看,双方当事人出具的引证报告似乎可以归入当事人的陈述,专家出具的引证报告似乎类似于“专家法律意见书”。然而,证据类型中的当事人的陈述,应该是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发生过程的一种回忆,而非对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的阐述。所以,当事人提出的案例引证报告无法归入“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分类。专家法律意见书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但一般也是由当事人自行委托专家出具,且其并非法定的证据种类,如何对其进行定性,实践中也存在分歧。综上,如何对案例引证报告定性,实属一大难题。
若允许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从法律适用方面为法官提供意见,实际上赋予专家学者隐性的法律解释主体地位,这种角色定位与法官独立的裁判地位是相互冲突的。
2.提供主体角色难以定位。提供案例引证报告的主体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也可以是由法院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提供引证案例,可以将其定性为辩论意见以供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作为参考,但由法院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提供案例引证报告时其角色该如何定位?首先,这就关系到法官的角色定位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因有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事实问题一般由陪审团判断,而法律问题由法官裁判;而在我国,不存在事实审与法律审的问题,法官必须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寻找可适用的法律从而作出判决,也就是说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是法律适用的唯一主体。法官作为法律适用专家,当对同一法条存在不同理解时,就应适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对法条作出解释,从而适用法律作出判决。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不是适用法律或者解释法律的主体,由其出具引证报告对法律适用单独发表意见,是否合适,其发表意见是否会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这些问题均值得讨论。其次,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是以自然规律为研究对象,对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均有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其追求“精确”。所以法官在遇到一些专业问题时,如笔迹、指模、工程量、软件设计、账目审计等,必须借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专业问题作出判断,由专家作出鉴定结论以供法官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断,但这种专业问题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基本有唯一正确的结论。但人文社会科学中蕴涵大量的心理、情感、意识等方面的因素,不可能纯客观地得到反映,有的甚至不可能再现和重复,具有不可量化性。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其在很多问题上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或者立法机关中的个人,对同一法条也常作出不同的理解,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否则就不需要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所以法学问题由不同的人进行解释经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若允许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从法律适用方面为法官提供意见,实际上已经赋予专家学者隐性的法律解释主体地位,这种角色定位与法官独立的裁判地位是相互冲突的。因此,笔者认为,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学者不适宜作为案例引证报告的提供主体。
3.判决书如何引用引证报告难以确定。案例引证制度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引证报告是写入事实查明部分。但如上述,不管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提出的引证报告还是专家学者提出的引证报告均不能定性为证据,故在判决书中将引证报告作为查明的事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如何引用引证报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提出的引证报告可以定性为辩论意见,在判决书中可以将其写入当事人起诉意见或答辩意见或争议焦点提出的意见中;而专家学者出具的引证报告又该如何书写?实际上,笔者认为,专家学者不宜作为引证报告的提供者,所以该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
4.未得到在审判决认可的引证案例难以评价。在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引证报告时,必定是收集了不同判决结果的案例,如果被在审判决认可的一方所收集的案例均是生效且由同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而另一方收集的案例判决没有生效或是由低级别法院作出的判决,那么引证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作为判决理由不存在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收集的案例均为生效判决,且均是由同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那又该对最终未得到在审判决认可的引证案例如何评价呢?是认为引证案例是一个错误的判决还是以未生效或作出判决法院级别太低为由不予采纳其判决理由呢?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笔者提出上述浅薄意见,仅代表个人意见,且系以资共同探讨和学习为目的,并非对案例引证制度持反对态度,而是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存在的问题,以弥补目前成文法及案例指导制度的缺陷。
Observation of Case Citation System—The Object of the First People's Court of Dongguan City
The case citation system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f rst people's court of Dongguan City, is a characteristic case application system. Through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ase citation system and the case system of the Anglo American legal system and the case guidance system of our country are obvious dif 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e, case range, the main body and how to apply. The key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s how to mak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 report. It relates to how to evaluate or quote the rule of the re feree in the f rst case in the judgment. From the case citation system operation situation, It uses the case report as evidence. Whether this method is appropriate or not, it is worth further study.
Case citation;Case guidance; Case law
孙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硕士研究生;洪碧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