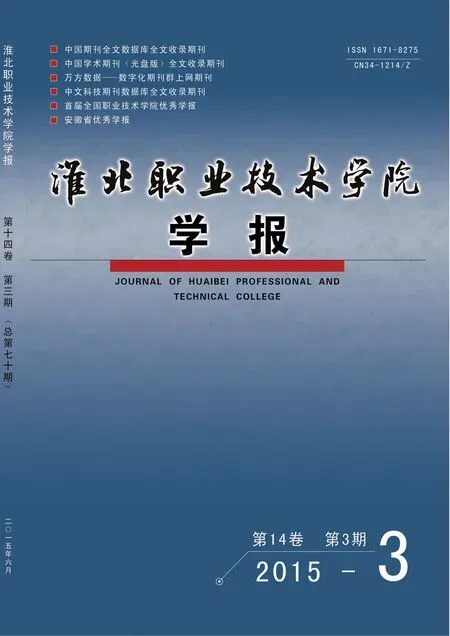汉乐府诗中汉代婚恋民俗文化探析
2015-03-28李爽爽
汉乐府诗中汉代婚恋民俗文化探析
李爽爽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摘要:作为汉世街陌的歌诗,两汉乐府诗广泛反映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情绪,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俗文化色彩。其中体现婚恋题材的居多,特别在男女恋爱习俗、婚嫁礼俗、女子改嫁和再醮习俗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颇为值得关注。
关键词:两汉乐府诗;婚恋嫁娶;民俗文化
收稿日期:2015-04-12
作者简介:李爽爽(1990-),女,安徽淮南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I222.6文献标识码:A
乐府诗是地方歌谣采集而来,反映了普通百姓遭遇各种生活境况时或悲或喜的感慨,因此,它是来源民间或直接接受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成果,与广大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息息相关,这给我们考察汉代的民俗文化带来丰厚的资源。汉乐府现存有四十多首,其中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占绝大多数。以下笔者将从汉代男女恋爱、婚嫁礼俗,女子改嫁和再醮三方面来探讨汉乐府诗中所体现的汉代婚恋民俗文化。
一、汉乐府与男女恋爱习俗
汉乐府中关于男女相思相恋的题材很多,从这些诗中可以发现男女对表达爱意的方式及恋爱场所的选择等都反映了一定的风俗习惯。
(一)男女示爱的方式
总结起来,男女示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时而含蓄时而大胆地向所思所念之人倾吐缠绵爱意之辞,二是赠送礼物用以定情。
在大胆倾吐爱慕之意方面,可以从“汉铙歌十八曲”中的第十五曲《上邪》看出: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此篇是男女间的誓词,而且似与《有所思》篇内容上是连贯的。此篇诗歌所洋溢的情感是热烈的,女主人公用大胆的誓词向男主人公起誓“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更是用五种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来表明她的坚贞不渝。再如《陌上桑》,当“使君”想要向罗敷示爱时,直接问罗敷“宁可共载不?”除却这种大胆的风格,含蓄真挚的表达爱意也是有的,如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一):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这是司马相如对新寡卓文君表达好感所作,他并没有大胆示爱,而是含蓄地“以琴心调之”[1]830,真挚地表达出对卓文君的绵绵爱意。可见,汉代男女在表达爱意时,既有大胆热情之语,又有含蓄真挚之辞。这种示爱方式的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与当时的封建礼制对男女自由恋爱有所约束有关;其次,这与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的不良婚姻礼制习俗也有关。如《陌上桑》中“使君”大胆地向有妇之夫示爱。
另一个示爱途径是赠送礼物,也是我们常说的定情之物。比如“汉铙歌十八曲”第十二曲《有所思》,在这首民歌中女子所思念的人住在大海的南边,为了表达其爱意,她想赠送男子双珠玳瑁簪:“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古代男子出门要戴帽子,必须用簪束发,簪是他所离不开的,因此女子就送一枚光滑斑斓并系上美玉的玳瑁簪。通过对簪子的细心装饰,可见女子对男子的用情之深,她将赠送的东西看得越慎重越珍贵,越见得她对这份感情的珍视,对心仪之人的热烈爱慕。《羽林郎》篇,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说,从“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可以看出,冯子都向胡姬示爱时,将青铜镜赠与胡姬,系在她的红罗裾上。从这一点也证明男女在示爱时赠送物件来传情的这一习俗。当然,对于像冯子都这样登徒浪子,胡姬是坚决抗拒的。
(二)男女相识相恋场所
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恋爱不是自由的,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约会场所是必备的。汉代男女恋爱场所多在江河边,这种现象自古就存在。例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首篇《关雎》就是写一位痴情男子在黄河边思念心上人的场景。这种发生在江河边的爱情故事在《诗经》里屡见不鲜。这种风俗习惯也延续到汉代,例如《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这段话的意思即今天是最后一次聚会,明晨沟水边分手。女主人公漫步沟水头,往事浮现,爱情宛如这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
《迢迢牵牛星》也可以考证。这首诗是从牛郎和织女的故事衍生出来的,牵牛娶织女的故事,大约完成在西汉时。作者将写作的视角转到天上,牵牛与织女隔河相望:“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见,自古河边是男女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
(三)表示配偶、求偶的隐语
关于汉乐府中男女恋爱方面,所涉及到的除了示爱方式与地点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男女求偶常用的隐语及意象。从中也可发现汉代广大民众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心理以及所受何种文化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来看看隐语“鱼”“钓鱼”。乐府诗《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民歌我们从表层理解是劳动人民在采莲时所唱,将劳动的欢乐与江南独有的美景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令人向往的江南风俗画卷。我们在作品中发现了这几种意象:鱼、莲叶。这里,“鱼”实则是男子的意思,“莲”喻指女子。闻一多先生从民俗、民谣和古诗里考释鱼的隐语,指出鱼为配偶、情侣之意,打鱼、钓鱼喻合欢或结配:“‘莲’谐‘怜’声,这也是一种隐语的一种,这里是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2]50可见,这里的“鱼”与“莲戏”是一种恋爱的表现,是一种风俗文化。
《枯鱼过河泣》也可证明。《枯鱼过河》载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四之《杂曲歌辞》类。其诗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对于此诗的旨意,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五《卢仝传》中有诠释,余冠英在《乐府诗选》中也赞同郭的观点,认为“这诗以鱼拟人,似是遭遇祸患者警告伙伴的诗。”[3]53而闻一多先生对于此诗却有了颠覆性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首失恋哀歌。叶修成、梁葆莉在《〈枯鱼过河泣〉为弃妇诗考》中就大量举证闻一多先生的观点进行考证,最终认为此诗的旨意为一位弃妇(枯鱼)因触景(河)生情,用失败的婚姻告诫那些正春情萌动的少女们(“鲂鱮”)。因此,诗中的“枯鱼”的隐语是被丈夫抛弃的女子,而“鲂鱮”则隐喻为情窦初开、春意荡漾、正处于热恋之中的青年女孩。显然,这也充分体现了汉代百姓以鱼隐喻配偶、情侣之意的习俗。这种习俗也同样隐藏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如《饮马长城窟行》,诗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诗中双鲤鱼就是古人送信,用两块刻成鱼形的的木板把信夹在里面。所以,烹鱼而“中尺素书”。显然,这里的寓意是象征爱情的。
综上所述,古代人在表达配偶、情侣之意时时,常用隐语——“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习俗文化。并在“鱼”这一隐语的基础上,又繁衍出“打鱼、钓鱼”这类隐语,意为求偶。如《白头吟》中也有这样的描述:“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即男女情投意合就像钓竿那样轻细柔长、鱼儿那样活波可爱,男子应当以情意为重,失去了真诚的爱情是任何钱财珍宝都无法补偿的。可见,“钓鱼”这一行为是隐喻男女求偶行为的。
除了“鱼”“钓鱼”以外,还有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吃鱼的鸟类”,如白鹭、雁、鸳鸯等。
如《朱鹭》篇中朱鹭则是喻男子,鱼喻男子的女友。闻一多认为此篇是“讽刺男子和他的女友,老维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既不甘心放弃,又不肯娶她的。”[2]61再比如《焦仲卿妻》:“……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里的鸳鸯也是象征夫妇的坚贞不渝的爱情。
出现以上这种意象,追根溯源,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离不开的。自古娶妻就是为了生子,传宗接代,这与鱼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闻一多在《说鱼·探源》中写道:“种族的繁衍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繁衍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2]63因此,当封建传统思想与自然本身结合时,广大民众就会选择某种事物传递其情感思想,形成某个时代一种特殊的习俗文化。
二、汉乐府与婚嫁礼俗
婚嫁自古以来就是男女的终身大事,婚嫁之礼,自然受到重视。因此,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就非常浓重。以下笔者从婚姻的决定权、婚嫁的程序等方面分析汉乐府中所体现的婚俗文化。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汉代,儒家思想是主导思想,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对女子的“三从四德”的提出,更使得男女婚嫁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嫁礼制。这一礼制在汉乐府中也充分的体现出来,如《焦仲卿妻》中焦母凭借家长意志,强行让儿子停妻另娶。而刘兰芝是否另配县令之子,由于她父亲死的早,儒家文化中长兄如父就代其决定。可见,在汉代的婚嫁中,父母之命,是男女婚嫁的决定性因素。
而何又为媒妁之言呢?媒,就是谋合;妁,就是斟酌。媒妁,即斟酌情况,谋合两姓,使其相成。例如《焦仲卿妻》中县令派遣媒人来刘家提亲说合,媒人主要就是起中介作用。因为古代生活圈子很小,很少往来,对彼此情况都不熟悉,需要媒人加以介绍、说合、联系。比如《焦仲卿妻》中媒人来刘家说合道:“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可见,在婚嫁方面,男女双方的情况都是通过媒人的介绍加以认识结亲的。所以有谚语云:“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思想即只有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合理的婚姻,才具有社会普遍承认的合法性。
(二)繁琐的婚礼程序
中国古代的婚礼过程分为六阶段,故而被称为“六礼”。这种制度在周代已经萌芽,秦汉以后,逐渐成为定制。这“六礼”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汉乐府诗中关于婚嫁程序描写最为全面的当属《焦仲卿妻》这一篇。诗中“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以及“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这几句都是反映男方派遣媒人到女方家说合亲事,试探女方的态度。这就是“六礼”中的第一礼“纳采”。“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这与六礼中的第五礼“请期”相似。请期,是男方将择定的结婚日期告于女方。用请,只是表示客气,表示男方不敢擅自做主。后诗中又写道:“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以及“賫钱三百万,借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这是给刘家准备的彩礼用于“定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第四礼“纳征”。另外,诗中也写到“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这是描述迎亲所用的车驾,并对车驾进行了详细的描写突出迎亲车驾的华丽与壮观,反映当时车驾的讲究。这体现出“六礼”中的第六礼“亲迎”的装备。
除了《焦仲卿妻》中提到关于男女婚嫁的程序环节以外,《冉冉孤生竹》中也有反映“订婚”和“亲迎”这两个程序。
汉乐府诗歌中所体现的汉代男女婚嫁礼仪的文化,除去一般的婚嫁礼俗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婚俗仪式,比如《乌孙公主歌》《昭君怨》等诗作中反映的人。
三、汉乐府诗与出妻、改嫁、再嫁
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常喜新厌旧、三心二意,使得我们在汉乐府诗中也看到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她们或遇负心汉,或遭抛弃,亦或是丈夫纳妾。因此,就出现出妻、改嫁、再嫁的现象。
汉乐府有不少诗篇是反映男女婚后生活的,它用朴素的语言、直白的写法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真实再现出来。例如:《上山采蘼芜》通过弃妇与故夫偶然相逢时的对话,反映出女子遭夫家抛弃的悲惨命运以及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残酷。再如《焦仲卿妻》中的刘兰芝,尽管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谓德才兼备,但是仍然遭到夫家的抛弃。这种悲剧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制在作祟。
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婚姻往往不是以男女爱情为前提,而是取决于家族的利益和家长的意志,并且封建礼教更是把女子置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诸如“三从”之礼,以及明确女子被夫家休弃的“七出”法律条文等。另外,男子自身的三心二意,对婚姻的不忠,同样也使得女子深受其害,例如:《白头吟》《怨歌行》等都反映出男子喜新厌旧而造成女子被抛弃的社会现象。出妻现象自然成为封建社会中一种对女子不公的习俗。
女子改嫁和再嫁,在汉代则是被允许的,并且不受封建礼教约束。例如《焦仲卿妻》中刘兰芝被休之后,县令又到刘家替儿子提亲,兄长劝其兰芝改嫁。同样,在《怨旷思惟歌》中讲述了昭君本是元帝的后妃,而后元帝又将其嫁给匈奴的单于之事,诗句“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就真实地反映了昭君改嫁之事。可见,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于女子的改嫁都是认可的,允许的。对于寡妇再嫁,也同样认可,如《琴歌二首》就写的是新寡卓文君私奔后再嫁给司马相如,反映了“再醮”的习俗。
这种习俗的出现,有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汉代初期封建礼制并不完善,另一方面董仲舒在婚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即他不主张女子从一而终,认为女子可以改嫁和再醮,认为夫妻双方都应对婚姻持重视、忠贞的态度,这样才能保持婚姻关系的稳定。在这样一种婚姻文化的影响下,女子改嫁和寡妇再醮就不受道德约束和社会谴责,使这样的现象成为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习俗。
四、结语
汉乐府诗是集结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歌吟。它用质朴、生动、感人的语言,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因此,它具有充分展现两汉民俗文化的审美价值。特别在婚恋民俗方面,汉乐府诗都深刻地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仅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更给我们带来独具魅力的婚恋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郭茂倩.乐府诗集[M].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闻一多.古诗神韵·说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3]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