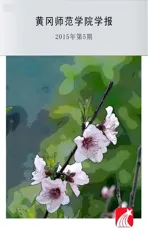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与现代小说研究范型的建立
2015-03-28陈娟,王炜
陈 娟,王 炜
(1.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00)
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与现代小说研究范型的建立
陈 娟1,王 炜2
(1.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00)
鲁迅将“小说”这一类目从四部分类法中的子类中清理出来,将《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白话作品与《世说新语》、《唐传奇》等文言小说并置于一体,确定了这个新的体系与“小说”这个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研究《金瓶梅》时,他从传统的学术路径入手,同时,也融入了近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开辟了全新的小说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小说观念和小说研究方法的更新。鲁迅在确定《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流派归属的同时,他还立足于知识要素自身的统系之内,从多个角度、从各层级上总结、归纳《金瓶梅》等“世情书”的质性和特征。
中国小说史略;世情书;研究范式
鲁迅论《金瓶梅》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第19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通过分析鲁迅研究《金瓶梅》的治学理路,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20世纪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人,从何种向度入手推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一
要了解鲁迅治《金瓶梅》的成就,我们首先要考察《中国小说史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和地位。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学术体系由“四部之学”转型成为“七科之学”。[1]如何贯通传统与现代,融会国故与西学,建构全新的知识统序,是学人纷纷探求的重要问题。“小说”作为一套知识类别,也处于重新建构的状态中。如何划定小说的界域,是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他顺应着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型,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在文学学科的构架下确定“小说”特定的界域。
在中国学术史上,目录学是治学的根基。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既是对书籍的归类,同时,也是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目录学的实质是,以例明类,划定知识的统序。宋代史学家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2](P1806)鲁迅从目录学入手,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梳理了《汉书》、《隋书》、《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官修史志著录“小说”的情况。在传统官私目录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小说”是二级类目。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小说”作为特定知识类别的命名方式以及它对应的知识要素,一直归属子类之下。鲁迅尊重并承认传统知识统系的体系建构和命名方式,他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3](P10)《中国小说史略》不仅梳理了“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而且在第三篇中专论“《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这样,鲁迅从目录学入手,在中国自身的学术统系内确认了“小说”作为知识类目的命名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它自身曾有的稳定性,以及这套统系内在的合逻辑性及合理性。
鲁迅承续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进而从目录学的内部寻求小说研究的突破口。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重新划定了小说的类例,确定了小说在近现代学术构架中的位置。中国知识要素的数量、规模、类型总是处于持续的增长之中。特别是宋元以后,新兴的知识要素,如戏曲、话本等民间的娱乐形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知识要素渐渐产生了归类的要求。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知识体系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之际,如果继续在传统目录学的体系建构之内对小说进行归类,难免会出现概念不明、分类混乱的情况,宋元以来出现的戏曲,以及明清时期出现的《三国演义》、《金瓶梅》更是无法安放。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内部入手,突破了经史子集的基本构架。他将《世说新语》等从子部小说类中提取出来,又将《搜神记》等从史部杂传类中分离出来,将这些作品与明清以后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纳入到共同的统序之中,划定了小说的基本界域,并清晰地厘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梳理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山海经》——六朝志人志怪——唐传奇——宋代话本及拟话本——元明之讲史——明代的神魔小说及人情小说——清代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这样,《中国小说史略》借鉴传统目录学的基本理念,融汇明清以来的小说观念,在近现代学术体系的构架下,重新划定了小说的基本类例。
《中国小说史略》既从小说数量的层面上对中国古代小说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又从知识体系的建构上对这类知识进行区画,确定了《世说新语》、唐传奇、《聊斋志异》等文言作品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白话作品共同构成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统系。《中国小说史略》不否认《世说新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鲁迅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长篇白话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共28篇,其中涉及古代小说理论建构的1篇,论及文言小说的11篇,论及宋代出现的白话小说的16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立足于近现代的学术构架之下,建构了传统知识建构的、全新的“小说”统序——以白话作品为主体的小说的历史。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他还借鉴了传统学人在研究集部的诗文和子部的小说时建构的体类观念,对明清以后新兴的长篇白话小说进行了明晰而准确的归类。他把《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归于讲史类,《西游记》等归于神魔小说类,《金瓶梅》等归于人情小说类,将冯梦龙《古今小说》等归于拟宋市人小说类。
鲁迅从建构近现代的文学学科体系入手,上承清人考据的方法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思路,下开现代治学路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深入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流程中,将“小说”这一类目从四部分类法中的子类中清理出来,将《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白话作品与《世说新语》、《唐传奇》等文言小说并置于一体,确定了这个新的体系与“小说”这个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思想观念,又融入了他本人的理论思考。鲁迅清晰地梳理了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延续、替代、共生等多重关联。鲁迅建构的这一新的小说统序和小说观念,标志着小说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
鲁迅的《金瓶梅》研究从传统的学术路径入手,同时,也融入了近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开辟了全新的小说研究范式,推动了中国小说观念和小说研究方法的更新。
明清两代,谈到《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白话小说,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小说作者的情况。到了近现代,仍有部分学人完全沿着传统的路径继续前行,他们对《金瓶梅》的作者进行索隐式的考证。鲁迅在对《金瓶梅》展开研究时,他并不刻意地否定传统的治学路向和既有的观点。在研究中,他关注作者的问题,理性地梳理了前代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一章谈到《金瓶梅》的作者说,“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这里,鲁迅简要而明晰地罗列了前代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讨论,如,沈德符认为是嘉靖间大名士,有人认为作者是王世贞,清代的谢颐则认为作者是王世贞的门人。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作者不知何人”。鲁迅客观、简略地陈述《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情况。这与部分学者过度关注作者问题,甚至从作者入手,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索隐,有着根本的区别。鲁迅曾经批评索隐法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4](P321)20世纪初期,也有其他学者对索隐法进行反思。1927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谈到《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时,也对这种索隐法提出批评。不否认作者的重要性,但摒弃索隐法,这是鲁迅、郑振铎等近现代学人推动学术转型所做的努力。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还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中提炼出有效的要素,将之应用于《金瓶梅》的研究,从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深化了学界对《金瓶梅》的认知。
《中国小说史略》在简要地陈述作者的情况后,鲁迅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金瓶梅》的文本上。鲁迅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国小说发展流程中给《金瓶梅》以合理的定位。鲁迅在确定《金瓶梅》的类别归属时,他有整体的观念,他将《金瓶梅》定位为“人情小说”一类,他还对《金瓶梅》、《红楼梦》等人情小说做了更为细致的统系划分。他从前代对《金瓶梅》的评点入手,进而将《金瓶梅》定位为“世情书”。他说: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鲁迅提出的这一观点,是从前人的评点中衍化而来。明清评点者在批评《金瓶梅》时,“世情”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如,《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9回回评说,“一篇世情语”,张竹坡明确将《金瓶梅》命名为“世情书”。欣欣子序《金瓶梅》说,《金瓶梅》“寄意于时俗”。这种“时俗”正是“世情”的体现。传统的评点法以小说文本为中心,而不是以批评主体的观念为中心,这种批评范式显然不适于近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但是,传统学者的研究中,有许多合理且有效的要素。评点法具有“诗性”特征,评点家往往多有精辟之见。比如,张竹坡等人提出的“世情”这一概念。鲁迅在治小说时,有意识地从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汲取合理、有益的成分。鲁迅在研究《金瓶梅》时,融会了中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他以知识自身的形态和特质为中心,从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确定了《金瓶梅》这部小说在知识统序中的归属,推动了中国小说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变革。
20世纪初期,鲁迅等近现代诸多学人既“知国性之有不尽适”,又“知国性之有不可蔑”。[5]在建构近现代的小说研究构架时,鲁迅充分融会了中国传统的治学要素和学术理路,承续了中国传统学人有关《金瓶梅》的论述,同时也有意识地采用“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比较学的等等”[6],这些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中,就包括西方学界在从事文学研究时惯常使用的方法——流派研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融贯中西方小说的研究方法,他将西方学界常用的思潮研究、流派研究与中国传统学人提出的“世情书”这一特定概念融会于一体,将《金瓶梅》归于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书”一类。这是鲁迅对《金瓶梅》给予的精准的定位。
三
鲁迅不仅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源流变迁,关注《金瓶梅》在小说流变史上的定位,而且还对《金瓶梅》作为“世情书”的内在特质进行了剖析。鲁迅在确定《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流派归属的同时,从多个角度、从各层级上总结、归纳《金瓶梅》等“世情书”的性质和特征。这种归结和总结,是鲁迅等近现代学人在20世纪初期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鲁迅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长篇白话小说的统序,以讲史、神魔小说等类型为参照系,阐明了《金瓶梅》等人情小说的基本特点。他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以神魔小说为参照系,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的序列上,《金瓶梅》等人情小说是与讲史、神魔小说处于共同的统系之内,它们之间是平行、并列的关系。从时间上看,《金瓶梅》等人情小说与神魔小说的盛行,在时间上大体是同步的。从渊源上看,人情小说源于宋代的市人小说。“世情书”作为一种特定的小说类型,它们讲述的内容“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从题材上,人情小说“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人情小说正是指这类小说着眼于现实和现世,它与神魔小说超出日常生活逻辑的书写方式形成了根本的区别。
鲁迅在“人情小说”这一构架下,进一步确认了《金瓶梅》与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多层次的关联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的流程中,指明了《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内在一致性,高扬了《金瓶梅》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清楚地厘定“人情小说”这一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特定的类型模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的流变中研究《金瓶梅》时,他不仅关注《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正向关联,他还关注这些类型相同的小说彼此之间的差异。鲁迅谈到明代的《金瓶梅》、《玉娇李》等小说,将之归为“讲世情的”;谈到清代的《红楼梦》等,鲁迅将之归为“人情派”。从鲁迅的归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情小说”是一个总集的概念。“人情小说”涵括了世情书等情色文学作品、才子佳人小说等言情作品,以及《红楼梦》等。与《金瓶梅》等作品相比,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是,“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红楼梦》的特点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在人情小说这一统序中,“世情书”《金瓶梅》更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特质。“世情”关注人性,强调的是人与人在沟通过程中展现出的本性,强调的是人如何受到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其他个体的影响;而“人情”则关注人的存在本身,人从某种本性出发,如何去探察世界、了解世界、面对世界。此外,“世情”暗含着对世事炎凉、世道人心的褒贬,而“人情”一词则更偏于中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这部书的特点是,它“尽管写社会上的罪恶,作者对人性的兴趣其实更大”。[7](P98)《金瓶梅》不仅仅关注“社会上的罪恶”,更关注“罪恶”的根源——“人性”本身。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还进一步在“世情书”的内在统系之中,思考《金瓶梅》这部书在小说史、在人情小说史、在“世情书”的统系中特有的价值与意义,探究《金瓶梅》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范例的内在原因。
鲁迅梳理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书的统系。他说,世情书中还有《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等《金瓶梅》的续书。在“世情书”的统系之内,《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叙述技巧、叙事结构等方面都自有其特点: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鲁迅还谈到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他说,《金瓶梅》着力于描写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作者的笔锋所向并不是“淫夫荡妇”,而是指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些人可能来自于市井,也可能是世家缙绅,也可能是权贵豪族,也可能是儒林文士。鲁迅还说,《金瓶梅》并不是仅仅写市井间的不良情态,而是以西门庆一家为切入点,“骂尽诸色”,展现了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相较之下,“世情书”中《玉娇李》已经散佚。《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续金瓶梅》将儒、佛、道混同于一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
鲁迅还客观、冷静地论及《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恶谥”——“淫书”的问题。鲁迅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金瓶梅》被视为“淫书”,受到歧视,甚至成为低级、下流的代名词。鲁迅说,“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8](P403)《金瓶梅》自问世以来,世人对这部书褒贬不一。《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十年后,郑振铎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仍反复强调“不要怕”《金瓶梅》“是一部淫书”。郑振铎的劝导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金瓶梅》遭时人唾弃的境遇。鲁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他坚持破除俗见的拘囿,将《金瓶梅》置放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流程之中。他深入到文本、文本的传播、文本生成之时的社会风习等多个层面上探讨这部作品被视为“淫书”的原因。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我们可以看到,《金瓶梅》小说史、人情小说、世情书等不同的层级上展现的意义与价值。鲁迅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正体现出近现代学者治小说时,对传统的突破,即由关注书籍、关注作者,转向关注知识要素自身的特点,在知识要素建构的统序中探究其中多重的、复杂的关联关系。
四
确立小说的独立地位,将小说作为文学学科研究的核心要素,这并非鲁迅独自一人所能力行。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般厚重、精深,开拓学术新范式者,为数不多。阿英谈到《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的小说,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了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9](P12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确立了《金瓶梅》研究的基本路向,建构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鲁迅之能如此,其原因有三。
一是鲁迅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中国小说史略》的成书过程不长,却影响深远,这正是厚积薄发的结果。“鲁迅治学从根本做起,注重辑佚和考据”,[10](P91)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前,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辑录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辑佚并不是随机地、毫无目的地收录作品,辑佚要求学者具有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也要求学者具有宏观把握分析的能力。黄霖将传统小说研究方法分为目录型研究、注释型研究、辨伪型研究、汇辑型研究等四类。他谈到,在从事汇辑型研究时,“汇集者选什么?从什么角度选?用什么标准选?这自始至终都是在一定的小说观点和研究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更何况有的汇集者还要对入选作品予以一定的校勘和整理”。[11](P4)鲁迅对古小说的辑佚工作正延续和拓展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对书籍的辑佚“自唐陈翰的《异闻集》,特别是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后,历来对于小说的汇集都比较重视,……到清代,小说的辑佚随着整个辑佚工作的繁荣而受人注目。其中如马国翰的规模宏大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就收罗了相当数量的古小说。后来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又把这一工作推向成熟”。[11](P6)鲁迅的研究工作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他对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流程自是了然于胸。因此,虽然“鲁迅真正全力以赴从事小说史研究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从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讲课,到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满打满算,也还不到四年”,[12](P28)但是,《中国小说史略》却具备了“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的特色。[13](P709)
二是鲁迅“承清学而又不为清学所囿”。现代学术研究不能离开传统而独立存在,但却也并非是对过去原封不动的承袭,鲁迅的治学沿着传统的路向展开。如,关于史料考辨工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同代人的研究成果(如胡适、孟森、王国维、罗振玉、吴梅、俞平伯、钱静方、蒋瑞藻等),全都局限于史料考辨;此后十几年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着眼点仍是史料考辨。鲁迅重考据,但不重一般意义上的‘考据家’”,[10](P91)从整体来看,鲁迅超越了传统的考据学。另外,关于辑佚的方法。鲁迅将治经史常用的辑佚方法施之于小说研究,“从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到黄奭的《子史钩沉》,再到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佚考证的对象随学术思潮与价值观念的转变而转变”。[10](P91)鲁迅用传统治经、史的方法辑佚小说,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三是鲁迅确立了现代化的学术表达范式。在传统学术中,因受到教育普及程度、印刷技术等的限制,以及知识的数量等影响,传统学术特点是,留存知识与建立知识谱系融汇为一。近现代以来,随着知识的迅猛增长,留存知识与建立知识谱系分为不同的路向。鲁迅等学人以传统的留存知识的方式来留存知识,以系统的学术论著建立知识谱系。在治学时,鲁迅果断地将“史料”单独归类,完成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鲁迅着意于表达“史识”,建构独立的知识谱系。《中国小说史略》以时序为基本框架,察源辨流,梳理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的规律,并对中国古代小说流派进行了精准的分类。相比之下,与鲁迅同时代的学者,如胡适等,则擅长使用传统治“史料”的路数,多辨订,多考据,将留存知识、建立知识谱系混为一体。
《中国小说史略》之能成其厚重,正源于鲁迅对传统治学方式的深入领会;《中国小说史略》之能成其精深,正源于鲁迅融会西学,扬旧学之优长,改旧学之流弊,在学术研究上自成一家。鲁迅在研究《金瓶梅》等小说时,同样如此。鲁迅承继传统的治学路向,如考据的严密、小说评点派的精辟,吸收其优长,再融以现代的科学方法,推进了《金瓶梅》研究的现代化历程。
[1]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钱基博.今日之国学论[J].国光,1929,(1).
[6]顾农.《中国小说史略》导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2, (1).
[7]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M].台北:时报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85.
[8]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A].鲁迅.坟热风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9]阿英.小说四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A].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12]陈平原.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A].陈平原.掬水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3]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A].胡适文集(第3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张吉兵
I207.41
A
1003-8078(2015)05-0028-05
2015-05-20
10.3969/j.issn.1003-8078.2015.05.08
陈娟(1976-),女,湖北公安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王炜(1973-),女,河南南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