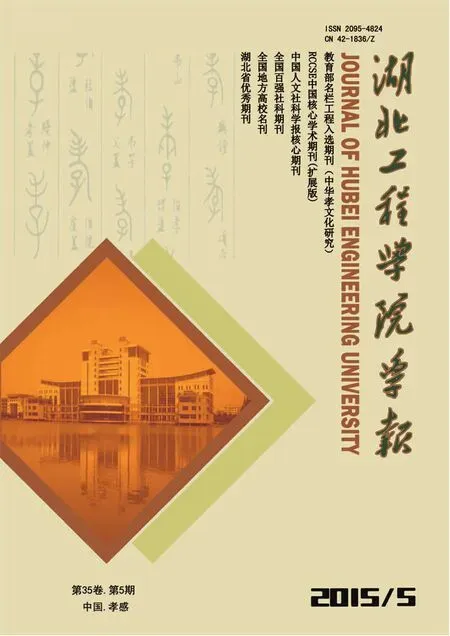当代政治文化视域中的二元对立叙事及其文本的经典化走向
2015-03-27周水涛
周水涛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当代政治文化视域中的二元对立叙事及其文本的经典化走向
周水涛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当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决定了部分文本特定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方式。尽管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十七年”的话语体系影响着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在“十七年”,特定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政治价值诉求决定了特殊的文学经典阐释及认定偏好。在1979-1985年,反思历史和拥戴新政的二元对立结构文本大量出现,并很快被纳入经典化轨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阐释或演绎新老政治元话语的文本和“类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文本受到高度关注,很多文本进入经典化视域。总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导、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不同文学资源在特定范畴内的通约等因素,决定影响着二元对立文本的经典化走向。
二元对立;元话语;思想资源;经典化
二元对立叙事,是叙事文学的基本叙事方式之一。当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元话语决定了部分作品特定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这些文本的经典化走向。
一、二元对立叙事的特定政治文化支撑
在当代中国的部分二元对立叙事文本中,敌/我、新/旧、好/坏、进步/落后、公/私、传统/现代等属性两两相对的范畴(或“元”)发生冲突,二元冲突构建文本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不同的二元对立,有不同的思想文化支撑。其中,有一种二元对立叙事是由特定的政治文化支撑的。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内涵。
在“十七年”,这种特定政治文化的主要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具体政治目标的结合体。特定的政治内涵蕴含在特定的政治元话语中。“十七年”政治元话语包含的话语基本范畴有: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认识法则,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驱动论,社会演进的劳动人民动力论,暴力革命与被压迫阶级抗争的内在关联理论,等等。特殊的政治语境使这些话语范畴成为对社会思维发挥宏观导向作用的哲学范畴,具有特定逻辑推导过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便应运而生了。这种特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直接决定了“十七年”的二元对立叙事的生成。例如,敌我较量、穷富对立、新旧抗衡是相关政治元话语的隐形体现或折射,某些“元”被先验地进行政治价值定位,如贫穷意味着革命或进步,富有意味着罪恶或反动,剥削阶级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劳动人民”则是社会演进的动力,等等。
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定的政治元话语继续生成特定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十一大和十二大的相关精神是特定的叙事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左”倾错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话语范畴决定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进入90年代之后,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先后出现了“深化改革”、“关注三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反腐倡廉”等话语,与之对应的二元对立叙事也随之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作为思想资源的政治元话语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叙事的关系日趋复杂。首先,有些“经典”话语范畴被继承(如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哲学理论、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等),有些曾被奉为圭臬的话语范畴则被慢慢疏远(如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认识法则,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驱动论等),并最终淡出政治叙事中心。其次,政治元话语叙说重心的“战略转移”使得新时期政治元话语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日趋丰富。例如,“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之类的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政治话语,被打上了鲜明的经济学印记。再次,许多元话语同与之对应的话语范畴的对应关系渐趋模糊,元话语范畴在哲学或方法论层面对二元对立叙事的作用显现出弱化趋势,甚至出现了“泛政治化”的二元对立叙事。例如,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对立、城乡冲突、历史与道德的冲突等非政治性的二元对立叙事有时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从整体上看,政治元话语在两个层面促成了特定的二元对立叙事。一是提供了逻辑思维元素——蕴含“斗争精神”的逻辑思维材料:每一话语范畴在客观上规定了谁与谁发生冲突、怎样冲突,以及“元”的进步性与反动性;二是政治元话语暗示“斗争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层面提供抽象思维方式,而针对既定历史事实和特定现实的元话语则暗示具体的“对立”或冲突。例如,“改革开放”话语决定了锐意改革者与阻扰改革开放的保守人物的斗争,“反腐”话语决定了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的斗争。很明显,二元对立结构具有特殊的“内容”和“形式”。
尽管元话语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在“十七年”确立的话语体系却是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它确定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当然,由政治元话语到文学思维,其间有一个转化过程。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种转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通过媒体宣传、课堂教育、文学批评引导等途径,使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潜移默化地接受一种思想体系,将“元话语”内化为逻辑思维元素和人文精神底蕴;二是将“元话语”具象化为美学-文艺学逻辑话语,并且通过不同方式、途径使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接受并自觉运用这套逻辑话语。李怡认为,这种转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当臧克家、田间、李季等作家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批判”在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时,当艾青等诗人以“新思维”来解读“五四以来中国的诗”时,表明“二元对立思维”已经“真正内化为每一个中国诗人的自觉追求”[1],以阶级论为精髓的元话语已融入包括作家、诗人在内的中国文人的血液。毋庸讳言,政治干预在上述政治元话语转化为文学思维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文学批判运动”是政治干预的典型表现。在新时期,刚性的政治干预不再起主导作用,但柔性的政治诱导与政治介入仍然影响着新老元话语的转化。这种转化规范着二元对立叙事文本的产生及其经典化。
二、二元对立结构文本的生产及其经典化走向
何谓“经典”?在此,笔者对“经典”给出一个宽泛的界定:文学“经典”是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曾经具有或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人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经常当作参照系或标杆的文学作品。很显然,笔者所指的“经典”即人们常说的在文学史上留下印痕的“文学史经典”,而非思想艺术两方面均有极高造诣、经过历史淘洗、能被不同时代读者接受的“文学经典”。笔者所说的文本经典化,是指文学文本通过文学批评及选辑、改编、授奖等途径而凸显其思想艺术成就与特殊价值而最终获得经典名号的过程。
特殊的思想资源与特定的语境,在决定特殊的二元对立文本结构之际,也决定了二元对立结构文本的大量产出及其在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在此,我们分三个时段讨论当代中国二元对立结构文本的产出及其经典化走向。
1.“十七年”二元对立结构文本的产出及其经典化走向。毋庸赘言,“十七年”是演绎特定政治文化元话语的时代,二元对立是当时叙事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方式。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两种路线的斗争、人与自然的抗争、新旧思想的冲突,是当时文学文本二元对立的主要范式。当然,“二元对立”是文本内在的逻辑框架,是具体思想资源艺术化的推导过程,因为,或演绎历史结论,或盛赞当下现实盛景,或发表历史预判,其最终目的是要得出特定的逻辑结论,如肯定已有政治行为的合理性,申说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证明发展走向的正确性等。在此阶段,因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享同一思想资源,所以特定的政治文化在决定特定的创作模式之际,也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方式,继而决定了经典的认定与遴选,亦即特定政治文化视域中的政治价值诉求决定了特殊的文学经典阐释及认定偏好:“优秀作品”的遴选对象主要是二元对立叙事的文本,而在二元对立叙事的文本中又特别重视在阶级或路线层面设定“二元”的文本。
翻检在“十七年”受到普遍好评或认可度较高的叙事文本,我们会发现主要是“阶级对立”的二元对立结构的文本。《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等描写人性人情的作品,不仅不能进入经典化的视野,而且还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即便像《百合花》之类展示“军民团结”(茅盾语)的作品,也因没有反映“重大题材”而只能被列入次一等的“优秀作品”。而那些展示两条路线斗争或阶级斗争的文本,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则得到极高的评价,并迅速进入经典化的视域。例如,《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 年9月出版)在出版后一年时间内,仅发表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就有50多篇,大多数文章都认为“它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伟大变革”,“它反映广阔农村生活的深刻程度,简直是无与伦比的”。[2]《创业史》虽然引起了论争,但批评家们仅仅在局部问题上看法不一,大家对小说所展示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都给予了肯定,换言之,大家高度肯定小说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例如,严家炎指出主要人物梁生宝的“三不足”时,充分肯定梁三老汉在阶级斗争描写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梁三老汉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3]《青春之歌》之类文本虽然没有直接展示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但作品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阶级矛盾,更重要的是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选择,歌颂了共产党的伟大。作品虽然引发论争,但论争的焦点仅限定在林道静形象的塑造、如何评价余永泽、作者修改文本的得失等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文本隐在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诱发人们注意,引发论争及最终赢得好评,成为“文学史经典”。
演绎“阶级对立”的文学文本受到重视,意味着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被“轻视”。“十七年”文学文本的经典化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不演绎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文本不被看好。例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洞箫横吹》、《赖大嫂》等文本,其基本架构是二元对立的,也展示了矛盾冲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展示的是“进步力量”与“消极力量”的斗争,《洞箫横吹》揭示的是“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和革命干群的斗争,《赖大嫂》展示的是损公利己、自私自利的小农思想与新时代的矛盾——很显然,这些矛盾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完全是特定时代政治元话语的折射,这些矛盾冲突的逻辑结论并非直接在政治文化层面上肯定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不可能进入经典化的视域。二是直接或间接展示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二元对立结构文学文本受到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红日》、《红岩》、《创业史》、《艳阳天》等直接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无疑会受到热捧。人与自然抗争的文本(如《耕耘记》)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文本(如《不能走那条路》等),如若涉及“党的领导”与路线之争,一般会受到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并很快进入经典化视野。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作品(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都具有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因而自然会进入经典阐释的视野,但由于在这些作品中民族斗争居于首要地位,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被置于次要位置,所以这些文本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顶级经典”,因此,这些文本在“十七年”的影响及受到的关注、得到的好评,远远不及《红日》、《红岩》等描写阶级斗争的文本。在后来人们认定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八部经典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集中描写民族斗争的。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将二元对立结构作品作为经典遴选的主要对象,并对其中部分文学文本进行经典阐释的同时,还从二元对立视角出发,对前代经典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或认定。例如,从阶级论角度解读《红楼梦》的“革命红学”受到官方肯定,在阶级斗争层面阐释“官逼民反”的历史剧《逼上梁山》受到领袖赞美。
“文革”期间,在极左政治潮流涌动的语境中,文学批评对二元对立叙事文本的青睐逐渐演变为病态的嗜好。我们不得不指出,“文革文学”是一种经典匮乏的文学,因此,我们在此对“文革”文学经典化问题略而不谈。
2.1979-1985年二元对立叙事文本的产出及其经典化走向。进入新时期之后,二元对立叙事文本仍然是经典遴选的重要选择对象,但由于政治元话语内容发生了改变,经典文本遴选的倾向也随着变化。政治元话语内容的变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部分话语内涵。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国通过)为代表的一批“历史性”文件对已有元话语进行了修订,如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纲领性的口号,否定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纲领相关的话语体系;对过往的历史作了新的阐释等。二是增添新的话语内容——核心语句是“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元话语内容的调整并未改变“十七年”话语体系原有的叙事指向,但确立了两个新的言说基点:“反思”历史和拥戴新政。由于思想文化资源的相对单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的同源、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基于这两个言说基点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受到追捧。
基于第一个元话语言说基点(“反思”历史),揭示“文革”伤痛和批判“四人帮”的叙事文本得到了高度评价,如《班主任》、《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文本中的“二元”分别是“四人帮”的代理人和“受迫害”的人(包括干部、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根据新的话语资源,批评家们从不同角度阐释这些文本的经典性。例如,沙汀认为《芙蓉镇》是“反映在‘四人帮’阵阵妖风横扫下四川农村生活的佳作”[4],张炯充分肯定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思想价值与美学价值,认为其价值在于:不是正面展示政治斗争,而是通过一个老农的生活波澜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变化,揭示了一场内乱“给农村人物关系带来的投影”。[5]文学评奖,既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或途径,也是“初步”经典化的结果,而每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学奖”则是新时期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正是由于批评家们从第一个元话语言说基点出发,对揭示“文革”伤痛和批判“四人帮”叙事文本内在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高度认同,在1982年举行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展示政治斗争的作品获奖,且排名靠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获“茅盾文学奖”的六部长篇皆为二元对立结构的叙事文本。
基于第二个元话语言说基点(拥戴新政),关注改革发展的“改革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也备受人们的青睐。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腊月·正月》、《燕赵悲歌》、《新星》等。这些作品中的“二元”的构成比较庞杂。代表正义、进步的“元”,其构成相对单纯,主要是锐意“改革”的弄潮儿或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而代表落伍、落后或反动的“元”,其构成则比较复杂:既有“四人帮”残渣余孽,又有新时代的堕落者,更多的是身处时代大潮中的观望徘徊者和护卫眼前利益的保守主义者,如阻挠改革、谋一己私利的冀申(《乔厂长上任记》)、顾荣(《新星》),因留恋旧有经济文化秩序而压制乡村新兴生产力的韩玄子(《腊月·正月》),品格败坏、破坏改革的丁晓(《花园街五号》)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二元对立结构文本更形象地演绎了主流话语。总的说来,文学批评界对“改革文学”的关注程度不及“伤痕文学”,但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如“改革”话语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精英群体与主流意识的亲密媾合所致的精英群体对“改革”话语的高度认同,社会信息传播效率的快速提高以致文学作品经典化途径的增多等),二元对立叙事文本被经典化的速度更快,成为“文学史经典”的文本也比较多。《沉重的翅膀》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排名第一,《乔厂长上任记》、《腊月·正月》、《燕赵悲歌》、《新星》、《花园街五号》等文本,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被改编成了影视剧。
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主要途径,而影视改编、评奖、收入选本、列为大学文学课程的重要讲授篇目等,既是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又是经典化的结果。纵观上述两类文本的“受关注史”,我们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有一大批作品被遴选出来,先后获得不同的奖项,被改编为影视剧,收入不同的选集,被确定为高校课堂的重点讲授篇目,有些篇目甚至进入中学语文教材。随后,这些文本继续受到关注和好评;经过短期的过滤与淘洗,至今仍然有数量可观的篇目保留在经典化的视域中——这些作品至少可以暂时被视为“文学史经典”。
简言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基于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仍然是经典化的重要对象。
3.80年代中期之后二元对立结构文本的产出及其经典化走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创作资源与文学批评资源的多元化以及当代文学“一元化”格局的消解,在“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多种文学浪潮的冲击下,基于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的产出量及其影响力逐步变小,但关联特定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元素融入了不同类型的叙事文本中。与此同时,“二元对立”也作为一种逻辑思维元素融入了当时的文学批评逻辑体系中。因此,文学批评对二元对立叙事作品的兴趣并未消退。笔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批评主要对两类文本给予高度关注,并将其中部分文本纳入经典化视域。
第一类是阐释或演绎新老政治元话语的文本。
众所周知,主流意识形态的元话语在不断更新。例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等“反腐”话语,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阐释或演绎新老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不断问世,而这些文本也被文学批评界所关注。《第二个太阳》( 刘白羽)、《浴血罗霄》( 肖克)、《战争和人》(王火)等文本,它们承续了《红日》、《保卫延安》等“红色经典”的余绪,因而受到高度关注;《骚动之秋》(刘玉民)等文本,拓展了《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改革文学”的创作思路,也赢得了好评;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等基于“反腐”话语的文本井喷般地涌现,并引发热评。上述几种作品被不断纳入经典化视域。《第二个太阳》、《骚动之秋》、《战争和人》、《抉择》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等涉及“反腐”题材的文本被多种“选本”选入,部分作品被改变为影视剧,并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第二类是“类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文本。这类叙事结构并非依傍政治元话语而生成,并不将阐释政治话语作为全部的创作指向,但与主流政治话语有着一定的亲和性。“类二元对立叙事结构”的思想依托多元化,叙事指向不一,文体多样。这类文本中的两个亚类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及好评。
第一个亚类是容纳或隐含特定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这些文本不以阶级对立、民族冲突、进步与落后斗争等“对立叙事”建构文本主干,但阶级对立等冲突模式作为叙事元素隐含在文本中,这些特殊的叙事元素从侧面阐释或演绎了政治元话语。《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父亲进城》(石钟山)、《亮剑》(都梁)、《父亲是个兵》(邓一光)、《我是太阳》(邓一光)、《英雄无语》(项小米)等是这类文本的代表作。这些文本一般以“革命英雄主义”男性的传奇人生为叙事中轴,顺带展示国共两党之争或民族冲突,歌颂共产党的光辉业绩和革命领袖的伟大。例如,《父亲进城》在叙述父亲的传奇人生及近于荒唐爱情经历时,展示了国共两党之争,赞美了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展现了国民党的溃败。文本中出现了这样的议论:“中国伟人毛泽东远见卓识,早就派出了中共传奇将领林彪深入到东北指挥作战。争争夺夺拼拼杀杀之后,解放军滚雪球似的壮大了起来,在中国伟人们的调度下,东北打响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从这段议论中不难看出,文本的政治立场鲜明,是非判断明确。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文本既受到主流意识的欢迎,又受到精英群体的热捧,还颇受出版商或市场青睐。因此,这类文本被迅速纳入经典化的轨道。例如,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直接或间接评论这一小说的文章多达百篇,这部小说先后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首届“最佳优秀作品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十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后来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同名电视剧又获得“飞天奖”等多个重要文艺奖项。
“类二元对立叙事结构”的第二个亚类是关联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这类文本的二元对立虽然不在政治层面上展开,但它们以不同方式隐射、依托政治元话语。例如,“劳工”与资本的对立、乡村与城市的抵牾、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常见的文本结构类型,其中有很多文本立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展示经济冲突,以阶级论解读阶层对立或贫富差距。这类文本构成一个庞大的“族群”,其中一个创作分支受到批评界的关注。这一创作分支的思想倾向是:因怀念过去的某种“元价值意识”而质疑拒斥当下的价值意识。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内当家》等作品是这个创作分支的滥觞。卢万成的《内当家之死》,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问苍茫》,刘继明的《茶叶鸡蛋》、《小米》等,是这类文本的代表作。在《那儿》、《问苍茫》等文本中,曾经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如今沦为底层贱民,处境可悲,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资本权力再度横行的愤怒,倾诉了因共产主义幸福彼岸(“那儿”)渐行渐远的悲愤。这类作品一直受到精英群体的关注,一直让评论界激动、兴奋。从《内当家》到《那儿》,这类文本在受到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批评界的争鸣。《那儿》等文本的价值立场成为批评界争鸣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新左翼文学”的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与《那儿》等文本也不无关系。但论争归论争,批评界对这类文本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这类文本很快进入经典化视野,而且有可能进入“文学史经典”的行列。
总之,从“十七年”到90年代,基于政治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一直受到青睐,这些文本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处于特殊位置。
三、余论:当代叙事文学经典遴选偏好的主要成因
我们在前面讨论二元对立叙事的形成时,也讨论了二元对立叙事文本受到青睐的原因,但有些原因需要在此特别强调,故特立一节进行讨论。我们认为,特定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大量进入文学经典化视域,有三大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层面决定了特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促成了经典遴选者的特殊嗜好。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个层面决定了包括当代作家、批评家在内的中国文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宏观层面确立了中国文人的“矛盾”思维方式。从事物的矛盾角度切入看待问题、对“矛盾”的敏感、用“矛盾法则”解决现实问题,是这种“矛盾”思维方式的主要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中国文人身上发生作用的最突出表现。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微观的思维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之后,建构了特定的逻辑思维元素,进而决定了中国文人处理具体问题、看待当下现实的方式方法。例如,中国阶级斗争现实或阶级斗争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结合而生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本质属性认定学说及阶级斗争规律理念,中国本土革命理想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结合而生成的斗争泛化思想,等等,这些思维元素既给了批评家发现“二元对立”的眼睛,又为批评家提供了从事“二元对立分析”的工具。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作为一种逻辑基因深植中国文人的思想精髓,影响了中国几代文人的思维,因此依傍元话语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大量进入文学经典化视域,而且在经典化过程中备受青睐。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影响着二元对立叙事文本的经典化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
一是强制性规约。这种规范方式主要出现在“十七年”。其具体运作有两种形式:(1)以政治性的文学批评/批判从反面指出哪些作品不好,哪些作品是毒草而不是经典,如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2)通过权威理论家、批评家,指出哪些文本优秀,具有哪些经典质素。例如,茅盾、郭沫若、周扬、何其芳、陈荒煤等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们的文学批评文章直接影响着作品的经典化走向;而 “某某研究小组”、“某某评论组”、“某某编写组”等集体署名的文学批评文章或著作,更直接表达了主流意识的经典遴选愿望。进入新时期之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倡文艺“二为方向”等言行,也具有一定强制性规约意味。强制性规约直接影响着文本经典化的方向及最终结果。例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文本在“十七年”就被认定为典范性的名作,进入新时期后,当有人将这些文本冠以“红色经典”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些现象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规约有着直接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文本成为“经典”,就是强制性规约的结果。
二是诱导性规范。与强制性规约的刚性介入不同,诱导性规范主要通过审美观念提倡、文学表彰、文学评奖等柔性方式干预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与结果。其中,文学评奖对经典生成的影响最大。现行的文学评奖在两个层面影响文学经典化的走向及结果。首先,引导批评界确立某种隐含特定政治诉求的“佳作”考评标准,使之将其作为核心标准去遴选获奖对象。这一行为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向社会推广了一种经典认定标准,又使获奖文本成为“经典典范”,为随后的经典遴选提供比照蓝本。——在新时期,许多小说奖项的评奖都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经典”的遴选。其次,是设立文艺奖,依据特定标准直接确定“精品”。事实表明,“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官方或半官方的“文艺奖”,其正统性与权威性已经使许多获奖文本成为有较大认可度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文艺奖”的正统性与权威性激发、强化了作家的“获奖意识”,而作家的“获奖意识”反过来又赋予“特定标准”合法性、权威性及认可度,使之成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经典认定标准,从而导致更多类似文本进入当下经典化视域。
第三,两种文学资源的通约强化了批评家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选择嗜好。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由多种思想资源支撑,其中,毛泽东思想和“五四”精神,是主要思想资源。毛泽东思想与“五四”精神的交集之一是“反封建”,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与批评家而言,两种文学资源在反封建这一界域内通约。这种通约产生了两种具有因果关联的文学效应:(1)大量二元对立叙事文本同时接受两种思想资源的支撑,同时从阶级论和反封建两个视角建构文本,于是,从毛泽东思想出发的二元对立(如阶级斗争、新旧观念冲突)与从五四精神出发的二元对立(如专制与民主之争、文明与愚昧对立),形成了同构与“互文”;(2)因此,大量文本既可以从当代政治元话语角度进行解读,又可以从五四文学精神角度进行评判,具有同构与“互文”属性的文本既让精英群体乐于接受,又强化了精英批评家的二元对立叙事文本选择嗜好。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格局消失之后,许多演绎政治元话语的文本仍被精英群体看好,从而被迅速纳入经典化轨道。
[1] 李怡.20世纪50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中国新诗世纪回顾的一个重要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5):141-160.
[2] 於可训,吴济时,陈美兰.文学风雨四十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54.
[3]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J].文学评论,1961(3):63-69.
[4] 周扬,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J].文艺报,1980(4):14.
[5] 张炯.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55-60.
(责任编辑:李天喜)
The Binary-narrative Text and Its Classical Changing Tendency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Zhou Shuitao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HubeiEngineering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000,China)
The specific political culture determines the specific binary-narrative structure of some texts. Despite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the “seventeen years” discourse system is still affecting the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the political value of particular political philosophy determined the spe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dentification preference of literary classics. From 1979 to 1985, many binary-narrative texts which reflected on the history and supported the new ideas appeared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classics soon.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80s, the texts which interprete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texts of “Classis Binary-narrative Structur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nd were included in the classics very soon. All in all, the binary-narrative texts’ classical changing tendency is determined by the guide of the Marxist methodology,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mensuration of different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specific areas.
binary; meta discourse;thought resources;classical change
2015-08-06
湖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3D103)
周水涛(1956- ),男,湖北天门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I106
A
2095-4824(2015)05-004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