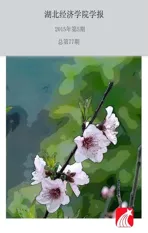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伦理动因探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读
2015-03-27赵亮
赵 亮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91)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是近代以来诸多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一书中,马克斯·韦伯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必然性。这也就是学界所谓的“韦伯命题”①的由来和内涵所在。从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意义上说,韦伯命题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二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发生?三是怎样才能发展资本主义?[1]对此,韦伯遵循历史的、逻辑的方法,通过对路德教派天职观和加尔文宗预定论的考察,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伦理动因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展示了新教伦理所特有的经济社会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何以源起于西方
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是《新教伦理》一书的主旨所在。韦伯在开篇引言中通过对中西方文明的对比,盛赞了西方在科学、政治体制和文化方面所达到的较高发展程度。他毫不讳言西方文明所具有的优越性,并明确指出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就是“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即“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2](P14)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古已有之,这是“世间所有时期、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会有的,人们的活动目的从根本上说无一不是指向利益。从原初形式来看,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与西方资本主义本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客观上促使西方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通过中西方之间这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对比,韦伯顺势提出了问题:在这种获利欲望的驱动之下,为何中国和印度不能同样走上这种西方独有的理性化道路呢?很显然,各种物质技术、规章制度等都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2](P16)并把这种“理性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韦伯认为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资本主义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有理性的”,②[2](P7-8)正因为这种对理性化的诉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与以往时期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
这一特点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理性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全面掌控。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根据这种新的 “经济理性主义”组织的经济活动。不仅如此,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部分以及文化的所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种理性化,理性主义已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理性主义驱使之下,把赚钱盈利视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同时节制各种非理性的欲望享乐,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最具实质性的内涵所在。
韦伯注意到了广泛存在于西欧商界和企业界的新教教徒现象,证实了社会分层与宗教伦理信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他通过考察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和在现代工业里的不同身份是由生活和居住环境中的宗教因素潜移默化所造成的。此外,根据宗教少数派群体在社会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特质比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强化了宗教因素对于一定群体的行为的影响作用。对于新教教徒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韦伯认为,“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2](P37)
韦伯所言的“这些精神”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在资本主义生成的过程中,追求财富的内在动力并没有与获有财富而尽情享受现世生活相结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韦伯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新教的理性伦理观念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加尔文宗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和预定救赎论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在以后的篇章中,韦伯对这些新教伦理观念作了历史的逻辑的的考察,以求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与这种独特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
二、路德“天职”观:时代价值与局限
(一)“天职”概念的缘起
我们现在所广泛称为的“新教”,常被用来指称16世纪以来兴起的“那些不接受教皇权威的西方基督教形式”,[3]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新教派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韦伯认为,早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前,天职(Beruf)一词的观念就已存在,只不过当时被译为“职业、职务”的形式。在这里,“天”无疑指代神圣的上帝,作为一种宗教观念,这是指上帝交付给人类的任务,体现为对“上帝的召唤”的积极响应。后来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根据需要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意志,明确把“天职”的概念提出来,将上帝的神圣意旨与普通人的世俗职责相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天职观,并用以宣扬自己的宗教改革理念。
在这一重新解构的过程中,路德成功实现了“天职”观念的两个转向:一是受职主体的大众化,把中世纪只有罗马教会神职人员所拥有的天职转变扩大为普通大众所共有;二是职责内容的世俗化,使“天职”逐渐剥离虚幻的神性色彩,实现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俗生活相联系。这两种转向实现了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赋予“天职”以积极的现实意义,使之广为教徒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 ”[2](P76)“天职”观正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考察的源头,并进而考察了世俗活动中的新教理性行为。
(二)劳动是“天职”观的核心内容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体力劳动是持一种轻视的态度。而实际上从古代犹太教的“旧约”时代起,基督教就已开始了其世俗化的历程,早期的基督徒们对待劳动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劳动和工作为尊贵且讨上帝喜悦”的,[4]不仅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并且认为劳动是一种有尊严和高贵的行为。到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真正具有了革命化的特征。在韦伯看来,作为宗教改革的成果,路德的最大贡献即是确定了劳动在“天职”中的核心地位,肯定了世人“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相比于天主教的态度,宗教改革的影响只是使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2](P79)与天主教传统观念告诫人们“安分守己”、超越世俗生活相对照,路德的宗教改革则为世俗活动进行了道德上的辩护,使世俗劳动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神圣职责世俗化、世俗劳动神圣化,神性与世俗在履行天职的劳动这里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完美契合点。
韦伯还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不同技术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分析,阐述了他对于劳动的具体看法。他认为,“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2](P30)这表明,由于受到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不同群体和个人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也会有不同。与所信仰宗教的教义结合起来看,这种不同职业的选择无疑体现着上帝的意志,都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要求认真去履行这一职责。路德“把工作视为不仅讨上帝喜悦更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呼召(天职)”,这种工作概念的革命性转变在于使工作的意义从 “什么”、“怎样”转向“为什么”。[4]早期的基督徒把工作本身视为人生的目的,而路德更突出强调工作的目的指向和意义指向,认为工作是人本身的一种职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荣耀上帝和为他人服务的差事。很显然,在路德看来,人所从事的是何种具体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该职业应尽职尽责的意义。既然所有工作都是作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而存在,那么工作就没有好坏和优劣之分,“所有正当类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5]
此外,韦伯还通过结合富兰克林对于金钱的道德劝诫,深刻形象地阐明了遵守天职、合法赚钱的必要性。在富兰克林看来,时间、信誉和金钱本身都是我们进一步赚钱盈利的资本,“除去勤劳节俭,对一个年轻人安身立命最有益处的就是保证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守时和正义的”。[2](P44)当然,在韦伯看来,富兰克林的所言所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伦理”,是“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在现实行为中的具体体现。韦伯指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2](P48-49)勤奋劳动、努力赚钱,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的现实体现。
(三)路德“天职”观的保守局限性
韦伯认为,尽管天职的观念最早被路德引进,但这并不表明路德具有前述富兰克林所拥有的那种同样激进的“精神气质”。③因为就当时的宗教改革者(包括之后的加尔文宗等清教派别)来说,只有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命和工作的中心,各项伦理改革计划也只是从属于并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具体到当时路德所持有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应该一直安分地保持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和天职,并且应该根据已经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动”,他“认为绝对服从神的意志与绝对接受现状是一致
韦伯首先从分析加尔文宗等禁欲主义派别的“预定论”入手来逐步说明问题。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说,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在天主教的传统主义观念中,人是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获得上帝谅解的。随着赎罪券的推行滥用,也孳生了教会的种种腐败行为,这是引致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何才能够获恩得救呢?“预定论”被视为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按照韦伯的分析,“预定论”实际上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内容所构成:一是人在现世的得救与否由上帝“预定”,上帝的“选民”注定得救,“弃民”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二是上帝的预旨神秘不可知,“一切事物,包括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都隐匿于冥冥的奥秘之中,而这是不可能被参透的,也是不容的”。[2](P81)透过这些简要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路德在强调天职的必要性的同时,刻意夸大了天职观中“神的旨意”的重要作用,教导要安于现状、被动适应,显示了其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也表明路德本人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始终是传统主义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按照韦伯的分析,这与路德毕生所从事的牧师职业、赖以解读的文本带有传统主义性质等多种因素有关。
很显然,仅仅依靠路德的天职观并无法全部回答资本主义精神所应具有的全部意义。在韦伯看来,作为一种更具现实价值理念的天职观,是在加尔文宗等禁欲主义各教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三、加尔文宗:预定论与入世禁欲主义的现实演进
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生活在比路德稍晚的一个时期,作为一名思想上更趋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新教理念。与前任改革者相比,加尔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他已有的神学思想为基础,同时融合进了路德的天职观,并将“天职”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信徒确证自我上帝选民身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正如韦伯所指出,“尽管没有路德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宗教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改革在精神层面上长期受到路德个人品格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就不可能拥有持久而具体的成功。”[2](P83)正是由于加尔文的与时俱进,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出现一种创新发展的局面。
(一)作为教理前提的“预定论”
置疑的”;三是“上帝的预旨不可更改”,“上帝已经给予恩典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典,而上帝拒绝给予恩典的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恩典”,[2](P101-102)除此之外,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不难看出,“预定论”带有强烈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色彩。
可以说,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上帝的“预定”主宰着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而这一“永享恩典、永堕地狱”特征鲜明的教义又极度脱离人性,“选民”或“弃民”身份的不同成为其一生人际遭遇的根本区别。因此,这也成为教徒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为上帝所选中呢?“我是上帝的一个选民吗?”[2](P108)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又因关于上帝的不可知论和揣摩“上意”属“不道德行为”而似乎陷入绝境。这也为天职观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入世禁欲主义的提出奠定了教理上的前提。
(二)入世禁欲主义提出的实践必然
作为对于“上帝的选民”问题的解答,加尔文提出了“救赎确认”的两种途径:其一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自信蒙受上帝恩典;其二就是“紧张的世俗活动”。与前一种救赎途径的不确定性相比,后者在现实中“世俗活动可以驱散关于宗教的疑惧,并给予人们蒙恩的确定性”,[2](P164)因易于量化把握而被视为确证救赎的最合适的方法,即以实践中的实际行为验证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
在这里,加尔文把天职观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上帝选民的唯一证据就是现实中的每个人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天职,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而天职完成的好与差取决于世人获得财富的多与寡,“一项天职是否有益并且就此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是依靠道德标准进行衡量,进而就是根据这一天职为‘共同体’所提供财富的重要性来衡量。然而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在现实中也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私人的可营利性”。[2](P164)与路德相信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为他人服务因而给上帝带来荣耀的观念不同,加尔文宗与那些逃离俗世而归隐于修道院的隐修士一样,他们亦否定自身快乐,但认为拥有的财富越多即是受到上帝祝福和挑选的证明,因而把勤奋工作和生活节俭视为获得这一证明的必备途径。选民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天职,通过勤奋劳动集聚大量的财富,这是取悦上帝,“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行为,理应获得救赎。如此看来,要分析说明加尔文的预定论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路德的天职观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意义,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则赋予了职业劳动者以神圣意义。[6]
但是,我们这里要明晓的是,在对于财富问题的态度上,早期基督教派与加尔文宗的实质差异并不在于追求财富本身,而在于拥有财富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方面。早期基督教徒“他们真实的道德异议在于,拥有财富会使人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懒散并沉溺于肉体的享乐,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时精神涣散”。[2](P159)拥有财富“有使人懈怠的危险”,有损于上帝的荣耀,忧心的是一种潜在出现的不良后果,这是前者对财富抱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鉴于此,在韦伯看来,与“恪尽职守”的天职观相结合,加尔文宗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提出了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理念,“这种伦理的‘至善’就是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结合”,[2](P48)获取财富并不是为来用于生活享乐,相反是要身体力行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获取财富仅仅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确证自己“选民”身份的途径和手段。“上帝召唤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而是在履行天职时的理性劳动”,“清教天职观的重点始终在于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条理性”。[2](P163)入世禁欲主义的“理性”就是通过正当的理性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把钱财用于非理性欲望的节制相结合,这样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就是韦伯所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7]这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2](P182)入世禁欲主义的实践发挥最终催生了具有理性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论证了他在开篇提出的那个假设,对此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解答。
四、结语
韦伯以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通过“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这一逻辑进路,证实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亲和性,显示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生成方面的巨大价值。新教伦理从本质上说是作为一种宗教思想而存在。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思想生成并发展出具有理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产生了相应的物质经济形态。这似乎夸大了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然而,这一论断为我们科学认识伦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注 释:
① 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韦伯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的伦理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学者称之为“韦伯命题”。
② 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意味着对资本进行投入—产出的成本核算,以便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追求更多的利益。
③ 在韦伯的论述中,这种“精神气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1]吕东伟.解析韦伯命题及其现实性意义 [J].社会学研究,2000,(5):11-20.
[2][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M].马树林,孙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0.
[4][美]阿尔文·丁·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M].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62-163.
[5][英]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M].杨征宇,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33.
[6]张申娜.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J].学术论坛,2007,(7):23-26.
[7][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