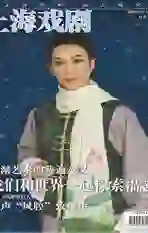围观“戏剧奥林匹克”之困惑
2015-03-26安莹
安莹
2014年12月7日,美国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演出第二场,两名前排观众在演出谢幕时分高声大飙中英文脏话。当晚,京城戏剧人的微信朋友圈一片哗然,有批评国人观众素质的、有心疼大师的、更有表示支持,坦言自己也有此动议只是不敢或出于礼貌没有付诸行动的。一直到事件发生一周后仍有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其实演出遭遇哄场本是寻常,斯特拉文斯基、贝克特都遭遇过愤怒的观众,我国导演孟京辉也曾在阿维尼翁国际戏剧节IN单元作品演出现场边鼓掌边喊中文脏话退场。哄场既不能使佳作蒙垢也不能单纯地判定观众凶猛。作品好不好,时间会给出公论。剧场内打电话、拍照、玩游戏关乎观众素质,而哄场,有时候却是权力。事件发生后,笔者甚至与戏友玩笑,若现场真有愤怒观众与“铁粉”两方大打出手,最终逼得罗伯特·威尔逊越窗而逃,或许还能成就老头儿在古稀之年再火一把,如此才算是一次名实相符的戏剧事件,可以写进戏剧史册。
笔者并不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在各方描述中甚至无法确知喊倒好者喊的是“Get Out”还是英语粗口。个人私见以为,在没有找到喊话者其人(为什么找不到?),未能追问到本人彼时到底因为什么,未能询问罗伯特·威尔逊如何看待这个喊倒好的中国观众的情况下,任何基于臆测的判断及讨论都显得站不住脚,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借题发挥表达的是各方的立场与态度,在笔者看来这是比这次不成其事件的“事件”更值得关注与讨论的。而这需要从邀请《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来京的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谈起。
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在北京举办,来自22个国家的45出剧目先后上演。1941年生人的罗伯特·威尔逊,1939年生人的铃木忠志,1936年生人的尤金尼奥·巴尔巴,以及Google都不能知道生卒年月的特尔佐布罗斯……这些在当代世界剧坛声名显赫的名字不仅密集地出现在北京戏剧人的交谈里,甚至他们本尊也现身北京街头。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戏剧奥林匹克邀请的作品和作者虽然在我们看来都是功成名就、一呼百应的大师,但其实他们也大都是世界戏剧的边缘人。1976年,铃木忠志因小剧场租约到期且厌倦了东京剧场界的商业氛围毅然深入利贺山村,选择在一片处女地上开垦自己的戏剧王国;同年,印度导演拉坦·提亚姆从繁华都市德里回到自己的老家英帕尔,在这个戏剧受众稀缺但民风淳朴的地方,创立了自己的合唱演剧团;意大利裔戏剧人尤金尼奥·巴尔巴旅居北欧,以异国丹麦为基地实践自己的戏剧理念,创立了蜚声国际的欧丁剧团;委员中最为主流的当算留比莫夫,他甚至在获得了国民艺术家冠冕之后仍主动兼被动地选择流亡西欧多年,留比莫夫的许多作品在苏联解体后才重获开禁……戏剧奥林匹克委员名单中的很多人都有着从主流戏剧圈逃逸的经历。幸好,这些作者在出走、垦荒、凭一己之力开山立派之余,并没有固步深山去做彻底的修行人。他们持之以恒地吸纳同道和追随者,与主流戏剧节保持着密切联络、着意传播,在几十年的耕耘之后,他们大多拥有了国家或社团基金会的支持。同时,他们在交流中渐成联盟互为犄角,聚合成了一股独特而相对强大的势力。创立于1994年,由希腊名导特尔佐布罗斯首倡的“戏剧奥林匹克”便是这一股戏剧势力四年一次的集中汇演。与他们相对的,是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是“皇莎”、“NT”、“宝冢”和“四季”,是巨头院团和驻场商业剧。在笔者看来,非主流势力的存在、壮大就如在野党一般,其最大价值是在其与主流戏剧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对双方的自省与更新的促进作用。
去中心化、反商业化的“戏奥”盛会发生在商业戏剧渐成主流的当下中国。北京市文化局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两家联合主办,为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提供了政策面与资金面的主流支持。实话实说,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大手笔请来声名卓著的戏剧大师团,因场次限制到底无力惠及普罗大众,更多还是滋养了戏剧圈内人及近于圈内的资深观众们的见识眼界。这份便宜,身为受惠者不能不暗自偷乐:好多年没这便宜占了!因此上,我和我的戏友们早在“戏奥”开幕前一个月便奔走相告,展开了囤积低价票大作战。欧丁剧团的《盐》等在小剧场演出剧目,更是开票三天就被我辈抢购一空。兜里有票开心过节,期盼着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把北京拉回十年前,带我们回到那个文青占领剧场,不知何谓商业的文艺社会主义年代。
对于大多起于草莽、必须靠着成功卖出一张张戏票来维系作品生命的年轻一代中国戏剧人来讲,“戏奥”汇演不仅是守在家门口的业务学习大好机会,更如灯塔一般给迷雾中求生的他们指引方向:商业毕竟不是创作的终点,交流才是。高规格的“戏奥”为专业二字竖立了标尺,不仅是做戏也是做人,这对于因野蛮开采而日趋沙化的中国戏剧市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反拨作用。当然,赶场看戏不亦乐乎的同时,困惑也不是没有:海面上灯塔太多,到底应该跟着哪位带头大哥走?这是其一;华山论剑后东南西北各回各家,中原武林还是商业带队,贫瘠而残酷,这要小的们熬到哪天是个头?这是其二;大哥们高深莫测,内功心法都非短期可以练成,想要偷师学艺,抄点儿鸡零狗碎的招数蒙混国内观众的愿望频频落空,这算其三;还有四五六七困惑重重……随着“戏奥”进程延绵几十天,困惑无处求解,耐心损耗严重,眼看年关长假即将结束,怎不心焦?就这样,大家等来了罗伯特·威尔逊的《克拉普的最后碟带》的演出。
在并未遭遇哄场的首场演出结束后,尽管许多戏友观摩了演出如鲠在喉,但大家多在社交网络上保持了谨慎的沉默。然而,随着次日哄场事件的发生,吐嘈的声音如门闩开启一般,终于得以大量扑街。近身监督关机的不爽只是情绪的诱因,持续近两月的媚雅活动中积累的太多困惑才是负能量之源。大家是来看大师的,可是,大师在哪呢?
中文“大师”这个词与它被对应的英文单词Master两者内涵外延并不十分相符。Master词源为拉丁文Magister,意旨男教师,再进一步,就是比常人知道多一点的人的意思。现代英语拓展为主人、雇主、老师、信用支付平台等更多义涵。《功夫熊猫》里的Master无非就指师傅,带有一定尊称态度,但也仅此而已,拯救世界的还是阿宝。东方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百度大师词条,孔子像赫然在目。众望所归,孔圣人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资格成为大师的代表人物。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西方思潮涌入,大师一词渐趋流行,艺文界尤其爱给赫赫有名者、成绩斐然者,甚至自己有所了解大众闻所未闻的偏门人物贴上这个标签,似乎从此便有了膜拜依据。很多时候,膜拜大师不过是一种精神不独立的表现。Master也只是比常人多知道那么一点儿的人罢了。尊重老师,但已不用磕头。带着精神依附的惯性围观朝圣,是这样一场大师云集的文化盛事的题内之事,当只看到了一个不过比自己强那么一点儿,甚至没看出强在哪的“大师”时,落差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太想要瞻仰大师风采了。
最晚开票的瑞典小戏《纯粹》上座惨淡,反响寥寥。但于我个人而言,品味一场绵延几十年的鸡肋婚姻关系的结束与开端,令我在看戏走神时构思了一出与此无关的小戏提纲。虽然表演状态的一般不能令它惊艳四座,但这仍旧是一个颇有收获的夜晚。或许,看启发,不拜山头,是治愈戏剧人业务学习焦虑症的一帖良药,而相信自己的审美直觉,则是我作为一名观众时的最好状态。2014年最打动我的一出戏不是在本届“戏剧奥林匹克”上看到的,她是在乌镇上演的韩国独角戏《墙壁里的精灵》。一个叫做金星女的大婶,演出自己丈夫改编执导的作品,把一段苦大仇深的家庭史演得乐观真挚。因为这份真挚,她把我从一个业务学习的戏剧人打回成一名普通观众。平心而论,若讲作品硬水准,《墙壁里的精灵》显然比不上同为独角戏的《克拉普的最后碟带》,但在我的个体判断上,它是一出好戏。所谓文无第二,好戏如是。
说回《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出不知所谓还派头十足的大师作品不是好戏。然而稳下心神,从剧场压暗场灯,“咔嚓嚓”一声音量失控的炸雷开始,超越感官非写实的音效即带我们进入了主人公克拉普病态的唯心世界。掺杂着爆裂声的雨点在最密集的时候很好地拢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前来业务学习的那个我想说:技术尺度绝赞!作为观众的那个我则反驳:表演非常塌台!也有落座在前排的戏友说折服于精心设计的表演细节,可惜,这在我的剧场一楼第14排的80元票区是无从捕捉的,不知二楼怎样。这便是同一座剧场内的我和我的戏友的个体差异,平心静气地说出来,自有反对与认同。
作为个体,当然可以表达罗伯特·威尔逊的表演逊毙了,远远不及他自己训练出来的优秀演员的观点;作为个体,也大可以判定欧丁剧团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国际草台戏班的结论。做观众,我们发声,凭借自己的审美直觉作判断。应该允许无知者代表自己做无知状。因为无知的个体也是个体,而不是乌合之众。由此,我很期待这一次久违了的去中心化、反商业的戏剧节能否提示中国戏剧走出膜拜大师的时代。若建树于此,第六届“戏奥”才真算是值得写入中国戏剧史册的一个事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商业戏剧环境下作为消费者的观众们已经鲜有自卑感,与之难以匹配的是我们的戏剧人显然还不够自信。为何不自信?与哄场事件各方态度反映出来的戏剧圈内外心态相比,真正叫我担心的反而是一些循着赶节上会的常例自顾自地上演着的参展精品剧目。在依靠亲友赠票填满剧场的火爆氛围里,在领掌欢呼一团和气的观演关系中,享受着山大王般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不慎旁观类如此的场面,才不禁替中国戏剧捉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钱与叫嚣都赚不来心悦诚服的尊重。与其不忿名团大导歧视中国观众,控诉国人同辈浸淫文化自卑主义而不自知,与其空怀一腔怒火无可奈何,只得在朋友圈里口诛笔伐,与其如此,不如踏实创作,交出能够与“大师”等量齐观的作品。德国导演迈克尔·塔尔海默、立陶宛导演科索诺瓦斯,他们与特尔佐布罗斯、铃木忠志相比,都是后来者。对于他们的作品,不同的观者看法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立足本民族文化、都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立场及高度。谁说我们就做不到呢?
四年一届的“戏剧奥林匹克”盛会的举办是“理事轮流坐庄制”。因此,下一届盛会注定不会再在中国举办。也就是说,四年之后我们需要派出能够代表中国戏剧实力的作品与作者。不是出战,是交流,某种意义上这比真刀真枪的比赛要更难。奥林匹克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算惨败至少有个重在参与。可是交流呢?先要有个彼此平等你来我往的对等关系。支撑交流的,是作品作者的真实力。开个“大师”工作坊,再来蒙世行那一套,人家观众心里必定说:“什么玩艺儿!”当然,我们还可以送戏曲出国,只要不是新编评奖戏,相信博大精深的中国表演艺术还是很能够折服他者的。然而,当代中国戏剧到底要集体失语到何时?放诸世界舞台,如果我们存在的方式是“不存在”,那么能否成功举办众星云集的世界级的艺术盛会,能否参与到盛会进程中去高价陪跑,似乎也不是那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了。
作为一名中国戏剧从业者,我觉得我们没问题。当然,大家须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