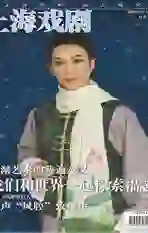张庚论评周信芳
2015-03-26吴乾浩谭志湘
吴乾浩 谭志湘
张庚一生钟情独树一帜的戏曲艺术,在嗣后半个世纪的戏曲研究中,遍及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评论等各个领域,对周信芳的表演艺术有独到精辟的论述与品评。据七卷本《张庚文录》的初步统计就不下二十来处,在张庚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中则有更多的论述。时值周信芳诞辰120周年之际,有必要梳理研究这批有关资料,认识周信芳的表演艺术,重温张庚老师对周信芳,对麒派艺术的评价,是我们认识周信芳,认识麒派的一把金钥匙。
周信芳的表演艺术个性鲜明独特,张庚有细微的观察和透辟的分析。《乌龙院》中,宋江与阎惜娇有一段看绣花鞋面的对白。宋江称赞阎惜娇的绣工:“花儿好,叶儿好,这叫作好,好,好!”阎惜娇让他有点褒贬,宋江道:“颜色不对。”此时阎惜娇变脸:“既知道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呀。”这是一段潜台词非常丰富的对话。张庚认为周信芳饰演的宋江表情语态非常集中洗练(见《戏曲表演问题》)。张庚非常肯定周信芳把戏剧中最重要的地方再三再四加以强调。如《乌龙院》的宋江找书信,从街上到阎惜娇的卧房不多几步路,却演成了一场戏。由此肯定周信芳“充分运用了观众的想象”,“扩大了表演的领域”(见《试论戏曲的艺术规律》)。
1962年,文化部举办了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出活动。张庚看了演出,非常高兴,“兴奋得不能入睡”。看了《打渔杀家》后,张庚“在好几处地方抑制不住感情,甚至泪水都在眼眶中转动起来”。由此他追忆年轻时看周信芳的戏,“看后总感到心弦震动不已。它似乎有一种力量,迫使你进入艺术情境,去关心同情这些人的命运,迫使你不能不被感动”。
周信芳为我们留下来许许多多的舞台艺术形象,让观众难忘,成为京剧舞台上永恒的经典,张庚总结说:由于周信芳“对角色有强烈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并且要把这种态度充分地,不故作矜持地渗透到创作活动中去”,“他的创作是充满激情的,是爱憎分明的。对肖恩的反抗,他是同情,是赞美;对宋士杰的仗义行为,他是歌颂……他热爱他所扮演的正面人物”(见《用全身心演戏的艺术家》)。
张庚明确提出“一个剧种的兴衰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是否出现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大演员,则是一个最突出的标志”,“有大演员剧种就兴旺;无大演员,剧种就衰亡”,“凡称得起大演员的,那么他不仅仅是本剧种艺术的忠诚继承者,同时也是本剧种艺术勇敢的突破者,革新者”。周信芳“可贵的精神,就是不拘泥祖法,不墨守成规的革新创造精神”(见《京剧泰斗丛书·序》)。
周信芳的舞台活动主要在二十世纪中叶。二十世纪戏曲领域最为突出的是新旧交替现象,把过去,现在,未来扭结在一起。处在时代漩涡中的艺术家努力跟上形势,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京剧流派的再度繁荣,是这个阶段的特殊成就之一。周信芳是京剧艺术忠诚的守卫者,又是勇敢的突破者、革新者。张庚说:“信芳先生,不愧为当代戏剧大师。独树一帜,形成流派,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这是一种豪放的艺术风格。它贯穿在唱、念、做、音乐伴奏、人物造型等各个方面。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和他的演出剧目,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分不开,是和他的艺术师承,艺术素养分不开的;归根到底,是和他对现实,对待政治的态度分不开的。”(见《用全身心演戏的艺术家——周信芳》)
在京剧观众之中,有部分老观众推崇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京派表演艺术家,把周信芳、唐韵笙等统称之为“外江派”,褒“京朝派”,贬“外江派”,这虽没见之于文字,但情绪情感上总是有所流露。张庚对此深有所感,因此他一再告诫我们,研究京剧不能不研究“南麒北马关外唐”;特别是对“关外唐”的研究,我们还很不够。他认为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是因为“周信芳主要以上海为活动基地”,虽说活动区域是上海,但与京派京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小就尊重京派,学习京派,与京派演员合作亲密无间。因此“他的艺术不但受南方观众欢迎,同样受北方观众喜爱,在国外也享有盛誉”。张庚又进一步分析了麒派艺术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喜爱的原因:“他很早就接触了新文艺,观念开放,胸襟开阔,勇于革新。他的表演风格,有许多人爱好,许多人学习,被称为‘麒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就会有许多特点,其价值却不限一个流派。”
张庚把麒派艺术置于总体流派中观察,又从麒派艺术的特点来论证麒派对流派艺术的贡献,完成了从个体到总体,从一般到普遍规侓的理论升华。他认为被观众认可的流派主要是一种表演风格的肯定,“一种表演风格的形成是与演员所演剧目,和其中人物的关系十分密切的”。麒派的代表剧目,如《徐策跑城》、《坐楼杀惜》、《义责王魁》、《海瑞上疏》、《四进士》等,其中人物多种多样,徐策、宋江、海瑞、宋士杰、王忠……年龄、身份、地位、性格、经历、文化修养……各不相同,但却贯穿了流派的表演风格。张庚的解读是“这些人物形象,都是运用了周信芳所特有的艺术技巧创作出来的。人们所着迷的就是这些有麒派特点的唱、做、念、舞的表现方法。就是这些表现方法活生生地表现出剧中人物,而这些人物又是使观众同情、佩服以至于敬爱的。由于人们同情、佩服、敬爱,就禁不住要学他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叹,这就形成了麒派。这也就是艺术的潜移默化之功”(见《周信芳与麒派艺术·序》)。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张庚的思想也在飞速发展,他向我们提出研究的“视野应该更加开阔一些”,“研究要有新的视角,进行新的思考,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从学术上作新的探讨,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对于1994年出现的涉及周信芳的戏剧观,美学思想,在更广阔背景中研究周信芳的历史作用,地位和艺术创作特征的论文,张庚予以充分肯定。
在周信芳诞辰百年之际,张庚提议,在确立周信芳“麒派”表演艺术的同时,在学术上应该开辟一门“麒学”。他认为《红楼梦》能引出一门“红学”,“我看周信芳就是一部书,一部内容丰富,值得很好研究的书。在‘麒学研究方面开辟出新天地,对振兴京剧会大有好处”(见《周信芳与麒派艺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