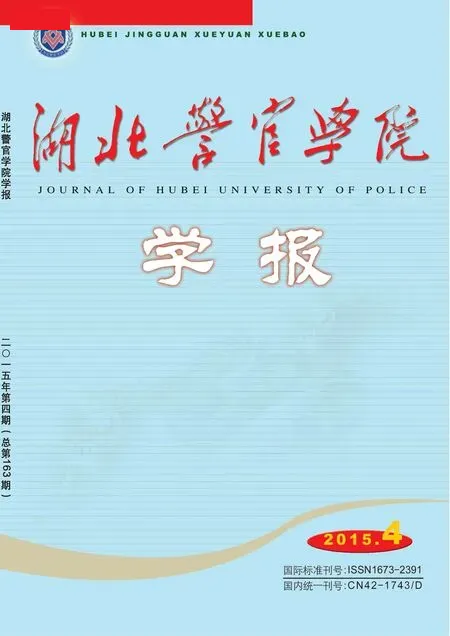环境犯罪客体研究
2015-03-26樊芸旭
樊芸旭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刑法之客体
我国刑法理论中最早引入客体概念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刑法学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人或物。其客体相当于现在的行为客体。
李斯特的法益论严格区分了刑法意义上的保护客体与行为客体,以杀人罪为例,具有生命的他人的身体作为外在的客观存在,属于行为实际能够直接指向的对象,即行为客体,而人的生命属于价值评判的对象,不能直接感知和触摸,是作为法益保护的对象,即保护客体。对于李斯特的客体划分,我国学者陈兴良认为这是一种过于哲理化的逻辑,按照李斯特的观点,行为客体属于事实范畴,法益属于价值范畴,在此前提下李斯特认为作为保护客体的法益属于不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对象。[1]
笔者较同意陈兴良教授对李斯特观点的评价。依照常识,法益的侵害往往是最直接的,这也是目前刑法立法的一个出发点,即保护法益不受侵害。我国近代以来的刑法经历了借鉴苏俄到德日的过程,在早期对于行为客体和保护客体并未做明确的划分,而是将犯罪客体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作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应用于刑法中,显现出空泛性的缺陷。
1978年以后,犯罪客体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从质疑社会关系说到提出社会利益说、法律关系说,最终形成了利益说,张明楷认为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2]
二、环境犯罪客体之辨析
基于上述论述,环境犯罪的客体理应是刑法所保护的一种法益,但是我国学者往往受到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仍然在社会关系层面讨论环境犯罪的客体,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因此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应是国家对环境的社会管理制度,这种观点已与如今刑法所提倡的“法益说”脱节。
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六种观点:[3](1)公共安全说,环境犯罪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2)环境保护制度说,即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3)双重关系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4)复杂客体说,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犯罪同时侵犯了人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犯罪侵犯了国家环境资源保护制度、公民的环境权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5)环境法益说,该观点将环境法益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相比前面几种主张突出了环境犯罪客体的独立性;(6)环境权说,环境犯罪侵犯了国家、组织、公民的环境权,但是对于“什么是环境权”存在概念模糊的缺陷,而且环境权在实体法中并未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以上六种观点都难以准确概括出环境犯罪的客体。
第(1)项的公共安全说的片面性在于单纯地认为环境犯罪侵害了人的利益,这与环境形势是不符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在遭受了工业革命造成的大气、水、土地等环境资源污染之后,就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出了“公共信托”、“环境权”等理论,举办了诸如斯德哥尔摩会议等环境保护的会议,这些行为都显示了环境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人类不能仅仅将环境资源作为掠夺的对象,更应该对环境抱有“尊重”的态度。另外,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也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对环境本身的重视,承认其具有独立的价值。
第(2)、(3)、(4)项的观点属于依托传统刑法客体理论提出的观点,无论是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为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等,都显现出概括性太强、缺乏操作性、表述模糊性的缺点,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应当准确、直接地指向法益,法益的载体也应当具有明确性,“制度”、“关系”等抽象的词汇不具有利益承载的主体资格,本身也难以理清是何种利益,何谈刑法保护。社会关系本身是马克思政治学理论着重讨论的一个概念,我国将之应用于刑法是受到前苏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刑法理论逐渐转向研究德日刑法理论,正是在这种去政治化的背景下,以张明楷等为代表的刑法学者才提出了犯罪客体的“法益说”。笔者认为,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子部分,理应与刑法整个体系保持一致,离开“法益”探讨环境犯罪的客体,没有任何意义。
第(5)项的环境法益说和第(6)项的环境权说似乎较为合理,但是这两种观点也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关于环境法益说,将环境利益作为“法益”(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保护,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具体什么是环境利益,利益享有的主体是人还是广义上的物,不得而知。如果环境利益的享有主体归结于“人”,一方面否定了环境本身的价值存在,另一方面显示出环境利益提出的不必要性,因为我们大可直接根据影响环境的因素,有针对性地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人的各项权益的保护即可,如生命权、健康权;如果环境利益的享有主体归结于“物”,即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等环境因素,则易导致法律关系中利益主体的泛化,毕竟法律在传统意义上研究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社会秩序加以规范,但是当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关于环境犯罪的条文时,表明刑法调整的对象指向了环境本身,可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追究环境犯罪的混乱,如何将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可能是探讨环境犯罪客体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6)项的环境权说,一定程度上为环境利益纳入“法益”的范围提供了可能性,这样说并非笔者认为基于环境权的权利主体为国家、组织、个人,所以环境利益的享有者为国家、组织、个人,进而只要我们将环境权在法律中加以完善,环境利益就可以上升为环境法益,而是认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可以被认为是环境利益的“代表”或者“受托人”。人类为何关心环境问题,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功利性的。上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开始萌芽,环境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人类基于对生存的地球环境的主动关心而引发,而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其一,在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对生命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不仅追求温饱以及住房消费,而且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渴望更多的草坪、洁净的沙滩以及在清澈的湖里钓鱼等种种娱乐享受;另一方面,工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污染触动了人类的利益。上世纪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作为一本关于农药污染的畅销书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其核心也是阐述了农药通过食物链在人体累积,进而危及人体健康;世界著名的日本四大公害案件之一的1910年日本富山县骨痛病事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的重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矿毒对人体的危害。总结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无不是公民个体出于对健康的向往、对死亡和残疾的恐惧,或者国家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社会秩序、政党利益的维护。可见,唤醒人类对环境关注的前提在于日益恶化的环境影响了人类利益的维持和获取(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法律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慢慢发展起来的,对法律所能涵盖的内容的探索不能离开人类社会的范畴,当法律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时,其归宿仍是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各阶层利益的分配。因此,人类作为环境利益的“代表”的提法更恰当,毕竟不能否认环境要素本身是享有正当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加强对环境权的立法工作、明确环境权的内容就会使环境利益上升到法益的层面。行文至此,其实环境犯罪的客体已经明了,即环境法益,但是环境法益并非字面含义,这种法益的归宿在于法律对环境权的规定,也就是环境权的享有主体载有环境法益。环境法益和环境权是实质与形式的关系,这也是笔者认为第(6)项环境权的提法带有片面性的主要原因,具体关系为环境法益的载体是客观的环境因素,如大气、水,环境权的享有者为国家、组织、个人,而国家、组织、个人作为环境因素的“代管人”同时作为与环境利益有关的共同体,以环境权的形式维护环境利益。
作为构成权利结构的主体、客体、内容三个方面,环境权的主体和客体其实分歧不大,主要是环境权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自环境权提出的半个世纪以来,其一直难以作为实体权利写入实体法的原因之一。当诸如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这些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法律成员中加入研究自然环境的法律的时候,不禁令人思考法律是否已经突破了人类社会走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其实,无论法的历史如何演进,都是以人类的利益获取和分配为目的的,在此前提下的法律仅是一种实现手段,因此法律作为工具来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时候,当然也是从人类利益出发的。笔者提倡环境权应当作为一项实体性权利,其内容须关乎权利主体国家、组织、个人这些社会细胞的利益,能够成为诸如健康权、生命权一样可以价值评判的权利,是一种能够救济的权利。国内学者关于环境权的论述较多,但是大部分观点概括性很强或者多为程序性的权利,如吕忠梅认为公民环境权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4]陈泉生认为环境权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如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等,后者如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5]这些权利的划分要么过于概括,难以操作,如公民环境使用权;要么太过极端,陈泉生先生在之后还提到了环境监督权、环境改善权。笔者认为诸如监督和改善作为具体的救济途径比加上“权利的帽子”更合适。环境权的内容一定要具体且不脱离实际,这样才能成为实体法中的权利,才能成为可以得到救济的权利,侵害的法益模棱两可,必然谈不上救济,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谈及环境犯罪的客体时,谈到环境权就如同谈及刑事犯罪的客体一样谈及法益一词,这对于追究犯罪是远远不够的,环境权是一个很宏观的权利范畴,必须把每一个环境犯罪的客体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权的内容之中。
关于环境权的内容,可以从主体上进行划分。
1.国家环境权
国家环境权包括:(1)国家环境所有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土地、湖泊、矿藏、河流等环境因素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对这些环境因素的污染和破坏行为都视为对国家环境权益的侵犯;(2)国家环境使用权:国家作为国际主体在使用环境资源的时候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干涉;(3)国家环境管理权:作为履行环境保护职能的机构和部门,在其代表国家对环境因素进行管理时,禁止非法干涉和暴力抗拒以及故意隐瞒环境污染。
2.企业环境权
企业环境权包括:(1)企业环境收益权:企业在基于国家授权或许可后,对矿藏、森林等环境资源进行开发时,有权从中获得利益;(2)企业排污权:有学者指出排污权的设立有将排污行为对环境污染合法化的嫌疑,对此笔者认为这只是咬文嚼字,排污权的真正价值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在环境治理中引入市场调节,肯定排污权是必要的,如同平衡杆,左边是企业受益,右边是环境损害,居中调节的是排污权交易制度。
3.公民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包括:(1)公民环境健康权: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旨在强调人有在健康环境下生存的权利;(2)宁静权:公民享有在安静的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国家和政府的开发活动要严格考虑这一点;(3)采光权:主要针对房地产开发对居民房屋采光的影响;(4)清洁水权:政府和企业活动要保证居民饮水安全。
三、结语
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法益,但是其承载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组织、个人这些属于人类社会细胞的客观存在,实质表现为确定这些主体的环境权内容。目前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集中表现为对国家环境权益的侵害,对于公民、组织的权益内容未作出足够的规定,立法有待完善。
[1]陈兴良.犯罪客体的去魅——一个学说史的考察[J].政治与法律,2009(12):91.
[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81.
[3]皮勇,刘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危害结果问题[A].生态文明的法制保障——2013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C].2013:560-56.
[4]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
[5]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