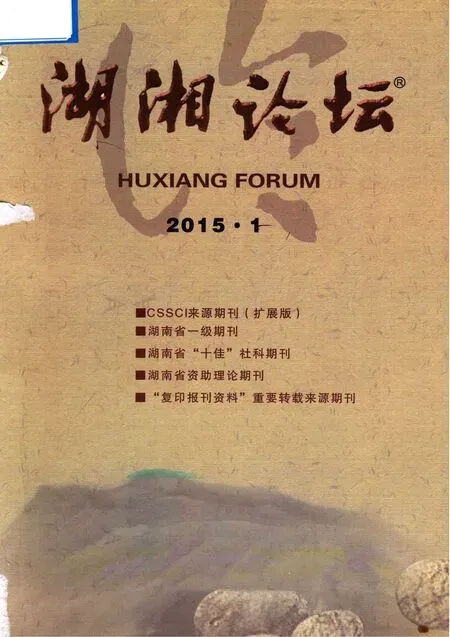儒家思想在古代东亚诸国的流变及影响*
2015-03-26范业红
范业红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130024;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116029)
儒家文化是春秋末期由鲁国人孔子创立的,它承继和概括了中华的远古文明,强调国家的集团维护以及个人的修身存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孔子学说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一个“仁”字,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它以强有力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成为中华传统民族价值观的主流,在道德信念和家庭伦理等方面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儒家思想发源自中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还是封建文化的载体,儒家经典都涵养并丰富了巨大的民族文化。而且其所涵盖的范围也远超中国境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东亚国家的各个领域以及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日韩越等东亚诸国受其光芒辐射的一大文化圈,对那里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文明或者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儒家思想在古代东亚诸国的传播
日韩越等东亚国家均是因接触到先进的中国文化而立国,并在文化往来中逐渐开化。作为经过长时期的锤炼而形成的精纯、严谨的思想理论系统,如同在中国具有历史沿革一样,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传至周边国家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
(一)在朝鲜的传播
据史书记载,朝鲜可以算作是最早接受儒家思想的东亚国家。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前往朝鲜开创生活。据《史记》记载,在殷商末年,箕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称为“古朝鲜”。韩国学者张志渊肯定箕子东来说,也认为韩国对儒学的接触始于当时。[1]P6
从传播的具体内容及社会地位来看,朝鲜半岛对儒家思想的吸纳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朝鲜王朝之前的以汉唐儒学为主,此时的儒学尚不具备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一是朝鲜王朝时期的以程朱理学为主。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上占有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其影响力也要远远超过前者。
从4世纪初,处于三国鼎立局面的半岛国家——高句丽和百济便先后设立“太学”,作为传授儒学的最高教育机构,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相对于高句丽和百济,兴起较晚的新罗国在接受儒学上也较为落后。676年,新罗国统一了朝鲜半岛,此时的半岛在学习吸纳儒学上更是不遗余力,设立太学,建设太庙,设置博士及助教等文职来传授《论语》、《尚书》、《礼记》等儒学经典,并且具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新罗还派出贵族子弟远赴唐朝学习儒学,“往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进一步掀起了儒学学习的热潮。而以薛聪、崔致远为首的本土儒学大家的出现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深谙儒家文化,为儒学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10世纪初,新罗灭亡,朝鲜半岛进入高丽王朝时代。此时的佛教虽然作为国教在官方的庇护下得到了发展,但在选拔官吏等国家政治的展开上依然需要依赖儒教。设“书学博士”、“始制科举”、设国子监等等来自国家层面的积极措施令儒学一时间大盛,正统地位得以确立。
朱子学于高丽末期传入并快速传播开来。1392年,高丽大将军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定国号为朝鲜,定都汉阳,史称朝鲜王朝。在朝鲜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排佛崇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朱子学在排除佛教的势力影响后获取了“国学”的地位,并且在到19世纪初的超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道德成为朝鲜哲学的核心和立国教民之本。
(二)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经典最初乃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正史,其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公元284年)8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能读中国经典的使者阿直歧前往日本。翌年,五经博士王仁更给日本带来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自此,儒学传入了日本并逐渐得到日本贵族阶层的重视。
7世纪初,作为中国文化仰慕者的圣德太子在执政期间亲自制定《十七条宪法》,全面吸收中国的儒学思想并付诸于社会改革实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603年颁布的《冠位十二阶》,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的儒家道德条目来表示身份的高下,并且其中多采用中国经传中的语句,如“以和为贵”、“上下和睦”、“惩恶而劝善”等,其要旨都在于以儒家理想为准绳来安民以及行清明之政。只是作为大化改新先声的圣德太子改革因为具有不彻底性而最终偃旗息鼓,儒家思想中的“尊君仁民”理想也没有在现实政治中得以实现,而最终使儒学的传入走向了文字教育的狭窄方向。
圣德太子的政治理想在40 多年之后的“大化革新”中才得以变为社会现实。大化革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标志着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作为大化革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中国封建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朝的范例来实行各项改革。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中的“学令”是针对儒学教育特别设定的章节,规定在中央及地方分别设立太学和国学来传授以《论语》和《孝经》为主的儒家经典。在统治阶级的积极推动下,儒学不再囿于贵族等上层社会,开始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期,程朱理学通过日本的僧侣直接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且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逐渐深入宫廷。只是由于当时的佛教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儒学并未获得主导地位。到了17世纪的江户时期,朱子学逐渐摆脱了相对于佛教禅宗的从属地位,获取了独立的发展,并最终进入全盛时期。出身相国寺的僧人藤原惺窝的脱佛入儒事件是日本朱子学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这一事件“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2]
朱子学获得幕府的尊崇并能在江户时期得以迅速发展是与当时的国家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1192年开设的镰仓幕府是武士阶级执掌政权的开始,在经历了“公武两重政权”的时期,以及群雄蜂起的战国时期之后,德川幕府最终力挫群雄,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在解释其政权正当性时,德川幕府采用了儒学的天道观。德川幕府的创业功臣本多正信在《本佐录》中认为,德川家康能够夺取天下并非借由武力,而是“天”所选择的“可治天下的有器量的人”,是“天”让德川家康成为“日本的主人”的。[3]P303而大一统局面的开创仅靠儒学的天命观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高度集权的统治秩序,这也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一元政伦理秩序提供了体制基础,由此,朱子学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在越南的传播
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北属时期和独立时期。所谓的“北属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世纪起,越南作为中国郡县之一被中国的封建势力所统治,一直到968年丁部领建立独立的封建王国为止的时期。此时的越南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落后状态。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家思想以及生产技术的传入为越南的文明开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越南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有了质的飞越,迅速脱离氏族社会而进入到封建社会。而在这一时期,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也从简单的理念精神传播发展到了形成从思想到形式都非常完备的传播体系。而在此传播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越南人士燮可算是功不可没的历史人物之一。
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统治获取独立自主的地位。据《越南通史》记载:“吴权设官职,制朝仪,定服色,并整顿国内政治欲为长久之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强化中央集权,历代越南王朝都沿袭中国制度,将儒学提升到“国教”、“国学”的地位,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在民间教育层面,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将四书五经列为主要考试内容。
1226年,越南发生朝代更迭,陈朝建立,但对儒家理念的一贯秉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反而有不断强化之势。在陈朝,科举考试更得以重视,在人才录用上完全效仿宋朝的评定方法。并创建国子院,重修国子监。1251年,陈太宗亲自撰写铭文,希望其子孙能够“忠孝和逊,温良恭俭”。可以看出,此时的儒教思想已经真正渗入到越南人民的血液中,而非仅仅的一项政令。
到了最后的黎朝和阮朝,在奖励儒学方面更是不遗余力,颁布了许多以普通百姓为对象的儒学教化读本。黎玄宗时的《教民四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对礼义忠信、和睦勤劳的劝导。并且为了儒家思想的推广及稳固,越南皇帝们对佛教、道教等宗教采取了限制发展的措施。身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双重影响的越南,没有发展成一个佛教国家,也可以理解为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发生制衡作用的结果。”[4]P122虽然在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儒学在越南逐渐式微,但从越南各地所遗存的文庙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儒家思想风行的盛况。
二、儒家思想在古代东亚诸国的影响
追溯儒学发展的漫长轨迹,可以发现除却中国,它更笼罩着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散发其不可小窥的影响力,甚至成为其思想文化的主流。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民族哲学中都包含着浓厚的儒学气息,直到当代,儒学在各自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中,仍是重要的思想基石。
(一)对朝鲜的影响
朱子学支配朝鲜学术界数百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政经文教等方面均可看到儒教思想的影响痕迹。在政治方面,新罗的国号由来是取“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络四方”之意,新罗历代国王均醉心于中华文化,讨论国事也常引经据典,因此唐玄宗曾经赐诗于新罗王,云“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到了李朝时期,儒学更具有无尚的权威,以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为模板建立政治体制,政事决策均以经义为最高准则。
儒教思想的效果也延及到了经济方面。《三国史记》卷二《新罗本纪》就有记录。这是对《孟子》“不夺农时”训条的一种继承。新罗之后的高丽王朝自建立伊始也采取劝农政策,热心奖励农业。到了李太祖开国之时,更以《易经》中的“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为宗旨,提出节用政策。
而在伦理纲常等方面,韩国所受的儒学熏陶则更为深厚。历代国王都热衷于维护名教,“取则六经,依规三礼”,遍寻国内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对他们的事迹予以赞扬并通过免除徭役等方式给予奖励。而对于不孝不悌之人,则加以严厉制裁。因此,朝鲜的道德规范非常重视“孝”的思想,同时将以儒学的“仁”与“礼”为基础的“三纲五常”作为时至今日仍不可动摇的伦理规范。
儒学思想融入朝鲜的本民族文化中,以水乳交融之态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其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基本的儒学理念仍深植于韩国文化当中,即便在当今,韩国人仍然尊奉《朱子家礼》,朱熹的伦理观、道德观及人生价值观仍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基础规范。
(二)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学为圣德天子改革、大化革新等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政治理念。而在其他政治思想上,儒家思想也具有重要功用。如儒学认为为政者要首先从“正身”做起,才能达到“平天下”的目标。因此古代日本在历经革新政变并得以成功之后,都会发布诏书,借以强调正己正人的重要性。比如《日本书纪》卷二十五中就有云。并且由于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古代日本的领导集团都颇具儒学教养,奉儒学的政治思想为圭臬,时刻以仁政为念,涵养品德,大力推动政治改革。
古代日本人的抽象伦理观念不甚发达。在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传入之前,日本的固有道德观念长期处于原始的、蒙昧的状态,随着儒家的“忠”、“孝”等道德观念的传入,日本人开始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力争“吾日三省吾身”。虽然道德观念的移植与转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期,但从大化革新以后,许多日本人非常热衷于中国文化并主张全面吸收,在道德领域的理想层次上也以儒家道德为理想道德。
即便在现代日本,儒家思想虽然不再以一种完备的思想体系出现,但它仍是日本民族伦理价值观的基本构成元素,其特有的民族心理也籍此形成。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此精辟地指出:“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日本在吸纳中国儒学的过程中也根据日本人的思维特点将其“日本化”。
(三)对越南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也是始于治国层面。统治者认识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在维护封建大一统时的重要作用,因此开始大力宣扬,使之成为立国、治国的理论基础。儒学思想也推动了越南社会教育的长足发展。士燮就大力提倡诗书礼乐,“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历朝历代将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在科举考试中基本全部使用汉字。为求得功名,人们埋头苦读圣贤之书,这不光为封建统治培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也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对于没条件学儒家经典的普通百姓,也耳濡目染地了解了伦理道德等丰富的儒学元素,形成了忠、孝等基于儒家学说的传统道德。
从治国思想到伦理观念,儒家思想可以说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儒家思想对越南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历史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不可磨灭的。越南著名的学者潘玉对此认为:“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都 带有可以被视为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也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即儒学思想已然内化为越南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越南的文化内涵也因此得以丰富和发展。
三、结语
中国的儒家文化自其产生伊始,就不断地被诠释和解读,在这一过程中,其影响力也如波浪一般层层推进至古代东亚国家及地区。东亚诸国也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蓝本,根据自身的社会实际创建新的文化模式。也正因为此,很多史学家都倾向于将中国及亚洲的其他国家看做是基于儒家思想的文化共同体,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文化共同性和文化共识,有着相当强的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和合体”,因此,东亚更应该理解成一个深层的文化圈,中华传统儒教文化的遗传基因于圈内处处可见。或许从东亚儒家文化入手,坦诚面对东亚各国在文化发展当中存在的共性与特性,才能更加确定与发扬东亚各国承古至今的精神构建与彼此关怀。
[1]金炳珉.朝鲜—韩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
[2]王明兵.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J].古代文明,2014,(4).
[3]宇野精一等编.讲座东方思想第10 卷东方思想的日本型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
[4]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