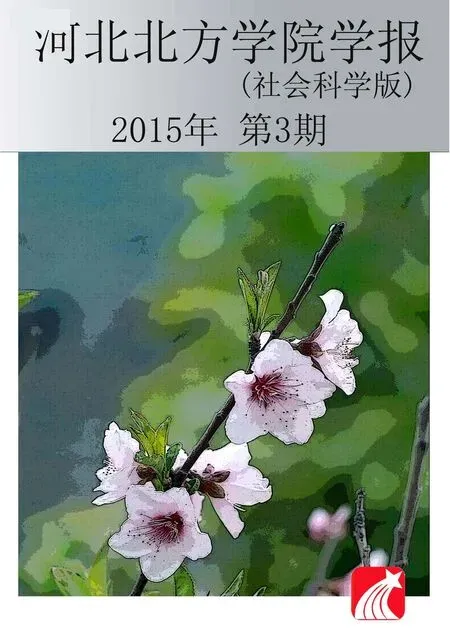从黑色幽默小说看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反审美
2015-03-26张金玲
从黑色幽默小说看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反审美
张 金 玲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凤翔师范分院,陕西 宝鸡 721400)
摘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审美观念呈现出与传统审美观念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即反审美倾向。以黑色幽默小说为例来论述后现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反理想、反英雄和反叙事,在对传统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比较中阐释这种反审美。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学;黑色幽默;反审美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张金玲(1981-)女,湖北枣阳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凤翔师范分院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及大学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I 109.9文献标识码:A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0604.1431.01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04 14:31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印上了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烙印,后现代主义强调非理性和个人主观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观念呈现出与传统审美观念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即反审美倾向,它是对传统审美方式自觉的反抗或疏离。总的来说,后现代文学专门以丑恶、灾难、危机、死亡及一切阴暗污秽的东西为审美对象,从中再也看不到传统文学中的那种和谐、崇高和诗意。该文以黑色幽默小说为例论述西方后现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反理想、反英雄和反叙事。
一、反理想
“文学中的理想,既包括文学作品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理想生活、理想爱情等内容的价值判断,也包括对文学环境和文学审美特质的理想追求。”在西方传统文学史上,人们最大的审美理想就是追寻事物的和谐有序与静谧之美,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形态,传统文学一直承载着给人教益和快感的功能。贺拉斯在《诗艺》里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155也就是说,文学审美应“寓教于乐”。纵观整个西方文学发展史,很多传统文学都体现了这种审美理想和艺术功能,他们对人生、未来、爱情和道德都作了美化的书写,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良与凶残、真诚与虚伪、崇高与渺小的二元斗争中,崇高、正义和光明总能战胜渺小、邪恶和黑暗,表现出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求与赞美,以此来感染人,教育人和引导人。从《伊利亚特》《浮士德》《悲惨世界》到《人间喜剧》,都是一曲曲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颂歌,表现了人们对真理和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
而后现代作家们不再是崇高理想的追求者,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泯灭了心中最后一点理想,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希望,拒绝对生活进行美化处理,只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人的生存困境。生命中的正面价值被放逐,使文学只剩下丑恶而无崇高,只展现现实而看不见憧憬,活着就是唯一目的,人生只剩下虚妄,无终极价值意义可寻。显然,后现代作家们已由“启蒙者”变成了“看客”,他们的作品疏离了崇高,消解了理想,充满了悲观主义。
黑色幽默小说家“善于含着眼泪讲笑话”,他们揭露了许多荒谬丑恶的现象,突出描写世界的不合理,社会对人的压迫,环境和人的不协调等,这些都是以玩世不恭和嘲笑的口吻描写出来。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描写了皮札诺亚岛的空军驻扎地,那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与疯狂的景象,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疯人受勋,坏人当道,正义与理性受到无情的嘲弄:飞行大队长为求飞黄腾达,不断提高飞行次数,置他人生命于不顾,千方百计地欺世盗名;两名指挥官常为小事相互纠缠,在精神上骚扰对方;还有一些军官大搞“忠诚宣誓”活动,使士兵受尽威胁和折磨,而自己却欣喜若狂;军医丹尼尔为冒领津贴,挂名于别人的飞机,最后成了一个“活死人”;士兵中有的酗酒闹事,有的开小差,更多的是醉生梦死,浑浑噩噩,找妓女胡混,互相敌视,吓唬同事,冒险解闷。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世界,多数人在此丧失了人格,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传统战争“正义、真理、自由、荣誉、爱国”的理想已不复存在,人的尊严与神圣也无从谈起。在冯尼格的《冠军牌早餐》中,不知从何时起,夏威夷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成了几十个富人的私人财产,而私人财产不容侵犯的铁律使岛上其他的几百万居民只能借助气球升在半空中苟延残喘地度日。品钦的小说《V》中有两个场景:一是地面上的“海员酒吧”,这里充斥着醉生梦死的海员和放浪形骸的妓女;另一个场景是肮脏的下水道,一位牧师怀着虔诚的心情钻到这里给老鼠布道,一个中年人穿过下水道来寻找母亲和自己的生活道路。地面酒吧本是人类正常的生活场所,但人们却在这里干着乌七八糟、非正常的勾当,本不是人类生存的下水道,人们却在这里寻找上帝、自我和正常的生活。由此可见,作者运用结构上的反讽来发掘荒诞之中的幽默。
总的来说,荒诞和死亡是黑色幽默小说家们表现的主题。人除了在绝望中嘲笑痛苦与不幸外,没有其他出路。作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揭露现实的丑恶来“引起疗救的注意”,相反,他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荒谬,人们无力改变它,只能走向最后的毁灭。传统文学家们相信世界是美好的,虽然社会上也有邪恶与丑陋,但最终真善美会战胜一切。读传统文学可以使人受益非浅,心灵得到慰藉;而读后现代文学总是给人沉闷与压抑的感觉,对现实世界产生厌恶和绝望的情绪。显然,后现代文学没有了对人类正义和前途的终极关怀,没有了崇高的震撼精神,他们不看重过去,也不重视未来,只注重现实本身,难以承担精神指导的重任。因而,在后现代文学中,作为传统审美理想的“寓教于乐”的文学价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消亡了。
二、反英雄
西方传统文学强调崇高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一美学思想指导下,作家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追求对“典型”的创造。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完美的,他们形象高大、信念坚定、毅力顽强,往往表现出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身上闪耀着英雄的光辉。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体魄健壮、意志坚强,充满英雄气概,在与人、自然和命运的抗争中体现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宗教、反神学的思潮运动中,作家对人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高度赞扬,哈姆雷特的“人是宇宙精华,是万物灵长”就是对人类的赞歌,这种主旋律一直贯穿于歌德、席勒、拜伦、雨果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说,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西方传统文学一直执著于对英雄人物的挖掘与赞美。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品里,再也看不到人身上高尚正义的品格和悲壮崇高的震撼力量,有的只是行为乖僻、思想古怪猥琐的“反英雄”。他们无能为力、荒唐可笑却又怀疑否定一切,蔑视天地万物;他们消极厌世,充满孤独感;他们可能是卑劣的小人物,却又保持某种尊严。他们已不再是古典式的英雄,只是被现代社会扭曲了的反英雄。
黑色幽默小说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的《第五号屠场》,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故事背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3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不是在战场上建立奇功的英雄,有的甚至还是千方百计逃离战争的怕死鬼,或者是疯疯癫癫的精神病患者。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主人公尤索林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对他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死还是不死”。他是一个上尉投弹手,但他厌恶战争,以求生为最高目标。为了逃避战争,他多次装病住院;为了保全生命,他偷偷往飞行员食物中投入肥皂水,造成集体腹泻,迫使上司取消飞行;他深夜溜进作战室偷改轰炸线路,以便飞临没有防空系统的安全区,升空后又说飞机出“故障”,要求返航,飞临目标后根本不管命中与否,俯冲投弹一瞬即马上做好向上飞逃的准备。他自始至终都在为生存作着极尽疯狂的努力,最后终于选择出逃到瑞典。然而在作品里,作者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刻画的,因为他是岛上唯一为了生存而勇敢作出选择的人。他所处的是一个善恶颠倒的世界:英雄就是小人,精英就是渣滓,上层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部下死活,一再提高飞行次数,增加飞行危险。尤索林清醒地看穿了这一切,与丧失了求生本能和麻木不仁的同伴相比,尤索林才更像一名正常人。显然,尤索林这个“反英雄”的英雄已与传统的英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综观后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到,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了“普罗米修斯”,有的只是像尤索林那样的“西西弗斯”。
反英雄人物的出现是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20世纪,尼采曾发出悲鸣:“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传统的真理死了,没有了信仰,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也崩溃了,既然人生价值已没有意义,人类也就不再苦苦追求崇高的理想。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有的只是悲观焦虑的绝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也就不再试图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来拯救世界,或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塑造了一个个孤独异化的反英雄,这种反英雄化倾向是西方精神危机在文学上的反映。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倾向,同时也看到传统审美观念受到的巨大冲击。
三、反叙事
有学者认为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关注“写什么”,现代主义作家关注“怎么写”,而后现代主义作家关注的只是“写”本身。“写”本身就体现了传统叙事艺术的反审美倾向,“小说是用叙事方式在主体和客体生活之间结成的审美关系中进行审美创造”16。从这个定义可见,小说是一种通过叙事进行的审美创造活动。
传统小说常以叙事宏伟为人称道,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作家用精心安排的结构、华美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细腻的心理与环境描写,精心营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使作品成为经典的不朽之作。而后现代小说情节淡化、结构松散且时空跳跃,作家用陌生、抽象的而不是抒情的、描写的语言,以冷漠的叙事视角,冲出了传统叙事权力话语的囚笼,对话语重新分布调整。
传统小说的叙事表现出一种训话式的经典话语,如教训与受教,灌输与接受,强迫与服从,“唤醒”、“批判”、“揭露”和“歌颂”则是它的出发点。而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不再是训话,而是对话;叙事不再是对生活的解释,而是一种语词游戏,叙事圈套模糊着故事。如黑色幽默小说家巴思的小说《漂浮的剧院》,书名既是小说主人公托德企图炸毁的演戏船的名字,又是主人公托德为自己所要写作的小说拟订的标题。这“漂浮的剧院”作为一个中介符号,既是巴思的小说,又是主人公托德的小说。所以,托德既是巴思小说的主人公,又是自己小说的主人公。这样,巴思的小说文本与托德的人生生活,托德的小说文本与托德的人生生活既构成了双重虚构,又成了浑然一体的真实。实际上,不管是托德还是巴思,他们所重现的不是讲述什么,而是讲述本身。因为讲述什么既不清楚也不重要,讲述才是借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这种故事套故事、主人公兼作者的叙事模式为小说创作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虚幻性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
传统叙事还是一种人格化的叙事。作品中的叙事主人公经常对叙事对象加以道德评价,有一套普遍的道德评价标准,好坏、美丑可以分辨清楚。而后现代文学叙事转向非人格叙事,在后现代文学里,情节淡化了,作家们不再指点江山,随意议论,也不再以道德的审判者自居。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常被认为是极端的拼贴之作,小说没什么故事情节,由各种零散的插曲和似是而非的议论组成。内容涉及现代物理、高等数学、性心理和火箭工程等多种领域。巴尔塞姆的小说行文极其庞杂,广告、图象、画片、市井俚语、陈词滥调和插科打诨杂糅交错,好像把大堆碎片粘合在一起,如迪克斯坦·莫里斯说:“巴尔塞姆有意识阻碍我们读者在传统小说中进行低劣而肤浅的识别,但他却找不到什么东西取而代之,我猜想巴尔塞姆从戈达德的电影中得到启示,删除大部分原始的叙事渣滓,以便使当代文化的糟粕能更加势不可挡地显示自己。”221在这里,传统文学叙事所追求的永恒和完美被彻底消解了。
在传统叙事文学里,如此叙事是对美的亵渎,而这却是后现代文学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传统叙事过分注重单纯、简洁和精确的形象,排斥模糊、断续和非具象的形象。而后现代文学家们正努力逆转这一点,他们追求的正是非美的效果。他们认为传统叙事的追求属于表层心理,只有对非美的追求才属于深层心理。所以,后现代文学追求的是非美和无意识的视觉。
综上所述,后现代文学在内容、形式方面的反审美特性是对传统文学审美观念的否定性批判和改写,这种反审美使传统的文学艺术走出“象牙塔”,去关注更广范围内的审美现象,它对拓展审美范围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有的后现代文学家完全摒弃传统美学概念和原则,一味标新立异,对传统审美方式彻底消解,这就割断了与传统美学的内在联系,让人难以接受。但不管怎样,后现代文学的反审美特性实际上是以冲击人们旧有的审美观念来表现人们对社会的困惑和陌生,从而给人以新的心灵震撼与启迪。
参考文献:
[1]周志雄.论文学与理想精神.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1):59-61.
[2]贺拉斯.诗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陈志平,吴功正.小说美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4]迪克斯坦·莫里斯.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小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Anti-aesthetics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West
from the Black Humor Novels
ZHANG Jin-ling
(Fengxiang Teachers’College,Baoji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Baoji,Shanxi 7214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the aesthetic ideas of the western post-modern literature show th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cepts,namely,anti-aesthetic tendency.Taking the black humor novel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anti-ideal,anti-hero and anti-narrative,and interprets the anti-aesthetics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post-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post-modern literature;black humor;anti-aesthetics
(责任编辑白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