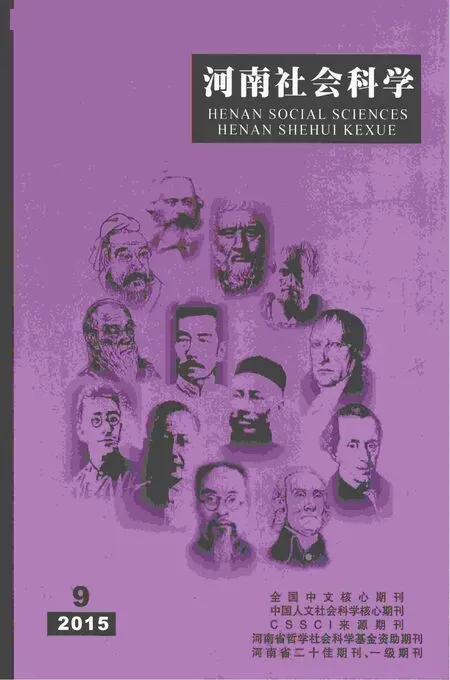论《荀子·正名》逻辑的类型与规则
2015-03-26曾昭式
曾昭式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在逻辑学科下研究《荀子·正名》思想毕竟不同于历史上非逻辑学科下的研究,在逻辑学科下研究《荀子·正名》文本所提炼的逻辑有两种倾向:其一,如五卷本《中国逻辑史》“荀子的正名逻辑”包括荀子的逻辑规律、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理论[1],这种研究难以找到文本《荀子·正名》的内容;其二,如《中国逻辑史教程》强调荀子正名逻辑突出“正政”之特征,讨论了名的性质、“制名”的认识论基础、“制名”的原则方法、辩说的性质与原则、类、故、理、对“三惑”的批判等内容[2],这一研究明显没有把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区别开来,虽然先秦时期文史哲汇通,但我们毕竟是基于当下逻辑学科的先秦逻辑研究。台湾学者李哲贤教授在例举美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荀子名学的本质为:“荀子名学之核心乃是名或概念之理论。荀子对于辞或命题之探讨较为简略,虽然,荀子对于命题作过分析,且亦有合于有效推论形式之论述之实例,然而,荀子并未能抽象地提出有效之推论形式。因之,根据逻辑学之定义可知,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逻辑。”[3]“所谓名学正是以‘名’或概念作为研究对象之思想理论。荀子之名学详于概念论而疏于判断和推理之理论,正符合名学本身之涵义。因之,唯有依据名学而非西方之逻辑作为判准,如此,对于荀子之名学始能作出客观而正确之评价。”[3]由引文看,一方面李教授还是以逻辑作为名学的参照物,如其言“荀子之名学仅为概念论”;另一方面,此语“唯有依据名学而非西方之逻辑作为判准”有一问题:名学与逻辑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早在章太炎身上就发生过,如其言:“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论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驳倒,就是希腊所谓‘诡辩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学’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4]这里“名家”(名学)是“逻辑学”(论理学),而“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显然没有区分“名学”与“逻辑学”的关系。他们研究的困难在于:不知将名学归为何种领域,如归为逻辑,名学显然不是有效性推理的学问;如归为逻辑学科,只能成为“逻辑+中国元素”形式。
近几年也有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符号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研究荀子“正名”思想,有大量成果面世,如中国哲学领域的博士论文《先秦诸子学中“类”的思想新研究》《孔子正名思想研究》《正名与正道——荀子名学与伦理政治思想研究》等研究先秦“名”“类”理论,研究颇有深度。这些研究尽管关注中国逻辑,但中国逻辑一定是逻辑而有别于中国哲学等,它们需要我们的“中国逻辑”的定义;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国逻辑是如何有别于中国哲学。这就需要有一个包含不同文化传统的“逻辑”的论域。本文给出的逻辑是“论证的结构与规则”的边界中,逻辑不仅仅是纯形式(逻辑常项与变相)的结构。基于此,《荀子·正名》逻辑的类型为“正名—用名”,“正名”是确定“名”之所指,关注名实关系;“用名”是研究“说、辩”中“名”的确定性问题,二者合为荀子逻辑的论证结构。先秦诸子逻辑均为此结构,其同与异在于不同学派的“正名”与“用名”理论。《荀子·正名》逻辑的规则包括“正名”规则与“用名”规则,“正名”规则是如何确立名的内涵;“用名”规则是在论证中如何正确地用“名”。
二、“正名”及其规则
荀子“正名”理论实质是研究“名”如何称谓“实”的问题,即如何“制名”,确立名之所指。在荀子观念里,“实”包括经验世界之实在和社会现象之政治伦理之规定两个方面内容,荀子“正名”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正名就是正实,正前者之“实”的目的是“辨同异”,后者则为“明贵贱”(《荀子》引文均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就正名以“辨同异”而言,荀子认为:人有认知能力,人识“物”是靠人的五官(眼、耳、嘴、鼻、身)和心,五官接触万物,心感知、辨别万物,获得对不同物的属性的认识。这些认识需要用“名”来确立下来,确立的原则是“约定俗成”原则(就人而言)、“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原则(就物之特性而言)、“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原则、“径易而不拂”原则(就语词而言)、“大共名”与“大别名”称谓原则、“稽实定数”原则(就物的范围及变化而言)。《正名》里有系统的论证,如下: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
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为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就正名以“明贵贱”而言,荀子把制名分为“制散名”和“制非散名”两类,其对应于物名和社会之名。物名可以约定俗成(“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社会之名则贯彻着荀子之政治主张、伦理规定和价值取向,所以荀子要求“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这是荀子所说的正道,在此层面,荀子之正名(或制名)就是正道,荀子的“道”是什么,这在《荀子》诸篇里各有侧重而有回答,如《劝学》要求学习《礼经》《乐经》《诗经》《尚书》《春秋》,只有如此,方可成圣(“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修身》要求学习礼义(“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不苟》要求君子之行合礼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荣辱》区分荣与辱,指明“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非相》考察其思想与处事之法(“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得出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结论;《非十二子》批评“十二子”之说,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仲尼》由“言羞称乎五伯”(因“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引出“王者”之道(“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提出:“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和“天下之行术”三术。《儒效》用大儒,即人道,即礼义(“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王制》讲君王之道:“礼义者,治之始也。”《富国》:“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王霸》掌握国家政权之道:“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君道》为君之道:“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臣道》用臣之道:“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致仕》讲用贤标准:“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议兵》讲:“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强国》讲君王三威(“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得出“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天论》讲知天、顺天(“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正论》讲君王清明、正直,以刑法制度为治(“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礼论》论礼(“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乐论》论“乐”(“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解蔽》讲如何解除蒙蔽,产生正确认识问题。《正名》讲君王如何制名以利治。《性恶》分析“性、为”,讲养善(“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君子》讲圣之五能:“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成相》讲“治之经”(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赋》讲“礼”等。《大略》讲“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宥坐》讲孔子如何学习修身礼义的。《子道》讲为子之道,为臣之道。《法行》表达理想君子形象。《哀公》表达荀子用人与为政观点。《尧问》涉及人才问题。由此可知,这种名之规定必须以荀子之规定而规定,显然此“正名”之规则具有价值特征。
二、“用名”及其规则
如果说“正名”是“正实”(含“道”)的话,那么,“用名”就是正确使用“正名”之后的“名”。从《正名》的结构看,荀子在讨论“正名”思想后,便论证“用名”理论,包括批评三种错误的“用名”类型和正确“用名”的方式。
三种错误“用名”的类型及解决途径。其一,以名乱名,办法:用制定的名称验证之;其二,用实乱名,依据事物的同异验证之;其三,以名乱实,用约定之名以验证之。换句话说用“正名”之规则纠正错误之用名。原文为: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如何“用名”?体现在“言、辩”中,《荀子》之“言”指言论;“辩”指论证、“讲道理”之意(与“说”差异不大)。《正名》关于“实、名、辞、辨、说”诸范畴在论证中的作用有着非常清晰的说明,它们是“用之大文”,其落脚点是在“言、辩”中如何用好名的问题。而且在“用名”层面,荀子由一般意义上“用名”的讨论转移到“王业之始”上来,转移到“用道”上来。《正名》有好的论述: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
也许荀子像孔子一样,一般意义上的“用名”不需要讨论像坚白、同异、有厚、无厚问题,因违反限度,君子无须去争论(《修身》:“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辩,止之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不苟》)。他讨论“如何用名”的重点是如何用好“道”名。其“道”名如上在《荀子》诸篇里已“正”(批邪说、“非十二子”与树正名目的一样,为正荀子之“道名”),而“用名”则表现为如何通过言说论辩中使用正确之名,其规则是以传道为目的,即所有言谈说辩必须以价值观为标准,凸显荀子逻辑的价值特征。荀子关于如何通过“言、辩”而“用名”的讨论并非在《正名》一篇里,其他篇目也有论述,兹举例如下:
就“言”而论,荀子关于“奸言”与“君子之言”的区分,就在于荀子要求必须用荀子所正的“名”来言。如果这样,此言“重于金石珠玉”“美于黼黻、文章”“乐于钟鼓琴瑟”,而君子“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非相》);否则,为奸言。为什么说必须以荀子之“正名”之“名”来言,在《非相》里,荀子讲:“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
就“辩”而言,如何在“辩”中“用名”,荀子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的,从辩的内容看,荀子将“辩”中“用名”分为“仁”之辩和“小辩”两类,“仁”之辩必须讲仁道,目的是通过讲政令以引导百姓,通过仁道以规劝君主之过失;“小辩”是日常生活小事之辩,这类“辩”只要找到事物头绪,依名分来定即可。如其言:
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正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非相》)
从辩者看,分为圣人、士与君子、小人三类人之辩。如《正名》言:
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妖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俯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 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故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
如《非相》言:
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
如上两例讲圣人、士君子和小人(愚者)之辩,一方面侧重讲:辩者所辩之社会效果(“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另一方面更多是从辩论语言与内容要求而论(“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但是,荀子对“圣人”“君子、士”和“小人”有严格区分(如《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等,小人则与君子相反。如《解蔽》“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这说明荀子这种分类本身就带有自己的偏好在,其所讲的不同论辩者,其中仍是以弘扬荀子主张者为正,即圣人为通晓道者,君子为接近道者,士为追求道者,奸人(邪说者)为邪道者。
所以,荀子的“用名”是圣人、士、君子在“言、辩”中如何准确使用荀子之“道名”(如“礼、法”等),其“用名”规则遵循荀子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
三、“正名—用名”的逻辑学科特征
说“正名—用名”论证结构属于逻辑学科,是基于对逻辑的定义,如果说逻辑是纯形式的结构,是“空架子”(如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是一种必然的得出,所谓三段论的必然性是指由两个直言命题中主谓项关系构成的前提必然地推出一个新的直言命题的结论,其规则必须符合类与类外延间关系的要求),则荀子《正名》不是这种逻辑。基于逻辑不是唯一的观念的基础在于不同思想、哲学有其论证的结构与规则,如金岳霖先生讲“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者,就是以论理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5]。依此,除非说中国传统没有哲学,因为有哲学便有逻辑学。以论理的方式组织对于“中国哲学”各问题的答案绝不是拿西方逻辑的方式来组织,因为先秦哲学家并不知道西方的“论理”,他们只知道中国的“论理”方式,这里需要回答中国的逻辑(论理)是什么和中国逻辑不是中国哲学这两个问题。
荀子的“正名—用名”论证结构是逻辑在于它是一种不同于三段论的论证结构,只是“正名”是在论证过程之外首先确定的概念,论证过程是检验用名是否准确,这在先秦道家、名家、墨家都如此,如《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名实论》是公孙龙的“正名”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为公孙龙的“用名”论。它们的不同在于“名”所指“实”的差异等,与科学的逻辑不同,先秦逻辑有着价值的偏向。但是,这种价值的逻辑与西方逻辑一样,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的,论证结构与西方逻辑一样由“理由—主张”构成,规则为“理由”规则,从“理由—主张”规则。在先秦时期,这些规则涉及“用名”问题,“用名”涉及“正名”问题;说是价值的逻辑,涉及“名”的价值所指问题。同时,先秦逻辑不是先秦哲学,就在于先秦哲学研究“名”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先秦逻辑明确“名”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此名”在言说论辩中使用是否恰当(此问题另有专论)。非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亦如此。
作为《荀子》整个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正名》,是继《解蔽》后的一篇如何通过“正名”而达到统一思想、治理国家的目的的文章。通过分析如何制名和为什么制名而形成了荀子“正名—用名”逻辑思想,在荀子看来,如果社会秩序井然,没有邪说歪道,正道能够统一、引导百姓,也就不需要辩说了,但是,当今之世,圣王消失,天下大乱,奸言四起,君子无权势统治百姓,也没有法律约束人们行为,所以,只能采用辩说方式来晓谕天下,治理国家。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正名》)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在荀子看来“正名”是为了“解蔽”,由于人们的心被“邪道”蒙蔽,而不知道只有三代之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与孔子之认识才是对事物全面的认识,才是“正道”。所以《正名》篇开篇就对“人”进行正名: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围绕着“人”而正名,目的是为下文“凡语治而待去欲者”之后讨论的“用心悟道”服务,而整篇也没有离开人的“天官”与“心”,这是《正名》篇的核心内容。指“凡语治而待去欲者”后,从欲望、情感、心、行动关系分析如何消除奇谈怪论,进而达到治理天下之目的。人有欲望,欲望基于情感,心支配情感,由于多种考虑心节制欲望,只有心认可的欲望符合礼义而非情感的欲求,就有利于治国,欲望是人的本性固有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欲望是情感反应,节制是对欲望的遏制,实施治国之道的人,在可能情况下,应该使欲望接近于止尽;在条件不容许的情况下,就节制对欲望的追求。只有依“正道”而行,那些不符合正道的学者们的奇谈怪论的愿望自然消亡。人心亦如此,不能为物欲所役使,要内心宁静并役使万物,才可以治理天下。
所以,我不赞成伍非百先生认为《正名》既为儒家之学,又采有名家、墨家、庄子之义,为“名家”集大成者(“‘所缘有名’与‘制名之枢要’,则取诸墨。‘所缘以同异’,及‘异状同所’,诸分别义,则取诸《公孙龙》。‘名无固宜’,‘约定俗成’,则又《齐物》‘寓庸’之旨也”[6])的观点,我认为,《正名》逻辑是基于荀子价值观和宣扬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正名—用名”的逻辑。
[1]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先秦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2]温公颐、崔清田.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李哲贤.荀子之名学析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4]章太炎.国学讲义[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
[5]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