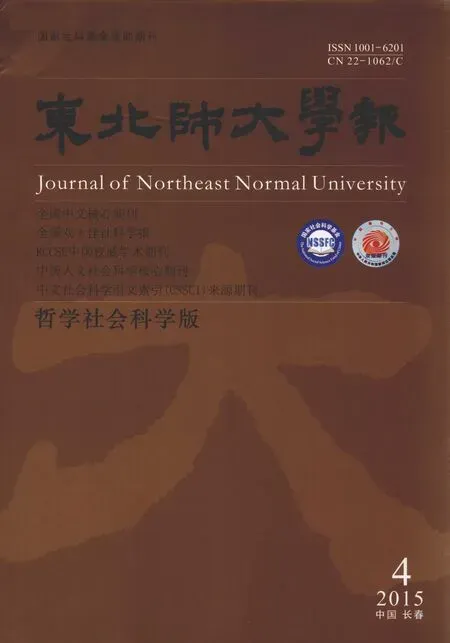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重构的路径分析
2015-03-22牛海彬
牛 海 彬
(1.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2.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重构的路径分析
牛 海 彬1,2
(1.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2.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大学作为理性而严谨的学术机构,具有自由、独立以及批判的精神特质。相较于遮蔽公共性的“政治人”、丧失批判精神的“经济人”和缺乏人文情怀的“专业人”等异化身份,大学教师具有“知识人”的外在形态和无限可能,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赋予了大学人格化的魅力,并使大学展现出自身的精神特质。若大学教师失却“知识人”身份及其意蕴,自由、独立以及批判的大学精神亦无以展现。大学与“知识人”身份的大学教师具有强烈的精神共契性和内在统一性。当下的大学教师与“知识人”身份严重疏离的事实令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的复归和重构十分紧迫且意义重大。而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倡导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重塑超越、批判的价值观,践行“以人为本”的大学教师职业理想,应是当下大学教师身份复归与重构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路径。
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大学精神
一、大学教师身份释义及“知识人”身份的确证
(一)大学教师身份释义
追溯词源,“身份”一词,中文原意为身体、本身,后发展为人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之意。教育学中的“身份”是指主体在教育中的职业身份或在教育场域中扮演的角色。法学中的“身份”是指归属于自然人或法人的一种资格和名分,强调基于身份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学中的“身份”一般强调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声誉”。与汉语“身份”对应的英文词汇为“Identity”或“Status”。“Identity”是一般指身份、本身之意。而“Status”则主要包含方式、状况、地位等意。
不同的学科及其学者对“身份”的理解各有侧重。社会学视域的“身份”概念有等级、地位、特权等含义。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学中的身份关系与现代“契约”关系高度契合,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规则以及权利、责任的合法化理由等等。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所谓身份,即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这种身份建立在一定的生活方式、教育过程以及因出身或职业而获得的声望之上。”[1]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则倾向于使用英文“Identity”之意。认为身份是“个体标示独特自身的重要标志,或是某一事物独有的内在品质,抑或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之独特标记”[2]。还有文化学研究者把“身份”理解为一定社会的人与其生存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
笔者认为,身份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自身有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大学教师身份即大学场域中的教师承担何种职责,扮演何种角色,享有何种声誉和地位,教师如何理解和认同其地位、价值和生存意义等。具体而言,大学教师“身份”主要有如下两种内涵:其一是指社会身份系统中大学教师的身份,即大学教师这一职业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声誉和地位。其二是指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机构、教育和文化场域中的身份,是大学教师对其生存状态和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实际上,大学中有一套复杂的社会职业身份系统,教师在大学中扮演着多重的、复杂的身份,这也契合了“身份”一词本身多重、复杂的内涵。
(二)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确证
大学教师究竟是“谁”,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角度而言,这一问题看似并无争议。但从“社会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道德化身”等近年来对大学教师的身份界定来看,众多理论研究者对其扮演或承担的身份也是众说纷纭,很难取得共识。如有学者认为,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前大学教师大多倾向于“学而优则仕”,很多教师丧失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大学教师成为官方(或者政府)代言人或阐释者,扮演着“经世致用”的“政治人”身份。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大学教师传授高深专业知识,以德育人,更多地承担着以学术研究和思想启蒙为志业的“学术人”身份。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当下大学教师强调专业化发展而遮蔽社会公共责任,强调忠实取向而丧失批判精神,强调教育教学技能训练而失落人文情怀,造成大学教师栖息于象牙塔内“两耳不闻窗外事”,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沦为彻底的“专业人”。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当前市场文化的浸润和工具理性的渗透下,大学发展成知识生产与人才销售的“企业”,这种“市场化”的导向,使大学教师研究风气浮躁,学术精神萎缩,独立与批判精神丧失,成为逐利趋向明显的“经济人”。这些观点再次验证了大学场域中的教师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笔者在2013年发表的《当代大学教师身份的迷失与复归》一文中也曾指出,受政治经、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大学教师身份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师与学生的成长和大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加强理论研究,重构大学教师的合理身份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十分紧迫且意义重大的课题。那么,如何重构大学教师的合理身份?笔者认为,大学作为理性而严谨的学术机构,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由、独立以及批判的大学精神特质。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精神的践行者和守护者,其具有“知识人”的外在特征和无限可能,大学教师的“知识人”身份与大学精神有着高度契合性和统一性。因此,重构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即大学教师除了在教育上兢兢业业之外,对社会、国家、人类还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切地关怀公共事物和利益并超越个人私利之上,能够依循人类的基本价值包括诸如公正、理性、自由、民主等原则进行独立思考、敢于批判和反思丑恶现象,并推动人类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身份”[3]。这对大学教师提升职业素养,形成独立人格,恪守大学精神,促进大学提升和完善意义深远。
也就是说,大学教师必须以大学精神为引领,回归其“知识人”身份,这也是当下大学教师寻求身份重构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这不但源于大学自身与“知识人”之间的精神“共契性”和“统一性”,也源于大学机构与“知识人”之间的相互依附性:“知识人”依托大学与社会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并充分展现自身的精神特质;大学也成为大学教师展现个人价值和理想的空间与平台,更是成为大学教师的精神家园。质言之,大学教师的“知识人”身份赋予了大学机构人格化的魅力,使大学展现出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若大学教师失却“知识人”身份及其意蕴,自由、独立、批判的大学精神亦无以展现。那么,大学教师如何复归或重构其“知识人”身份呢?笔者认为,大学教师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倡导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重塑超越、批判价值观,践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是大学教师身份复归与重构必然的路径选择。
二、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重构的路径分析
(一)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
随着当下大学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建制化”演进,大学教师发展更多地呈现出专业化取向、忠实取向、技能取向的趋势。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学教师一方面成为不同学科专业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过于关注自身的专业化发展,也使其远离社会公共领域,放弃社会公共身份,把自己等同于专业技术人员,导致大学教师某种程度上沦为逐利的“经济人”或单纯的“专业人”。大学教师作为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其自觉地代表着一定阶级,并以国家支配阶层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受控于权力和金钱,大学教师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其自由的翅膀也被折断,使大学教师“不是寄生在学院体制,就是以签约化的方式在资本主义文化企业或媒体中讨生活”而最终蜕变为“伪知识分子”。专业化趋向使大学教师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观照,进而丧失了公共良知[4]。这已经是大学教师当下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困境。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世俗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大规模入侵大学,也致使很多大学教师放弃公共关怀的责任,仅仅在体制内部专注于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如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aefie.Said)笔下所描述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少。大学教师过分地依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进而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大学教师要保有公共关怀的精神与责任感,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质言之,传统知识分子之独立与自由精神建立在其超然的立场——公共良知和中立、客观和进步的知识及理想之上。今昔对比,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已然不复存在,但如何确保大学教师的公共关怀精神的继续与传承,正是笔者要探讨的当代大学教师身份重建的应有之义。
“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要求大学教师超越专业化,突破个人功利主义和狭隘的专业视野,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意识决裂,立足专业而不囿于专业,以广阔的视野兼及出世与入世精神、科学与人文精神,以公共关怀和学术良知去探索世界,肩负起重建社会文化和良好秩序的公共责任感。“现代的、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新的立足点不再是政治,而是以社会为中心,以知识和人格为基本点。”[5]大学教师必须以学术为本位,潜心专业,注重人文修养,兼及科学精神,充满公共情怀,保有学术良知。可见,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与大学教师精神特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著名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被视为研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知识分子》一书中他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始终保持着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公共情怀”[6]。
因此,笔者认为,当代大学教师应该以独立的人格、渊博的知识、自由的精神以及强烈的责任感,成为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知识人。作为知识分子,要以知识或良知为基础,对不合理的秩序与权力关系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有说服力的批判;要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实现大学教师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理想的崇高责任。在笔者看来,这种身份是知识与人格兼备、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兼具、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共存,勇于探索真理并充满公共情怀的“新型公共知识分子”。实质上这种“知识人”身份的大学教师可以扮演两种社会角色——学者以及思想者。关于这一观点,也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既是大学内部自律的、自主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人,又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7]。
总之,大学教师必须基于专业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公共情怀,敢于担当社会道义,只有在专业发展的同时保持这种超专业性,并矢志不渝地把对公共精神的关怀作为“知识人”的天职,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即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观照人类共同福祉,充满社会责任感,既致力于知识传授与学术研究,又要承担改造社会和人类思想发展的使命。唯有如此,大学教师才能真正成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思想者”和“知识人”。
(二)倡导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
“知识人”身份与大学相互依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学教师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赋予了大学人格化的魅力,并使大学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因此,在笔者看来,大学教师如果不能达于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之境界,也必然会丧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批判精神。质言之,没有大学教师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大学精神无以存在和言表。思想自由是人格独立的具体表现,人格不独立,就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唯唯诺诺乃至思想贫乏,没有个性化的、多元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自由,独立的人格又何以呈现?正如陈寅恪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而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大学教师的自由精神,不仅表现为学术人格上的“消极自由”,还表现为超越专业发展,体现公共关怀和独立思想的“积极自由”。也就是说,大学教师在面对社会公共事务偏离理性的视域和正确的方向时,要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拍案而起,表达正确的观点,维护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念,恪守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8]。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以生命终结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这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绝不妥协、舍生取义、捍卫自由的最高境界。
同样,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独立精神也是其得以存在的本质特性和内在精神气质。大学教师的独立表现为对权威的拒斥,与权力刻意保持距离,并对真理和普适价值的守望。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如何彰显独立精神?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人”必须坚持“只问是非,莫谈立场,捍卫真理,超越世俗”的独立人格。大学教师的独立要以理性权威为基础,坚持“和而不同”的精神品格,秉持个体良心,忠于自身思考,独立进行判断,遵从多元价值标准,既不盲从,也不标新立异。总之,大学教师的学术人格完全依赖于其“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保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是体现大学自由精神的真谛所在[9]。由是观之,当代大学教师若要实现“知识人”身份的复归,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不唯上、不唯书、追求真理、客观公正,惟其如此,大学教师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和社会理想的捍卫者。
(三)重塑批判价值观
众所周知,大学传授的知识具有深奥性、前沿性、创新性。那么,这种知识传授只有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遵循理性原则并进行以价值引导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才能创新知识、发展学术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大学场域里,大学教师的批判特质是其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精神的天然衍生物。大学教师自由地思想交流和相互对话,不受权威束缚地自主决断使其在现实与理想相异甚至相悖时,他们总是能够挺身而出、表达己见。这种强烈的超出专业视域的理想主义情怀,使大学教师不断思考关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和普适性价值观念,这导致大学教师对于社会现实总是抱有反思精神和批判态度。“作为知识人,应该对既定文化和固有思维进行连续的、不妥协的批判……如果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不这么做,谁将这么做?知识分子总是无法对现实社会不保留地加以拥抱的……不论如何,知识分子总多少带着批判性格和反思能力的。”[10]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保持独特的精神向度,进行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思考,关注人类的终极命运,匡扶正义,推进社会理想和普适价值的实现,充当着“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精神守望者”的角色。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大学教师无畏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
追溯大学发展史,不难看出,大学是人类精神的寓所,大学教师是人类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守护者。正如著名学者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所言,大学教师是“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11]。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教师也必须体现出理性质疑与科学批判的超越精神,这才符合大学教师是知识传承者和创造者的“知识人”定位。布迪厄也曾指出,只有具有知识人身份意识的大学教师,才能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创造和生产具有批判、超越、创新属性的知识和文化。批判意识是构成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的根本要素,也是其自由、独立、超越和创新精神得以保持的前提与基础。换言之,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是“知识人”公共关怀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只有大学教师具备理性的批判精神,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进行反思、探索、创新和超越,进而彰显大学教师“知识人”的价值追求,自觉恪守大学精神,探寻教育的本真意义。
(四)践行“人本”的教育理想
正如普罗泰格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也只能是人。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就曾指出:“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学生独立思考,不误入歧途,进而能够导向事物的本源。教育应该实现人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灵性与智慧的启迪,人性不断的完善。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不是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12]因此,真正的教育总是要靠那些不断通过自我教育从而实现不断超越的“知识人”才得以实现。大学教师在与教育文体的交往和对话中不停地付出、倾听,严格遵守职业理想,通过主体间的灵魂交流和本真化的教育唤醒学生的信念。质言之,“以人为本”是当前大学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人本主义关注个性、尊重生命、追求人生意义的理想价值诉求,与大学教师关注人类自身命运和高度的社会公共情怀是高度契合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所追求的是对人自身命运的关怀,教育最终的归宿是关照人、完善人、润泽人和发展人。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大学教育是孕育人文精神、追求价值意义、具备生命品性和强调公共关怀的教育[13]。因此,倡导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回归与建构,必须强调大学教师“以人为本”的职业理想的坚守与践行,只有做到“以人为本”,大学教师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公共情怀和批判精神等价值诉求,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落到实处。
这就要求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既要积极倡导并践行人本主义教育理念,关注生命意义、敬畏生命、解放学生、充满人文精神,把教育过程真正变成雅斯贝尔斯所言的“人与人之间诉诸对话、理解和共享的情感交流”的过程,以价值引导的方式消除现实功利主义和科技理性对人和教育的消解[14]。同时,大学教师也要养成对话、理解、尊重、平等以及宽容的专业人格和职业品性,把尊重和“爱”作为大学教育的出发点与根本。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追求对人性的关爱,促进人的身心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因此,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必须“以生为本”、尊重学生、关爱学生,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总之,以爱和尊重为基点的“以人为本”的职业理想构成了大学教师的独特品质,彰显了大学教师作为“知识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公共精神。
综上所述,大学作为理性而严谨的学术机构,具有自由、独立以及批判的精神特质。而大学教师具有“知识人”的内在特征。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赋予了大学人格化的魅力,并使大学展现出自身的精神特质。若大学教师失却“知识人”身份及其意蕴,自由、独立、批判的大学精神亦无以展现。大学与“知识人”身份的大学教师具有强烈的精神共契性和统一性。当下大学教师与“知识人”身份疏离的现实令大学教师“知识人”身份的复归和重构刻不容缓。笔者认为,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倡导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重塑超越、批判的价值观,践行“以人为本”的大学教师职业理想,应是当下大学教师身份复归与重构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路径。
[1] 熊和平.教师是谁——现代教育理念下教师身份的重构[J].上海教育科研,2005(3):86-87.
[2] 阎光才.教师“身份”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及当下危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2-17.
[3] 牛海彬.当代大学教师身份的迷失与复归[J].教育与职业,2013(11):66-68.
[4]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8.
[5]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0.
[6]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76.
[7]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6.
[8]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84-85.
[9] 王小波.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70.
[10] P.Freire Teacher as culrural workers:letters to those who dare teach.Translated by D.Macedo,D.Koike,& A.oliveira.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8.
[11]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M].郭方,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76.
[12]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76.
[13] 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9.
[14] [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1.
Analysis of Path on th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s “Knowledge Persons”
NIU Hai-bin1,2
(1.Faculty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2.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s a rational and rigorous academic institution,the university has qualities of being free,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Compared with alien identities such as “political person”,which shields publicity,“economic person”,which loses critical spirit,and “professional person”,which lacks humanistic feelings,university teachers have the external form of and the possibility to be “knowledge persons”.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identity of “knowledge persons” gives the charm of personification to the university and makes the university represent its own spiritual qualities. If university teachers lose the identity of “knowledge persons” and its implication,the university spirit of being free,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has nowhere to show.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with the identity of “knowledge persons” have strong connection both spiritually and internally. The alien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teachers nowadays and the identity of “knowledge persons” mak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s “knowledge persons” urgent and important. The necessary path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cludes abiding by the spirit of “public intellectual”,promoting personality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ought,remodeling the value of transcending and criticizing,and live up to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al of “people oriented”.
University Teachers;“Knowledge Persons”;Identity;University Spirit
2015-01-21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规划2013—2014年度重点课题(GHZD13009)。
牛海彬(1976-),男,辽宁朝阳人,教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站博士后,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G650
A
1001-6201(2015)04-0234-05
[责任编辑:何宏俭]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