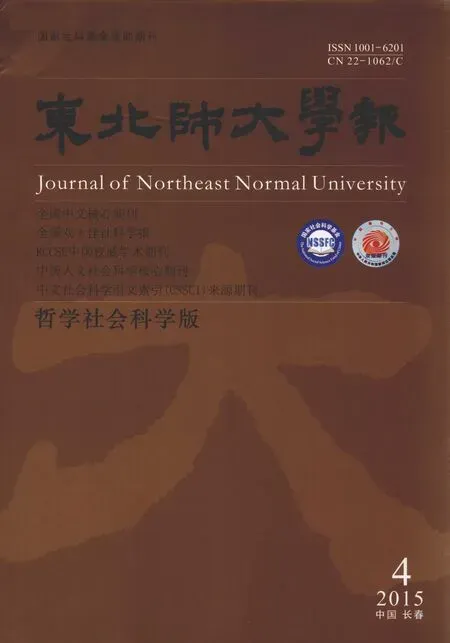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弱势文学”的存在
2015-03-22任洪玲王彦军
任洪玲,王彦军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弱势文学”的存在
任洪玲,王彦军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吉尔·德勒兹“弱势文学”思想中的弱势、生成、辖域化、解辖域化等重要概念是理解女性文学与弱势文学辩证互动关系的
。女性文学与弱势文学存在某种暗合,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学”的存在,这主要体现在生成—女人、女性文学作为弱势文学的三种特征、女性文学中语言的弱势化使用三个方面。探讨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弱势文学而存在的表征将为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提供新的路径。
女性文学;弱势文学;生成;弱势
“弱势文学”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提出的重要美学思想。对于德勒兹而言,弱势文学(minor literature,或译作次文学、少数族文学)“不是用弱势语言创作出的文学,而是一个少数族裔在一种强势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1]。具体而言,德勒兹所言的弱势文学并非是美国华裔文学或印第安文学那样由某个群族中的少数族裔创造的文学,也并非指的是它在自身的强度上具有弱势特征,更不是对于文学创造使用的少数族语言而言,而是说这种文学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弱势族性。弱势族性是在和主流话语的对照中显现出来的,弱势文学在主流话语中构建,又对主流话语产生对抗和疏离。“弱势”概念是理解德勒兹思想的关键词,其在论述弱势文学思想时,正是以对“弱势”的辩证解析为切入点。同样,“弱势”概念也是德勒兹阐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支点,学术界已经公认“德勒兹与瓜塔里的‘生成—弱势’概念对女性主义非常重要。”[2]实际上,德勒兹对弱势文学的定义与女性文学在特性上存在着某种暗合,这也正是本文想要探讨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弱势文学”存在,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路径的意义所在。
一、从生成—女人到女性文学
德勒兹“生成”概念是理解其“弱势”概念的切入点,在其哲学思想中,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千高原》中,德勒兹辩证地解析了二者的关联。对于德勒兹而言,生成的目的在于创造弱势,弱势依赖于生成的力量的构建,众多的弱势因素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无限生成力量的不可感知物。
如果要更为清晰地理解德勒兹“弱势”概念的本质内涵,需要将弱势置于与强势对比的语境中,这是德勒兹阐释“弱势”概念时使用的方法论。在德勒兹那里,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区分弱势与强势,弱势有时甚至会比强势更多,然而一旦被确定为强势,它就有具有某种固定的类型,如孩童、女性、手工业者等等如此的类型定义。弱势是没有被类型化的,弱势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是一种趋势和生成运动。德勒兹认为,弱势与强势处于一种辩证的对立与关照关系中,强势或者弱势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症候的表征,强势呈现为力量关系已经确定的特征,而弱势始终充满活力,仍然处于生成过程中,强势和弱势之间蕴含着一种二元对立关系。
一种弱势与一种强势斗争博弈的目的是要脱离与强势相关的语境,使自己活跃起来,进入一个生成的、多样化的、差异的世界,演绎出一种“生成—弱势”。实际上,弱势本身是一种生成,一种生成—弱势的过程。弱势的力量所在也正在于弱势是一种对传统和规则的颠覆与挑战,生成—弱势意味着打破一种统治状态。在生成—弱势基础上,德勒兹提出了“生成—女人”概念,这一概念也是理解德勒兹文学思想所不可忽略的。德勒兹指出,在写作中,人生成女人,生成众多不可感知物,写作和生成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生成—女人则是千万种生成中的一种。生成—女人不是与男性二元对立意义上的主体性女性,而是“在我们身上产生出分子性的女人,创造出分子性的女人。”[3]
德勒兹批判男人为身份与主体的克分子范式,而“这种克分子形式的抵制是由强势决定的”[4],在此,强势指的是男人。在“男人—标准”的强势下,生成—女人是弱势的,这不是因为女人数量少、权势低、是弱势群体,而是因为对女人来说没有确定的话语、标准和规则,生成—女人是有着弱势—生成的特性的,有着丰茂的生成力量。德勒兹的生成—女人概念和埃莱娜·西苏的“新生的女性”思想都根植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语境中,二者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都意欲建构一种关于女性主体的微观政治话语。对于西苏而言,女人也是处于生成的开放状态中,生成主要是由女人发起的。德勒兹与西苏都清楚地表明,哲学与写作是真正的权力,“哲学家和诗人以一种游击战的方式通过写作反抗权力。”[5]纵观西方文学史,女性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正是不断地通过“生成—女人”对抗、解构男性中心话语的社会,而生成—女人则是历来的女性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男性的话语统治中建构自己的话语权,生成属于女性的弱势性话语,与属于强势话语的“男性文学”较量与抗衡。由此看来,女性文学确实可以被定义为弱势文学,作为女性在男性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女性文学作为生成—弱势的文学,特意疏离男性话语权威,在主流语言中构建出弱势族性,以生成的力量力图摆脱被主导和压制的地位,试图获得生存和拯救。
二、女性文学作为弱势文学的特征
德勒兹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中提出“弱势文学的概念,并指出了弱势文学的三个特征:“第一,语言的解辖域化;第二,一切都与政治相关;第三,表述的集体性配置。”[6]女性文学无疑是符合这三个特征的。
(一)语言的解辖域化
德勒兹把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对欲望的压制过程称为“辖域化”,“辖域”本来是地理学中的概念,德勒兹将“辖域化”引用到哲学中使用,是指某种等级制中心主义、固化的社会和思想结构等,与此对应,“解辖域化”就是从此种秩序中逃离出来。德勒兹还从符号学的角度创造出“编码”和“解码”的概念,以对应“辖域化”和“解辖域化”[7]。对弱势文学而言,语言的解辖域化就是在写作中突破固有的规定与疆界,是语言的弱势化使用。这种语言上的弱势化使用只有在与强势语言的对比中才能存在,是在强势语言内部缔造的、与权威的语言特征疏离的语言。在弱势语言中,索绪尔所建立起来的能指与所指已经土崩瓦解,甚至它可能已经不具备能指与所指这两种指示功能,在弱势语言中,语言的使用已经演变为语言本身的弱势化与生成运动。弱势文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一边消解一边建构的过程,消解固有的语言学规则,使这种语言驶离固有的轨道,从而生成为弱势文学所用的弱势语言,实现了语言的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中,德勒兹以卡夫卡使用布拉格的德语为例详细解析了语言的解辖域化使用的问题。卡夫卡使用的布拉格德语正是在与强势的德语的比照中存在的,它建构于传统强势的德语内部,又极力消解传统德语的语言规则,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是一种已经比较典型的语言的弱势化使用案例。卡夫卡等弱势族裔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把布拉格德语的解辖域化运动一步步推向深入,使弱势文学的概念由此肇始。在语言的解辖域化运动中,传统的语言成分、词语都从原来的语境中脱离出来,肩负起新的使命,结构起弱势化的语言,这也是解辖域化后的一种再辖域化过程,弱势化了的语言就是要为弱势文学的写作服务的。
女性文学中语言的解辖域化集中体现在身体写作中。在文学史上,女性的身体体验是由男性作家代为书写的,女性的身体体验在传统的男性文学史中被打上了男权的烙印,女性们没有处所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一直处于一种失声的境地。女性的身体感觉被男性话语诉说和规范,诸多女性主义者都以身体书写为口号来反抗男性世界的樊篱。在女权主义者那里,身体写作是女性文学的构成主体,女性的自我欲望书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拿起笔来书写女性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对男性文学的疏离和抗争,它对语言本身的男权话语的拆解,并对语言进行重构,它使女性文学的语言从男性语境中脱离出来,驶入一条“生成—弱势”的轨道。它跟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这正是在强势语言的关联之中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弱势化使用。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正是践行了语言的弱势化使用原则,使语言脱离固有的疆界,从而实现对男权语言的解辖域化。
(二)一切都与政治相关
在强势文学中“一种语言的强势化可以对形式和意义进行固定、调整和规范,从而对变异进行结域。这种对语言的强势化使用加强了各种类别与差异间的区分,进而造就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隔离。”[8]通过对卡夫卡作品的考察,德勒兹发现了与强势文学中语言的强势化使用相反的情况,即弱势文学打破了这种隔离。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弱势文学作家可以拆解与消除语言的强势化中隐含的权力关系,使一切都进入到生成的配置中。对德勒兹而言,语言不是中立的实体,而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是一个各种力量不断发生关联和斗争的场域,弱势文学创作充分利用语言的这种特点,通过对一种语言进行弱势化使用,消解、破坏、颠覆了个人与政治间的隔离,消除了主导的规范与等级,在欲望的引导下,语言的“生成—弱势”实现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各个单元和节段的解辖域化。同时,借助这种解辖域化,语言彰显出其并不是中立的符号系统,文学创作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个人的内心独白,不是个人的叙事表达,而是演变为一场政治实验,一场欲望政治学,作家演变为表达欲望的政治家,通过文学创作将个人与政治关联起来,所有的个人私事都与政治牵连在一起,一切都与政治相关。
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最初走上历史的舞台时,就带有不言而明的政治色彩。在这个男性统辖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女性的声音,男性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如在小说兴起的18世纪,人们津津乐道的竟然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以男性的视角建构出的弱女子帕梅拉和克拉丽莎的世界。女性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反抗男性的压制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历来的女性主义者都曾主张拿起笔来书写,书写女性情怀、女性感受乃至女性世界,这种书写是女性反抗男性压制,突破传统藩篱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主张,女性想要改变受压迫的状态,自己就要勇于去主动斗争。这种斗争最主要的是“像男人那样介入社会话语阶层,而介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写作。”[9]只有建构起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书写特有的女性世界,才能开启一扇窗,为女性封闭禁锢的境地带来新的空气,表达女性自己的欲望。西苏也认为写作是女性表达自我的最佳途径,女性写作可以使女性夺回话语权,重获女性自我表达权。这不仅仅是女性自我书写欲望的表达,更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行为。女性写作的最初立场便是消解男性的话语霸权,为女性谋得一席之地,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发出女性的声音,所以女性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政治的相关性成为女性文学自诞生伊始就带有的一种独特色彩,这种与政治的相关性与弱势文学不谋而合。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将女性文学的发展归纳为女子气、女权主义、女性三个阶段[10]。第一阶段(即女子气阶段),女性写作者主要处于模仿状态,想要变为同男性一样的人是这一阶段女性写作者的标尺。所以女性写作处模仿男性权威,女性自我表达意识尚未在这一阶段萌发。第二阶段(即女权主义阶段),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阶段,觉醒即意味着抗争,呼吁女性自由,争取独立自主,这一阶段的女性写作充满着对男权的质疑与挑战。第三阶段(即女性阶段),过激的反抗退却,随之而来的是女性写作者对自己的重新定位,不再拘泥于批判与解构男权话语,而是将笔触深入更广阔的天地,探求更有意义的创作之路。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一条从辖域化到解辖域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生成—女性写作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女性写作被原有的男性话语所僵固,这正是德勒兹所言的第一条线克分子的节段性之线,或称作分段之线,在这条线里,女性写作被辖域化,男性的价值标准还是占据统治地位。在第二阶段中,女权主义对男性标准的全盘否定,对自我的全面宣扬,对父权的反抗和批判正是阐释了这一阶段的女性写作正处于德勒兹所言的分子性的节段化之线,或称作崩渍之线,女性写作极力挣脱各种辖制,极力彰显女权色彩。在第三阶段中,女性文学得到了一种深层次的发展,不再拘泥于反抗男权,这正是由于女性写作最终找到了生成—女人的途径,找到了自己的逃逸线,并在逃逸线上发现了生成的力量,创作出大量真正关注女性与整个人类的著作,谱出了生成—女人的轨迹。
(三)表述的集体性配置
想要厘清表述的集体性配置这个概念,我们有必要从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以及文学机器概念谈起。西方理性传统认为欲望是理性主体的欲望,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欲望。欲望的肇始是因为匮乏,所以欲望是非理性的,是需要主体去克服和压抑的,德勒兹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策略。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了欲望机器的概念,在他看来,欲望机器是生产性和社会性的,欲望机器是社会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在欲望机器的概念之下便有了欲望机器的“机能性配置”的概念,而文学机器的概念就是从欲望机器概念之中引申而来的,文学作品是欲望表达的机器,机器是靠配置运转的,而配置是集体性的。德勒兹认为因为不具备表述的条件,文学巨匠在弱势文学中并不多见,弱势文学的表达是群体性的,代表了一个弱势族裔的声音,这也正是弱势文学的优势和革命性所在,“文学正面的肩负起这种群体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表述行为的角色或者功能,积极的团结精神产生于文学。”[11]德勒兹所提出的“表述的集体性配置”是和德勒兹的反主体倾向相符合的。鲜明的反主体倾向在德勒兹的一系列著述中都有呈现,在《千高原》等著述中提出的块茎、游牧、精神分裂分析等概念,都打着消解主体的旗帜。传统的主体在德勒兹的哲学中被解构与消解,主体消失了,只剩下表述这种行为,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主体的语言,整个表述的表达不再代表主体。在弱势文学中,即使弱势写作者主观上是要表达主体,但是由于主体身份的消解,叙述者已经成为集体性配置中的一个零件,他所表达的是整个弱势族群的欲望,代表了一个集体的声音。
三、女性文学中语言的弱势化使用
辩证地解析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是理解弱势文学的重要基点,作为一种典型的弱势文学,女性文学中并不存在对语言的强势使用。德勒兹认为,强势语言是占统治地位的、与权力相关的支配性的语言,它的使用是和政治领域密切相关的,因此强势语言具有稳定性和同质性等特征。实际上,在德勒兹的语言思想中并不存在多种语言,只是语言的使用方式不同罢了。自从女性文学诞生以来,在女性文学中,作家们一直试图通过在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的强势化使用的氛围中开拓性地建构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的弱势化使用方式,在文学界谋得属于自己的位置,从而使女性文学占有一席之地。
女性文学中语言的弱势化使用主要建立在强势语言中,女性文学具有弱势文学创作中对语言的弱势化使用的表征,即“通过对语言内部因素的反复变动—语法、句法、语义不规则使用,重读或韵律意想不到的强度,旧词新意,意象的增生等方式实现。”[12]在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界,文学创作通过一套所谓规范性的语法、语义、句法和词法规则,隐形地树立起一种文学话语中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根深蒂固的,本质上具有稳定性特征。语言的这种强势化使用限制、控制、指导着文学创作语料,从而彰显、支撑、维系着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模式。为了对抗这种既定的强势语言规则,女性作家通过在语言内部颠覆隐含着权力关系的语言结构,将强势语言进行弱势化使用,创造出一种所谓的“外语”,一种“生成—他者”与“生成—女人”的语言模式,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弱势话语,生成一种异于主导性语言体系的逃逸线。在后现代女性文学和后殖民女性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的对句法规则的“破坏性”使用和赋予旧词以特定的新意等创作手法,这些所谓新颖的创作手法并非是文学创作中形式上的美学实验,而是体现出德勒兹所言的语言中充满权力关系,语言成为一种“行动”,演变为一种带有隐含意识形态的能指,通过对语言的弱势化使用,不断地在语言内部解构语言中隐含的权力关系。
在创作中对语言进行弱势化处理和使用,需要颠覆和消解主导性文学创作中惯用的语言的强势化使用模式,由此解构固有的权力关系模式,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体系,隐形地建构出一种“生成—弱势”,以此对抗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的强势化使用趋势,是内在于女性主义中的一种弱势化运动,而女性主义本质上即是一种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的弱势运动。实际上,尽管这种弱势运动要求赋予女性权力,但是,女性别无选择,她们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男性。在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试图通过对语言进行弱势化使用,对抗既定的社会权力关系模式,或公开或隐性地挑战男性话语的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自己的诉求。就此而言,女性文学创作中语言的弱势化使用从属于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作家以此对抗拥有强势话语的、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强势文学”。在传统的男性文学统治内部缔造出具有弱势文学特性的、生命力顽强的女性文学。
综上所述,女性文学自诞生伊始,就作为一种“弱势文学”而存在着,是女性在男性语言内部缔造的文学。在男性文学长久以来营造出的“人为的辖域化”内部,通过不断地对文学创作语言进行“生成—弱势”,施加一种特定的女性主义斗争,从事实现文学创造中的“解辖域化”。
[1] Deleuze,Gilles & Félix Guattari.Kafka:TowardaMinorLiterature[M].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16.
[2] Goulimari,Pelagia.AMinoritarianFeminism?ThingstoDowithDeleuzeandGuattari[J]. Hypatia,1999 (2): 97-120.
[3] 德勒兹,伽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390.
[4] Young,Eugene B.TheDeleuzeandGuattariDictionary[C].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13:45.
[5] Buchanan,Ian and Claire Colebrook.DeleuzeandFeministTheory[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27.
[6] 王彦军.德勒兹弱势文化视域中弱势概念的诗学解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31.
[7] 由安立.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初探 [D]. 山东大学,2012:18.
[8] Bougue,Ronald.Deleuze’sWay:EssaysinTransverseEthicsandAesthetics[M]. Aldershot: Asgate,2007:23.
[9] 张向荣.传统精神与现代视野——女性文学之辩证[J].外国文学,2012(11):117.
[10] 陈橙.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从肖瓦尔特的女权主义批评看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J].中华文化论坛,2007(4):91.
[11] 德勒兹,伽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36.
[12] Smith,Daniel W & Henry Somers-Hall.TheCambridgecompaniontoDeleuze[C].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2.
Feminist Literature: As a Form of “Minor Literature”
REN Hong-ling,WANG Yan-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The important concepts minor,becoming,territorialization,deterritorialization concerning Gilles Deleuze’s thought of “minor literature” are key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dialectic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feminist literature and minor litterature. There is a certain underlying connections between feminist literature and minor literature. Feminist literature is a form of minor literature,which embodies in three aspects: becoming-woman,the three characteristic of feminist literature as minor literature,and the minor practice of language in feminist literature. Exploring feminist literatur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or literature can provide new way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feminist literature.
Feminist Literature;Minor Literature;Becoming;Minor
2015-03-06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SQ1411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4YJC752022)。
任洪玲(1983-),女,河北衡水人,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彦军(1979-),男,河北廊坊人,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文学博士。
I109
A
1001-6201(2015)04-0147-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