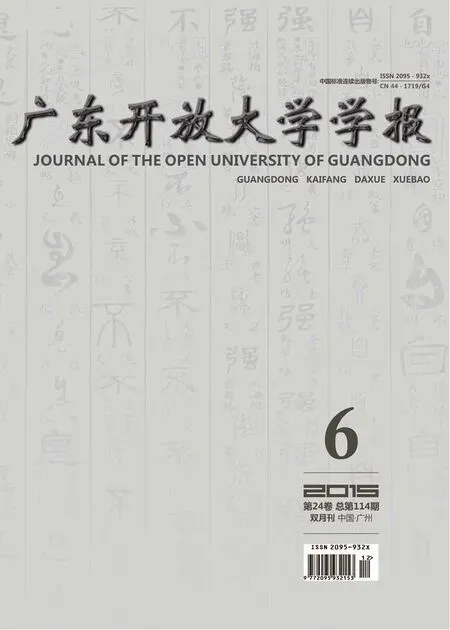公共管理价值新视角——论生态思维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2015-03-21陈琼
陈琼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
公共管理价值新视角——论生态思维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陈琼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
生态思维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管理系统整体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它要求重新审视公共管理的价值倾向,追问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并认为生态决策是政治民主的新形式,政府应该带头遵守环境道德。生态型政府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行政行为的实施和绩效评估等公共管理全过程中“生态化”,以生态社会的建设为终极目标。它与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价值逻辑一致。
公共管理;生态思维;生态价值;生态型政府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地球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生态思想逐渐渗透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发展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目前,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因此,要求公共管理具备“生态思维”的呼声日益高涨,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管理职能的一种期盼:既是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也是生态型政府。这也许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的公共管理价值的又一重大变革,也是国家治理的新内涵。
一、公共管理生态思维的内涵
所谓生态思维,是运用生态学的概念、观点和原理来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它是从系统整体的视野出发,关注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以其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思维方式。按照包庆德教授的观点,生态思维具有四个特征:人与自然依存关系的整体性与进化的协同性;人与万物存在关系的多元性和价值联系的多样性;自然界自组织的开放性与物质能量转换的循环性;地球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认识过程的无限性[1]。这些特征表明,公共管理活动不过是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一个环节,本质上毫不例外地受生态规律所制约,公共管理者应该怀着敬畏大自然的心态、顺应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流的方向和规律开展管理活动。与传统的公共管理居高临下地俯瞰自然、制定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公共政策与行为不一样,具备生态思维的公共管理把自己看做生态系统整体的—部分,追求社会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前提下的兼顾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公共管理中的生态思维也可以理解为:它是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以生态社会的建设为总目标,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协调,关注自然与人类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共同演进、共生共荣的可持续发展、蕴含生态价值观的思维模式。生态的公共管理是将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当中,改良传统的行政管理的实践框架和知识框架,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和美丽。把生态学知识与公共管理知识结合起来,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行使公权力,使权力行为更加科学合理,不但解决环境问题,还针对行政管理本身和社会其他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具体来说,公众对政府的定位有了全新的诠释: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表现出服务型政府,政府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出责任型政府;政府在公共决策中涉及与自然的关系时表现出生态型政府。具备生态思维的公共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建构节约型社会,打造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前提;相反,无休止的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就等于解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具备了生态思维就会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有可能积极采取节约有限资源、尊重生态系统的态度和行为,理性对待各类资源与生态系统,促使其朝着良性循环有序运作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会使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越来越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会不断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2]
传统的公共管理思维具有明显的单向度,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低估自然的复杂性,高估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在社会发展中只注重对自然的单向征服和索取,几乎从来没有考虑生态系统资源利用以外的各种价值;在制定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时,习惯性地将人类自身的利益放在所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之上,缺乏保护和建设等维护其平衡的自觉的生态意识。“环境危机是经济与政治发生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变迁造成社群消失、价值观狭隘化,公民日益丧失通过民主过程作出反应的机会。”[3]把人类地位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价值观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客观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多样价值的联系,反而损害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利益。公共管理的生态思维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视作相互联系的但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系统的各个要素都要协调有机地发展,而不再是单单看重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因此,用生态思维来指导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和生态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有利于政府在行使公共行政时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更好地行使行政职权。目前,各国政府运用生态思维来指导公共管理行为是大势所趋。
二、公共管理的生态价值观
如果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把政府从管制转向服务,实现了价值观的根本变革,那么,某种意义上具备生态思维的公共管理又是一次价值革命,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管理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这种公共管理的新价值将促成如下观念的大转换:
第一,否定盲从GDP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追求有幸福内涵的有质量的经济发展。在传统经济中,经济增长是无条件、永恒追求的目标,但是,经济增长必然会消耗资源,损害环境和下一代人的利益,所以,经济的无限增长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历史证明,经济增长了,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危机、社会公正(平)、贫穷、毒品等问题却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增长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是独立于生态系统以外的,其结果就是作为原材料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自然价值被低估,被随意丢弃、浪费和污染。我们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错位的GDP至上的价值评判体系。传统GDP核算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没有扣除作为中间投入的自然资源成本,也忽略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自然资源所存在的价值,对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及价值取向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它所衡量的是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得到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至于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增加社会福利(正作用)还是减少社会福利(负作用),是有利于发展还是不利于发展,它并不加以辨识。我们认为,传统管理追求的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没有节制的完全市场竞争和对经济增长的绝对追求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政府调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它可以调节“市场”,但调节不了单个“理性人”以及它们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形成的整体“市场力量”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破坏。生态系统承载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与资源是有限的,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减少生物的多样性或减弱生态系统的功能为代价的,这种代价终究会以其他方式反馈到人的身上[4]。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徒劳的。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更不是所谓的一边创造财富,一边破坏环境。公共管理应该是提高公民生活满意度、追求社会尽善尽美的行为——保证生态系统总价值的最大化。当人的利益与生态系统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不是向任何一方的偏斜,而是寻求两者的最佳结合点,确保人的基本利益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少地损害自然环境,因为好的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的美感、幸福感与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扩大基层民主,推进生态决策。公共管理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人民主权和意愿,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政治、行政与政策等信息的公开化,遏制政府及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去除行政低效,确保公众能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管理,保障利益不受侵犯。尽管传统的公共管理也是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己任,但是,作为生态系统整体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大化,政府职能有限,有可能既有的政策跟不上变化,因此,有必要把公共政策的制定自上而下的顺序颠倒过来,让包括生态科学家在内的民众和社群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行政目标的实现和效能的发挥日益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问题几乎是所有政治和行政举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生态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党派或政府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并折射其执政能力。因此,改变过去忽视环境问题的状况,把自然环境以及资源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倡导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生态思维来指导公共管理是顺应自然规律和管理学原理的智慧选择。
生态价值指导下的生态决策是政治民主的新形式。与传统民主管理相比,两者都赞同法制化和决策科学化前提下的公民政治生活参与,主张政府为民众的利益而开展管理。公共管理的生态思维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民主行政管理是生态行政管理发展的前提。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态参与的政治民主是一种积极民主,是在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行政习惯。生态决策对环境的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最高,能找到公众利益与环境利益的最佳结合点。生态思维指导下的公共管理强调公众参与,重视基层民主。“生态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生态公民权利的一种重要体现。它是指公民及公民组织通过参加生态管理听证会、提起生态行政诉讼等形式评议政府生态管理绩效、参与政府生态行政决策和监督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活动。有效的生态政治参与既要取决于政府的自觉,又要取决于公民的自觉。”[5]这种政府与民协作的管理模式能使政治、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全面发展。
第三,讲究环境道德,构建责任政府。关于责任政府的内涵,很多学者已做了较深入的研究,笔者在此只强调政府对环境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众所周知,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是我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它涵盖了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环境道德等方面。由此可见,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遵从环境伦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环境伦理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提出人对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对人同样的道德义务,赋予自然作为道德客体的地位。这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补充和升华。此外,政府是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管理者,负有保障与维护的责任。因此,政府在科学决策和社会管理中应该以身作则、敬畏自然,并促成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觉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或伦理规范,使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人们认识到我们拥有从自然那里获取各种生活资料的权利的同时,还肩负维护生态平衡的义务。简而言之,必须把生态责任当做政治责任来对待。“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性’(即产权界定不清晰)特征,如同其他公共物一样,保护环境需要公共伦理即以道德情怀关爱自然。”[6]各级政府把追求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作为价值目标,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相当数量的人对环境保护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和自律性,只把环境当作是与己甚远的公共物,责任意识淡漠,更谈不上把自己当做主体,意识不到环境利益遭受破坏时,可以对环境破坏者提起控告,维护自己的权益——享受自然资源给你带来福利的同时,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明确,政府官员不仅是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主体,还是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加强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建设离不开决策者,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各级政府应该以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带头运用科学发展观和环境伦理规范来指导、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环境伦理水平。由于公共行为具有道德示范性,因此,政府还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听证议政、民意调查等多种途径建立和完善各种有效的环境伦理责任监督机制,促成整个社会环境伦理意识的提升,彰显利用和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与公平性。
三、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成功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否从以管制为主向综合协调转化,能否从片面索取自然资源转向适应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在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生态型政府。“所谓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7]。它要求我们在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遵循生态规律,积极履行促进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职能,并与之相适应,积极协调地区与地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生态利益、生态利益与非生态利益的关系。西方国家广泛开展的生态政治运动是建立生态型政府的直接驱动力,而在我们国家,生态型政府的建立是自觉自愿的行为,是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现实选择,也是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发展趋势。柴秀波认为,生态型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就是实行生态管理,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的生态环境,政府责无旁贷。构建生态型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需要实现行政理念的创新、保障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8]。按此逻辑,我们认为,生态型政府必须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行政行为的实施和绩效评估等公共管理全过程的“生态化”。
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奉行生态优先的价值导向。政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必然蕴含关于自然的价值取向。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有关论述,到现代西方生态政治与环境保护运动无不如此。“与市场经济使价值观狭隘至单一的赢利指标正好相反,道德经济必须以较为宽泛的价值观为指针和目标。这些价值观将构成一个新的基础,由此审慎地应用技术,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和环境限制并因此而约束经济活动,以及建设一个具有生态智慧的社会。”[9]致力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首先需要变革的是管理理念的重构,扭转一直奉行的人是自然的主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环境价值观: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永不枯竭;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废弃物和污染物具有无限的净化能力;自然环境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是人类无偿消费的对象等错误观念。当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冲突时,能否坚持生态优先是区分生态型政府与非生态型政府的重要标志。这里所倡导的生态优先价值,既不是把人的需要和价值凌驾于自然之上,也不认为自然的价值优先于人类,而是两者的相互包容、谦让与和谐统一,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生态优先原则既考虑了生态系统的总价值最大化,也兼顾了人的价值和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肖显静教授认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单个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包括该经济主体在内的众多经济主体承担后果,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考察单个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框架——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关联[10]。所以,我们认为,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蕴含生态伦理的价值诉求,以确保环境责任的落实。这一价值原则应该始终贯穿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法律制度体系、道德行为规范和环境管理体制之中。通过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为生态型政府的建设保驾护航。
第二,公共行为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行为。传统政府与生态型政府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后者则只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者,最终以政府活动主体——行政管理人员的行为表现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的行为都是符合生态规律制约的生态行为,是出自生物的本能和物理化学规律的使然。公共管理的生态行为是指仿生态的、尽可能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流方向的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公共决策行为。它要求我们放弃那些与生态目标不一致的行政目标与政治目标,制定生态目标、政治目标和行政目标一致的共同纲领,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呈现给大家。或者说,把生态民主和生态服务作为优先的价值考量,分别作为公共决策和行为的起点与终点。市场机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往往带有很大的趋利性与盲目性,势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日益枯竭;与此同时,为了追求行政目标和政治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大搞基本建设和工业投资,对环境保护形成极大的压力。而政府在生态管理职能上的严重缺位、以邻为壑、条块分割、过分依赖行政审批等导致宏观调控失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政府管理为主导,市场调节机制为辅的模式,才能有效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管理生态行为有很多,例如,在机构设置上仿效美国成立环境政策办公室,在管理体制上把资源的管理与使用分开,实行生态决策机制一票否决,加大公共投入兴建生态保护工程,明晰环境资源的产权和合理定价等。目前,我们认为,推行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驱动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公共管理生态行为较好的模式之一。这一举措有两大好处:首先,使企业或个人对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自已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环境和资源,从而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尽量减少对环境不必要的破坏;国家也可以从中收取一定税收,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生态脆弱地区植被的恢复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等。运用生态效益补偿金这一经济杠杆,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有效地缩小东西部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差距。其次,建立新的经济格局和价格体制。征收生态效益补偿金是考虑了环境的生态价值,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为使用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以外的价值付款,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成本计算中考虑环境的各种价值,进而使经济格局和价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建立在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基础上的企业,由于成本上升,缺乏竞争力,必然濒临倒闭;而那些污染小,对自然资源破坏少的高科技企业将得到发展壮大。这样做的结果是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价格体制的理顺,更有效地促进了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
第三,建立政府绩效评估的绿色机制和生态问题行政问责制。政府的绩效评估不应该只停留在经济效益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我们应该积极倡议尽快推行把生态效益放到首要位置的绿色GDP的考核,它是生态思维的公共管理举措之一。建立绿色GDP绩效考核体系,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通过民主程序,公众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绩效的考核等,可以有效加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导向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举既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绩效价值观,又有利于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从生态价值层面看,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组织,应是自然环境“公共物品”可持续利用的维护者,对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的诉求是行政伦理的新形式。我国的环境问题之所以特别突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缺乏生态的行政问责制。基于政绩的追求和招商引资的压力,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企业放松了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的生态行政问责制,是契合生态文明制度的内在要求。简单地说,生态行政问责制包括明确各级政府与人民是生态行政问责的主体,制定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借助组织和行政的力量对任何破坏环境和滥采滥捕的资源耗竭行为进行法律的、行政的处理。进一步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树立生态责任与经济发展责任同等重要的认识,把环保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中去。
生态型政府的内涵是具备生态思维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以生态社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既注重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也满足环境的需求;生物的多样性与内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类生产与消费体现生态智慧,实现废物零排放或再利用。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可再生性资源基础上的并且消耗的速度小于自然再生速度,是自然、社会与公民的全方位协调发展。除了制定经济政策时考虑环境影响,保证国家之间、代际之间对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外,它还考虑了人的健康、接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的质量、社区的文化以及人的幸福度等指标。我们不但要求改变传统的经济系统,而且还要求建设适应生态社会的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体制。在这个社会中,政治制度、经济手段和社会游戏规则都进行了重新设计。生态系统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内在价值。生态社会不谋求经济的绝对增长,只是顺应生态规律生产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在社会的、生态的发展中谋求个人的兴趣、发展机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换句话说,政府公共管理的逻辑应该是把包括人在内的整体生态系统效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不仅是单纯的人的经济效益。从长远来讲,这样做也利于人类的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位一体的总价值目标的最大化。因此,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生态政府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并具有同等价值意义。
[1][2]包庆德.绿色视界:生态思维与节约型社会[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3][9]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M].梅俊杰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93,80.
[4]葛永林.绿色经济学思想及方法论特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5]黄爱宝.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公民养成的互动方式[J].南京社会科学,2007,(05).
[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61.
[7]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01).
[8]柴秀波.思维方式的演进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10]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15.
(责任编辑: 楚和)
A New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Values
CHEN Qiong
(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 Guangzhou,Guangdong, China,510091)
The ecological thought try to maximize overall value and interest of both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t requires re-examining the value tendency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ates that ecological decision is a new form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to comp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society, ecological government should centers on “ecological proces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ublic management, such as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value logic of an ecological government is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service oriented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ve; ecological thought; ecological value; ecological government
D035
A
2095-932x(2015)06-0105-06
2015-11-04
陈琼(1962-),女,广东湛江人,广东开放大学法律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