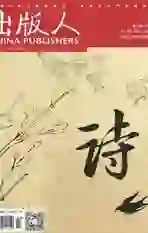不真实的热潮
2015-03-20邢明旭
邢明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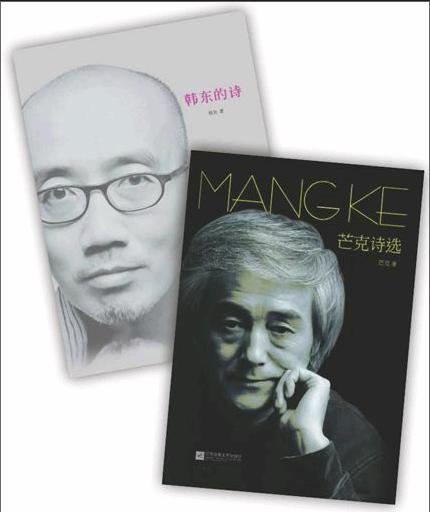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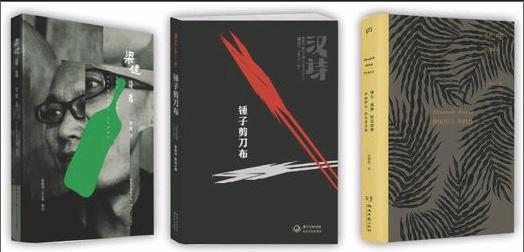
2013年的春夏之交,一首首抑扬顿挫的诗歌仿佛久违的乐章,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蓦然响起,中断了20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在那个傍晚“复活”了。而一本承载无数记忆与感动的《白天与黑夜的信使》作为该活动的纪念诗集同步上市,把读者对诗歌的热情推上了一个小高潮。
这并不是诗歌在近年来唯一的惊艳亮相。2010年《非诚勿扰2》的片尾,川川在其父的人生送别会上念诵的一首《见与不见》让无数人的目光望向了那个位于遥远西藏南部门隅纳拉山下的小山村。尽管该诗随后被证并非出自六世达赖之手,但仓央嘉措的名字还是如初春的燕子般飞进了千家万户,一场旷日持久的“仓央热”也接踵而至。
从仓央嘉措、夏雨诗社到顾城、海子,再到年前火到爆的余秀华,沉寂了20多年的诗歌在近几年像打了兴奋剂,不断跳出禁锢其多年的尘封结界,在大众视野里欢腾雀跃。爆棚的存在感甚至让不少人产生了诗歌盛世再临的错觉。
但在诗歌出版从业者看来,转瞬的复苏远不能与曾经的繁盛相提并论。保持适度的冷静,在细水长流中寻觅诗句下蕴藏的精神力量,诗歌这艘小船才能在文学浩瀚的汪洋中继续远航。
守望“无用的”诗歌出版
2012年9月,由“楚尘文化”策划的《新陆诗丛·外国卷》推出后,诗人于坚发微博盛赞“现在谁还出诗集呢?唯有楚尘!唯有楚尘!”2013年1月,“楚尘文化”再推《新陆诗丛·中国卷》(第一辑),汇聚了韩东、于坚、西川、翟永明、杨黎、春树等六位优秀诗人的最新力作。《新陆诗丛》出版后引起业界关注,其策划人楚尘也是一位诗人。他告诉记者,《新陆诗丛·外国卷》其实早在2000年就已着手,几经波折后得以顺利完成,并以《新陆诗丛》的名义陆续推出。据楚尘观察,在2012年以前,新世纪的诗歌出版基本上是缺席的。《新陆诗丛·外国卷》旨在让人们听到世界诗歌的声音,而《新陆诗丛·中国卷》的出版目的是梳理中国当代诗歌脉络,系统完整地介绍当代优秀诗人及其作品,力图填补当代大陆诗歌出版的空白。
楚尘透露,名声在外的《新陆诗丛》其实销量并不乐观。他坦言,想靠诗歌出版赚钱是不可能的。虽然被誉为“中国为数不多依然坚持为诗人出版诗集的人”,但楚尘自己却觉得受之有愧。在他看来,读诗的人和不读诗的人,在外表没有什么差别,不能用读不读诗来要求、评判一个人,但诗歌确实能让人的内心变得更丰富,拓展精神的疆域。“虽然诗歌在当代社会被视为无用的东西,但是出版好的诗集本来就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目前,“楚尘文化”仍坚持《新陆诗丛》的继续推新,坚持求质不求量,宁缺毋滥。
和楚尘文化一起默默守望诗歌出版这片净土的还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公司等出版机构。
在诗歌出版这块不大的领地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耕耘可谓持之以恒,虽不耀眼,但是却一直在稳步推进,多年来出版了包括顾城(选本及全集)、海子、西川、多多等国内诗人及盖瑞·斯奈德 、罗伯特·哈斯等国外诗人在内的优秀作品,翟永明、王小妮等诗人的作品集正在编辑中。
长江文艺出版社作为国内最大的文学类出版社之一,多年来也在诗歌出版领域颇有建树。据长江文艺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主任沉河介绍,2013年初,该社编辑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收录300多位诗人的近万首优秀新诗,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诗歌选本。另外,该社打造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旨在推出当下最具实力和创作活力的诗人,目前已出十六种,收录了包括雷平阳、余笑忠、哑石、桑克等多位优秀诗人的作品。而2013年6月出版的《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则是对中国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的一次集中检阅。
平静湖面上的涟漪
最近诗很火。
微博、微信、门户网站,但凡看得到文字的地方就能间或瞄见它的身影。纸书也不甘落寞,《万物静默如谜》《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给孩子的诗》《顾城的诗 顾城的画》《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都达到了数万册甚至近十万册的销量。
乍看下,诗歌确有复兴之象,但身处诗歌出版第一线的从业者们愿意用更为平和的心态看待这一切。“关于近年来的诗歌出版,有人用复兴、繁荣等词来形容,我则认为,这只是一种复苏,是在多年的萧条、疲弱之后的一种回阳。”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于奎潮指出,“诗歌出版不需要热潮,而是扎实,慢慢地用心去做。热潮往往让人联想到后面的退潮。”
“仅仅通过几年的变化来判断诗歌是否复兴并不准确。”沉河指出,唐宋之后,诗歌长期沉寂。而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尽管创作队伍愈发壮大,但以武侠、玄幻、盗墓、穿越等为代表的类型文学抢占了纯文学固有的阵地,诗歌的日子并不好过。“只有如北岛、顾城、舒婷、海子等经典诗人的市场影响力犹在,其他诗人的诗集则少人问津。”
对于这个观点,浦睿文化副总编余西表示赞同,“从国内诗集的销售情况来看,远远谈不上热潮。除个别诗人和诗集外,更多的诗集仍然无法知晓,被人遗忘,这是事实。”他指出,最近几年,读者的阅读趣味发生着变化,对短小、碎片化的读物开始感兴趣,短篇小说、情感治愈类的散文都卖得不错。“在这种趋势下,诗集作为之前出版门类中的冷门,比以往的销售情况要好很多。”他指出,《万物静默如谜》的畅销让更多的出版社看到了诗集畅销的可行性,而欧美经典诗人的诗集销售情况还算理想,但这一切都无法与1980年代的诗歌热潮相比。“那时候,诗歌在很多人看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诗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偶像。而现在,诗集离人们的生活还是越来越远。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余秀华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触及到了诗歌圈外。“湖北的一家中学的所有语文老师就在课堂上朗诵了楚荆都市报上刊发的余秀华诗选。”沉河告诉《出版人》,诗歌和事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深入人心的清晰的诗人形象。“这些事件就像一颗颗石子,将原本平静的湖面上激起了阵阵涟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余秀华和仓央嘉措没有改变我们的诗歌,而是我们发现了他们。诗歌长久以来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农民和脑瘫是余秀华揭不掉的两条标签,有些人想避开她的身份而来谈诗,这是不现实的,诗和人不能分开。”沉河指出,陶渊明的诗之所以优秀,与他的个人形象密不可分,屈原如若没有投江,他的魅力就将打折。“对于余秀华来说,恰恰因为她身上的标签,使得她的诗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
文学没落 如何卖诗?
诗人编辑诗歌就像剑客铸剑。
“诗人从事诗歌出版,在信息掌握、资源获取方面可能略有便利,对国内外诗人的作品也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作为诗歌的读者,对于读者的需求也会有一定的感知。”于奎潮指出,但诗人如果不能把个人的爱好、趣味和目标读者的需求做对接,过度沉溺于自己的趣味,优势也可能会变为劣势。“做书可以体现编辑的意图与追求,但编辑首先必须有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意识,必须明确,做书是做文化,也是做产品,需要考虑接受者和市场的反应,这既体现在诗人人选及其作品篇目的选定上,也体现在装帧、设计风格的选定上。”
余西也认为,诗人或者诗歌爱好者做诗歌出版并不一定带来优势。“做出版最可怕的就是,编辑经常把‘读者与‘编辑这两个角色相混淆。诗人做编辑更容易如此,从而受限于自己的阅读趣味。”他指出,做诗歌出版重要的不是编辑是否是诗人或诗歌爱好者,而在于编辑是否考虑过这本书的受众群体是谁。
“大多数投入诗歌出版的出版社、出版人,首先怀有的便是对诗歌力量和价值的坚信。特别是当代出版物品种爆炸,大量低质文字的消费破坏了读者的文化味觉,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一部分读者的需求层次的提高。”于奎潮指出,“在规模上,我个人的观点是宁少勿滥,要把每本书都当作一件精品来打造,包括选材、编校、装帧设计等方面,都需要贯穿‘精品意识。不仅内容可读可藏,形式上还可具欣赏价值。”
在如今这个文学“没落”的年代,如何更好地把书卖出去?
“出版诗集,要抓这本诗集本身有的特质,包括文本和作者等等。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判断,采取什么样的包装方式和传播方式。”余西指出,如果是如《奥登诗选》般足够经典的作品,围绕着经典的感觉去做就可以了,因为经典本身也是时尚的一种。“而如果考虑到作者本身在国内还不为人所知,就需花费更多的心思。首先要确定好这类书的读者群是谁,他们的审美趣味如何,怎样才能有效地传达信息等等。以《万物静默如谜》为例,我们将读者清晰定位于城市女青年,在书名上,我们没有选取辛波斯卡流传最广的《一见钟情》,也没有选择老实巴交的《辛波斯卡诗选》,而是取了一个留点韵味、带有情感共鸣度的名字。”余西说,“封面也是,灰暗中有一朵静默绽放的花朵,比较符合女性审美的图案。事实上,对于这本书前期的传播,书名和封面这两个一眼就看到的元素,帮了大忙。”
设计同样是于奎潮关注的焦点。“我们强调尊重每个具体诗人的特点,做个性化的对待,比如在设计上,回避那种多个诗人一个设计面孔的套路,尽可能通过个性化的设计,凸显每个诗人独特的艺术气质,这种做法,得到了作者和读者双方面的认可。”
于奎潮同时指出,诗歌是小众出版,在图书的汪洋大海之间,诗歌的小船仍然是孤独的。“而自媒体的兴起为诗歌出版物的推广营销提供了诸多的可能。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网上通信工具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诗歌读物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