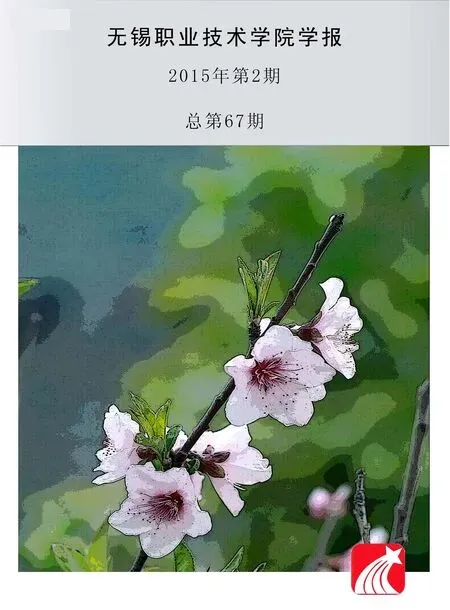《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男性价值的缺失对女性的悲剧性影响
2015-03-20操磊
操 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江苏 无锡 214121)
纵观古今中外,即便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各不相同,但女性主义作为对男权主义的抗争,似乎竭尽全力在改变这一普遍存在的事实与现象,即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发展完全受控于男性的操纵和定位,女性生存和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满足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趣味和价值体系。这一改变颇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劲势头。然而,在这种二元论思想指导下的女性主义改革之路尤为艰辛,因为男性和女性作为互立共存的生命个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女性主义对男权文化及价值的过分反击,只能带来男性价值体系的崩解,势必会进一步阻碍女性价值体系的健康发展,毕竟,价值选择以一种丰富的方式,紧紧地与人的生活和身份联系在了一起。[1]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改编自日本作家山田宗树同名小说的电影,于2006年搬上荧屏,上映之后便因其史诗般的叙事手法,浓墨重彩的声乐画面以及极富悲剧意义的女性主题而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和多方的关注。影片中的女主角松子悲剧的一生,与其说是对男权主义的强烈控诉,倒不如说是男性价值及文化缺失带来的女性悲剧。如前文所述,男权主义是男性对社会尤其是女性的“过分作为”的非理智表现,而女性主义的强盛势头使得男权中心主义得到极大的削弱,却进一步压抑了社会及女性发展所必要的男性文化及价值,造成男性价值的“不作为”,而这一“不作为”正是松子作为一个女性全部悲剧的根源。
1 男性价值的缺失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的一生是由形形色色的男人串联起来的,年幼时,父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角色,影片甚至特别弱化了松子母亲的角色来凸显父亲角色的重要性,尽管母亲有片刻的镜头,却从来没有一句台词。成年后,松子又与不同行业、不同性格的男人发生恋爱关系,这些男人如同一粒粒发光的珍珠,不时点燃松子对爱情、对人生的美妙憧憬与坚定信念,松子对每一粒都呵护备至,可这些珍珠终究是零散的碎片,无法给松子带来一整串项链的完整的幸福感。
影片中,小时候的松子活泼可爱,年轻时的松子善良纯真,中年时的松子敢爱敢恨,老年时的松子依然追求梦想。松子的一生是作为一个女性所具备的所有美好特质品格的写照。这样一位至真至善至美的女性却于晚年死于乱棍之下,让人唏嘘不已。然而不难发现,整个影片中,“我回来了”这句简单的台词贯穿始终,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不管是来自父亲、弟弟还是恋人们,让人揪心不已。松子每个人生阶段的悲剧都根源于同一个事实,即男性的不回应或男性价值的不作为。
松子临死之前还曾写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更让观者灵魂战栗,沉思良久。这也是松子的真爱八女川彻也的自杀遗言。如果说八女川彻也是因为无力回应松子的爱,选择懦弱逃避而说出这样的话,那松子这番话则是出于对男性的无奈以及不满而进行的令人为之动容而又肃然起敬的控诉。
1.1 男性父爱价值的缺失
女性主义思想尤其是文化女性主义特别强调女性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母性或母爱”这一特质。母爱作为女性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并没有受到很多来自理性的浸染,女性的母爱本性使其与子女有种奇妙的内在纽带,对子女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而相比之下父爱则带有更多的后天成分,父亲则更多倾向于子女的外在成长、家庭角色及社会价值。这往往使得父亲对子女内在感情心理的变化漠不关心,进而也忽略了子女的情感诉求和归属。
影片中,松子与弟弟妹妹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然而幸福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松子的妹妹久美生病以后,父亲全身心的爱都转移到了久美身上。松子作为一个小女孩的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所有来自父亲的关爱与指导都不复存在。可想而知,这对松子带来怎样的成长空虚、失落和无奈。“父亲在一个人的生长过程中是撞进他的生活中的第一个陌生人,是第一个异于自己而需要适应他、了解他、习惯他并渐渐接受他的人。”[2]父亲可以称得上是女儿认知异性,以及认知世界的开端,而松子在一开始就失去这样的机会。后来松子为了取悦和适应父亲,不惜做鬼脸来逗父亲开心,可这赢得的也只是父亲转瞬即逝的微笑。松子对病重的妹妹说: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可怜!因为松子从来没有像妹妹久美那样被父亲呵护关爱,她渴望得到父亲的爱,结果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影片特写了一个画面,就是父亲在病房照顾生病的妹妹,穿着漂亮红舞鞋的松子却一个人坐在门外,寂寞地唱着歌,这一画面看似美妙,却直击观者内心深处,那种怅然若失而又苦求不得的强烈落寞感,如同一张巨大的网,让人无处可逃。可以这样说,松子的父亲从来没有真正给予过松子完整必要的父爱,父爱的空缺,是她一生悲剧的最初根源。
1.2 男性恋人价值的缺失
松子成人之后,如同所有的少女一样情窦初开,与同校的佐伯老师互生好感,佐伯老师阳光干净帅气,与松子真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恋人,然而幸福甜蜜的恋情没有持续很久,不久松子就因为被诬蔑偷东西而被校方开除,松子百口难辩,有苦难言,而自始至终佐伯老师只是冷眼旁观,不曾关心松子,更别提为她辩护。在这场独角戏中松子不仅失去了初恋,更初尝了自我价值的冷遇。
接着松子遇到了自认为是一生挚爱的男人——八女川作家,为了维系他的作家生涯,松子不惜出卖肉体去做舞女,她飞蛾扑火般的爱情却并未赢得八女川的爱的回赠,却以八女川无情而自私的自杀而告终,亲眼目睹八女川在自己面前自杀的那一刻,松子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完了。随后,松子做了八女川的竞争对手冈野的情人,而冈野跟松子在一起的初衷却是因为在八女川面前的自卑感和对松子性感身体的迷恋,他根本就没有顾及松子作为一个女性的情感与婚恋需求,这段畸形之恋也以松子被抛弃而告终。
后来,在无比的失落和惆怅中松子又遭遇了一个社会混混小野寺,却遭到小野寺的背叛和嫌弃,带着无比的屈辱,松子杀了他,自己又想跳楼一死了之,然而强烈的求生欲望又使她继续活了下来。“眼神温柔”的理发师岛津贤治偶然间走进了她的生活,她以为自己能够从此开始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却因之前杀死小野寺而被警察追捕入狱。八年的监狱生活中,她没有不安和迷惘,因为她为爱而活,幻想着出狱后能和理发师继续在一起幸福生活,然而她对爱情对幸福坚贞不渝的守护换来的却是理发师的冷漠无情和长久遗忘。
松子最后一段真正意义上的恋情是与当年的学生阿龙。长大后的阿龙变成了社会黑道分子,松子一开始就明白和阿龙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地狱,然而出于爱情还是义无反顾追随阿龙,而后阿龙锒铛入狱,松子痴痴等待,最后在接阿龙出狱时,又被阿龙不明所以地抛弃。阿龙后来自己反省说因为自己内心残缺,不敢承受松子耀眼的爱,所以才抛弃她。然而他又承认松子是她的上帝,没有松子的世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
纵观松子一生的情感纠葛,不难发现,在每一段恋情中,松子都是倾其所有,全力以赴,然而她的每届恋人要么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要么自私自利,欺骗背叛。他们都不曾对松子热烈的爱做出正确而对等的回应。“为了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男人一样平等,女人一定要走进男人的世界,正如男人也要走进女人的世界一样。一切应该是完全对称的交流”。[3]松子的问题不在于她没有走进男人的世界,相反,她竭尽全力地去理解男人世界,亲近男人世界,并试图融入男人世界。但是,那些男人却始终没有为她敞开心扉,勇敢回应她,甚至故意抗拒及打击她的爱。男性在恋爱中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进一步加深了松子一生的悲剧。
在恋爱的长河中,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长河两岸的风景,缺失哪一岸都无法保持恋爱关系的完整,在“女权主义运动”呼声震天时,作品的主题创作都围绕着男性,由重视英雄式的男性,到漠视男性,讥讽男性,再到关怀男性,对男性的认识也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日趋全面,对男性的情感也随之深沉。[4]而这一深沉正体现在对男性价值的呼唤方面(这一呼唤不同于传统的男权主义的肆意妄为,而是要求在两性平等和谐下的男性价值的正确作为),在恋爱方面即为对女性情感的关注,与女性进行深层次的灵魂对话。
1.3 男性社会教养价值的缺失
传统的价值观念倾向于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在负责全家人的饮食起居的同时,还要对子女进行社会价值观、行为方式、态度体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教化和培养。而在一个男女平等的健全社会,子女抚育工作是由男女共同完成,如果说女性注重子女内在情感的培养,那男性更侧重子女社会道德及价值标准的塑造。
松子最后被深夜河边玩耍的孩子们乱棍打死,这一情节的设置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男性社会教养价值缺失的必然结果。松子作为女性试图对这些夜半不归的孩子进行行为上的矫正,这显然是在履行一名女性对孩子的社会教养价值。然而,此情此景下,男性角色空缺的设置让我们更多反思:单凭女性的社会教养价值,是无法给孩子们提供正确的行为及价值教化。那些年轻的孩子如果得到了正确的社会教化,表现出来的应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而非嘲讽和暴力。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松子的死是对男性社会教养价值缺失的终极控诉,更是一种深远的呼唤。
2 结 语
片尾中,松子的侄子阿笙反复强调,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松子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可是松子的一生却是一出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剧。中国当代女作家王安忆这样说过:“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切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地,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多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渺小劳动……事实上,佩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因此,社会需要的不是冷漠的英雄式男人,而是能够理解女性,与女性有效对话的现实男人。松子作为一个女性的价值实现过程没有得到对应男性价值的释放,或者说男性价值的缺失也使得女性价值无法欢欣呈现。
[1] 王军.现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性价值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7(12):34-37.
[2] 王富仁.母爱·父爱·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谈[J].云梦学刊,1995(2):49-57.
[3]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77.
[4] 何婷.女性视角下的男性观照——论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塑造[D].湖南师范大学,2008.
[5]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J].武汉:大学教育,2009(1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