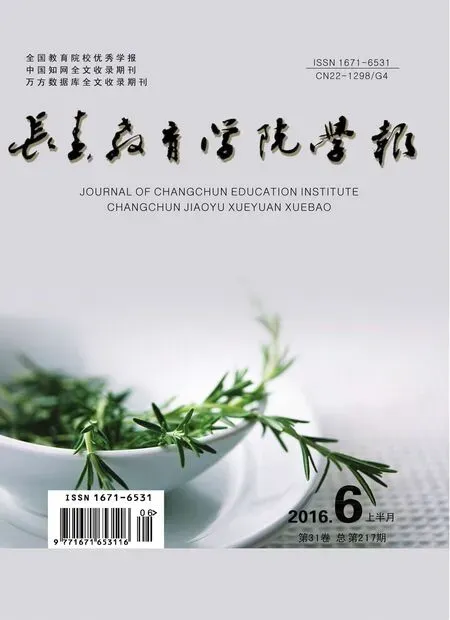生态批评发展简述
2015-03-20乔世燕
乔世燕
乔世燕/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800)。
长久以来,人们受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理所应当地以为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界,使其服务于人类自身的需求。然而人类在发展所谓的文明的同时,却忽略了自然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自然的过分使用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报复。正如在 《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生态批评便是在地球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批判思潮。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王宁讲道:造成生态失衡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二分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把自然看作为可以与人类社会分离的对象,人类可以对之任意征服索取,这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而作为生态批评家来说,他们采取了消弭人类与自然的鸿沟的方式来试图解决人类生存的环境,认为文学本身是取法自然的,把来自自然的东西回归自然也是一种消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途径,以文学融合于自然的整体性来唤醒人类的自然生态意识不乏为一种可取的方式。[2]
虽然关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话题早已有之,并非新鲜话题。但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尤其在最近两个世纪,这个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美学学者曾繁仁指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协调共赢,相互促进的形态,而非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从这个层面来说,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涉及改善环境的技术和条件。[3]
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相关部门相继展开了研究工作,尤其是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医药研究等部门,同时许多研究机构包括大学都开设了环境研究项目。相比之下,文学和艺术部门在环境的研究上还没发挥相同重要的作用。而未来的环境状况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进步程度和相关法规制定,还要在根本上受到相关人文科学的发展程度的制约。如劳伦斯·布依尔2002年在北京大学讲学期间讲到的:价值观和想象力将在某些层面上更深刻地影响到未来的生态环境。
其实,“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是来源于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作为一种文化倾向的批判形式而兴起,并且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也慢慢显露出它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围绕“生态批评”主题现今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行动,比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于1991年召开了主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Ecocrit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会议;1992年成立了 “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并创办了这方面的学刊:1993年出现了第一份正式的关于生态批评文学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之后,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接受 “环境和文学研究协会”(ASLE)为“联盟小组”(Allied Group)。可以看到,生态批评在短短数年间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壮大阶段。
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对生态批评的定义是由美国的彻莉尔·格罗菲尔蒂(文学与环境教授)提出的,即:生态批评是一种“研究物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曾在1996年,格罗菲尔蒂与弗洛姆合作出版了一本书:《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书中前言部分是这样来描述“生态批评”的:“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对于物理环境和文学之间关系的一项研究;正如女权主义者从性别的层面来考察文学和语言、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团体的意识和生产方式融入文本阅读一样,生态批评采用了一种以大地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方式。”[5]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生态批评的着眼点关键在于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层面,这种关系是以大地而非人类为中心的;当然,不能否认生态批评的研究与自然科学有某些层面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仅限于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而非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6]另外,格罗菲尔蒂也说明了eco-(生态)和environ-(环境)这两个词根的区别,后者明显带有二元对立色彩和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对此,她采用了美国女权主义者萧沃尔特“三段分法”,认为生态批评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考察在经典文学作品(包括:自然诗歌、自然散文、边疆叙述、荒野传奇等)中如何重新再现自然 以及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并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重新发掘以自然为主题的作品及其作家生活的环境条件和生态意识,呼吁恢复以自然为写作主体的传统;而第三个阶段的重点是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质疑二元论、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诗学等。
现今生态批评研究的范围已经从发源地美国向世界各国蔓延,其中,在澳洲、东亚和欧洲的发展势头尤为猛烈。中国大陆和台湾一批有为的学者积极投身于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和生态研究实践中,在受到北美生态批评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充分立足本土的丰富的生态批评研究资源,积极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构建。这都是生态批评的可喜发展方向。
但是,不可否认,生态批评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生态批评家们也在积极地反思与检讨。比如,劳伦斯·布依尔在北大的演讲中讲道:生态批评与无论何种类型的环境文本可能都有关系,任何环境(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都可以成为生态批评的应用素材,它的内容包括文学(或其他艺术)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4]生态批评家们的这些举动不仅促进了自身体论的完善,无疑更加推动整个生态批评研究阵营的发展壮大。
从古希腊“万物是一”到亚里士多德的“有机统一论”,生态整体观的观念自古就有。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的生存不能离开它赖以生存的世界,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平衡,物种才得以延续、繁衍生息。那种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面,并不断向自然索取的行为必将人类的生存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而生态批评正在为人类敞开一扇大门,它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究竟是如何生存的?该如何生存?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304).
[2]王宁.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
[3]王莉娜,苗福光.生态批评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4(4).
[4]劳伦斯·布依尔,张旭霞译.文学研究的绿化现象[J].国外文学,2005(3).
[5]Glotfelty,C.&Fromm,H.(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
[6]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