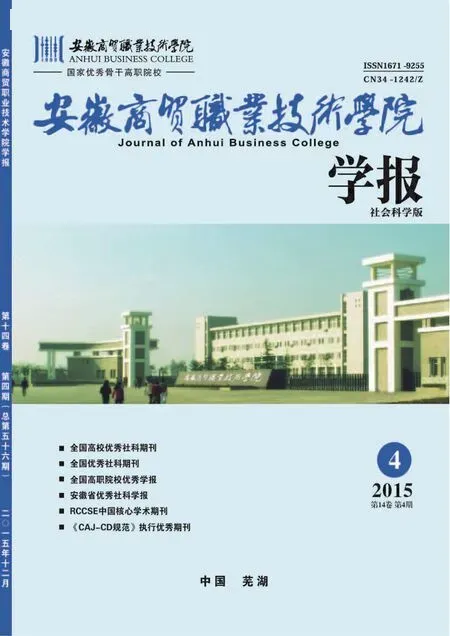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与“政治性”
2015-03-20张传霞
张传霞
(山东工商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与“政治性”
张传霞
(山东工商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其作品的特点之一在于充满了对经典文本的借用和改写。阿特伍德作品形式上的经典重构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文化的语境下与其“政治性”相关联,即阿特伍德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他者”借助文学的形式走到“中心”,传达了其为弱势群体谋求“生存”的“政治”诉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经典重构;政治性;生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也是一位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家。纵观其整个创作生涯,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戏仿、挪用和改写,表达现代人文关怀。
收在文集《好骨头》(Good Bone, 1992)中的《从前有个》(There Was Once)可看作她一生文学创作追求和创作特点的象征。文章开首写道:“——从前有个穷苦的姑娘,心地善良,长得也漂亮。她和她那坏心眼儿的继母住在森林里的一幢房子里。”[1[1]于是第一个讲故事的声音在第二个声音的要求下做了修改:“——从前有个穷苦的姑娘,心地善良,长得也漂亮。她和她那坏心眼儿的继母住在郊区的一幢房子里。”[1]接下来第二个声音又对故事叙述中的“穷苦”、“长得漂亮”、“心地善良”、“坏心眼儿”、“继母”、“姑娘”、“从前”的字眼一一提出质疑,第二个声音按照第一个声音的要求不断修改故事,最后传统的故事叙事模式被消解殆尽,只留下第一个声音发出的“什么?”的疑惑与第二个声音为什么不是“这里有个?”的质疑。“从前有个……”是典型的传统讲故事模式,阿特伍德在这个短短的小品文里巧妙地设置了两个对立的声音,艺术地表达了对文学经典质疑颠覆的态度。
一、文学经典与“政治”的同一性
以文学经典的元素进行再创作是中外文学史上历史悠久、普遍的文学现象。按照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的互文性理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2]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对其它文本的利用,这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在此意义上说,阿特伍德对经典文学的改写利用这种形式上的特征还不足以构成其独特性。从另一个层面来讲,用前人的经典作品构建自我文学景观,是否说明她文学才思匮乏?其作品是否是拾古人牙慧之作?从更深层次上来讲,借用西方古老的文学经典来传达现代加拿大人的生存体验,是否与阿特伍德立志寻求的加拿大民族特性存在悖论?若存在悖论,那么阿特伍德又何以担当“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的崇高声誉?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深挖阿特伍德“重构经典”的内涵与语境。阿特伍德之所以初踏文坛即崭露头角,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的“政治性”。加拿大著名后现代主义学者琳达·哈切恩(有的译作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对阿特伍德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她认为阿特伍德的出名“或许先是由于她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后是因为她的女权主义”随着阿特伍德后期作品的出版,我们或许还应再加一条,再后来是因为她的生态主义。尽管用各种“主义”去解读文学作品,有使文学沦为社会文化注脚的危险,阿特伍德本人也拒绝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但毫无疑问,阿特伍德本人和其作品都很难与“政治”分离。“政治性”是切入阿特伍德作品的重要路径。
阿特伍德反感被评论家贴标签,却欣然接受了评论家给她的政治标签。在格雷戈里·菲茨·杰拉尔德(Gregory Fitz Gerald)和凯瑟琳·克拉布(Kathry Crabbe)对她的访谈中,克拉布问阿特伍德如何看待评论家给她的“政治作家”的标签,她直接回答道:“我就是一个政治作家。”[4]当杰拉尔德请她做进一步解释时,阿特伍德讲道:“简单的回答是一切都是政治。任何写作都可以被分析为‘政治’。真正的答案是我这一代的加拿大作家不发展一种政治意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当一名作家,但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被自己的读者拒绝。出版社被外国人控制,或者对出版加拿大人的作品十分小心,因为他们感到加拿大人不会读加拿大人的作品。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殖民地心态(colonial mentality),即相信‘伟大的、好的地方’在别处——纽约或者伦敦。没有人生下来就有这种心态,但是我们慢慢地发展出了它。”[4]《使女的故事出版后,阿特伍德在一次访谈中谈起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她说:“我们的意思是人如何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以及权力结构如何与人发生关系。”[5]可见阿特伍德所说的政治不是狭义上的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的制度和机构,而是一种宽泛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政治领域。“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或许能更好地诠释阿特伍德所说的“政治”的内涵,她说:“我对边缘、下层逆流和置换排列感兴趣,我喜欢带走那些可能被视为古怪的或非主流的事物,并将他们带到中心位置。”[6]
阿特伍德的作品与社会活动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同步关系。这种同步关系绝非偶然巧合,而是作为一名“具有明确的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小说家”[3[7],“这位目击者所做的一切就是讲述故事,让这些故事为人所知。无可否认,这些故事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道德的权威。”[7]琳达·哈切恩指出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道德的内容便是政治的内容,因为它‘涉及权力:谁已经占有它谁追求它、它如何产生作用’。”[3]之所以琳达·哈切恩把道德等同于政治,原因在于道德背后正是一种隐秘的权力关系。除了写作,阿特伍德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政治活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事物发声。20世纪70年代以后,她参与国内、国际的社会事务,致力于改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为对抗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她主持成立旨在弘扬加拿大本土文化的阿南西出版社,组织成立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担任主席。80年代,阿特伍德一方面用写作和行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工作,一方面更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包括参加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运动,成为“大赦国际”成员“关注严刑折磨和政治监禁”。[8]
那么,随后会产生另一个问题:重构经典与“政治性”之间又有何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后现代语境中的经典解构与重构潮流。按照传统的观点,“文学经典一般是指由优秀作家创作得到学术界认可、并能够构成某种文学传统的精品”[9],其价值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热潮。这里文学经典重构包含两个逻辑层面的内涵:第一,在文学研究方面,对既定的文学经典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发掘被遮蔽的文学经典,即“拓宽经典”(Opening U the Canon有的译作“打开经典”),拓宽经典的结果导致对文学史合法性的质疑与重写;第二,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家对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进行颠覆性重写。首先在美国涌现了一批经典重写之作,著名的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 Barthelme,1931—1989)对同名格林童话的颠覆之作《白雪公主》。后殖民理论家把后殖民背景下的“重写”称为“反写”(Writing Back),如南非作家J.M.库切(J.M.Coetzee,1940— )对18世纪作家笛福的经典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 Crusoe,1719)的反写之作《福》(Foe,1986)。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逻辑层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偶然、独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在后现代文化反传统、反权威的解构精神旨归下必然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中的一个。
文学经典成为反传统、反权威的解构文化的前沿阵地,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是一个自为的过程,而是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事实证明,经典的构成既不完全是一个根据其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也非纯粹的机遇,而是一个还有着其他意义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某类作家和作品从一开始就比另外一些人具有入选的权利,无论他们是否拥有那些内在的价值。”[9]在这个“有着其他意义程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拥有话语权的评论家、文化机构,同时还包括非文化的经济、政治的因素。因此经典的形成背后是一个权力运作机制,经典成为强化社会权力的合谋。质疑、重构文学经典即是挑战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正如乔·韦克斯尔曼(Joe Weixlmann)提出的:“当我们意识到绝大多数经典作家……都是具有欧洲血统的白人男性,并且从传统上讲,经典是经过绝大多数具有欧洲血统的白人男性一致同意的结果时,我们至少会质疑现有经典的意义和价值。”[10]
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人们更强调社会文化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关注经典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强调经典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因素,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建构的,政治和文化权力在对经典的界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典成了权力运作的产物,因此成为被解构的对象。阿特伍德幼年接触了大量文学经典,大学期间主修文学,并师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21—1991),其文学成就的显现期正好与经典解构思潮同步。可见,阿特伍德不仅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学记忆,同时也有文学理论的自觉。由此可以判断,阿特伍德借用文学经典资源构建自我文学世界,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一种借此表达某种政治诉求的自觉行为。
二、生存:经典重构与“政治”的结合点
“政治性”是对阿特伍德本人和作品特性的一种宽泛定性。其“政治性”具体体现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弱者谋求“生存”(survival)。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性”和“生存”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互为表里的一个问题。“生存”是阿特伍德在文学评论专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1972)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她认为“每个国家或每种文化的核心都有一个单一的、一元的而且是明显的象征。”[11]美国的象征是它的拓荒,英国的象征是岛屿,而“加拿大的中心象征——它基于许多存在于英语和法语文学中的例子——毫无疑问是生存。”[11]“生存”不仅是加拿大文学的主题精神,也成为“阿特伍德笔下的永恒主题”。[12]
“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中具有多重内涵。早期加拿大的移民用生命和血汗换取了在这片陌生土地的生存,然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生存的阻碍从外部因素——土地、天气等,变成了内在的、隐秘的因素。“这些障碍变得既难以辨认又趋向于内向化,它们不再是实际生存的障碍,而是我们称之为精神生存的障碍,也就是说它是超出人类基本生活任何需要的障碍。”[11]身为女性作家,在现实生活和文学阅读与创作中的经历使阿特伍德感同身受地认识到女性生存的艰难;加拿大英、法殖民地的历史和毗邻超级大国——美国的地理位置,使阿特伍德认识到加拿大民族生存的尴尬;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使阿特伍德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前景堪忧。
表现在文学形式上,阿特伍德借助“经典重构”传达寻求“生存”的政治诉求,即“经典重构”是形式、方法、途径,内核是“生存”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独特性才真正凸现出来。她不像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等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彻底消解文学经典的意义,而是继续发挥文学的社会干预功能,将文学经典放置在现代的加拿大的生活土壤中,让传统与现代、西方与加拿大发生碰撞、对话,从而产生张力巨大的现代性内涵。“阿特伍德的小说没有成为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语境的语言游戏。她向传统的文学形式提出了挑战,但并没有完全将其否定,而是在反驳和诘问的过程中重新书写。”[13]
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把文学经典彻底颠覆之后的重新建构,而是一种“向死者学习”、与“祖先”对话的协商精神。一方面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和意识质疑传统经典的权力意识和僵化模式,另一方面以谦虚的姿态借鉴传统经典提供的文学宝藏:“所有的作家都必须从现在去到很久很久以前,必须向下走到故事保存的地方,必须小心不被过去俘虏而动弹不得。所有的作家也都必须动手偷窃,或者说重新领回,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死者或许守着宝藏,但这宝藏是无用的,除非它能被带回人世,再度进入时间——也就意味着进入观众的领域,读者的领域,变化的领域。”[14]阿特伍德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说明了写作、作家与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关系,与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在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表述的观点类似: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只有具备了传统意识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具体到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处于权力关系弱势方的边缘“他者”获得发言的权力,表达了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男/女、西方帝国/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寻求“生存”的困境与挣扎。
综上所述,阿特伍德的独特性不在重构经典,也不在其人其作品的“政治性”,而在于两者的巧妙结合。阿特伍德以重构经典作为表达其“生存”主题的突破口,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他者”借助文学的形式走到“中心”,即阿特伍德借重构经典的策略成功地表达了其为弱势群体谋求“生存”的“政治”诉求。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好骨头[M].包慧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2.
[2]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
[3]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赵伐,郭昌瑜,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26-27.
[4]Gregory Fitz Gerald&Kathryn Crabbe. “Evading the Pigeonholers”. in Earl G.Ingersoll ed. ,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M]. Princeton: Ontario Review Press,1990, pp.137-138.
[5]Elizabeth Meese. “The Empress Has No Clothes”. in Earl G.Ingersoll ed. ,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M]. Princeton: Ontario Review Press,1990, p.185.
[6]Rosemary Sullivan. The Red Shoes: Margaret Atwood Starting out[M] .Toronto: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 1998, p. 54.
[7]Margaret Atwood. Second Words: Selected Critical Prose[M].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1982, pp. 203-350.
[8]Beatrice Mendez-Egle. “Witness is What You Must Bear”. in Earl G.Ingersoll ed. , Margaret Atwood:Conversation[M] . Princeton: Ontario Review Press,1990, p. 163.
[9]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294-295.
[10]Joe Weixlmann.“Opinion: Dealing with the Demands of an Expending Literary Canon”.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J].Vol.114.p. 247.
[11]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M].秦明利,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22-24.
[12]袁宪军.生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永恒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1993(2):43-48.
[13]李娟.书写与跨越: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中心的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36.
[14]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与死者协商[M].严韵,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128.
(责任编辑 刘知国)
Margret Atwood's “'Reconstruction on Classics” and “Politicality”
ZHANG Chuan-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Margaret Atwood is a famous Canadian female writer with high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er works is the borrowing and rewriting of classic works. Her reconstruction on classics is relevant to her “politicality” under the post-modern context in which deconstruction culture is very popular, in which Ms. Atwood doubts the power relations behind the literary classics in history through reconstruction, and in this way she helps those marginalized “others” walk into the “center”, showing the author's “political” appeal to seek“survival” for the vulnerable people.
Margaret Atwood; reconstruction on classics; politicality; survival
I711.06
A
1671-9255(2015)04-0064-04
2015-11-17
张传霞(1980- ),女,山东邹城人,山东工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10.13685/j.cnki.abc. 000153 网络出版时间:2015-12-10 11:37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51210.1137.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