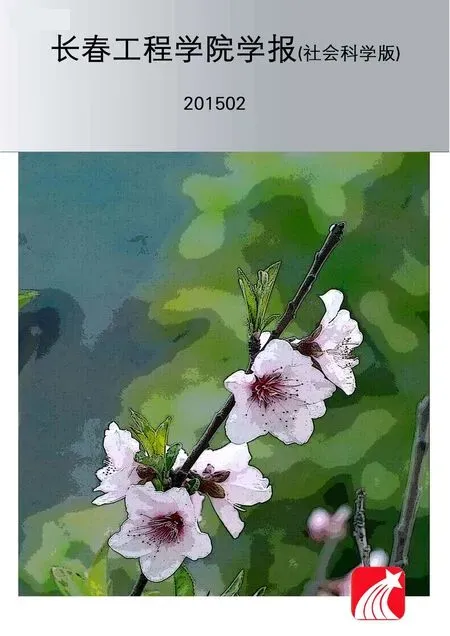食品安全问题的媒体效应——基于“道德恐慌”的视角
2015-03-20黄秋颖
食品安全问题的媒体效应——基于“道德恐慌”的视角
主要研究应用伦理学。
黄秋颖
(苏州科技学院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009)
摘要:道德恐慌是社会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其揭示了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对抗性行为和关系,其中媒介库存中固有的报道模式是形成群体性恐慌的主要来源。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需要辩证的看待新闻报道,通过了解道德恐慌运作机制来控制恐慌情绪的蔓延,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应对措施。
关键词:道德恐慌;媒介库存;食品安全
一、“道德恐慌”与媒体的关联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一步步逼近,不少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媒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在《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中用了78个媒介伦理的案例来表达大众媒介不仅提供日常操作的禁忌尺度,也建立了充满敬畏的内心评判。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会成为合力中的一种平衡和牵引,以此来改变此在的生活世界[1]。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在《道德恐慌与媒介》一书中分析研究了媒介,尤其是各种流行报刊在道德恐慌中所扮演的角色,帮助分析和理解政客,公众和压力集团如何面对社会秩序的新威胁。他认为,道德恐慌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需要与更广阔的理论思考建立起系统的联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2]。道德恐慌是分析媒介隐性意识形态导向的有利工具。同时,技术主义对社会普通阶层的大规模渗透拓展了道德恐慌的实施手段和其效果,但其同时也制造出了诸多悖论。技术主义本身不但成为了道德恐慌得以传递的新根源,主流社会控制群体和精英阶层也纷纷借用道德恐慌策略来谋取利益,而这会引发出基于尚未得到解决的旧有道德恐慌之上的新的恐慌性事件。那么,道德恐慌究竟源自哪里,它生成和消褪的规律是什么?在经历了大众媒介几十年的发展和衍生后,数字化时代下又应该如何警惕和防范?
“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社会学家卓克·扬(Jock Young)的《吸毒者》(The Drug-takers)一书中。他运用“道德恐慌”概念说明突发性的、针对假设的“犯罪潮流”或者其他假设的社会失序与社会崩溃等证据而引发非理性大众忧虑与警告,而媒介则被视为具有扩大这种“恐慌”的倾向。
道德恐慌是社会主流价值群体因感到对当下普遍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威胁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情绪。需要说明的是,“道德恐慌”中的“恐慌”并不是个人的恐慌,而是集体的或人群的恐慌。“恐慌”一词被“道德”所限定。它是集体或人群共同经历的,被某种事件共同激发的,具有共同指向性的一种社会文化或道德现象。“道德恐慌”与“道德规范”相关,通过建构偏离群体或对象、贴标签式的方法来呈现“好”与“坏”的简单二元对立。
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认为,如果“道德的”这个形容词是有含义的,那么,“道德恐慌”必须不断把自己从恐慌与其他问题中区分开来。界定一场体现道德观念的“恐慌”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必须聚焦于一个群体、一种情况或一种行动中与生俱来的、与之共存的偏离行为;二是必须涉及一种能感知到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于道德规则的全面威胁,而不仅仅是一种局部问题;三是必须最终将这种威胁投射到最基本的好与坏的词组上[2]。
但“道德恐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也不能单纯地将焦点置放在人们的焦虑之上。事实上,“道德恐慌”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演变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多种社会机构和群体互动的过程,即,围绕浮现出来的某种社会议题做出不同的反应,并展开互动和争议。
二、道德恐慌下的媒介库存
根据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博士论文《民间魔鬼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 Moral Panics),“道德恐慌”的进程模式包含首尾相继的七个环节或步骤:出现(emergence),媒介库存(inventory),道德卫士,专家(experts),处理和解决方式,消褪(fade)和社会遗留(legacy)[3]。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在对其研究中在关于“道德恐慌”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道德恐慌的“诠释模式”。他指出:“之所以提出这个模式不是因为要为其争得理论的正当性,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工具。这个工具的意义在于它对一个特定的事件所能揭示与未能揭示的一样多。”[2]在新闻报道上,媒体不仅挖掘并呈现被表征了的现实,与此同时也带有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一般而言,多数传播媒介似乎都会成为传播坏消息的渊薮,这与人们在接受新鲜消息时首先需要满足生理需求的状态不无关系。暴力的、血腥的、灾难的画面和新闻通常能够满足受众对于生理的需求。那么,在连绵不绝,甚至首尾相接的道德恐慌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衰落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对固定的生成规律。而这个规律集中体现在道德恐慌的七个进程中便是媒介库存的积累和运用。
“媒介库存”(inventory)所意指的是,大众媒介可利用的使这一问题变得显著起来的多种方式。但媒介常常通过一种模式化和象征化的报导来完成。它主要关涉到四种策略,即“夸张”,将小范围的数值和事件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扭曲”,对事件具体的物象进行有悖于原意的理解和发布;“预言”,根据已有的事件现象随意预测类似的未发生事件;“象征”,即当中下层媒介的程序化、陈规化、夸张和歪曲等特点能够被高端媒体所复制,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议题进行反应,“象征”便产生了。单一媒介的议程如果不能迫使或说服其他的媒介接受并跟进报道的话,媒介之间很难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而产生范围性的影响;只有当某一部分的利益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媒介议程时,道德恐慌的发生才有可能。
在周而复始的道德恐慌循环之中,媒介总是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内积累下的舆论反应及社会主流价值规律导向和过去所选取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模板和参考对象,对接下来的类似事件进行简单的拼贴和复制。长期以往,导致媒介库存内被标签化了各种类型事件的应对措施、报道角度和道德评价。倘若是政府机构,抑或是一些处理紧急事件的相关部门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或是不确定性事件时,一系列固定的应对措施能够给事件本身降低因匆忙和紧张带来的恐慌感和错误感。然而在面对一些新型的突发性事件中,媒介只是一味地从媒介库存中提取旧有的规律和法则,则完全无法较为完整、妥帖地报道和传递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在紧急应对措施尚未完全建立之时,民众的恐慌性情绪将会很难平复。
三、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的道德恐慌及其成因
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将食品生产加工交托于市场后,食品安全问题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从2003年初的阜阳奶粉事件到2005年初的苏丹红事件,从2006年9月的瘦肉精事件再到2008年再次爆发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几乎每年都会有全国性的食品安全危害事件发生,并且都伴有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连续性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民众对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食品选择产生了怀疑和焦虑。在食品安全规范条例无法覆盖整个中国大地之时,媒介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所采取的报道将会成为影响民众情绪的重要因素。
2008年9月,三鹿奶粉经查其16个奶粉样本中15个监测出三聚氰胺成分,并经媒体跟踪报道有多名婴儿因使用三鹿奶粉而患有肾结石病。危机发生后,国内主流媒体对该产业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报道,使得国内奶制品行业严重受挫。据统计,当年国内三大乳业公司(伊利股份、光明乳业、蒙牛乳业)巨额亏损近30亿元[4]。尽管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系列出台了有关政策清查了乳制品行业并保证了奶粉生产的安全性,但事关婴幼儿成长的问题一直持续至今。2011年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调查显示,仍有近7成的中国民众不敢使用国内奶粉。2013年3月初香港出台了史上最严限购令,严格规定在港人均购买奶粉数量。可见国内民众对于国产奶粉的质量因三聚氰胺事件而形成的恐慌久久不能散去。
无独有偶,2009年,连陷“水源门”和“捐款门”风波的饮料业巨头农夫山泉又在11月由海口市工商局爆出其旗下9种商品总砷和二氧化硫超标。事件一经披露就在全国市场引起轩然大波。虽经一系列复检结果显示3种送检产品全部合格,但农夫山泉当年的产品销量也严重受挫。而在2014年3月由《京华时报》挑起的农夫山泉“标准门”更是让该领域的龙头老大倍受打击。在不断被媒体曝光后,即便产品本身并无质量问题“虚惊一场”,民众也会因之前媒体报道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产生担忧的情绪。而笼罩在这种情绪下受困的决不仅仅是问题产业的利润和信誉问题,更是包括民众在内整个社会所滋生的不信任状态所导致的一系列恐慌情绪的蔓延。
从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报道案例中不难看出,在面对不确定事件和突发性事件时,媒体的报道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报道内容和角度也左右着民众对事件的看法。而由媒介主导的道德恐慌事件无疑是其长期形成的媒介库存所决定的。主要导致媒介库存中运作规律偏离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暧昧的真实
陈力丹在《传媒假事件》一文中提到,任何传媒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三种真实,即社会真实,即客观真实;媒介真实,即传媒所呈现的事件情境;受众真实,即受众主观所感受到的外界真实[4]。往往受众所了解到的真实与实际的本源真实大相径庭,而从媒介报道事件到受众理解新闻中却并不包含虚假成分。事实是,相关事件只有经媒介的策划、组织和推动下才能发生,即,媒介并不是在报道真实,而是在建构“社会真实”。这种“客观存在”被媒介同时建构和报道着的,是一种暖昧的社会真实。
自2003年初的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连续对国产奶粉进行负面报道后,民众对国产奶粉的印象一落千丈,不惜高价买入进口奶粉甚至前往香港进行抢购。尽管社会真实是,经过相关部门的严加把关后,国内奶粉质量连年来都未有质量不过关的现象,但经历媒体的“狂轰乱炸”后,媒介真实所阐述的是市场上的国产奶粉质量存在许多隐患。而受众解读新闻后的真实就变成了国产奶粉全都不可信。从本源真实到受众真实中,所传递的渠道越多,二者的偏差就越大。
(二)媒体的匆忙报道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报道新闻时要恪守客观、中立、平衡得标准。尽管绝对的新闻客观真实因客观条件所限几乎无法实现,主观上的不作为和尽力却实现不了有着天壤之别。拉斯韦尔指出:“传递信息,监督环境,提供教育和娱乐是大众传媒的四大功能。”[5]可见,除了发挥监督社会和预警功能,为公众的利益提供警示性的消息,尤其在面对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时,媒介为了追求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信息,往往会“抢新闻”。
在信息爆炸时代,即时消息已开始用分,甚至是秒来计算新闻的时效性。在面对突发的重大事件时,一旦媒体稍稍维持等待最权威消息就可能意味着失去了最佳报道时机而处于持续被动的状态。然而,类似食品安全问题、地震、火灾等灾难性事件突发时,倘若仅仅一味追逐新闻的时效性就草率发布新闻,很可能会因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而成为“假新闻”。在外部大环境发生大变动并且呈现出一种非常规的状态时,大众几乎完全依赖并相信媒体所发出的报道来做出判断,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而忽略对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等问题进行调查和阐述,这不但不能消除大众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反而将一些社会问题越描越黑[6]。在前文提到的有关农夫山泉的“砒霜门”和“标准门”事件中,正是媒体为了抢得第一发布时间而轻信了单一部门的数据和言辞,并没有等待和查证更权威的结果就发布新闻,导致了新闻乌龙的尴尬情况,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恐慌情绪。新闻业的本职工作仍然是服务受众,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单一的追求新闻时效性而全盘放弃诸如新闻客观性、准确性,进而引发新闻伦理等一系列隐患和问题,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三)霸权政治
在道德恐慌的发展进程中,公众会在媒体及其他国家机器的引导下,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和参与事件中对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异常举止,甚至是犯罪行为达成一致性的认识,即社会共识,同时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这些行为能够威胁,或是具有潜在因素而形成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传媒不仅具有“为善服务”的导向功能,相反,它也可以成为“为恶服务”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不加以控制,则后者的可实现性势必会超越前者占据主导地位[7]。
造成道德恐慌的原因除了真实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媒体因追逐商业利益而追逐时效性外,政府监管,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霸权控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旦发生了紧急性事件,世界各地政府的反应和应对措施似乎都大同小异。在这一方面上需要引用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常识。葛兰西认为,构成“常识”的基本元素通常是一些独立的、毫无联系的概念,这些概念有的来自现实经验,但更多的是早先的社会意识所遗留下来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痕迹”——“历史过程中留下的无数不曾经过有条件的编辑,而凝聚在一起的痕迹”。由于“常识”缺乏内在意义上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连续性,因而常常具有意义的矛盾性,并“反映衡量尺度、立场和权力上的分离”。主导意识所具有的广泛包容性,为从属阶级的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并因此限制了从属阶级自身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在语境化的判断中,普遍规则的‘例外’并不常常产生能够挑战‘统治意识’的绝对霸权的相反意识形态,并导致另一种以整个社会改革为目的的斗争策略”。相反,从属阶级的意识会隐藏并融合到主导框架之中,激烈的斗争和妥协被利益的归化和高压的政策所稀释,从属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甚至会在特定阶段形成跨阶级的联盟。这也就是“常识”在社会赞同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粘合剂的作用。
社会赞同是形成道德恐慌的一个重要条件,其一方面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解构,一方面又表现为渗透在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社会赞同是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使从属阶级自发地接受并走进主导意识形态,实现“霸权”的手段。而只有当社会大多数人都普遍的持有同一种看法,认同同一种价值规律时,突发的负面道德恐慌才会孕育。社会赞同的达成可以被看作是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协商”的产物,是道德恐慌形成的先决条件。
道德恐慌并不会因为一项政策或是个人的观点转变而消褪或是打破规律,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因一次运动或是管理就焕然一新。深深嵌于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之中,道德恐慌正在用一个惊人的速度和强度占据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最让社会担心和焦虑的并不是某一个体事件所引发的后果和不安,而是人们在应接不暇、连续不断的道德恐慌中失去了对事件的敏感度,对周遭事件的麻木或是对恐慌情愫滋生的漠然或许会很讽刺地降低一些因道德恐慌所引发的消极影响和不安情绪,但不加思考便随意臆想答案将会使得更为广泛的误解和不信任蔓延,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和动荡。
想要从根本上有效地缓解道德恐慌对于社会的危害和影响,不只是政府,也不仅仅是媒介本身,每一个参与到新闻阅读和传递的受众在解读新闻时就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而不是任由媒体的导向而动。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是新时期下每一个受众所被赋予的新要求。只有当每个人,至少是绝大部分人都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突发的群体性事件,道德恐慌才不至于恐慌,道德标准才不至于虚设。
参考文献
[1]克里斯蒂安.媒介公正: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查斯·克里彻.道德恐慌与媒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Stanley Cohen.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t[M].New York:Routledge,2002.
[4]陈力丹.试论“传媒假事件”[J].北京大学学报,2006(6):122.
[5]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6]杭羽.大众传媒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理论分析[J].今传媒,2014(10):30.
[7]郭明姬.“群体恐慌”的伦理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DOI:10.3969/j.issn.1009-8976.2015.02.017
收稿日期:2015-02-17
作者简介:黄秋颖(1990—),女(汉),江苏苏州,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76(2015)02-0060-04
Media effects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 as the view of moral panics
HUANG Qiu-ying
(Suzho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uzhou215009,China)
Abstract:Moral panic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social conflict theory.It reveals the antagonistic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of people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while the inherent report pattern in the medium inventory is the main source of mass panic.Under the situation of frequent food safety problems existing,we need to treat the news reports with dialectical view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panic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moral panic operation mechanism,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ity.
Key words:moral panic;medium inventory;food 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