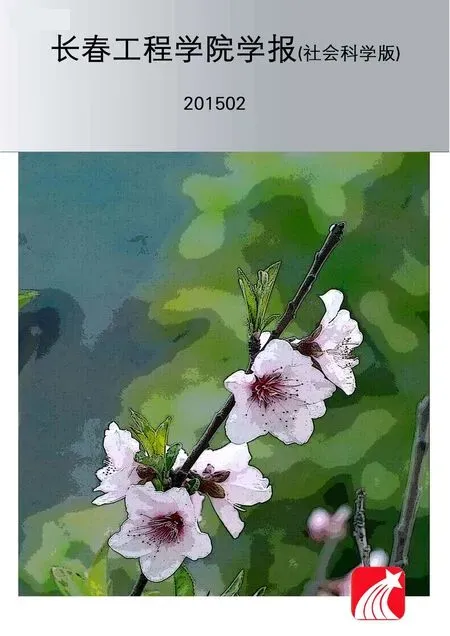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2015-03-20徐磊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主要研究中西哲学。
徐磊
(西藏民族大学,咸阳 712082)
摘要: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关键词:魏晋玄学;群己之辩;个体;社会
一、玄学的缘起
魏晋玄学的缘起,实际上在礼崩乐坏的东汉末年已初见端倪。那时,社会混乱,战乱不断,导致俊雅之士厌弃世俗,为摆脱肮脏的政治泥潭,纷纷弃世独行。因为,面对无可救药的混乱的政治和社会,那些看破红尘的士人并没有力挽狂澜于当下的魄力和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壮志,而是积极寻求避世的途径,以文人的嘲讽躲在暗处审视一切。他们放浪形骸的个性与冠冕堂皇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正统儒学的大胆叛逆。再者汉末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的动态,支离蔓延而穿凿附会的繁杂解说最终导致经学沉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下,老庄哲学的处事原则得到迅速的发展并流行。他们将满腔的苦闷与牢骚抑制在放任荒诞的行动中,从老庄的哲学中寻找自得其乐的处事原则。老庄哲学本来就是乱世之中的产物,人生的苦痛让沉溺其中的士人开始反思生命的真谛。汉魏之际的社会迫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哲学理论,魏晋玄学就是上族阶层用以替代儒家思想的精神家园。
到魏晋时期,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无道、秩序的消解,残酷的社会现实使许多无辜百姓朝不保夕,死于非命。士人们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因此对现实社会的希望完全破灭。在痛苦绝望之余,他们不得不由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转变为消极遁世的人生观。这一时期,士人深感自己的济世之志在这个黑暗的社会无法施展,在政治上感到失意绝望,于是纵情酒色,而归于消极颓废。魏晋玄学产生于社会分裂、动荡时期。面对强大的社会力量,哲人们以逃避现实的方式把握自我,这是魏晋玄学产生时的士人心态。所以,玄学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出现,并迅速风靡天下,与士人心态对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魏晋时期战争频繁,人们普遍无乐生之心,或托任达以全身,或托隐沦以避世。汉末以来,自汉灵帝遭黄巾之乱,献帝傀儡之祸,群雄并起,战乱成为最大的祸端。以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再者,汉末政治集团之间杀戮不断,民生哀悼,导致广大士人满怀悲壮情怀,眷恋个体生命价值,从而促动人们对情感的寻觅。
二、群己之辨的产生
玄学之所以最终归结到人这一主题,归结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因为“当时所谓名教与自然之异同者,从士大夫自觉之观点言之,实起于对群体与个体之着重点不同”[2]。这就提出了自然与名教之关系和个体与群体之关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魏晋时期,辨析名教与自然成为理论热点。名教代表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自然则与个体的自性相联系。因此,名教与自然之辨背后所蕴合的,乃是人的主题。”[3]伴随着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逐渐开始正统化,“群体的原则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原则,个体的存在则越来越依附于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结构”[2]。这一历史前提下,儒家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融入新的内涵,包括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对压抑个性的批评态度,对“我”这一主体的肯定等等。与实现大一统的两汉相比,魏晋时期崇尚个性更是成为一时的风气。再者,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局势下,个体生命在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如何达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成为思想家们所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而这—理论问题的具体展开即为群己之辨。群己之辨的产生有着必然性。
(一)乱世中个体存在的危机感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魏晋时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意识。众所周知,个体与群体之间从人类文明社会诞生起就伴随着矛盾而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存在着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两汉时期,当董仲舒把儒学强调的伦理关系变为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时,就彻底扼杀了人性,把人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东汉时期,儒家伦理观被提高到绝对的地位,外化为名教之治。魏晋之际,以司马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势力为夺取曹魏政权,滥杀无辜,草菅人命,那些性情刚正,为世俗所不容的士人则成为政治纷争的直接牺牲品。于是,极度的恐慌彷徨伴随着疲惫伤感的情怀开始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内心逐渐形成另一种个性,内心所隐藏着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演化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被压抑的个性相互融合,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
魏晋多故,名土常有不测之虞。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往往缺乏一种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生命个体又会导致孤独感,并伴随着一种生存境况的危机意识。当时的名人所作诗词就很明显地表现出自身的危机感。这种危机不仅根源于名教之沉沦,更是出于对个体生存的关怀。魏晋名士们的忧患意识,既包括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也包括对个体安身立命的思考。这在当时名士心中形成了解决个体与社会矛盾的焦虑。魏晋之际时势之艰险,使生命个体难以安立于世。动荡不安的人生,将个体存在的意义问题凸现出来。因此,个体既担忧自身的生存危机,又迷茫个体的生存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至始至终都是孤独的,他们独自徘徊在他之外,既希望以任自然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又因为这种方式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而难以实现。知识分子通常拥有敏感脆弱的心态,那么个体的孤独感自然而然的就萌生了。
(二)士人个体个性的宣扬
玄学作为经学的否定,必然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和张杨。魏晋时期的谈玄之风作为玄学的世俗化,是玄学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的表观。早期玄学以道家为主,从厌倦繁琐经学、厌倦政治的对立物,到中晚期转而大力吸收儒家的进取精神,为门阀士族统治阶级所认可,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中走了—条曲折的道路。以道家为核心的早期文学本来是与名教相对立而存在的,但玄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家学说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余英时先生就从儒道关系的意义上分析群己关系,指出:“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4]大体说来,魏晋六朝名士思想深处立身处世的准则是儒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十分向注个体精神自由,由此形成“动由礼节”与“性好老庄”的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在汉魏时代,由于名教礼法对仕人的禁锢相对松懈,促使人们对个性的宣扬和对精神的解放达到一个顶峰。他们遵循及时行乐的人生准则,将纵乐看成生活中的必须品。魏晋名士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感,就是力图证明自己个性的存在。他们相信,只有个体的情感表达才是真正的情感,要突破情感的桎梏,必须走出世俗名教的束缚。
汉魏之际,自然山水、风花雪夜和亲朋挚友所蕴含的情感是士人们乐此不疲、富于体验的生活元素,他们往往表现出丰富而率真的情感倾向,处处体现重情的时尚。在文学层面,他们善于“以情纬文”;而在人生层面,则表现出性情的率真。中国的山水诗歌就是萌发于汉魏之际,表现为士人们普遍喜爱的喜山乐水,追求自然美感,感受个体生命的自在自然。个体如若充分享受到精神的自由,就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寻找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或者说,建构个体的理想人格更容易吸引广大士人的兴趣。而汉魏士人构想个体人格的情感也来自多方面。首先是源于社会,士人对社会现实中发生的天灾人祸发出的内心感慨与情怀;其次是礼法层面,名教礼法的懈怠为士人产生放逸行乐的情感做了有利的铺垫;再次,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士人由于主体自觉,而自然产生率真放逸的情感。三者之间的交叉融合便成就了士人重情的时代风尚。这正好从情感侧面显露出魏晋人注重个体价值的倾向。
(三)嵇康、阮籍对个性的超越
就玄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从刘劭、钟会的“才性说”,到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从嵇康、阮籍的“越名任心说”,到郭象、向秀的“名教即自然说”,这些学说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远离一切事务和纷争,而在抽象思辨的背后,却隐含着个体身临现实困境时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在这里,让人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异”,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同”。这个共同的理论旨趣,就是他们对满足个体本位达到的精神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从刘劭、钟会到何晏、王弼;从嵇康、阮籍到郭象、向秀,尽管士人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寻求一种精神的超越,但他们的方式却又是大异其趣的。这里重点谈谈嵇康与阮籍的“越名任心说”。嵇康与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任自然,一开始就蕴涵着反对束缚人的个性之意蕴。而事实上,由于名教压抑个性,嵇阮籍一直对其抱批评之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名教不仅压抑人性的内在意愿,而且给人的思维套上了僵硬的框架,从而导致“思不出位”的现象。所谓“思不出位”,即坚持陈腐教条,放弃独立思考,其结果是扼杀—切创造性思想。从王弼要求顺应主体的内在意愿,到嵇康主张“思出其位”,个体性原则无疑得到更深层次的规定。当嵇康主张主体“思出其位”时,在逻辑上必须以个体存在的自觉体认为理论前提。而郭象在注《庄子》时,从“无待”、“独化”到“一气而万形”,万物生成演化的最终根源即“气”即“性”即“理”即“自然”。由此确立了个体感性生命独立自足的本体地位,由此探索出一条个体人生境界的超越之路。
思想自身的矛盾相斗争往往是深刻的、极富震撼力的。尤其在嵇康、阮籍的著作里,正是这种“既要抛弃社会名教而又不能抛弃它,既要任‘自然’而又不能纯任‘自然’的思想上的分裂、矛盾、对立、斗争”[5],深深地刺激和激发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体悟;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肉体的存在终将灭亡。人究竟应该怎么生存:是顺应社会现实,浑浑噩噩地过一生,还是对社会现实有所思想,面对社会现实的束缚而追求精神自由和个体人格的独立完满?是在现实社会现实中寻求超越之路,还是彻底地离开现实社会而遁入山林,两种生活之路,也是两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在嵇康、阮籍的灵魂深处发生了碰撞,产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常说,魏晋时代是人的自觉时代,是人自觉地发现自己的生命意义的时代。在嵇康、阮籍这里,他们以深切的思想矛盾和心灵震荡来感悟生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由此可见,从刘劭、钟会到何晏、王弼;从嵇康、阮籍到郭象、向秀,群己之辨已经成为当时一个富有争议的理论话题,关于他人与自我,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方面,思想家们做了多方面的探讨,而探讨的基础都离不开儒学思想,尽管竹林七贤从个性原则出发,却离不开儒学所宣扬的修己安人之思想。儒学注重群体关怀,群己之辨注重个体责任,但也因为二者相互融合吸收从而造就了更加完整的理论逻辑。同时,玄学仕人在群己关系上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做了某些调整,尤其是在对个体原则作了更深入全面的考察,力图使其获得更加适当的理论定位。
三、群己之辨的哲学基础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寻求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的本体论哲学,重在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达到超越人生之境界。最为明显的是,在关注群己之辨这一理论层次上,玄学理论的中心已由先前的本末有无之辨转向名教与自然之争,再转向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由正始玄学中的贵无论转向人性自然,由理想的圣人人格转向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嵇康、阮籍更倾向于探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名教与自然,还是个体与社会,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现实如何被个体超越,以达到身心的自由成为嵇康等人的理论追求。如果说正始玄学中,注重儒学和道家哲学的统一,那么,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名士则对正始玄学家的努力予以彻底的否定,充分批判虚伪的名教,全面肯定人的欲望与情感,极端厌恶政治仕途,而极度向往山水园林。他们或养生颐神,或放荡不羁,或任心以越名,或佯狂以避世,这些都应该被看做玄学中人格问题,由圣人到个体的一种标志。随着两汉神学的瓦解和汉王朝的崩溃,魏晋士人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个体而不是社会,在于内心而不是外部环境,在于精神而不是物质,恰好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哲学与这种时代的需求相契合。因此,当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转向个体如何安身立命的时候,玄学便必然要将关注的中心从《老子》转向《庄子》上来。庄子哲学终于经郭象等人的改造、阐释,照完了整个时代的心灵,达到了魏晋人士的人生态度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极度吻合又一脉相通。正是与这种转变相适应,玄学家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玄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对隐逸的人生态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以竹林名士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实践精神为主的独立自由的个性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嵇康“这样一个玄学人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它之注定被社会所摈弃,也就势在必然。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而感动人心;而以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而告终”[6]。
从本来意义上说,庄子哲学就是一首乱世中个体生命的悲歌。庄子哲学突出人性自然,为士人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魏晋士人追求个体自觉,从某方面来说与汉魏时代社会经济庄园化的趋势有着紧密联系。天下处于太平时,庄园则充当士族阶级的游乐场所,天下处于混乱时,庄园则又成为避开祸端、隐身自保的避难所。这样,庄园就成为士族庄园主及其宾客出入自得、进退无虞的理想天地和精神家园。因此,魏晋六朝士人个体意识增强的这一状况,是可以从经济形态方面找到其原因的。也就是说,庄园经济既为士族阶层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又为士大夫树立相对独立的人格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对于士人崇尚老庄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庄园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士族人格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为自由平等思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关系在士人之间开始形成。这也是魏晋玄学注重个体价值的思想背景。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理想与现实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只会越来越尖锐,嵇康最终被杀害,阮籍妥协求生存,其内心之痛苦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竹林七贤”后来发生严重分化,一方面表明嵇康、阮籍的这两种处世方式,在当时很难被士人所
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无奈。庄子哲学就像一面镜子,在极度复杂的环境下,让士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自身的现实处境,更加明确个体的自我意识。然而,庄子所倡导的无己无欲无求,不计是非得失的处事原则和方式,在现实中是很难付诸实践的,因此,庄子哲学被重新重视。而如何理顺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调整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仍然是玄学家们诲而不倦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总的来说,汉魏之际个体个性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名教的衰落,个体原则的融入,使群己关系获得了一定的伸张度,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道家所倡导的人性回归自然的文化风尚流行于世,社会与个体之辨,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张弛。但不管怎么样,以人这一主题为中心的思想的发展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建打下了良好的主体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达津.古典文学研究丛稿[M].成都:巴蜀书社,1987:131.
[2]郭茜.有无、自然、生命:论魏晋玄学主题[D].西安:西北大学,2006.
[3]杨国荣.群己之辩:玄学的内在主题[J].哲学研究,1992(12):28.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1.
[5]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9.
[6]卞敏才.魏晋玄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3.
DOI:10.3969/j.issn.1009-8976.2015.02.009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徐磊(1988—),男(汉),浙江宁波,硕士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76(2015)02-0032-04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alysis of “Argument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about 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XU Lei
(XizangMinzuUniversity,Xianyang712082,China)
Abstract:The three argumentative topics in the 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refers to existing and nothing;emotions and reasons;and group and individual,which has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each other.From the aspect of human being,the argument of existing and nothing is the very argument of emotions and reasons between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nature.Meanwhile,the key subject implied in the argument of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nature is just the human beings.Individual prizes nature;and society upholds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Necessarily,the argument of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nature can extend to the argument of group and individual.During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and Two Jins dynasties,and due to the turbulent social environment,nature and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had been separated seriously.Obviously at the same time,this separation also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freedom and morality,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It becom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metaphysics that how to cognitive or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and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and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unity of each other.
Key words: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argument of group and individual;individual;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