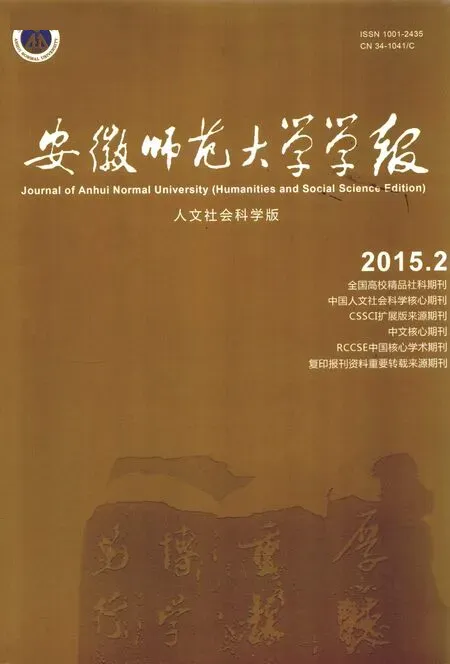余恕诚先生的唐诗研究
2015-03-20王树森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合肥 230051)
2014年8月23日,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余恕诚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5岁。余先生执教长达半个世纪,育人无数;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在唐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广受称誉。他与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30年合作无间、倾心磨治的 《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都是能代表时代水准的学术精品。余先生本人独立进行或领衔的“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诗家三李’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也无不饮誉学林。那么,他穷尽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是唐诗研究,究竟具有怎样的与众不同的特色?又体现着怎样的深入思考呢?笔者师从余先生多年,受教尤多,本文拟对余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思想进行评述。
一、鲜明的时代底色
余先生乡籍安徽肥西,这里曾是清末淮军的摇篮,见证过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风云。生性多感的先生,对所闻、所见、所经历的一切,不可能无所触动。1943年日寇轰炸肥西将军岭,年仅4岁的他望着不远处的满目疮痍,“眼中冒出怒火”,后来他回忆幼年读书遭逢国难痛苦心境有诗作云:
学唱 《黄河》泪汪汪,黄河百姓最遭殃。后方学子亦何幸,麦收带馍进学堂。①转引自余恕伦 《悼恕诚弟》,载2014年9月25日 《新安晚报》。《黄河》指抗日战争时的著名爱国歌曲 《黄河大合唱》。
既沉痛于生活在黄河两岸惨遭日寇蹂躏的同胞苦难,也为自己于滔天战火之中尚能“带馍进学”感到庆幸甚至愧疚。一个民族在积弱之时所遭受的屈辱,就此即在一个幼小而敏感、稚嫩却有肝胆的心灵中埋下根来,不仅影响着他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学术研究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试看先生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唐诗对时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中对杜甫 《悲陈陶》的分析:
用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性事件的时间和牺牲者良家子的身份,渲染战场和长安的惨痛景象。让读者从战士的牺牲中、从人民悲哀的心底上,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听着杜甫的长歌当哭,人们就仿佛站在英雄纪念碑前。[1]15
这种对诗歌描写战争苦难感同身受的体验、如在目前的解读,很难说没有他幼年时的记忆在。而文章竭力注意发明杜甫 《北征》《彭衙行》《赠卫八处士》等乱离之作“一方面很悲,甚至悲得痛入骨髓,另一方面常常带着某些憧憬或温存的插曲。在悲感中又有一阵阵温暖的回流,让读者在复杂的感情冲动中,更加激起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1]15的抒情特色,也可与上引他自己的诗作对读。有时候苦难也是一种可贵的磨练和补偿。余先生讲杜甫的诗歌,那么让人身临其境,与他自己的经历确实有着莫大的关系。
余先生1951年进入肥西初师学习,后来被连续保送到六安师范、合肥师院,1961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青春年华,正赶上共和国十七年虽然屡经曲折但仍然激情燃烧的火热岁月。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或许对那个年代有一定隔膜甚至误解,但那毕竟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独立与新生的光辉起点,也必然因其无可抹杀的奠基之功彪炳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余先生的学术人生起步于那个年代,理想与浪漫,注定成为一位华枝初放的年轻学者最鲜明的底色。
“文革”之前,余先生的学术论文大概有四篇,其中讨论李白的,一是 《读 〈李白欣赏“池塘生春草”〉一文后》,发表在1963年3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二是 《天才的诗人,骄傲的狂士》,是一篇长文,原也被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录用,遗憾的是,因政治风云突变,文章后来未被刊出。尽管如此,这两篇唐诗论文与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李白、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人民性的浪潮密切呼应。他所发明的李白的“天才”与“骄傲”的两方面个性特质,也很明显能看出1962年调整之后社会情绪重新获得舒展的强烈时代印记。设若没有恢弘时代大潮的鼓荡触动,没有对于时代大潮的敏锐把握与细腻感知,恐怕就很难有这两篇论文的写作。
“文革”以后,已至不惑之年的余先生迎来学术研究的丰收期。这个丰收,首先是以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研究为发轫。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在浩劫之后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余先生不是一个盲目跟风的人,但能够将那个时代特有的热烈氛围,化作审视古代作家作品的积极动力。试看他几篇重要论文的发表时间:《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1982)、《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从两种不同类型之作看盛唐边塞诗》(1985)、《地域、民族与唐诗的刚健气质》(1987)。这三个年份,都是改革拓荒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我们再来看论文中那飞扬的文字:
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在那春潮般涨满的生活江面上,烟云缭绕,浮动着一种热烈的情绪,一股深情的期待和展望。[1]8
这些文士在独处和思念家室时情调并不低弱,而当众人会集在一起时,更能激发意气:……多么兴会淋漓,豪气纵横!他们有感于时光流逝,功业未建,但不叹老嗟卑,感伤唏嘘,而是表现出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豪饮、大笑和“岂能贫贱相看老”的感慨,都基于一种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念,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心志。他们怀抱功名欲望,但不加隐讳,显得开朗而有进取性。透过这些作品,不难觉察到,感应着盛唐的时代精神,这些富于血性的男儿脉管搏动得多么有力![1]229
这是论文吗?是的。但这更是诗!孤立地看,这样的论文语言,或许显得突兀,然而当我们充分注意到,那是一个朝气蓬勃、怀抱大开的岁月,便会了然:这实在是受时代芬芳之露浇灌,绽放的一朵学术雪莲!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朦胧诗的异军突起,这也给余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来启发。1970年代中期起,余先生和刘学锴先生合作从事李商隐诗文的整理工作,但在一开始,难免受到束缚,《李商隐诗选》初版本 《前言》中,无论观点还是文字表述,还有比较明显的“文革”痕迹。①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选·前言》,载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到了1986年的修订本中,情况则有了重大改变,大幅增加了对义山更具审美艺术特征诗歌的甄选与分析,尤其是修订本 《前言》中增写的“以心象融铸物象”与“朦胧的诗境与凄艳的色调”两节,其灵感明显来自于当时的朦胧诗。②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2页。这些新见,使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多年以后,余先生在一次学术讲演中曾经如是分析李商隐诗史地位在当代被重估的原因:“这是因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李商隐诗从审美上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李商隐诗在体现文学本体、诗歌本体这一方面是能够和前面几个大师 (按,指李白、杜甫、韩愈)相抗衡的。”[2]200敏锐地把握住诗人的接受与时代之关系,同时又将这个时代所倾爱的特质精到地揭示出来。这是他学术研究始终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动力源泉。
学术研究紧扣时代主潮,其末流常常是陷入趋时跟风,甚至失去判断,丢掉立场。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深刻教训。且这种教训,并非只在1978年前存在,新时期以来同样难免。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成绩,评价过于简单化、标签化。《“诗家三李”论集》中,有这样三篇论文,颇值得重视:一是 《“诗家三李”说考论》,二是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例证》,三是 《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其中,第一篇是对毛泽东欣赏三李的倾向提出艺术上的合理解释,第二篇是从李白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中“乡关渺安西,流浪欲何之”两句所提示的信息,为郭沫若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寻求内证。这两篇论文的更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具体问题的讨论,肯定毛、郭的艺术判断力。他曾多次跟我说,郭老的书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有些看法是不好轻易否定的。同样的,他可以通过对中唐诗坛分野的深入分析,彻底否定史学家范文澜眼中一条并不客观的中唐诗歌演进轨迹,但这并不会导致他因噎废食,连范老赞扬李商隐骈体文艺术成就的卓见也一概抹杀,他本人对范老的名著 《中国通史简编》也是服膺有加。在我的记忆里,他对郭、范,以及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很钦佩,常常赞扬他们是真正的大家。他公开声明: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做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2]103
如,《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一文,从20世纪中国政治史、外交史、学术史的全局高度对李杜研究百年得失进行观照,客观评价各期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如他肯定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论文,“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不少)“均有独到之见”[2]107;又如实指出新时期以来关于杜甫的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2]107这些看法,容或引起年青一代的不解,但实在又是一个仁厚的老学者,经过全面回顾与慎重考量之后,所得出的中肯之论、恳切之论。
社会主潮与学术变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相依相存的关系,或许还值得进一步考察,但无可疑问的是,能否善于抓住那些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以先知春暖的自觉与敏锐,真正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而大大将学术向前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确实检验着一个人文学者的眼界与担当。
二、宏大的学术气象
余先生的唐诗研究,在诸多领域,如文化背景、文艺心理、诗歌迁变、文体关系等,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开拓。若以历时性的眼光看,无论是关注的焦点,还是论说的方式、甚或语言的风格,他前后期的研究也有明显不同。总体而言,早期更有情采,晚年更显朴质;早期追求浑融,晚年看重分析;早期思致发越,晚年人书俱老。但是贯穿始终、体现在他论著中的,则是一种既大气包举,又细致深入的宏大学术气象。
余先生一生,特别是晚年,反复强调古典文学研究要有大格局、大气象,要关注大作家、大制作,以及文学史的大问题。读其论著,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善于拈大题目,总是自觉站在文学史全局的高度提出与审视问题。请看其三部专著中对研究对象全局意义所进行的概括:
重点结合唐代文化精神对形成有关风貌特征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以见唐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我们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备的积极健康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唐诗风貌》)
本书研究唐代诗歌与其他各体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关系……这对唐诗史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对协调文学园地中多种文体的发展,自觉将其作为系统工程加以建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三李诗歌既各有特色,又有一些很重要的相近之点。阅读研究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到他们诗歌天地的丰富多彩和各自在艺术上的巨大独创性,同时也可以亲切感受到三李文脉的潜通,进而亦可能对中国诗歌演进获得某些更为深微的认识。(《“诗家三李”论集》)
无论是考察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还是研究文体互动及其文学意义;无论是辨析三李诗歌各自的艺术独创,还是发明三李文脉内在的相近相通,他都注意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宏大的文学坐标系中加以衡量定位,这样做,最终又是为了加深对文学史全局的认识。
《唐诗风貌》与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均为余先生十年一剑倾心磨治的学术精品,两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在具体论述之外,那些全景式概括,更显宏大气象。 《唐诗风貌》首章,在前人揭示基础上,大笔如椽地勾勒了“唐诗一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与唐人在将丰富的生活体验化为精神产品时超胜于其他时代的诗美”[1]1,次章则从地域和民族两方面的因素着眼,发掘唐诗“姿态万千而皆内秉刚健之质”这个“又一方面带总体性的风貌特征”[1]29。同样,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一书,设若不是绪论和结语两部分既“是全书精神所聚,亦全书精粹所在”①刘学锴:《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序》,载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的重要提炼,我们恐怕也难从理论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到“诸体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对成就一代文学繁荣所起的巨大作用”[1]1。
中国文学烟波浩淼,但真正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真正具有深远历史价值的内容,并非漫无边际。余先生的学术研究,总是异常严格和审慎地选择研究对象。清人吴乔 《西昆发微序》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认为唐代具有开拓性的大诗人,只有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四家,甄选不可谓不严苛,但这个看法自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合理性。余先生一生所讨论的作家,唐代下功夫最深的是“三李”和杜甫、韩愈,唐代以外,则延伸至屈原、宋玉、司马相如、阮籍等,全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始终认为,要想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涵,关键是要抓住历代已经被公认的代表性作家,读深读透,深味细察。
当然,强调关注大作家大作品,绝不意味着余先生对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家怀有偏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3]4-5一些一般作家,虽然被大作家的光环湮没,“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3]5。反过来,要客观深入地发明一般作家的价值,也只有将他们置于和大作家大作品以及文学大势相参照的位置。初唐时期的宫廷诗,总体成就不高,“未出现一流作家和太多的佳作”[1]51,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但一则初唐宫廷诗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其积极的能够展示新朝健康精神状态的质素应当被足够估计,未宜与齐梁诗的淫亵萎靡混为一谈。尤为重要的是,“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集着大量高层人材,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1]5,且与四杰、陈子昂等宫廷外诗人形成有益互补,从而才能最终推动诗坛走出初唐“百年徘徊”②袁行霈语,见其 《百年徘徊》,载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的困顿而迎来盛唐的大潮涌起。同样,晚唐诗坛除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少数人,人数众多的学贾岛的一派,诗思局促、境界狭窄,他们的作品自然难免在整体上给人以“沉沦”①袁行霈语,见其 《在沉沦中演进》,载 《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的印象。但如果充分注意到他们强烈而自觉的艺术精品意识,注意到“穷士诗人的歌唱”,也是时代社会条件以及当时士人们贫寒处境与凄苦心态的折射,就能给穷士诗人在晚唐诗歌演进的大势中以合适的定位。因此,在面对总体水准不高的研究对象之时,如何能点铁成金,化出高远的立意。
《老子》第六十三章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成就余先生宏大学术气象的,视野的宏阔之外,论述的深入细致、委曲周详,也是关键所在。他的唐诗研究,不仅见解得透,而且挖掘得深、发散得开。
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入挖掘首先体现在作家心理研究上。余先生对于作家心理,甚至是最幽僻最隐微处心灵痕迹的捕捉,都是那样敏锐细腻。对李商隐多感复有情的性格心理揭示,以及由此而探讨义山朦胧多义诗歌风貌的内涵与表现,早已成为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佳话。其实不独李商隐,他对其他一些重要作家乃至某一时代社会总体心理的分析,同样令人叹服。《杜甫在肃代之际政治心理的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一文,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杜甫这段时间内的政治心理,特别是分析杜甫颠沛陇蜀与流落江湘两个时期的心境与诗境,十分精彩。而 《变奏与心源》(《江淮论坛》1990年第3期)一文谈韩愈精神状态的“躁劲”,亦鞭辟入里:
作为一个有多重身份的地主阶级实干家兼思想家,韩愈亲历许多复杂的矛盾斗争,在心底激起种种撞击:正与反,是与非,利与害,廉与贪,进与退,出世与入世,妥协与坚持,勇敢与怯懦,庄严与滑稽,崇高与卑下……彼此互不相让,轰车曷不已,其心境千象百态,与外部世界同其光怪陆离。“狂波心上涌,骤雨笔前来”,他在写诗时感受和表现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一方面把切身的感受表现出来,一方面还常常在这种感情中过活,故而矛盾刺激的冲突性还相当强。进而从多个方面和层次具体展示韩诗的矛盾冲突与躁动不安,使人们对于韩愈诗歌耳熟却未必能究其详的“不平则鸣”风貌,对于韩诗何以能当起大变唐诗的声名,终于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又如一般易被笼统认识的盛唐时代心理,余先生说:
具有“盛唐气象”的诗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建功立业;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发出的怨怼之词。感激与怨怼看似相反,但实际上联系非常紧。感激而望建功立业,遇挫即成怨怼。所以在具体作品中,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感激与怨怼,盛唐人所注入的情感是非常充沛的。[1]81
对于前人一直有一般性认识却又难以协调各种矛盾的“盛唐气象”概念,余先生在继承宋人严羽以及当代学者林庚的有关论断基础上,抓住“感激”与“怨怼”这一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键词,从多个层面进行创造性发挥。这恐怕不仅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盛唐时代心理,也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文学中各种复杂问题所应该秉持的正确态度。
文学史中的很多问题,前人不是没有揭示,时贤也非没有共识,但往往没有深入展开。在这一方面,余先生则做得十分出色。 《唐诗风貌》中,对“生活美和精神美”的论述,将生活分为日常生活、士大夫生活、边塞生活,以及苦难但又有“美的成分、素质与品格”的生活等多个方面;将精神分为豪壮开阔的胸襟、执着的精神、轩昂的傲气、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怀等方面,每一方面又进一步有细分。如,李白与长江的关系,从长江的自然与人文两方面予以观照,人文方面又细分上中下游的不同文化与文学传统……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其思维缜密性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诗与文的关系,过去人们更多注意韩愈的“以文为诗”,余先生则不仅细致分析了“以文为诗”的内涵,而且强调文之影响诗,不独只有散文,也应充分注意骈文。他以李商隐为个案,探究骈文与诗歌的关系,在钱锺书“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观点基础上,从对偶、用典、句法、章法等多个方面探究骈文对于玉溪诗风的影响。杜甫所受赋体影响,胡小石 《北征小笺》已有“化赋为诗”的揭示,但余先生从“诗史与赋笔”“解构与变体”“赋之描写与诗之比兴”“铺叙与讽刺感慨相结合”等四个方面,全面探讨杜诗对辞赋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这不仅解决了杜诗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杜甫的巨大艺术创造力。
具体问题的深入论证之后,能否进一步提炼升华,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也考验着一个学者的宏观把握能力。余先生的论著中常常有一种特有的兼论模式,譬如收在 《“诗家三李”论集》中的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与移位现象》等篇,而体现在文章具体论述中的例证就更多。譬如从李白所受长江的沾溉,引申出中国文学的“江山之助”;李商隐诗接受传奇小说影响,其是其非,人或有见,但余先生却赞同纪昀评李商隐 《隋宫》诗,“是晚唐别于盛唐处”,为诗史“升降大关”(《玉溪生诗说》上)的判断,指出“从总体上提高到诗史升降大关,并由此途径来加深对文体间交融互动和中晚唐诗歌演变的认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2]269。可见,着眼于文学史发展全局,以宏通的视野指导着深刻的论述,又力求从具体对象中抽绎出普遍结论,是他学术研究的基本追求。
在他晚年的论文中,《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注定是新时期以来讨论诗词关系最为妥帖周详细致公道的论文之一。请看 《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后记》的评价:
(本文)是一项古典诗词关系覃思精研的优异成果……余先生在这里,深思熟虑后先凿开一口通“风”的活眼。从“中晚唐诗风”与“晚唐五代词风”的活眼切入,再细辨“风色”,蹑“风”追影,即从两“风”的通贯、重迭、递进及演化关节探寻中晚唐诗派在词体构建过程中的影响,最后夹入“情境意味”与两“风”在审美感知上气格异同的甄别,这样诗与词在文体建构上的质性演化图像就浮现出来了。
这段饱含感情、富有诗意的 《编后记》,正是对余先生学术研究特色的精到概括。“覃思精研”“深思熟虑”,有层次,有首尾,既具体又宏观,既元气淋漓又毫发无遗,正是这多方面的特质,构成了余先生宏大开展的学术气象。
三、坚定的作品意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幸听过余先生上课的本科生,都一定会津津乐道于他一字一句讲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讲 《长恨歌》的场景,甚至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不完一首寥寥二十字的《春晓》。我也曾亲眼目睹他为王维的名篇 《送元二使安西》写的讲义,300格的稿纸写了满满20页 (页眉、页脚处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补记)。在他看来,文学史的串讲,只有融入到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才能真正具有意义。
对于作品的突出重视,强调对名家名作进行精细的思想与艺术分析,不仅从不间断地贯穿于余先生的全部教学活动中,在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他的研究,总是立足于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深度解读阐发,来获得实事求是的结论。无论是正面支持前人或提出自己观点,还是从反面指出某些看法的不足,他都无一处不凭作品说话。他的论著,一个引人瞩目的特色,就是包含着极为丰富密集的作品信息。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他的某些具体结论,或许只为专业工作者所关注,但那一段段诗意纷披的文字表述,精彩入微的作品解读,依然能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鲜活感人的印象。
如有关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面临的是种种复杂而隐蔽的文学现象,并涉及到文体学、风格学、语言学、音韵学等多方面理论问题”[4]3。解决这些困难,最重要的办法也只能是紧扣作品,以坚实的作品证据作为支撑。余先生有关赋与唐诗语言、赋与唐代古近体诗关系的探讨,以及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具体作家对辞赋艺术经验的继承发展的探究,全是通过大量作品来说明问题。唐诗与传奇小说的相互影响,从大的文化层面考察背景,固然必要,但根本上还是需要从作品出发。“诗歌在传奇小说中的修辞功能”“唐传奇的 ‘诗化’及其表现”“中晚唐小说影响于诗歌的具体体现”等章节,不仅通过列举了大量作品,证实诗歌与传奇两种文体互相存在于对方肌体内的实际,尤为精彩的,则是对这种文体互动在艺术上的重要作用,予以深入细致的发明。他不仅通过李商隐诗歌,研究小说影响诗歌的具体表现,而且以 《李章武传》《柳毅传》为例,探讨了唐传奇的“诗化”特征,认为唐传奇“重视抒情、情节凝练,善于通过环境布局来营造气氛,意境空灵,文字简约含蓄,从而形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言小说(有别于民间 ‘说话’、现代小说以及欧洲小说)的普遍特点和努力追求的艺术境界”[4]236。
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从作品出发,所以即便是对于一些流行已久的论点,他往往也能指出其明显的错误。对李清照 《词论》中“乐府”“声诗”二词的诠解,就是立足作品与文学史发展实际,对前人“深度误解”进行的典型纠正。李清照 《词论》既是理解其词学观点的主要依据,也牵涉到词体起源的重大文学史问题,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余先生则凭借他对唐代文学发展实况成竹在胸的深厚学术背景,遍检 《全唐诗》、《全唐文》、两 《唐书》、《旧五代史》等典籍,指出在唐人语境中,“声诗”主要的所指都与音乐有关,尤其是“跟音乐机构相关的用例最多,也最为郑重严谨”[4]298。至于“乐府”,则对它的渊源做了回溯,特别是考察了玄宗年间中央朝廷音乐谱制的兴盛,最终得出结论:
李清照 《词论》中“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按最正常的解释即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教坊音乐与诗人们的声诗创作,为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舍此正常解释,而作其他诠解,是难以成立的。[4]299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观点,纵然是后来面对多方商榷,依然不改己见。这个底气,无疑是因为他对自己不妄谈空头理论,一切从作品出发的研究遵循,有着自觉地坚守;无疑是因为他对自己正确理解作品、准确把握文学史实际的能力,有着十分的信心。
刘学锴先生在 《唐诗风貌·序言》中曾称赞该著说,“(书中)更有许多对具体作品的深刻独到感悟和文采纷披的诗意表述。”确实,余先生的论著,在具体的结论之外,那些夹在论述中间的作品赏析,同样值得关注。试看他对刘禹锡《踏歌词四首》其一的分析:
女郎连袂结伴,用情歌挑引男方,这在中原地区是见不到的。从月出唱到霞升,对方却躲而不见。所见者却是红霞映树,鹧鸪双鸣。情郎和环境都似乎在作弄女子,但这些又并不构成什么实质性的痛苦,相反使得这幕爱情喜剧格外曲折和富有情味。[1]11
诗歌本已写得活泼,这段分析文字也显示出对女主人公娇羞心理的悠然心会。再看其分析盛唐诗人王湾的名作 《次北固山下》:
首联“客路”二句,一开始就形成开展的、向前行进的气氛,诗人眺望眼前的山水,带着欣赏的意味。而“青山”、“绿水”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种季节特征。颔联写出长江下游水势浩淼、风帆高举的情状……腹联写残夜还未消尽之际。海上一轮红日已喷薄欲出;旧年还未过尽之时,春天的气息已经预先进入大江。虽是一年将尽,且又在旅途之中,然所表现的却是一种光明展望、辞旧迎新的情绪。尾联写年节将到之际对故乡的怀念,但没有客愁,而是借归雁乡书,把诗人的心理空间扩展至唐时繁盛无比的东都洛阳。诗在阔大的境界中有一种和乐的气氛、雍容的气度。那种残夜中已见红日涌现、旧年中已有春气潜入的景象,诗人虽可能只是写一时感受,但无意中对于盛唐时代具有一种象征意味。[1]78
既有对作品本身的细致品读,也有对其时代象征意义的合理而又有情韵的联想生发。这些文字,即便离开具体的讨论语境,独立出来,不也是富有感发与启发性的优秀的鉴赏小品么?
近年来,有关古典文学研究,首先是唐诗研究,到底是应侧重于从外围的“文化学”或“背景”研究入手,还是以更加贴近文本内部的“文学艺术分析”为根本的争论,一直纷纭不断。其实,在余先生看来,无论哪一种研究,只要是为了解决文学问题,只要是有助于更深入阐释中国文学,都是有益的。内与外并无明显轩轾。关键是能否紧扣作品,是否坚持一切从作品出发,又一切以作品为归结。
余先生一生从事唐诗风貌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可被视作较为重视“谈艺术”的一类学者,但他也不会画地为牢,对其他研究方法简单排斥。《“诗家三李”论集》所收的最后三篇论文,分别谈四六、辞赋、小说等文体对李商隐诗歌的影响,重点自然是谈艺术,但分析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诗“体物和抒情融合得更为紧密”[2]228的艺术特质,不忘提及义山开成三年(838)落选博学宏词科,转赴泾原幕府的人生遭际;探究李商隐四六技巧纯熟精湛的原因,又指出他少时受四六高手令狐楚、崔戎的“怜爱器重”,后又因两度任职秘省,得有机缘大量阅读古籍,因而“大有所获”[2]238,打下了扎实的骈体文功底;至于认为“李商隐把杂记小说乃至史书中的奇事异闻运用入诗,非独处于个人好尚,亦是当时整个文化背景、文学潮流使然”[2]252,就更是将文学现象纳入历史背景考察的有见之论。
尽管余先生对于文学的外部研究的态度,是辩证开放而非机械排斥,但是对近年来某些外部研究存在过于空泛、零碎的积弊,也持有高度的警惕。他始终认为:
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对于实际的阅读、写作和文化建设来说,最关紧要的是对文学作品艺术生命的把握,是要揭示作家作品的美学价值。[5]
因此,他的许多论文,如早年的 《地域、民族与唐诗的刚健气质》 《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等文,尽管也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文学外部研究,但是其围绕、针对与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诗歌作品。他的著名论文 《李白与长江》,稍微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变成空洞、生硬的文化概念的堆砌,但是经过其匠心独运,却成了学者眼中“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曾大兴语)。何以能及此?我认为,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对作品的突出强调,一切以作品出发,才是成功的关键。李白受长江上游纵横家文化影响,若只做泛泛之论,自无不可。但他则举 《南陵别儿童入京》《永王东巡歌》《上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多篇诗文,发明其与赵蕤 《长短经》的关系。李白豪放诗风受庄骚、辞赋艺术经验沾溉极大,并非难察,但究竟如何体现?他则以李白多篇诗赋为例,从气魄、体制、语言、甚至章法句法等多个方面细致揭示李白对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发展。长江流域自然景观影响李白,他则同样是通过大量作品,证实其对长江的亲切,证实了长江“宽广浩瀚、充满活力、清明透彻、奔腾不息”的总特点,“与李白胸襟阔大、精神飞越、不受羁束、追求不止的主体精神特征相契合”[2]22。可见只有深入具体作品,以李白为个案,中国文学所受“江山之助”,才算有真正的落实。
结 语
余先生年轻时十分推崇鲁迅的名言:“战士在战场上,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他积五十年心力,执着耕耘在古典文学教学科研的百花园中,开拓了一片片沃土、艺植出一株株蕙兰,其不懈的追求至老仍不稍减。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还有很多计划有待展开,但现在都已无从说起了。坦白说,有些事情、有些工作,随着他的离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可能真的是难以为继的。好在他留下了这一篇篇的论文,这一部部的论著。文如其人,那充满着智慧、渗透着情感、体现着功力的文字中,自有其真精神在,值得用心、用真情去体会。
[1] 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2] 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 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 余恕诚.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余恕诚.加强本体研究,多向拓展贯通[J].社会科学战线,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