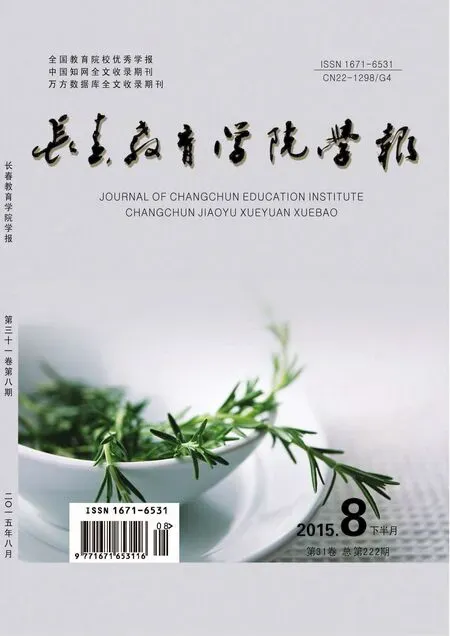崔致远交游考——以高骈为例
2015-03-19黄义华
崔致远交游考——以高骈为例
黄义华
摘要:崔致远是晚唐时由新罗入唐的著名文人,其《桂苑笔耕集》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高骈淮南幕府中的诏书政令、军事行动以及人员调动等,涉及幕府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拟就崔致远投职幕府、与高骈交往、对高骈的复杂态度和史料价值四个方面,对崔致远与高骈的交游进行考证,以进一步深入对崔致远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化的研究,弥补《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对高骈记载的不足。
关键词:崔致远;高骈;淮南幕府;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崔致远是晚唐时由新罗入唐的著名文人,于十二岁离家西泛,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返乡,在唐时间长达十八年。诗人笔耕不辍,创作颇丰,投职淮南幕府四年间,曾自云:“蒙高侍中专委笔砚,军书辐至,竭力抵当,四年用心,万有余首。”[1]13然诗人淘之汰之,仅得《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全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至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高骈淮南幕府中的诏书政令、军事行动、人员调动等,涉及幕府生活的方方面面,弥补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通过《桂苑笔耕集》对崔致远与高骈的交游进行考证,有利于研究崔致远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变化,同时对高骈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 、投职幕府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冬,崔致远任溧水县尉期满,本欲暂时归隐山林,幽居学习,以备参加吏部铨选,报考一年一度的博学宏词科试。然而唐末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黄巢义军叛乱四起,十一月叛军攻破东都洛阳后,十二月西京长安也相继沦陷,唐僖宗匆忙逃亡西川,崔致远自江南东道前往长安应试候调的计划自是中断。
崔致远自西渡以来,常常为生活所困,“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1]744“且如蹋壁冥搜,杜门寂坐,席冷而窗风摆雪,笔干而砚水成冰”,[1]578经济十分拮据。任职溧水县尉后,其生活虽有所改善,然三年期满,又陷入困窘,“禄俸无余,书粮不济”,[1]625只能自叹“投客舍而方甚死雠,持何门而欲安生计”?[1]578没有经济来源,崔致远只能另辟蹊径,寻求其他出路。
中晚唐时期,除了参加科举进入官场以外,文人入幕府担任幕僚是做官的另一途径。白居易在《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 》中就有载:“今之俊又,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2]2924晚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落和藩镇势力的不断增长,幕府对文职官员需求增多且官员升职空间增大,士人入幕府做官的风气由此盛行。唐僖宗乾符六年,高骈进位检校司徒、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其初至淮南,便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土客之军七万。乃传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赖之”。[3]4704多次集结兵士力挫黄巢叛军,并招降了华世铎等人,为淮南创造了相对安宁的环境。高骈还重视对文人志士的吸纳,广布文告,招揽人才,礼贤下士。加之淮南东南形胜,都市繁华,物产丰富,淮南幕府一时间成为世人争相聚集之地,“间生贤哲,年当五百之期;广集英豪,客满三千之数。既纳之似水,则来者如云。……万物投诚,八统乡德,不谒相公实阅,不谒相公德门者,词人之所怀暂,群议之所发诮”。[1]572-573由此可略见一斑。出于社会局势、个人经济困境和淮南幕府强盛之故,崔致远最终选择了投奔高骈,入幕淮南,《初投献太尉启》《再献启》《七言纪德诗三十首谨献司徒相公》等诗文正是其投书之作。
二、 崔致远和高骈的交往
崔致远进入淮南幕府后,很快便得到了高骈的赏识,不论是官职仕途还是个人生活,高骈对崔致远都多有照顾,二人交往甚密,文学往来频繁,建立了亦上下、亦长幼、亦挚友的关系。
在官职任命上,高骈对崔致远颇为器重。考虑到崔致远不远万里入唐求学,孤苦无依,入幕不久,高骈便任命其为馆驿巡官,并委以笔砚,负责书记之事。广明二年五月,高骈驻兵东塘后,特使客司传处分令崔致远从军,“忽赐招呼,猥加驱策,许随龙斾,久倚鹢舟”。[1]625令崔致远受宠若惊,备感涕零,撰写文书更加尽职尽责,“每恨布鼓音凡,锐刀器钝,纵倾肝胆,莫副指踪”。[1]625其代表作之一《檄黄巢书》便是从军东塘时所作之公文。从东塘撤军后,高骈又特上奏任崔致远为都统巡官、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唐代有赐绯、赐鱼袋的制度,绯,即绯色官服;鱼袋,是官员佩戴的证明身份之物。《新唐书》有载:“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4]526又,“五品已上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已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3]1954因此,本品为从八品下的崔致远,是不应该被赐予五品以上官员才允许穿着的绯色官服和银鱼袋的,正是由于高骈的看重,崔致远才能获此殊荣,可谓一日官升三级。其后,虽然出于“诸厅郎官,早陈公议,盖以贱无妨贵,欲令夷不乱华”[1]626等缘故,崔致远自辞都统巡官一职,但高骈对崔致远的器重并不减分毫。四年间,崔致远和高骈建立了和谐而融洽的上下级关系。
对崔致远的幕府生活,高骈也多有关照。崔致远罢离一尉,生活贫困,入不敷出,在献上《初投献太尉启》《再献启》后,“司空相公俯念海人久为尘吏,特垂记录,继赐沾濡”,[1]582特赠崔致远生料,资助其生活。高骈还有意识地提拔他,增加其俸禄,崔致远在本职馆驿巡官外,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职事衔和承务郎散官衔,据《唐会要》载:“推官每月料钱三十贯文。巡官准观察推官例已,上每员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5]1659“补阙、殿中侍御史、通事舍人,各三十五贯文”。[5]1661-1662每月合计六十五贯零二十文,远远超过了其任职溧水县尉时二十贯的供奉。每逢中国佳节,高骈更如长辈一般,时时关心背井离乡、孤独无亲的崔致远,派人送上衣料绸缎、酒肉食物,《桂苑笔耕集》中《谢新茶状》《谢樱桃状》《谢冬至节料状》《谢寒食节料状》《谢社日酒肉状》等诗文正是最好的佐证。
高骈和崔致远还保持着频繁的文学交往。高骈虽然出身禁军世家,但其“幼而朗拔,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3]4703在文学上颇有所得。高骈常常将自己的作品送给崔致远品评,如《谢示延和阁记碑状》就记载了崔致远对高骈书法的鉴赏,“太尉相公志切迎銮,喜胜览檄,既赞美于凌云百尺,将掩能于入木八分。遂乃亲染彩毫,俾镌翠琰。随手而龙蛇旋活,迎风而剑戟交横。画玉点珠,岂可比兰亭醉本;撇云挑雾,只宜示蓬岛真仙”。[1]638正是通过诗文品评、书法赏鉴等活动,高骈和崔致远关系愈近。
三 、崔致远对高骈的复杂态度
在融洽的上下属、长幼以及朋友关系外,崔致远对高骈的态度又是非常复杂的。投职淮南幕府前,崔致远对高骈是抱着崇敬态度的,诗人看到高骈的文韬武略和赫赫战功,并深深为此折服,“伏惟司徒相公独抱神略,一匡圣朝,誉洽于良哉康哉,名标于可久可大。龚、黄德政,则郡民有遗爱之碑;韩、白功勋,则国史有直书之笔。况某劣同窥豹,浅比倾螺,难将篆刻之词,辄颂陶镕之业。但以间生贤哲,年当五百之期;广集英豪,客满三千之数。既纳之似水,则来者如云。斯乃司徒相公,镜于心而宽兮绰兮,秤于事而无偏无党”。[1]572崔致远以龚遂、黄霸和汉将韩信、秦将白起喻高骈,也正是希望能在高骈的门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展宏图,故而诗人在《陈情》中表白了心迹:“此身依托同鸡犬,他日升天莫弃遗。”[1]607
入职幕府后,崔致远在同高骈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看到高骈的所作所为,其崇敬和感激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崔致远本身受儒家影响较深,是一种实践的儒学。他认为:“人能弘道,贤臣以致尧舜为先,世实才俊以效巢由是耻。”[1]690“伏以臣子之所以立身者,以孝以忠,慎终如始,若遂荣亲之望,必勤事主之诚”。[1]90主张积极用事,忠心报国,遵循先王的足迹施行仁政。而高骈的行为恰与之相反。“(广明元年)其年冬,賊陷河洛,中使促骈讨贼,冠盖相望。骈终逗挠不行。既而两京覆没,卢携死。骈大阅军师,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3]4705“(中和二年五月)其月,尽出兵于东塘,结垒而处,每日教阅,如赴难之势。……骈在东塘凡百日,复还广陵,盖禳雊雉之异也”。[3]4705“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宰臣王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副之,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增骈阶爵,使务并停。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3]4705“明年四月,王铎与诸道之师败贼关中,收复京城。骈闻之,悔恨万状。而部下多叛,计无所出,乃托求神仙,屏绝戎政,军中可否,取决于吕用之”。[3]4711高骈以黄巢起义为名,行藩镇割据之实,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在被罢黜实际军权后,又沉溺于神仙之术,不理政务。崔致远想尽忠的对象始终是唐王朝,而不是藩镇。高骈的行为就同崔致远辅佐君主、忠君报国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冲突,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崔致远对高骈的尊敬也转为失望。
四 、史料价值
探究崔致远与高骈的交往关系,考察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对研究高骈的生平事迹、思想变化,乃至晚唐时期淮南幕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都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高骈的事迹都有所记载,这些文献资料从整体上勾勒出他一生的际遇,然而由于晚唐史料继会昌以后,无复底本,修史大抵取朝报、史牍等补缀而成,在细节处亦不免有所疏漏,因此,通过《桂苑笔耕集》中的启、状、别纸、诗歌等对高骈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关于高骈任职天平节度使一事,《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天子嘉其才,迁检校工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3]4703认为高骈由静海军节度使迁天平军节度使。《资治通鉴》与前两者有所不同,载:“以前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6]8121《资治通鉴考异》亦言:“骈为金吾,半岁始除天平。”[6]8121认为高骈是由静海军节度使迁右金吾大将军,后又迁任天平军节度使的。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为考察高骈的任职情况提供了线索,诗人投书高骈时,曾做纪德诗三十首,其《执金吾》一诗对此事有所录:“一阵风雷定八蛮,来趋云陛悦天颜。王孙仕宦多荣贵,心为匡君不暂闲。”[1]597又,此诗顺序位于《安南》《岝口径》《收城碑》之后《天平》之前,可知“定八蛮”,当指高骈出任安南都护,平定南蛮。高骈应是任右金吾大将军后才任职天平节度使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更为准确。此外,《桂苑笔耕集》中还保留了高骈失势后向宦官田令孜求助的别纸,请唐僖宗巡幸江淮的表章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对高骈的记载,弥补了史之不足。
考察崔致远与高骈的交游,还可以订正史之讹误。如关于高骈进纳贡赋一事,史书多言曰:“始骈自乾符以来,贡献不入天子,赀货山积,私置郊祀、元会供帐什器,殚极功巧。”[4]6401“骈先为盐铁使,积年不贡奉,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6]8355“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6]8271认为其自乾符六年(880年)任盐铁转运使后,中饱私囊,多年不贡奉,而在中和二年被解除使职后,“贡赋遂绝”,实际上这些记载还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中就保留了四篇高骈向朝廷进贡的使状,如撰于中和元年前后的《进漆器状》:“当道造成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右件漆器,作已淫巧,用得质良。……伏缘道路多虞,星霜屡换,器贡难通于万里,纲行遂滞于三年。”[1]128文章对高骈任职后未能及时上贡的原因做出了解释,指出其时黄巢起义四起,进贡道路被阻,贡赋被迫于淮南滞留三年,直至中和元年(881年)前后才得以进献。又如作于唐僖宗幸蜀期间的《进绫绢锦绮等状》:“进奉绫绢锦银绮等一十万匹段两,谨具色目如后物色。”[1]132此时高骈已经被罢免了诸道行营都统和盐铁转运使的官职,然从文中可以看出,高骈对朝廷依然有所上贡,他并没有将贡奉收为己用。由上可知,史书中对高骈“贡献不入天子”说法的记载是不够恰当的。
总而言之,通过对崔致远和高骈的交游进行探究,可以从侧面了解晚唐时期社会的政治局势和军事状况,考察崔致远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情感变化,补充文献资料未曾记载的幕府生活的细节,这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对象,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新罗)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丁金荣

张鹏鹏/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在读硕士(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