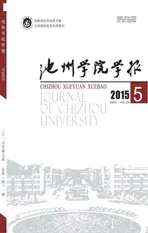再论《简·爱》中“圣经场景”原型结构模式
2015-03-19段小莉田德蓓
段小莉,田德蓓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再论《简·爱》中“圣经场景”原型结构模式
段小莉,田德蓓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夏洛特·布朗特谙熟《圣经》已为众人所知,其代表作《简·爱》不仅在言语、人物、情节结构、思想内涵等层面与《圣经》有着多重紧密联系,同时其文本宏观叙事结构也与《圣经》的宏观叙事结构有着极其巧妙的暗合,此关联尤其反映为《简·爱》中的一定序列的“圣经”场景原型。力图以神话原型和叙事学相关理论为依托,以《简·爱》中众多“圣经”场景原型为切入口,希冀探寻《简·爱》中以“圣经场景原型”为叙事元素的宏观叙事结构。
[关键词]《简·爱》;《圣经》;场景原型;叙事结构模式
夏洛蒂·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自出版以来,一直激发着各国读者的阅读、思想和研究的兴趣,成就了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景致。《简·爱》的文学魅力源于何处?一两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不断试图通过各种文艺批评理论对其作不同视角的深入研究,获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其中,神话原型理论者认为:“一部表现了原型的艺术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1]4。荣格说:“他们作品的感动力与深刻意义却不是凭借这些史实与神话,他们所凭借的是幻觉与梦想”[2]252,“亦即原型”[1]4。弗莱更是说:“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变成了为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3]13。另一位神话原型学者莱肯也曾说道:“《圣经》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3]13。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圣经》是由六十六本组合而成,其写作时间先后跨度约一两千年,但《圣经》有着一个神秘有序的宏观叙事结构,即“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在堕落中寻找肉体的欢乐→灵和肉都麻木的人类回归上帝→耶稣为救赎人类受死、复活、二次降临→末日大审判→人类回归乐园”[4]。同时,我们不难看出《简·爱》蕴含着许多“基督教言语”、“圣经故事”和“宗教活动”,故事主人翁生活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浸染着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气息;更重要的是,该文本的深层语义与《圣经》有着许多惊人的“暗合”之处。这种“暗合”也体现在“圣经”叙事场景的“暗合”,即《简·爱》与以上“圣经”叙事结构相对应的原型场景有:“西印度群岛(伊甸园)→欧洲大陆(堕落的世界)→桑菲尔德(浪子回父家)→泽庄(耶稣回归天堂)→焚毁的桑菲尔德(末日大审判的世界)→芬丁庄园(复乐园)”[4]。
1 西印度群岛:梦幻幽远的伊甸园
《简·爱》文本中的西印度群岛仿似《圣经》中的伊甸园。在文本中,有关西印度群岛的笔墨甚少,大多都是通过极度痛苦中的罗切斯特自我回忆而晓知,那是一个人类心灵中隐没的幽远世界。它似乎在人们遥远的苦涩记忆里,忽隐忽现于文本的叙述中,同时又浸透在文本主人翁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中。西印度群岛似乎是罗切斯特一切人生灾祸发端的伤心地,也是令罗切斯特魂牵梦绕的心灵圣地,同时也是罗切斯特怀念和不断追寻的心灵生存景况。
少年罗切斯特在西印度群岛这个东方神秘国度里,也像在东方的伊甸园中亚当那样过着“清心守节、无忧无虑”、恬淡虚无的幸福精神生活,同时也享受着他父亲给他的一切生活物质所需,在蒙昧和简单中独享和谐的天地。罗切斯特对那时候自己的心灵景况感慨地说道:“那时候很好,清澈、健康,没有污水涌进来把它变成臭泥潭。在十八岁的时候,我同你不相上下——完全不相上下”,“可能象你一样善良——更聪明一点——差不多同样天真无邪”[5]123。
也像《圣经·创世记》中所说的那样,罗切斯特的父亲在他迷迷糊糊之中将一个女子带到他的面前,并使之成为了他的妻子;《简·爱》和《圣经》两个文本对主人翁沉沦败坏历程的叙述也具有惊人的平衡一致的关联性。在《圣经·创世记》中,夫妻起初的生活也是美好的,然后,先是女人受了诱惑,吃了禁果,堕落败坏后的女人又让那男人吃了那果子;《简·爱》中的罗切斯特也正象那因其女人堕落而失去乐园的亚当一样,他也将这原罪归咎于那女人,罗切斯特悲愤地说道:“不到四年她就已经折磨我够苦了;她的性格用可怕的速度成熟着、发展着;她的邪恶迅猛地滋长着……硬拖着我让我经历了所有可憎的、使人堕落的痛苦”[5]287。更有意义的是,罗切斯特在简·爱面前如此急切地发表此等言辞,是因为简·爱相对于罗切斯特就正象《圣经》中的上帝相对于亚当一样,简·爱可以宽恕罗切斯特在那“原罪事件”中的罪过,并且也有能力让罗切斯特重新获得那美好的乐园生活,这也正是罗切斯特这么多年流放生活中苦苦追寻的。
此外,在医生宣布伯莎·梅森发了疯以后,小说文本在主人翁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等细节描写上也与《圣经》有着许多的映照之处,真实地再现了失乐园的痛悔场景。在《圣经·创世记》中,因着人类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与之所立的约,原本美丽和谐的伊甸园就“起了凉风”[6]2,自然不再福佑人类。同样,在伯莎·梅森沉沦堕落致疯后,西印度的自然环境便第一次在文本中呈现为飓风四起、空气灼热、蚊虫营营、云腾海啸、月红如火等一系列末日般的恐怖景象,罗切斯特直接感慨道:“‘这种生活,’我最后说,‘真是地狱!这种空气,这些声音,都属于无底深渊”[5]288!如果说作者在此只是间接地展现失乐园时伊甸园的场景,那么罗切斯特即将离开西印度前的那幕“雨后园中漫步”就能直接地构建起这两个文本间的文化语义联想空间,更加深刻生动激发人们思考原罪、失乐园等人类永恒命题。
2 欧洲大陆:纵情堕落的流浪之地
罗切斯特离开了“令其痛悔”而又“崇敬”的东方“伊甸园”后,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打破阻碍幸福和善良的障碍”在欧洲大陆追寻自由幸福生活,最终却陷入纵情堕落的流浪式生活,欧洲大陆这一整体性场景在文本中也就成了基督教文化中“旷野场景原型”的映射。
在《圣经》中,自亚当在《创世记》失“乐园”之后,“复乐园”就反复出现在此后各部经卷中,成了基督教文化中一个核心主题思想,最终演化为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原型。“复乐园”这一主题也随之拥有了自己丰富的语义内涵和完善的思想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归“乐园”的道路并非一撮而就,人们常常因周围环境的引诱或生活中种种挫折而自我放逐,“进而坠入纵情堕落、迷失自我、灵魂麻木的苦毒光景中”[4],此生存境况常常喻为人类在走向伊甸园之路上必须经历的阶段,是人类自我拯救不断被证明是失败,进而仰望上帝完全救赎的心灵转变过程。《简·爱》不仅非常巧妙而准确地展现了这一情节上的暗合,而且还在言语表达中呈现了这一圣经原型所赋有的许多思想内涵。
首先,众所周知,基督宗教神学思想认为人是有限的、蒙昧的、罪恶的,其行为的合理性人只能通过与上帝联合方能得着保障,进而确保自身的圣洁性和以及上帝的祝福。然而,罗切斯特却在“通向乐园”的道路上毅然弃绝上帝的救赎,选择了“自我为中心”,他不惜打破一切家规礼法,冒着重婚的罪名,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建立“乐园”。这一切的劳碌因着罗切斯特远离上帝必归于捕风,他不仅找不着“理想的女人”,自己也陷入与众多情妇鬼混的淫乱生活中。对此,罗切斯特在末后也忏悔道:“上帝的惩罚是有力的;一次责罚就使我永远抬不起头。你知道我以前一直以自己的力量为骄傲;可是现在,这力量怎么样了呢?……简——只是——只是最近——我才看到并且承认,上帝掌握着我的命运。我开始受到良心的责备,开始忏悔;开始希望和我的创造者和解”[5]288。
其二,自由意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可以自由选择“智慧果”或“生命果”,在复“乐园”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上他们仍然有权选择“坚守正道”或“逍遥堕落”,但可以确定的是选择罪恶的代价便是“死”。罗切斯特在失去东方的“大花园”之后,终日顾影自怜、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好像是“太阳在正午时刻因为日食而变暗了”,而且感到“在日落前无法摆脱它”[5]202,进而认为“既然幸福已经从我这里被不可挽回地剥夺了,那我就有权利从生活中去寻找乐趣;我要得到它,不管花多大代价”,罗切斯特放弃了“保持冷静”、“改过自新”、“胜过环境”[5]124,却选择了“四处徘徊,在流浪中寻找安宁,在放荡的生活中寻找快乐”[5]202,他自述道:“我变得不顾一切;接着,我就堕落了”[5]202。罗切斯特如此就变得沉沦堕落,不仅在情节上和许多“圣经”旷野情景原型是契合的,其最终的结局及文本内涵和这一原型也是暗合的,即“罪的工价乃是死”[7]173。
其三,在基督教文化中,“罪”是阻隔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是一切灾祸的源头;同时人的“自我救赎”是必须的,但不是完全的,因为“赦罪”的权柄在于上帝。罗切斯特在复“乐园”的道路上流放至“旷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原罪的存在和上帝救赎的缺失。在欧洲这片“旷野”上,疯妻伯莎·梅森似乎是罗切斯特在“伊甸园”中所犯原罪的象征。罗切斯特设法用厚厚的墙壁将那“原罪”藏在古老的桑菲尔德城堡的幽暗中,幻想自己从此可以与那遥远的罪恶彻底隔离,获得那久违的洁净身心,重新开始“自由神圣”的生活。其实,那“原罪”却真真切切地藏在罗切斯特心灵深处,甚至成了他本我的一部分,于是,罗切斯特“把自己变成鬼火”,“象三月的鬼魂一样到处游荡”[5]290,进而崔成了他此后一切灾难。在《圣经》中,人类重新回归“乐园”的前提是除灭罪恶,且只能籍助“上帝之火”使之焚烧,方能得救;在“原罪”派生出来的“快乐原则”指引下,复“乐园”的道路必定是通向更深的地狱。这就是为什么罗切斯特会失去简·爱,同时也是为什么罗切斯特在“上帝之火”中脱离“原罪”之后奇迹般地重获简·爱的深层宗教寓意。
3 桑菲尔德:浪子回头式的世俗父家
在《圣经》中,人类充分享有“自由意志”的权力,在复“乐园”的道路上往往因此弃绝上帝的引领和帮助,随从心中的骄傲、贪婪、自私、悖逆作出“愉悦”的抉择,进而使得他们陷入各种患难之中,在走投无路之时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与创造者和解”,这便形成了《圣经》中“浪子回父家”的情节原型[7]89。该“圣经”情节原型中的场景在《简·爱》中便是桑菲尔德,两者之间有着许多文化语义暗合之处,使得世俗的文本《简·爱》充满了宗教救赎的思想内涵。
《简·爱》文本中罗切斯特和《圣经》中的那个浪子一样,他“‘在流浪中寻找安宁,在放荡的生活中寻找快乐’,终使罗切斯特心灵‘贫乏’至极、‘心倦神怠、灵魂麻木’,整个人浸染在‘失望’、‘愠怒’、‘怨恨’之中,心灵充满着无尽的悲伤和苦毒”[4]。此时的罗切斯特物质上虽极其富有,但他的灵魂却一贫如洗,象个破落的乞丐,整日以一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热切地看着每一位从他面前经过的少女,祈望她们中有一位能够让他那干渴的心灵得到爱的滋润。然而,一切劳碌却都归于捕风。万念俱灰之时,罗切斯特“摆脱了所有的情妇”[5]292,象那个浪子一样,走向了那个他心目中既爱又惧的地方,即父亲的家,亦即文本中的桑菲尔德。
在《圣经》中,父亲或上帝是慈仁的,充满了无限的宽恕和怜悯,他(祂)不仅没有拒绝或嫉恨他那曾“恣意挥霍、放荡无羁”的逆子,相反却“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7]89。这浪子不仅在物质上得着了满足,而且也必定在忏悔中改过自新。可见,基督教的救赎是上帝充分尊重人类“自由意志”,在需要给予救助时,祂无条件地将救赎的恩典施舍与人,以使人获得完全的救赎。
在《简·爱》中,似乎有一双无形的上帝之手接纳了罗切斯特落魄的灵魂。令罗切斯特惊讶的是,当他从欧洲大陆疲惫不堪地徒劳而返时,桑菲尔德却有他久违的心灵喜乐和平安。在“简·爱”身上,罗切斯特发现有种他少年时曾经有过的“神韵”,他说那是“可以使人获得新生的”,因为简·爱象征着人类在“伊甸园”中圣洁的生存状态,正如罗切斯特诉说地那样:“这是你二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而未能遇到的;它们都新鲜、健康、没有被玷污或败坏。这样的友谊使人复活和再生;…有了比较崇高的愿望,比较纯洁的感情;你希望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希望用一种比较配得上一个不朽的灵魂的方式度过你的余生”[5]202。有意改过自新的罗切斯特情不自禁地向简·爱忏悔道:“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走上,或者不如说给推上歧途,而且从此就没有回到正道上来;…我羡慕你心境的平静、纯洁的良心和没有玷污的记忆”[5]123。罗切斯特家族个个“骄傲”,罗切斯特能够在一个小姑娘面前如此谦卑,坦诚地象个无忌的孩童,实属不易和令人费解。从基督教文化来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6]545,罗切斯特在简·爱这一洁白无瑕的羔羊,即“耶稣基督”面前忏悔,其心灵必然得着上帝的安慰,此为该文本的深层宗教内涵。至此,罗切斯特在该“圣经”原型中的确像那个浪子一样,在忏悔中自我内在生命获得了重生。
4 泽庄:恬淡喜乐的彼岸圣洁国度
《简·爱》这部世俗性小说不仅展现了上述失乐园的苦楚和复乐园的艰辛,更令人惊讶的是,文本几乎与《圣经》平行地精确展现了该“圣经”原型的后续核心主题,即耶稣道成肉身、羔羊受死、死而复活。围绕着这些主题思想,《圣经》以“天国”为核心场景,构成了一个赋有内涵体系的圣经原型,《简·爱》文本中这一圣经原型场景“天国”便是泽庄,两者之间存在多个层面上平行对等的契合关系。
首先,在基督教文化中,《圣经·旧约》里的上帝给予人类丰富的恩典,并赐人“十诫”以免于罪恶和患难,悖逆的人类却一直放纵自己耳目的情欲,致使无力地挣扎于腐朽败坏的生活之中不能自拔,绝望中孤独地面对自我灵魂的萎缩和死亡。于是,《圣经·新约》中的上帝就赐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人类,在这一有血肉之身的人身上,活生生地将上帝的“圣洁”、“宽恕”、“博爱”、“能力”等光明之道表明出来,让人类看到了“圣洁”的可能和必须,以及上帝救赎的真实和完全,此即为耶稣“道成肉身”及其功效。在《简·爱》中,简·爱是纯洁的、无瑕疵的、无罪的,是羔羊耶稣在这一世俗性文本中的象征性语义符号,她将上帝的“道”陈明在罗切斯特面前,让污秽败坏的罗切斯特看到“圣洁”的真实存在,让绝望的罗切斯特看到“重生”的希望,让无法脱罪的罗切斯特学会“自洁”的方法,简·爱因此在该“圣经”原型的整体语义系统中拥有了“道成肉身”之宗教救赎语义功能。
其次,在这一“圣经”原型中,《简·爱》文本中的泽庄仿似“天国”,那里的空气宁静、祥和、友善,那里的人们不仅以圣洁的基督教信仰为生活的核心内容,而且在简朴的生活中实践其信仰准则,展现出一个与罗切斯特那污秽败坏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圣洁国度。果不其然,简·爱不仅与泽庄的这些天使般的圣徒是同属一宗,而且简·爱的亲生父亲更是那些圣徒中的殉道者,进一步证明该“圣经”原型中喻表“耶稣基督”的简·爱是来自于那个圣洁国度,只是因着“救赎计划”而“道成肉身”在桑菲尔德,这正是从基督教文化角度透析简·爱在危难中如何进入泽庄的内在原因,即她本就属于“泽庄”。
另外,在基督教文化中,“人非圣洁,不能得见神的面”[7]291,所以“藏有原罪”的罗切斯特是不可能与“完全圣洁”的简·爱结合的。这正象《圣经》中那些钉死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里面的恶而拒绝喻表圣洁的耶稣。简·爱也是因着罗切斯特内在仍然藏有的“罪孽”而从桑菲尔德出走,路上九死一生的艰辛只是为了完成对罗切斯特的完全救赎,因此这一切苦难又都是为了罗切斯特而受,简·爱在文本中又如此这般地经历了“死亡”,来到了象征天国的神圣国度,即泽庄。《简·爱》文本就这样艺术性地把“羔羊受死”、“复活升天”的场景原型也生动而准确地再现出来。
5 烈焰的桑菲尔德:末日审判中的恐怖图景
“末日审判”是《圣经》演绎“上帝救赎”的系列原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型”要素,是人类去往彼岸世界之前各人在此岸世界一切言行举止之是非曲直的最后清算,是一切非基督教徒的罪恶灵魂进入硫磺火湖承受永远不灭之火的恐怖景象,是基督教信徒灵魂接受圣灵和火的最后洗礼进入圣洁国度的荣耀时刻。这一“圣经”原型在《简·爱》文本中又再次清晰、细致而又准确地呈现出来,这不仅体现在焚烧的“桑菲尔德”这一场景原型上,而且也体现在与该“圣经”原型相关的宗教思想内涵上。
在《简·爱》文本中,桑菲尔德似乎正象《圣经》中罪恶深重的此岸世界,人们吃喝嫁娶、宴乐无度、视金如命、自高自大、心无良善,除了简·爱以外,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宴会上的绅士、贵妇人和小姐们是如此,桑菲尔德里的仆人们也是如此,更是不曾在文本中看见任何人谦卑地阅读《圣经》或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有的只是吉普赛的巫婆和阁楼上代表邪恶的疯妻,这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便是罪恶满盈。如此罪恶深重的桑菲尔德也绝逃脱不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二城被“上帝之火”焚烧的悲惨命运[6]16。在这场象征上帝“末日审判”的大火中,首先,火是由“罪恶”的伯莎·梅森引起的,这个“罪恶”的象征体最终也不能免于“末日审判”里恶人的结局,即跳入“硫磺火湖”里,承受不灭之火的刑罚。其次,罗切斯特与“罪恶”是十几年的“夫妻情深”,在不舍的情感中奋力救护“伯莎·梅森”,“上帝之火”便使他在苦难中洁净,即失去一只臂膀和双目的光明。
另外,从文本表层来看,大火之后的罗切斯特似乎变了个人,他不再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财富而骄傲使性,反倒极其谦卑地承认“上帝掌握着我的命运。我开始受到良心的责备,开始忏悔;开始希望和我的创造者和解”[5]420。从基督教文化视角来看,罗切斯特在那场“圣灵和火”的洗礼仪式之后,已经完全脱离了罪恶的“辖制”,成了完全的圣洁者,为此后与“圣洁羔羊”连合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6 芬丁庄园:天堂般的福土乐境
《简·爱》文本中的“芬丁庄园”作为一个“圣经”场景原型的映照,它包涵着《圣经》中“天堂”多个角度的形象特点和思想内涵,如“天堂”是那极少数历经“圣灵与火”洗礼后“与创造者和解”且完全洁净之圣徒的终极归属,是《圣经》叙事的终点所在,即《圣经·启示录》。
《圣经》中的“天堂”其语义尽管浸透于每一部经卷之中,但不曾有关于“天堂”形象的直接描写,我们只能间接地通过《圣经·新约》中的一些比喻对形而上存在的“天堂”有所了解。《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13至14节记载道:“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简·爱》中,芬丁庄园被描绘成极其偏僻,且去往芬丁庄园的路是“杂草丛生”、“枝桠交叉”、“逶迤盘桓”[8]478,尤其荫幽可怖的黑暗中“狭窄的门打开了”等意象很容易让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读者联想起《圣经》中去往“天堂”的艰难道路以及那扇“窄门”,并在两者彼此映照中极大地丰富了《简·爱》文本思想内涵。芬丁庄园中的罗切斯特在经历桑菲尔德大火之后,不再骄傲、怨恨、堕落,其灵魂远离了世俗的喧嚣和躁动,进入“忏悔”和“谦卑”中静默灵思,在“良心的责备”下开始“诚恳”地向上帝“祈祷”,寻求与“创造者和解”[5]420-421。令人不可理喻的“隔空传音”也正是脱离罪恶后的罗切斯特在其极度“凄凉、痛苦、备受折磨”中向上帝祷告的话语,上帝必垂听和成全谦卑人的祈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7]8,故而神秘的“隔空传音”也只是此基督教思想的文学化的表现方式。可见,此时的罗切斯特已完全洁净,文本中作为救赎羔羊的简·爱此时的出现并与罗切斯特连合为一体自然是圣洁的连合,而且可达到对罗切斯特“完全救赎”的功效。罗切斯特对此也忏悔道:“我以前做错了;我那样做会玷污我那无辜的花朵,把罪孽涂上它的纯洁;上帝就把它从手里夺走了。我,出于顽固的反叛,几乎诅咒了这种神意;不但没有屈服于天命,还反抗它。神按常规作出祂公正的裁判,灾难深重地落在我身上:我被迫穿过了死荫的幽谷”[5]419。
另外,《简·爱》文本的“尾声”是以《圣经》最后一本书的“结语”结束的,即“‘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7]292!更加巧妙地是,《圣经》的最后那一卷书是耶稣的使徒约翰而写,在《简·爱》文本中,此语也正是那位为宣扬上帝荣耀国度而殉道的圣·约翰,两者之间如此严丝合缝,再次让读者联想《简爱》和《圣经》之间内在情节平衡一致的奇妙吻合。
7 结语
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作为承载基督教文化信仰的经典,《圣经》在其自身的传播过程中不仅通过系统性的原型故事构筑了人们的“信仰世界”,同时,这一“信仰世界”又一再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提供了认知结构模式,即文本中的叙事结构模式。此类原型结构模式为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具渗透力的文本资料和思想源泉。更重要的是,它也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映照面,使某个单独文本的阅读不再是单向而孤立的文本性信息输入,而是在众多文本性材料和原型结构模式为触点的切口上,与此文化文本泉源进行多维对冲的思想对流。
参考文献:
[1]曾繁仁.荣格“原型论”美学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1995(4):1-5.
[2]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3]莱肯,勒兰德.圣经与文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4]于凤保,张文杰,段小莉世俗版本的基督救赎“圣经”原型的经典重现——论《简·爱》中“圣经”场景原型的宏观叙事结构模式[J].名作欣赏,2012(21):78-79.
[5][英]夏洛蒂·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圣经·旧约[M].简化字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
[7]圣经·新约[M].简化字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
[8][英]夏洛蒂·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段小莉(1985-),女,安徽界首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19世纪英国文学,认知文学批评;田德蓓(1956-),女,上海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17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2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