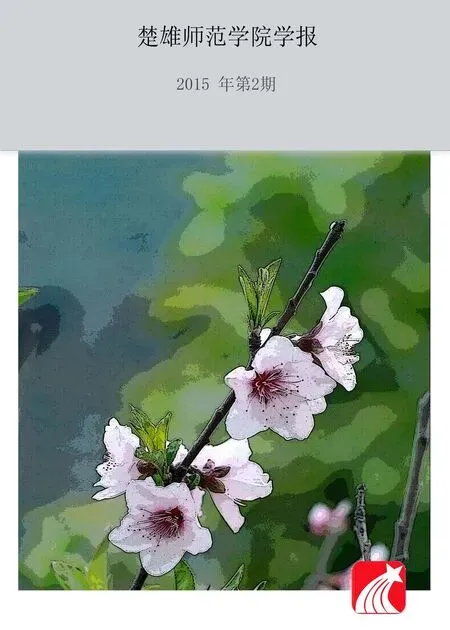家族生活与人的存在:“五四”新文学的家族叙事
2015-03-19耿玉芳
耿玉芳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五四”新文学虽然未能像传统家族小说那样对家族进行详尽的描写,但将其片段连缀起来,还是可以见出“五四”前后家族生活的全景。就像鲁迅的小说那样,既有家族内部的礼教吃人,宗族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亦有受家族伦理影响至深的小家庭的生活悲哀。新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家族的全景,揭示了其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一
从文化批判的高度来看,家族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家族文化事实上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其控制社会与人的超稳定能力。家族制度最完备的是那些封建官僚和地主家族,它们既是家族制度、家族伦理的制定者,又是家族制度、家族伦理的维护者。“父权制”是家族制度的根本,“父之于君,谓由一字孳乳而来可耳。《孝经》曰:‘家人有严君焉,父之谓也。’父之本义如此,即家族制度所由成立也。”[1](P5082—5083)在 “三纲五常”的伦理制度下,父权的专制和残暴无所不在。杨振声《贞女》里的阿娇,定亲几个月未婚夫就死了,而父母仍然遵守婚约将她嫁给木头牌位为妻;夬公《一个贞烈的女子》中的父亲为了能得到官府嘉奖,而将死了未婚夫的女儿活活饿死;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化卿先生,在儿子颖石向他辩解自己在学校的演讲行为并非像校长说的那样是暴乱时,便将茶杯、花瓶摔在地上。尽管颖石热血沸腾,但还是“退到屋角,手足都吓得冰冷”;《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为拆散莲姑和黄大傻的恋情,对莲姑拳脚相加,一顿毒打;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先生在女儿田亚梅的眼中似乎是一位开明的家长,他反对烧香拜佛、算命抽签,认为女儿的终身大事不应该由泥菩萨、瞎算命来定,但最终他还是拒绝了田亚梅和陈先生的婚事,理由是田、陈本为一姓,不准通婚,正如女儿所说,他“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风俗,到底还打不破迷信的祠规”。
有时候“父权”的执行者是母亲、兄长或其他长辈,如《狂人日记》中的大哥,《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秋风秋雨愁煞人》(冰心)及《慈母》 (冯沅君)中的母亲,苏雪林《棘心》与庐隐《弃妇》中的婆婆等。但无论是谁处在“父亲”的位置,父权专制与残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有时候这些人——包括“父”本人也是家族制度的受害者,但可悲的是当他们一旦处于“父”的位置,就会不自觉地维护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孙俍工《家风》中的“伊”是一个节妇,19岁丈夫去世后,婆家出于承宗接嗣的观念不允许她回娘家,后来生了个遗腹子,以至于公公要为她立石牌坊以表彰她的节孝之心。令人悲哀的是,当“伊”想到正在筹划兴工建筑的石牌坊时,“伊底前途更加地光明,又几乎要把伊一生所受的苦痛与悲哀的事迹忘记净尽”,她忘记了自己所受的包办婚姻之苦,又以“父”的身份将孙女志清许配他人。《终身大事》中的田先生从心底里认为陈先生人品好:“拣女婿拣中了他,再好也没有了”,但在祠规族谱前还是对女儿说出了“不能”两字。
如果说“父权制”是家族稳定的权力来源,人们的家族意识则是家族稳定的精神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比“父权制”更难根除的家族痼疾。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维护家族的完整和家族的历史延续方面。叶圣陶《一个朋友》中的那个“朋友”自己十三四岁结了婚,等到儿子到了这个年龄时也让他“把当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之所以把儿子“按在自己的模型里”,无非是为了完成面对祖先的一份责任:“将来把这份微薄的家产交付给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无愧祖先。”叶圣陶的另一篇小说《遗腹子》中,化卿夫妇因为没有男孩延续香火竟然一死一疯。汪敬熙的小说《一个勤学的学生》写一个“从来不告假”的勤学的学生丁怡,在考上高等文官之后便不再上课,并做起在家里大宴宾客、升官娶妾的美梦,小说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受过现代文化思想冲刷的青年心中根深蒂固的家族情结。
家族意识使人们有了一种繁衍子嗣的责任感,即使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如此。如阿Q虽是光棍,却表现出比那些有家的人更顽固的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家族意识。当听到赵太爷的儿子进秀才的锣鼓声时,“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与人打架时骂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而他时常也在心里幻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阿Q看来,家族的荣光就是他的荣光,所以他为祖宗感到自豪,又对后代抱有极大的期望。阿Q总是以家族式思维看待社会人生,被人打是受了儿子的欺负,圆圈画得圆的是孙子,而自己则是老子,是祖宗。他自认为最有成效的对别人的打击就是骂别人“妈妈的”,以攻击对方的父母、祖宗。他对人生虽浑浑噩噩,但有一点是清醒的,那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想到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他想: “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其实,不仅是阿Q,整个末庄的人家族观念都非常顽固,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而末庄的人却就此尊敬了阿Q,因为万一他要真姓赵呢?“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赵家对家族的竭力维护,阿Q非要拉扯上自己姓赵,末庄人对赵氏家族的敬畏,都表明了家族意识的广泛性和无意识性。
二
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尊卑等级、长幼秩序也是那些普通家庭建构的基本原则。鲁迅说过,即使一个地位最低下的“台”,在家中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供他奴役、驱使。[2](P227)宗法社会中,女性处于社会最底层,封建等级制度将她们拘囿在“家”中默默地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人间》(潘漠华)、《蚯蚓们》(台静农)、《赌徒吉顺》(许杰)、《一生》(叶圣陶)中的丈夫视妻如物,或任意打骂,或典卖他人,祥林嫂、《遗腹子》(叶圣陶)中的妻子沦为生育工具。
“夫为妻纲”并不为旧家庭专属,新式小家庭也遗传了这种封建陋俗。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中对新式家庭的批判一语中的:“小家庭不过范围缩小点儿,实质却仍是一样。故家庭制度一日存在,那女子常驻委员的职任一日不能脱离,又那里能够在社会与男子同样活动呢?现在一般提倡新家庭的人,不啻又把女子送到一个新圈套里去,这可算得真正解放吗?”[3](P51)郁达夫 《茑萝行》中的“我”是一个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为抗婚在“无情的异国蛰居了八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桩婚姻。尽管他对妻子也有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带她离开老家,过起了小家庭生活以躲避婆婆对她的欺辱,但这并不表示在新的家庭中就能给她平等的地位。相反,他却以“家长”的口吻给予妻子严厉苛责的恶骂:“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可怜你从去年十月来,竟变了一只无辜的羔羊,日日在那里替社会赎罪,作了供我这无能的暴君的牺牲。我在外面受了气回来不是说你做的菜不好吃,就是说你是让我受苦的原因。我一想到将来失业的时候的苦况,神经激动起来的时候每骂着说: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这虽是忏悔之言,但“夫为妻纲”的影子清晰可见。
《茑萝行》中是“新”丈夫和“旧”妻子的婚姻模式,如果说其不平等还可以找到情感、事业和理想差距的理由的话,那么,《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五四新人”,但涓生对待子君仍有着居高临下的夫权意识。“从子君的生存精神困境中我们看到了自由、平等的现代婚姻背后不平等的一面。”[4](P181)涓生经常以子君养小狗、喂油鸡为由责怪子君落后,其实涓生的理想并不见得就高出子君,只不过子君要求的是世俗的家庭生活,而他所要求的是神圣的爱情和事业,是“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及“读书和散步”的文人雅趣。他将子君的“功业”定于吃饭,认为子君“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的生活很俗化,但他到处找工作与译书其实不也是为了“吃饭”吗?涓生除了空发牢骚之外并没有提出一种更有价值的理想目标,只是模模糊糊觉得“新的生路还很多”,但这生路又不见得“实有”:“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相比较之下,子君的养小油鸡倒更有一种生存的现实意义。我们看到,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在子君这里转化为生活实景而不仅仅只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也许子君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倒有着建构自我的可能性,而涓生的目标固然美好,却因缺乏通达的途径显得虚无缥缈。爱情终究没有给从家族中解放出来的个体以独立和自主的快乐,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理想幸福的家庭或许应该是冰心《两个家庭》中的三哥和亚茜一家,或者是苏雪林《绿天》中的婚后生活那样,在与世隔绝的伊甸园中吟诗作画、琴瑟和鸣。这是“五四”知识分子所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的家庭,但理想的获取却都是以女性遵行家族伦理所要求的“贤妻良母”原则为前提。
在家庭中,“子”的遭遇与“妻”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时候还不如“妻”。阿凤(叶圣陶《阿凤》)、翠儿 (冰心《最后的安息》)被送出去作童养媳,寿儿 (庐隐《西窗风雨》)被卖,六斤(《风波》)被裹脚,5岁的妹子(《狂人日记》)被吃,阿菊(《低能儿》)虽然有父有母却得不到一点关爱。也许最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是刘半农散文诗《饿》中遭受饥饿折磨的孩子:“饿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饿得他全身的筋肉,竦竦地发抖!”吃饭时想再多吃一点遭到了父亲“睁圆了眼睛”的斥责:“小孩子不知道‘饱足’,还要多吃!留些明天吃罢!”这些家庭对妻子、儿女并非没有温情,只是因为生活过于贫苦,只好将对社会的不满转嫁到妻与子的身上。
家族伦理同样影响到儿童心智结构的形成,使他们牢牢束缚在伦理范围之内。《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勇敢活泼、热情机敏,会瓜地刺猹,会雪地捕鸟,他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而人到中年的闰土变得苍老呆滞、木讷寡言,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曾经有过的生命活力和表现力。造成闰土人生巨变的固然有“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社会因素,却也有着封建礼教、家族伦理的影响。尽管他在昔日的玩伴前有着重逢的欣喜,但封建等级制让他“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一旦作声,喊出的却是“老爷”;受“多子多福”家族意识的熏染,他生了6个孩子,生活方面总是“吃不够”;他拿了香炉和烛台以做祭祀之用,还在幻想着能够得到祖先的庇护。在宗法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闰土意识不到自己深受其害,还要以封建礼教文化培养自己的子女,当他叫水生“给老爷磕头”打拱时,可以想象得到将来有一天水生就有可能是闰土人生流程的继续。《狂人日记》中的那伙小孩子看“我”的眼光和大人一样,“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也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长明灯》中围攻疯子的小孩也正是娘老子教的结果,而《孤独者》中的“儿子正如老子一般”、“都不像人!”正如鲁迅所说:“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5](P311)在踏入社会之前,“子”已经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和帮凶,“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6](P581)若不从此 “救救孩子”,将来他们长大了,在社会上无非又是“昏天黑地地转”。
三
在乡土文学作品中,宗族利益之争得到充分表现,展示了宗法乡村社会的愚昧与落后。“械斗”是常见的宗族景观。许杰的《惨雾》中的玉湖庄和环溪村是两个隔着一条河的邻村,常有婚姻往来,但为了争夺一片被河水冲出来的沙渚的开垦权,双方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这是一个权利和财富的冲突”,双方的冲突一轮轮升级,械斗的场面也一次比一次大,参加械斗的不仅是两个村的人,还有双方各自向同姓村庄借来的族人,事情的结局是枪炮相对、流血死人、两败俱伤。鲜血淋漓的械斗带来的是双方仇怨的加深,同时也给像香桂姊、秋英等无辜的女子带来丧失亲人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胡也频的《械斗》同样表现了宗族械斗的惨烈,浏村一个孀居的媳妇被濮村人侮辱之后带着遗腹子跳井自尽,浏村人为此杀进濮村报仇,双方死伤几十人。
如果说《惨雾》、《械斗》、《岔路》(王鲁彦)中的宗族之争是以野蛮和血腥的方式呈现的有形暴力械斗,那么,彭家煌《怂恿》中的宗族之争则是无形的,也是乡村中最为常见的“械斗”。冯、牛两大姓在溪镇都是不可一世,却又势均力敌。牛姓“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牛七在与冯家的争斗中接二连三失利,丢尽颜面,就连冯家的一个伙计都敢对牛七不屑:“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之后牛七总算得到一个机会,利用从堂兄弟政屏卖猪给裕丰店老板冯郁益的事件向冯姓发难,他让政屏以卖猪时没有答应为理由要求冯家“活猪还原”,事情闹开后又要政屏娘子到冯郁益大哥原拨家上吊,以发生人命案的方式将事情闹大,但结果却是计划失败,政屏娘子受尽侮辱和作弄,成为“怂恿”下的牺牲品。
在对待外姓、外人的时候,宗族总能够保持利益的一致,显示了血缘关系的牢固,但在宗族内部却也是互相倾轧和剥夺,同族之间欺凌孤儿寡母、霸占族人房屋财产、自私自利的现象比比皆是。赵四爷 (台静农《新坟》)死后遗留下四太太母子三人,在一次兵变中女儿被强奸,儿子被杀,四太太发疯,这一惨剧本可避免,赵四爷的亲兄弟赵五爷“要是着人招呼一声,她们母子不也跑掉了么?”赵五爷不仅未尽到告知的责任,反而在“她家凶事出了以后,他便猫哭老鼠假慈悲地替她伤心,趁着四太太死去活来的时候将红契都哄去了。”赵五爷的做法令人不齿,就连旁人也骂他将来不得好死。史伯伯 (鲁彦《黄金》)的儿子没有寄钱回家的消息在陈四桥这个偏僻冷清的乡村传开后,同族之人马上就看不起他、嘲笑他:穿的衣服太旧,吃喜酒坐不到“为老年人而设,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养的一条狗被人砍死,祖宗祭日做的饭菜遭同房晚辈挑剔。陈四桥的人就像史伯伯大女儿总结的那样:“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辱你,没有一点人心。”《家风》中老太太的堂侄仲爽为她筹划建造贞节牌坊,却将她数十年辛苦积攒下来用作牌坊建筑费的两千元挪用买了个官职。就连不属于乡土作家的张资平在小说中也涉及到宗族问题,他的《冲击期化石》中的凌氏家族有个习惯,婚丧嫁娶得请族人吃几台酒。凌君父亲去世,因家境困难就想将丧事和葬事从简,尽管家里连吃的米都没有,但在族长的干涉下母亲还是将房屋卖掉请酒。
学者钱杭曾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过宗族存在的人文意义:“宗族最能令汉人感到充足和满意的‘本体性’意义,首先是可证明的血缘性;其次是可追溯的系谱性;再次是不可知的先验性;最后,是可探求、可体验的历史性。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就是从这些本体性意义中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这4种心理需求也就成为汉人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7]可见,人们对宗族存有心理依赖是源于对历史化的血缘亲情的理想想象,而当新文学作品以批判的眼光看取现实时,宗族对社会的阻滞和人的伤害也就暴露出来了。
[1]梁启超.中国文化史 [A].梁启超全集:第 17卷 [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鲁迅.灯下漫笔 [A].鲁迅全集:第1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向警予.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A].向警予文集 [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4]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鲁迅.随感录二十五 [A].鲁迅全集:第 1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上海的儿童 [A].鲁迅全集:第4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