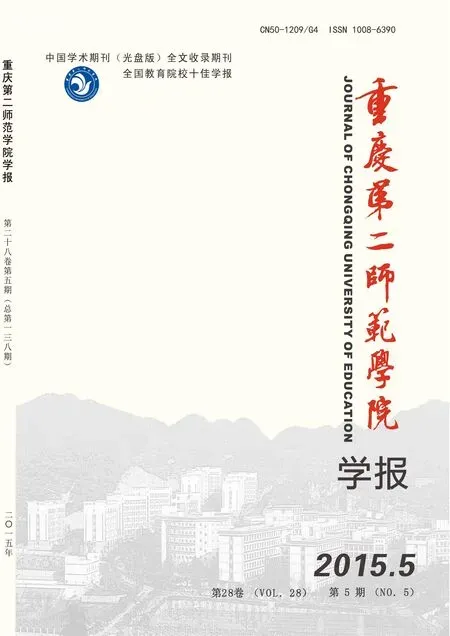从女性角色的设置看作者的价值观——以《西厢记》和《红楼梦》为例
2015-03-19张天羽
从女性角色的设置看作者的价值观——以《西厢记》和《红楼梦》为例
张天羽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西厢记》和《红楼梦》虽属两种文体,但两部作品在爱情婚姻题材和叙事模式上都属于才子佳人一类。而曹雪芹对《西厢记》所持的双重态度,使得宝黛钗爱情故事不可避免有着与崔张爱情故事相通相异的方面,也使得两部作品具备了可比性。本文以女性人物为切入点,分析作品所要表现的男性人物,提出了前人论述中被忽略的观点,并以此探析作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女性角色;设置;爱情;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5-04-01
作者简介:张天羽(1988-),女,福建龙岩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74-04
《西厢记》和《红楼梦》虽属两种文体,但两部作品在描写爱情婚姻题材和叙事模式上都属于才子佳人一类。[1]两部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均体现了青年男女与家长的矛盾,由于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差异,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简而言之,前者是空中含情的价值观的代表,后者则是以情写空的价值观的体现。将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西厢记》抱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曹雪芹认为:“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2]5“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2]6可见曹雪芹并不认可《西厢记》这种才子佳人的框架套路。另一方面,曹雪芹又借宝玉黛玉二人之口称赞《西厢记》“词藻警人,余香满口”[2]315,更重要的是以共品《西厢》预示宝黛二人心意相通:“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2]315可见,故事所演绎的崔张之情又是曹雪芹所认可的。这一相互矛盾的双重态度使得曹雪芹在处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故事时,不可避免有着与崔张爱情故事相通相异的方式。本文不揣浅陋,参照各家论述,以女性角色为切入点,特别是以崔莺莺和薛宝钗、林黛玉三位佳人的角色设置为突破口,进一步分析作品所要表现的男性角色,即张生和宝玉各自的特点,并由作品的中心人物进而探析作者的价值观。
一、崔莺莺与钗黛角色设置的相通之处
莺莺与钗黛角色设置的相通之处体现在:确定作品的主人公(即小姐)及其他人物。主人公(小姐)周边的人物(即丫环)设置是主人公(小姐)形象的巩固、映衬,也是主人公(小姐)形象的延伸。[3]袭人之于宝钗,晴雯、紫鹃之于黛玉,恰如红娘之于崔莺莺。曹雪芹除了沿袭传统的主婢关系中——婢女发小姐未发之言,做小姐想而未做之举——的角色设置外,还为袭人、晴雯等人加入隐含钗黛性情及命运走向的特点,如袭人的判词:“谁知公子无缘”[2]75,不仅预示着袭人与宝玉有份无缘,也暗合了钗宝婚姻终为空;晴雯抱屈而丧,“多情公子空牵念”[2]75,预示了宝玉无法改变晴雯最终的命运,也暗含了宝黛爱情的无疾而终。
莺莺和钗黛都是才情与相貌双美的“异样女子”[2]5,都生于诗书礼仪之家,崔父“官拜前朝相国”[4]1、林父“钦点出为巡盐御史”[2]23、薛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2]59,不凡的家世使得三位佳人有着旁人没有的才情;也使得她们的言谈举止必须符合礼仪规矩,而限制了她们的行为。由丫环们将小姐们所想化为具体的行动,一方面是她们了解小姐内心所想;另一方面她们的地位相对下等,行为上少了些矜持和顾虑,从整体上不影响女性主人公的形象设置。
崔莺莺的内心所想通过红娘外化为实际行动。崔莺莺一出场便唱道:“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4]2她应是知道自己已与郑家订了婚约的,但这桩婚事并不能打消她心中的烦闷。直到张生出场,并且由红娘转述了张生那番“好笑的勾当”,崔莺莺的心才开始有了情的萌动,于是在焚香祷告时,才有了犹犹豫豫不敢说的悸动,才有了红娘的话“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于是“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4]33为了强化戏剧冲突,迅速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符合人物自身的身份,王实甫安排了红娘说出崔莺莺心中难以掩饰的情意,很贴切。
紫鹃在宝黛爱情中也起到类似“密针线”的作用[5],将女主人公的情思和顾虑表达给读者知道,更重要的是让宝玉知晓黛玉的所思所虑,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紫鹃从宝玉处回来,向黛玉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2]786“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2]787黛玉何尝不明白自己处境,所以“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2]787。情意可以通过言语来确证,但是家境的苦楚又该如何述说和弥补呢?史太君是黛玉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长辈,但是有多少把握能让自己的婚事最终得偿所愿,黛玉内心的担忧唯有紫鹃明白。
红娘对崔莺莺的帮助,突出了后者受自身礼仪所约束,紫鹃对黛玉的帮助,突出了后者在贾府实际生存中的孤零。相较于红娘和紫鹃对崔张、宝黛爱情的推动,袭人更多是起到一个规劝宝玉的作用,似乎对钗宝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这其实与宝钗对宝玉的情感及宝钗与黛玉不同的身份有关。从后者来看,黛玉孤身一人入府,她只能依靠外祖母的关爱存活下去,她可以把握的只有宝玉对她的感情,没了这份情,她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而宝钗不同,“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2]63所以宝钗年纪虽小,却有了持家之忧。相比较“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2]68,宝钗就显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2]68,她所接触的是实实在在的家计,她所计量的也是现实的生活问题。这也使得宝钗在对待宝玉的态度上有着与袭人相近的感受,第二十一回:“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2]281她对袭人的认同,源于自身对宝玉的情感态度,与黛玉不同。
二、女性角色设置服务于男性主人公
吴组缃曾说:“书里要写的正是他(宝玉)和林的恋爱悲剧,正是他(宝玉)和薛的婚姻悲剧……因此,书里其他的众多人物……还是拿贾宝玉做中心而展开的。”[6]《红楼梦》的中心人物是宝玉,围绕着他的众多人物,又有了钗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代表。在分析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故事时,不应简单归为类似于张生崔莺莺郑恒的三角恋关系。崔莺莺之所以背离与郑恒的婚约,正因为她被张生的情所感动。而她自身又是张生的情之唯一来源,王实甫所要展现的就是无情与有情的对立。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要表现的是“宿孽总因情”[2]86。这就使得宝玉与黛玉、宝玉与宝钗分属不同的情感类型。除了传统的“阶级论”的解读,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解读三人关系,即钗黛之别是宝玉内心矛盾的外化。
上面分析过,是张生的出现才让崔莺莺有了第一个违礼的举动“回顾觑”[4]8,而崔莺莺的出现让张生有了性的幻想到情的冲动。在这点上,曹雪芹也有相类似的处理。在第六回中,他安排了宝玉将警幻仙姑教授的云雨之情与袭人同领。性乃人之本能,而爱情是一种脱胎于性又高于性的人类社会关系。外表的秀美带给男女主人公相见时第一次视觉上的愉悦,而后发生的种种则将视觉的欣赏上升到了心灵上的共鸣。笔者认为传统的宝黛“一见钟情”观点带上了些“溯源”分析的意味,因为宝玉后来选择黛玉作为他的精神伴侣,所以连带肯定了他们第一次照面时的意义。宝玉对黛玉的选择是伴随着他对家族预定轨道的叛离,而他对宝钗和黛玉的情感区别是站在他知晓男女之情的基础上的。
黛玉和宝钗一出场时的身份及家庭的差异就注定二人日后在贾府不同的地位,黛玉所依仗的是与史太君的亲情,史太君是贾府最高权威,但是王熙凤才是贾府内院的实际操控者,而王熙凤背后的王夫人,代表了贾府的最高权力,她才是支配宝玉命运的家长,同时因为她与薛家的关系,使得宝钗一进贾府就有了不同于黛玉的地位。随着林父的丧亡,黛玉和宝钗的社会身份差异愈发凸显。同时也伴随着宝玉内心的不断权衡,从“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2]389,到“瞅了半天,方说到‘你放心’三个字”[2]434。但就算黛玉是宝玉心中的“第四个人”,前面还有“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2]389看似玩笑话的排列,也预示着宝玉无论怎么偏爱黛玉,都不可能也无法跳脱家族利益的最终安排。
《红楼梦》中处处写到宝黛的爱情,黛玉反反复复要确证宝玉对她的感情,宝玉反反复复强调他对黛玉的情意,正是因为这种情感关系的脆弱。越是渲染两人心意之真之纯,越表明这种真情的结合在贾府的实际生活中无法实现,黛玉比宝玉更早明白这一点,但她只得抓住这份爱,抓住宝玉不放,这是她存活于世的唯一精神支柱:“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2]9木石前盟的约誓使得他们这段感情“比历来风月故事更加琐碎细腻了”[2]9,而在与黛玉谈情写诗的互动中,使得宝玉从对世俗社会由观念的不满上升为思想与行为一齐脱离。宝玉选择了黛玉:“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2]479,也就是选择了理想;宝玉拒绝了宝钗,也就是拒绝了承担现实的责任。但是曹雪芹也并未完全将宝钗等同传统郑恒之类的家长意志的代表。
首先,宝玉对宝钗有情,这份情是宝玉自幼对以女性为代表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情。他对大观园里的所有女子都怀着痴情:宝钗、湘云、袭人、平儿、晴雯……他都视为圣洁的水来珍重。可是他无法改变这些女子的命运,无法为这些美好女子有更好的长远打算,只能眼见一个珍重一个。对于他自身的命运也是只知逃避眼前,“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2]432,也不讲“仕途经济的学问”[2]433。他拒绝了一切符合社会生存的安排,也不去思考自己及贾府的未来,从这一点看他与他厌恶的“浊臭的男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一代不如一代了”[2]26,一起将贾府推入衰败。
其次,宝钗对待宝玉也存在双重的思量。对于宝玉本人,她是有情的,且其情并不比黛玉浅,却比黛玉隐藏得更深,这点论者已多有涉及,不再赘言。笔者在前面已从钗黛二人不同的身份及家庭现状分析了造成宝钗对宝玉在个人情感表达上更矜持的一个原因:是宝钗比黛玉、宝玉更加成熟,更早有了持家之忧。如第三十四回宝钗心中想道:“打的这个形象,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2]450宝钗对宝玉细心、体贴的性情是认可的,她的内心是有所触动的,但触动之余难免遗憾“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2]450。
可见,宝钗面对于寄托了贾府上下未来希望的宝玉的态度是:不认可。因为她比宝玉更早感受到了家族衰败带来的苦涩。第四十二回,宝钗训诫黛玉时,道:“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2]567-568这番话除了传统的“封建”思想,笔者认为还包含着另外的意思:宝钗表面上是训诫黛玉,实际指桑骂槐地说那些把书糟蹋了读书人,所谓“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的人何尝不包括宝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本使人“明理、辅国治民”,站在更高的支点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宝钗眼见自己的薛家男儿读书识字后并未将家族发扬光大,反而渐渐落败。“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宝钗知道,薛蟠却不知道。第五十七回,邢夫人觉得薛家大富,但宝钗却对岫烟说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2]790这番话再次表明了宝钗凡事以大局为重,曹雪芹在写贾府衰败的过程中,已经安排了宝钗、湘云、黛玉先体会了家败之痛。他之所以称赞女性,不仅因为她们的秀丽才情,更因为她们比男人更早更透彻地看到家族兴衰。
白灵阶曾指出,宝钗一边是不喜欢这等“富丽闲妆”,一边却坚持佩戴象征命定姻缘的金锁,[7]并且对“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的红麝串“羞笼”,心中还庆幸“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2]389如果说宝钗对妆饰的否定有出于她对薛家家境的忧心,有出于博得贾府家长认同的考虑,那么她对金锁及红麝串的默认则是她对事关薛家利益的联姻的默许。同时,她对金玉议论和宝黛之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7]这个回避态度与她入贾府后一贯采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是一致的,她比宝黛更清晰地明白婚姻之事非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加之她对宝玉持有的双重态度,这就使得宝钗与黛玉在贾府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而在《西厢记》中,崔莺莺所面对的琴挑、联吟、围寺、赖婚等一系列事件,所烘托的是张生的情痴、智勇、专一。她与张生的关系相对简单,而张生也并没有宝玉那般左右为难的抉择。王实甫理想的社会是有情的社会,张生与郑恒的差别其实在一个情字,张生的社会身份和条件是:“先人拜礼部尚书”,有情谊匪浅的“同郡同学,八拜之交,官拜征西大元帅”[4]5。而郑恒则“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先人在时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儿莺莺为妻”。[4]186王实甫设定有志有情的张生在情的冲动下变成了“傻角”,莺莺点亮了他性情中最纯真的一面,如孩童般不掩饰的大喜大悲,为得到莺莺而狂热地忘乎所以,为老夫人赖婚而心如死灰,垂下泪来。张生坚持似乎不可能的姻缘,“只因红粉一娇妻,把性命全轻视”[4]286。王实甫将张生的“至诚”,认定为爱情、婚姻的关键。[8]
更有趣的是,王实甫设定了与郑恒代表的父母之命的婚约相抗衡的是另一个社会重要道德规范:信。如红娘所言:“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150张生有救崔家母女之恩,崔母赖婚已是失信一回,张生用至情再次感动莺莺,使得崔母不得不再次许下高中状元即成婚的信约,并且有了第二次失信。而当郑恒带着曾经的父母之命出现时,犯了与崔母曾经相类似的道德错误:欺骗(无信)。这样的不诚男子从道德层面上就已经失了支持,作者在最后点评道:“显得有志的状元能,无情的郑恒苦。”[4]201《西厢记》全篇歌颂张生的至诚至情,崔莺莺被这种至情所感动,红娘被这种至诚所感动,普救寺的僧侣亦被这种至情所感动,而后张生科举顺利,乃至“金銮殿上,染翰侍君王”[4]295,最后“书锦荣归”“夫荣妻贵”[4]297,都倾注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三、结论:空中含情与以情写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西厢记》被安排在普救寺内,要求四大皆空的道场却处处含情。而《红楼梦》写大观园,写宝黛恋,写钗宝情,却处处为空:情为空,姻缘为空,人生为空。空中含情与以情写空,是王实甫与曹雪芹所体现的价值观的最大不同之处。都是才貌异样的女子,都是情痴至真的男子,剥去王实甫加诸张生的那些外部的条件,如有白马将军这位掌控一方军权的挚友、一举高中的才能和崔母及郑恒的失信行径,一位完全无权无势的书生是否还能与相国家的小姐成眷属?对二人情感推动极大的红娘,之所以能游走于小姐、夫人及张生之间,就因为其言辞看似“越礼”实则都在道德规范之中,然而讽刺的是:如果这套礼仪规范真能起到约束人的作用,故事就不该因“私情”而发生。所以王实甫内心并不认可这套道德规范,他认可的是情,所以将此情托于笔下,才有了这对怨女旷夫,使得按部就班的社会出现了一丝美好,这是普救寺之外的社会所缺失的,也是作者人生中所缺失的。
而曹雪芹连这份情也一起否定了。所谓的“宿孽总因情”,其一,在于宝玉无论选择了谁,都无法摆脱情的毁灭。宝玉无法改变与黛玉寄生于贾府的现状,也无法与宝钗共同承担家族的责任。其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深刻的道理,由家族的女子们先明白,但是社会又没有给予这些女人以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机会,更不必说还在富贵温柔乡沉醉的各类男子了。其三,贾府到宝玉这一代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府内并无一个会筹谋策划之人,府外与贾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史、王、薛三家,及甄家、林家均已渐次凋零。作品表面上写了各家美好的女子一一登场:黛玉、宝钗、湘云、宝琴……大观园越来越热闹,实际上暗指贾府及他的盟友们在这场政治角逐上越来越处下风,即便宝玉选择了仕途科举,也未知其是否有能力周旋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圈里。虽然后四十回高鹗极力“挽救”贾府的颓势,但是前八十回为贾府埋下的种种伏笔,已经宣告了贾府这棵大树最终的倒下。而贾府终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缩影,盛时压榨他人,败时遭人倾轧。曹雪芹的心是冷的,看到的世事是空的,而改变家族陷入轮回的力量又尚未出现,通过对情、人生、社会的反思,作者要表现的是古代社会不仅毁灭了它的叛逆者同时也毁灭了它的顺从者。[9]
参考文献:
[1]张正显,姚秋霞.《西厢记》《牡丹亭》到《红楼梦》爱情主题深化及不同[J].鄂州大学学报,2015,22(1):60-62.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刘勇强.古代小说的人物设置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6-90.
[4]王实甫.西厢记[M].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崔正.她们都是“红娘”——红娘、春香、紫鹃的人物比较[J].戏剧丛刊,2014(3):66-67.
[6]吴组缃.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J].人民文学,1959(8):112-119.
[7]白灵阶.关于宝钗的藏与露——薛宝钗形象“阐释之谜”的文本解析[J].红楼梦学刊,2007(1):123-136.
[8]张艳新.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5-87.
[9]厉平.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思维机制的嬗变[J].社会科学辑刊,1993(5):125-130.
[责任编辑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