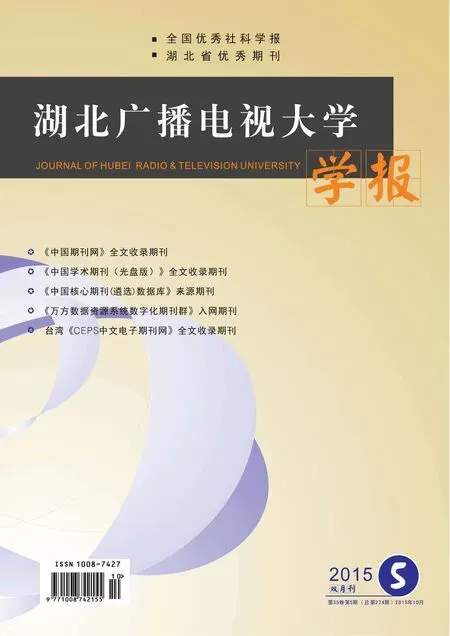创意造言——李翱文质思想略论
2015-03-18陆双祖
陆双祖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唐时期,以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为中心,形成了以其友人和学生为主体的文学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以文章革新的方式复兴儒学,以应对中唐社会的政治文化危机,为唐帝国的中兴从文化上寻找出路。在这一文学共同体中,李翱是继承发扬韩愈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独特文学见解的一位重要作家。李翱师从韩愈学文,深受韩愈影响,其文学思想较为深刻,尤其对文质问题有独到的思考。
一
李翱 (774—836),字习之,陇西成纪人,中唐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员。李翱在早年孜孜于学儒,“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1],后拜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为师,“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故有司亦谥曰文。”[2]韩愈《送孟东野序》也提到:“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3]李翱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也说:“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4]由此可见他们二人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李翱继承了韩愈崇儒排佛的思想,致力于复兴儒学。李翱以《中庸》“天命之谓性”为其重建儒学的依据,提出了复性说。李翱《复性书》提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4],认为“性善情恶”,因此提倡正情以复性,由此复兴儒学之“道”。在文学思想上,李翱继承和发扬了韩愈的主张。李翱的文学思想以六经为旨归,以儒家之道为核心,认为“有德者必有言”。在文质观方面,李翱认同“文以明道”的观点,提倡“创意造言”,在文质关系上推崇“中道”,主张文质兼顾。在创作方面,积极向韩愈学习,“为文以明道”,继承了韩愈文章“正”,“浑厚”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皇甫持正集》也说:“翱得愈之醇”[5],“醇”即“浑厚”。“正”与“醇”作为文章的特色,是属于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范畴。李翱正是接受了韩愈文章中最具儒家传统的“本色”特质,并极力发扬之。由此可见,李翱在思想和创作上深受韩愈影响,成一家言,与韩愈并称“韩李”,深为当时文坛推重。
二
在文学观念上,李翱秉持“文以明道”的主张。李翱继承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对“立言”的意义和价值尤为肯定。他在《答皇甫湜书》中说:
凡古贤圣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其著书者,盖道德充积,阨摧于时,身卑处下,泽不能润物,耻灰烬而泯,又无圣人为之发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4]
可见他对“著书立说”的意义是积极认同的。但李翱追求“立言”不是为了“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而是为了“明道”。李翱认为“明道”是“文章”之根本。其《寄从弟正辞书》曰: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4]
他否定“文章是一艺”的观点,认为文章是“仁义之辞”。他所说的“仁义”即是其所要“明”之“道”,从而赋予了“文章”崇高的地位。
李翱对当时脱离“道”的不良创作风气做了深入批评。他在《与淮南节度使书》中说:
近代己来,俗尚文字,为学者以钞集为科第之资,曷尝知不迁怒、不二过为兴学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为贵富之路,曷尝以仁义博施之为本乎?由是《经》之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办者为良吏,适时者为通贤,仁义教育之风,于是乎扫地而尽矣。[4]
李翱批评学界以科第为能事,汲汲于富贵,忘记了为学之根,丢弃了“仁义”之本,不求“经旨”,不讲“圣心”,致使“仁义”之风扫地殆尽。李翱明确表示他学古文是为了“明道”。《答朱载言书》云: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4]
李翱“学古文”,是因“悦古人之行”“爱古人之道”。这是主张“文行合一”,“文道合一”,“为文”最终是为“明道”。而李翱讲的“道”是指“古圣人所由之道”。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他在《答侯高第二书》中说:
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圣人所由之道也。吾之道塞,则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则尧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绝于世也。[4]
他所说的“道”的内涵非常明确,是“尧舜文武孔子之道”,指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李翱的“文以明道”强调“文”的道德教化作用。其《杂说上》曾言:“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4]他认为著书立言要以“教化”为根本,否则就是错误的。在《答朱载言书》中也认为:“义不深,不至于理;文不信,不在于教劝。”[4]这是要求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要以“教劝”为目的。可见,李翱主张“文以明道”,认为“为文”的最终目的是把圣人之“道”落实在道德教化之中。
三
从文质观看,“文以明道”是中唐古文家提出的对于文质问题的核心观点。这是以“道”为“质”,“文”为“道”的表现形式。对这一观点,李翱是完全认同的。但李翱以“文以明道”为基础,提出了自己对于文质的看法,且较有新意。
李翱文质观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出了“创意造言”观点。李翱认为,文章虽是“仁义之辞”,但不能把文章等同于“仁义”道,文章有其自身的价值。他在《答朱载言书》中说: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4]
李翱这是把“六经之旨”作为“质”,而“六经之词”作为“文”。李翱认为作为表达“六经之旨”的“六经之词”,“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其“创意造言,皆不相师”,“质文”各具特色。李翱由此认为,文章贵在独创,主张“为文”要“创意造言”。
“创意造言”是李翱对文质问题的具体主张。“创意”强调内容的创新,“造言”侧重形式的创造,可谓“文质并重”。李翱认为,内容和形式都不能因循守旧,不同的内容要用不同的形式,要文质相宜。在《答朱载言书》中他说:
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4]
在李翱看来,《六经》因各自的“立意”不同,所以“造言”也不同,都做到了“创意造言”,文质均有创新。
“创意”的重点是具体内容的创新,要根据各自篇章之特点而变化。“创意”的根本在于“因学而知”,来自“学”,主要包括学识、修养等方面。李翱提倡“创意”,是强调要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要以仁义为本,以圣人之道为旨归,从而使文章意义深远。而强调“造言”表明了他对“文”的重视。他在《答朱载言书》中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4]这说明李翱对文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把“词工”作为文的重要标准。《答皇甫湜书》曰:“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之必然也。”[4]他批评史家“言词鄙浅”,把“词高”作为评价文章的主要依据,说明他很重视文词的创新。李翱提出“创意造言”的文质观,主张内容和形式都要创新,二者并重。这在精神实质上与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一种创新。
四
李翱的“创意造言”涉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要真正实现“创意造言”就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实质是要处理好文质关系。对文质的关系,李翱主张文质兼顾,提倡“中道”,反对偏颇。
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批评了当时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六种不良思想倾向。他说: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4]
李翱所说的“六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六种不良倾向形成了三组对立的观点,在李翱看来都是“情有所偏,滞而不流”,偏于一端,没有处理好文与质的关系。
对如何处理文质关系,李翱主张文质兼重,提倡“中道”。李翱强调“质”的重要性。他在《答朱载言书》中说:“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4]他认为作为决定文章的关键是“义”、“意”、“理”、“气”这些“质”的因素,只有做到“义深”、“意远”、“理辨”,才能“辞盛”、“文工”。李翱这一观点显然是认为“质”决定“文”,内容决定形式。但李翱并不“轻文”。他在《答朱载言书》中又提出:“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4]李翱反对重质轻文,认为“词不工者不成文”,强调文的重要性。他说:“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李翱把“文”、“理”、“义”并举,认为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文”、“理”、“义”三者兼重,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才能“独立一时”,才能传之久远。因此,李翱“重质”但不“轻文”,文质并重。
在此基础上,李翱提出了“中道”文质标准,认为理想的文质关系是“居乎中者”。其《杂说上》曰:
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4]
李翱把儒家的“中道”作为文质关系的标准,以“中道”为标准划分文章的等级,把“居乎中者”定为最高典范。“中”就是文质适中,即儒家的“中道”,即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李翱显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文质观念。
总言之,李翱秉承韩愈的思想,在韩愈之后,进一步发展了“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提出“创意造言”的观点,提倡创新,体现了较强的文学本体意识。在文质观上,李翱主张文质兼顾,提倡“中道”,重质而不轻文,发扬了先秦儒家以“中和”为思想基础的文质论,深化了唐人对文质问题的探讨,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也对宋代的古文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05.
[2]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0.
[3]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2.
[4]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64106466.
[5]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