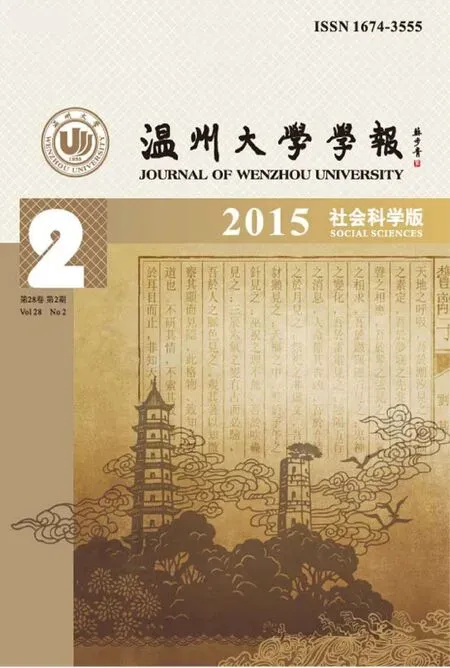佛教视野下丰子恺的酒肉观与护生观
2015-03-18郭战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郭战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佛教视野下丰子恺的酒肉观与护生观
郭战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除了归依三宝之后的几年时间以及生病以外,丰子恺终生都嗜酒与食肉,嗜酒的内在动机是对艺术家兴味与嗜好的坚持,食肉则出于对三净肉的认同。过于宽松的护生观、闲情逸致的文化取向和特殊时期的特殊情绪,是丰子恺的护生言行出现偏差的三种原因,三种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种原因,即丰子恺在修持方面的不足——不能精严持戒。酒肉及护生方面的观念与行为,展现了丰子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关键词:佛教视野;丰子恺;酒肉;护生
在酒、肉及护生方面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展现了丰子恺这位居士文学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也透露出他佛教态度的复杂性。
一、丰子恺的酒肉观
丰子恺善饮且嗜酒,“我宁可一天不吃饭,却不能一天不喝绍兴酒。”[1]他在写于1947年2月的《沙坪的酒》①本文所引丰子恺文章, 包括散文、日记、书信等, 均出自《丰子恺文集》, 其中“艺术卷”四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文学卷”三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下文不再一一注明.中提出了饮酒的境界:“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黄酒,原因很简单:就为了白酒容易醉,而黄酒不易醉。‘吃酒图醉,放债图利’,这种功利的吃酒,实在不合于吃酒的本旨……吃酒是为兴味,为享乐,不是求其速醉。”追求兴味的做法使丰子恺的饮酒带上了雅致的情怀。
生活中的丰子恺喝白酒且有喝醉的时候,比如1938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午餐饮茅台酒,味甚美。”《狂欢之夜》写抗战胜利之夜,与邻人喝茅台酒庆祝。醉酒的事情也不少,《狂欢之夜》写“酒醉之后,被街上的狂欢声所诱,我又跟了青年们去看热闹。”日记中常有醉酒的记载,单是1939年的2月、3月、4月就有五次醉酒,比如2月5日:“午彬然、丙潮联袂而来,章桂为厨司,办菜尚丰。吾多饮而醉,日暮客去犹未醒。”三天之后的2月8日:“午饮酒,醉。”
酒戒乃是优婆塞(居士)所受五戒之一,《优婆塞五戒相经》明令禁止佛弟子饮酒:“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2]944上佛教对于饮酒的危害有清楚的说明,《优婆塞戒经》卷第三中说:“若复有人乐饮酒者,是人现世喜失财物,身心多病常乐斗争,恶名远闻,丧失智慧,心无惭愧,得恶色力,常为一切之所呵责,人不乐见,不能修善,是名饮酒现在恶报。舍此身已处在地狱,受饥渴等无量苦恼,是名后世恶业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乱,不能系念思维善法,是一恶人因缘力故,一切外物资产臭烂。”[2]1048中,下文又说优婆塞不但自己不应饮酒,而且也不应该亲近饮酒的人:“受优婆塞戒,有四种人不应亲近,一者碁博,二者饮酒,三者欺诳,四者喜酤酒。”[2]1048下
丰子恺并非没有体会到嗜酒令人“丧失智慧”的苦恼,比如1939年5月8日日记:“……因痛悔昨夜之饮。渊明‘且进杯中物’,诗中语耳,非记实也。吾昨夜奉陪友人,而照诗实行,以茅台酒、金橘酒倾杯中,而大进特进,以致醉而忘其所为,愚憨之极!”但“痛悔”非常短暂,第二天依旧饮酒,5月27日的日记中则记述:“病痊愈。晚与周家骥君饮酒。醉后三学生来访。内有湖南倪君,以人生苦为问。乘醉竭力慰勉之。十余年前,吾亦患此苦,故深感同情。然醉后放言,恐欠诚挚,未能宣效耳。”这就不仅是自己头脑迟钝的问题了,而且已经影响到度化众生的事业了。丰子恺直至晚年仍嗜酒,最晚的饮酒记载出现于1974年8月21日致朱幼兰的信中:“十多天不吃酒了,昨天开始吃酒了。”晚年的丰子恺甚至违背自己坚守了近一生的“不是求其速醉”的饮酒信条而去刻意追求醉酒的感觉,他在1972年6月2日致新枚的信中说:“我近来吃烟大减(日吸六七支)。吃酒也换一种方式:同外国人一样,把酒一气吞下,取其醉的效果。因我不爱酒的味道,而喜欢酒的效果(醉)。”
丰子恺是居士,但是没有受五戒,这并不违背佛教的规范,《优婆塞戒经》卷第三中佛告善生:“若优婆塞受三归已,不受五戒,名优婆塞。”[2]1049上不过既然做了居士就应该尽己所能地精进修行,极重戒律的弘一法师为丰子恺授三归依之后开示:“受过三皈,虽未受五戒,但要行持五戒。因为学佛,便是根本的‘净心’行为;净心的方法,便是‘持戒’,如若不持戒而学佛,去佛便路遥了。因此,盼望居士先从少分戒行开始律己,如居士者,不妨先从‘邪淫戒、偷盗戒、杀生戒、……’持起,然后再扩及‘妄语戒、饮酒戒(丰嗜酒)’。”[3]弘一法师劝诫丰子恺应该逐渐持守五戒以净心,丰子恺虽未受五戒,但在自己极其敬仰的弘一法师的教诲之下,加上内心对佛教徒生活的羡慕,于是开始实行戒酒。弘一法师在1928年9月12日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说:“(你)礼拜、念佛功课未尝间断,戒酒已一年,至堪欢喜赞叹。”[4]188说明丰子恺已经戒酒了一年时间;丰子恺写于1934年的《素食之后》中说自己“三十岁上,羡慕佛教徒的生活,便连一切荤都不吃,并且戒酒……突然不喝,生活上缺少了一种兴味,颇觉异样。但因为有更大的意志的要求,戒酒后另添了种生活兴味,就是持戒的兴味。”可惜的是,丰子恺“持戒的兴味”最终还是抵不过“饮酒的兴味”,几年后丰子恺又恢复了饮酒。
丰子恺一生中在两种情况下中断饮酒,除了上面所述曾于皈依三宝后的最初几年戒酒之外,他在生病的时候也被迫戒酒,这种情况在他晚年的日记中多有记载,譬如1970年5月23日致新枚信中:“我上次吃了半斤黄酒,以致ヱズク(呕吐)之后,不再吃酒。想吃酒,才真病好了。”1974年8月21日致朱幼兰:“此间室内三十三度连续十天,使我患气管炎。服各种药,今已痊愈。十多天不吃酒,昨天开始吃酒了。”
丰子恺明知嗜酒属于“愚憨”之事为什么仍然嗜酒?答案可以在他发表于1920年4月的《画家之生命》中找到:“二者(引者注:指饮酒、吸烟)虽曰有毒,妨害脑筋,然其已成癖者,苟力遏之,则精神必受不快之感,竟有不能作事者,不若顺之可也。故烟酒虽曰害,或曰能助思想,不无原因。”丰子恺把饮酒等嗜好当作艺术家的修养之一,提升到艺术家的“生命”的高度,主张为了有助于艺术创作,不应遏制饮酒这种癖好,这可能是丰子恺虽为居士而不能彻底戒酒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在饮酒这件事情上,“艺术家”的嗜好压倒了“佛教徒”的追求。
对于汉传佛教的佛教徒而言,素食基本上等同于不吃一切肉(另外再加上受精的蛋类等);但对于丰子恺而言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素食之后》说“我的素食是主动的。其原因,我承受先父的遗习,除了幼时吃过些火腿以外,平生不知任何种鲜肉味,吃下鲜肉去要呕吐。”晚年的《食肉》说“我从小不吃肉,猪牛羊肉一概不要吃,吃了要呕吐……于是我成了一个不食肉者,连鸡鸭也不要吃,只能吃鱼虾。”“我入社会后,索性自称素食者,以免麻烦。其实鳜鱼、河蟹,我都爱吃。”可知丰子恺所说的“不吃肉”指的是不吃猪牛羊鸡鸭等动物的肉,而不包括虾蟹一类的水产,也即他的“不吃肉”是有选择性的偏食,与佛教中的“素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他不吃肉是由于生理而非佛教信仰的原因。丰子恺皈依三宝之后的几年时间曾经彻底食素,但后来丰子恺显然恢复了吃虾蟹的习惯,而且也吃鸡,譬如1938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在王星贤家吃鸡的经过。
丰子恺秉持佛教徒可吃三净肉的观念,这是他皈依三宝后继续食肉的理据,《护生画三集自序》写到:“假如动物毫无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净肉,其实并不残忍,并不妨害慈悲。”允许吃三净肉的戒律出自《四分律》等处,《四分律》第四十二卷佛告诸比丘:“有三种净肉应食,若不故见、不故闻、不故疑应食,若不见为我故杀,不闻为我故杀,若不见家中有头角皮毛血、又彼人非是杀者乃至持十善彼终不为我故断众生命,如是三种净肉应食。”[5]872中可见三净肉的关键是“不为我而杀”。《楞伽经》、《梵网经》、《大般涅槃经》等则严禁出家弟子食一切肉,《大般涅槃经》卷第四解释了不应食三净肉的原因:“迦叶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迦叶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迦叶,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6]386上可以理解为佛以前允许食三净肉是一种方便法门,现在禁止食肉才是本意。
除了皈依三宝的最初几年外,丰子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食素,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他对于三净肉原则也没有彻底遵守,譬如他在1973年10月4日致潘文彦信中说:“吴志厚君送来蟹二十余只,照收,已逐日下酒。虽嫩,至今死者只二只,余均可口。”既是送给“我”,又是活杀,自然不属于三净肉了。
丰子恺既视饮酒为艺术家的生命而不愿戒酒又没有严守三净肉的底线,即使不以严格的五戒作为标准,单从对一个居士的基本要求来说,执著于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哪怕是对他人无害的生活追求)也绝非精进修行的表现。
二、丰子恺的护生观
对护生的重视是丰子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蝌蚪》、《蜜蜂》、《放生》等散文表现出了丰子恺对动物的慈悲,六集《护生画》更是在僧俗两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体现了作为佛教徒的丰子恺的弘法热诚。
《护生画三集自序》集中表达了他的护生观念:“护生者,护心也(初集马一浮先生序文中语)。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待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天地创造这些生物(引者注:此处指植物)的本意,决不是为了给人割食。人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们,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无端的。这就似乎不觉得残忍。”丰子恺进一步解释道:“‘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在严肃的佛法理论说来,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这点我明白知道。但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
从引文可知,丰子恺的护生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护生是为了护心,即长养自己的慈悲心;第二,护生的目的是为人生(养成慈悲心),并不是为了保护动植物,为了人自己的生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食用动植物并不违背慈悲心;第三,自己的上述主张是为了接引众生入佛门而开的方便之门,目的是使末劫众生由浅入深先养成慈悲心,之后再逐渐体悟‘众生平等,皆具佛性’的佛理而护念一切众生。丰子恺的这种弘法理念符合佛教广开方便法门的本意,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它适合未入或初入佛理的阅读对象,也合乎弘一法师预设的读者群:“第一,专为新派知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随分获其少益。第二,专为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4]189
但是丰子恺的护生观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
第一,丰子恺认为不应残害动植物以免养成人的残忍心,又说“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其中暗含着一个观念即“植物属于众生的一类”,这是不符合佛教经义的。《杂阿含经》卷六:“时有侍者比丘,名曰罗陀,白佛言:‘世尊,所谓众生者,云何名为众生?’佛告罗陀:‘于色染著缠绵,名曰众生;于受、想、行、识染著缠绵,名曰众生。’”[7]即于五蕴染著者为众生,《大乘同性经》卷上,佛告楞伽王:“众生众生者,众缘和合名曰众生,所谓地、水、火、风、空、识、名色、六入因缘生。”“此众生者,无明为本,依爱而住,以业为因。”[8]简言之,“心识”是众生之所以为众生的必要条件,《大般涅槃经》卷七更明确表示“植物属众生”说乃是魔说:“若有说言听著摩诃楞伽、一切种子悉听贮畜、草木之属皆有寿命、佛说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经律作是说者,当知即是魔之所说。”[6]404上由上述经文可知植物不属于众生之数。
植物虽不属于众生之数,但《摩诃僧祇律》《四分律》《十诵律》等仍将伤害草木列为“单提”之罪而设戒律,《摩诃僧祇律》卷十四解释了不得伤害植物的原因:佛告诉营事比丘“是(引者注:指草木花果等)中虽无命,不应使人生恶心(引者注:指前文说营事比丘自己斫折草木花果而引起世人对佛教徒无悲悯心的嫌厌),汝等亦可少作事业舍诸缘务,从今日不听自手斫断种子、伤破鬼村。”注释说:“鬼村者,树、木、草。”[5]339上“鬼村”,指某些鬼神依草木而居,草木即是鬼神所居之“村”。佛说明了不得伤害植物的两种原因,一是为了避免世人对出家人“无悲悯心”的讥嫌,二是为了保护鬼神等众生的居住场所。可见慈悲动物与慈悲植物的逻辑前提是不同的,丰子恺将二者置于同一逻辑前提下讨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丰子恺认为植物由“天地创造”,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观念,与佛理相违,佛教认为,植物是众生的依报,由众生的共业而产生,不是由天地而生成的,若进一步讲,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故一切法都没有生起的源头,即一切法都是“无始”的,有造物主的观念是外道邪说,譬如《中论》卷二说:“……所有一切法/非但于生死/本际不可得(引者注:“本际”指事物的本源)/如是一切法/本际皆亦无。”[9]丰子恺如果希望简化议论而不谈论诸法性空等较深奥的问题也无不可,完全可以将生物起源问题搁置起来,但他将生物“无始”说成由“天地创造”,尽管便于国人接受,却非弘法正道。
虽然丰子恺表明自己的弘法方式只是一种较为浅显的“方便之门”,目的是使阅读者生起最初的慈悲动植物之心而不是在“众生平等”的逻辑前提下对慈悲众生形成深刻的理解,但既然是弘法,就要力求基本概念的准确性,道理可以讲得“浅”,但是不可以讲“错”。
丰子恺并非严守戒律的居士,《护生画三集自序》中表达出来的这种相对宽松的护生观念在他的日常生活与创作中得到了体现,在非佛教情感主导意识的时候,他甚至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宽松”性质以至于出现赞扬杀生行为的言行。
《护生画》第一集有幅“诱杀”图,画的是一男人在河边垂钓的情景,弘一法师题诗曰:“水边垂钓,闲情逸致。是以物命,而为儿戏。刺骨穿肠,于心何忍。愿发仁慈,常起悲愍。”《优婆塞戒经》第七卷中将“钓鱼”列为十五种“恶律仪”之一,因为钓鱼是伤害鱼类的行为,在散文《忆儿时》中,丰子恺对与小伙伴王囡囡一起钓鱼的行为表达了忏悔之情,然而反对“诱杀”的丰子恺却在晚年的《喝酒》中赞美一个每天到里西湖钓三四只虾下酒的中年人:“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丰子恺不仅赞美“诱杀”,且自己也实行“诱杀”,譬如抗战时期的《引蚊深入》,叙述自己张开被子,等蚊子成群结队钻进被子后就裹紧被子翻身将蚊子压死的行为,这篇文章的写作有抗战的特殊背景,引蚊深入带有象征意义,而且也符合丰子恺“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的护生观,但行文中透露出来的“杀气”还是显得过于浓烈了一些。
抗战的刺激使性情平和的丰子恺出现了明显的愤激情绪。佛教倡导报三宝恩、国土(国家)恩、父母恩、众生恩,爱国是佛教徒的本份,丰子恺抗战救国的呼吁与佛理相合,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则有待商榷。丰子恺的《一饭之恩》提出了“以杀止杀”的抗战救国观念:“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尽管杀的是荼毒生灵的恶人,丰子恺还是由“诱杀”动物进而主张“杀人”了,这有违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
“以杀止杀”与大乘佛教的“菩萨杀生”不同,“菩萨杀生”的动机是慈悲“一切众生”(包括恶人)而非仅仅慈悲部分众生,《菩萨戒本》说:菩萨若见到有恶人欲杀生, “(菩萨)见是事已发心思维: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落迦(引者注:那落迦即地狱),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意乐思维,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记心,知此事已,为当来故深生惭愧,以怜愍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反,多生功德。”[2]1112上可见“菩萨杀生”的动机是为了使恶人避免堕入无间地狱,它表现了菩萨的“大悲”精神(慈悲一切众生)。丰子恺“以杀止杀”的动机则是以“杀恶人”来保护“被残害的人”,以此维护人道,“杀”的心理是慈悲与仇恨交织的状态。太虚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中谈到对于战争应有的态度:“因为你杀来,我杀去,究竟不是做人的道理……故我们不要跟着人去学制造攻人的杀器,使国民成为互相屠杀的一架杀人机器。无论如何,须改变方法,如墨子非攻而注重防守的方法……我们中国既然并不想做帝国主义去侵略人,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即是自救自立。若能从防攻止攻方面战胜,则不但我们的国难可以自救自免,且可为全世界开辟出一条光明的坦道啊!”[10]太虚法师注重防守而不鼓励攻击杀人的观念才契合佛陀的教诲。从世俗伦理的层面讲,“以杀止杀”是维护正义的做法,自然有其正当性,但从佛理层面看,“以杀止杀”昧于三世因果之理,包含着分别心与嗔恨心,是需要清除的不良心态。
过于宽松的护生观、闲情逸致的文化取向和特殊时期的特殊情绪,是丰子恺的护生言行出现偏差的三种原因,其实,三种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种原因,即丰子恺在修持方面的不足——不能精严持戒。由于不能精严持戒,在护生观念上重视“心”而不重视“事”,致使在某些“事”上不能彻底贯彻护生理念;由于不能精严持戒,有时文化情志会压倒佛教徒的追求,引起搁置“护生”的现象;由于不能精严持戒,对“恶人”的暴行产生嗔恨心进而发出杀之而后快的言语。这些,都是一个佛子应该避免的。
丰子恺对于自己的缺点有清楚的认识,圆觉的《丰子恺先生》记述丰子恺的话:“我虽常年茹素,但是每天因忙于看书写稿,没有空暇来修持,心里很一觉惭愧,将来我总想勉力做到修持的这层。”[11]丰子恺说这句话大约是在1933年,遗憾的是,他终生都没有践行精进修持的愿望。
三、结 语
艺术家的情趣追求与对戒律的“宽松”态度相辅相成,使丰子恺的人生姿态表现为佛教徒的慈悲精神与艺术家的浪漫情怀相交织的特征,应该说,在丰子恺的多数文学作品中,两者的融合还是相当成功的,我们可以在他充满悲悯情怀的散文中找到许多例证;但是,当艺术家的浪漫情怀压倒佛教慈悲精神的时候,我们也能从不少地方发现佛教的慈悲精神被削弱甚至被损坏的表征。由此,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矛盾的一面,当然,如果纯粹从文学的层面来说,这种矛盾无疑增加了他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但是若从佛教徒的慈悲精神层面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缺憾。
参考文献
[1] 丰一吟. 梦回缘缘堂·丰子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46.
[2]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二十四[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3] 陈慧剑. 弘一大师传[M]. 北京: 中国建设出版社, 1989: 264-265.
[4]弘一法师. 弘一大师全集: 八[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5]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二十二[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6]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十二[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7]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二[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40上.
[8]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十六[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642中.
[9] 河北省佛教协会. 大正藏: 三十二[M].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 2008: 16中.
[10] 太虚法师. 太虚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778.
[11] 陈星. 丰子恺评传[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164.
(编辑:刘慧青)
Feng Zikai’s Views on the Consumption of Alcohol and Meat and the Protection of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m
GUO Zhan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Except a few years after Feng zikai became a Buddhist and when he was ill, he was fond of drinking and eating meat throughout his entire life. His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drinking is his adherence to an artist’s interest and hobby, and eating meat is out of his approval of Sanjingrou (the meat of an animal that the follower did not see, hear or doubt it is killed for him). Feng zikai’s excessively lenient view of protection of beings, his leisurely and carefree living style and his special sentiment in a special period have his statements and actions deviated, and those three reasons above can actually come down to one: Feng Zikai has weakness in his practice--he can’t follow the precepts rigorously. Feng Zikai’s views and conducts on the consumption of alcohol and meat and the protection of beings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his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Perspective of Buddhism; Feng Zikai; Alcohol and Meat; Protection of Beings
作者简介:郭战涛(1968- ),男,河南偃师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3-28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2.012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2-00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