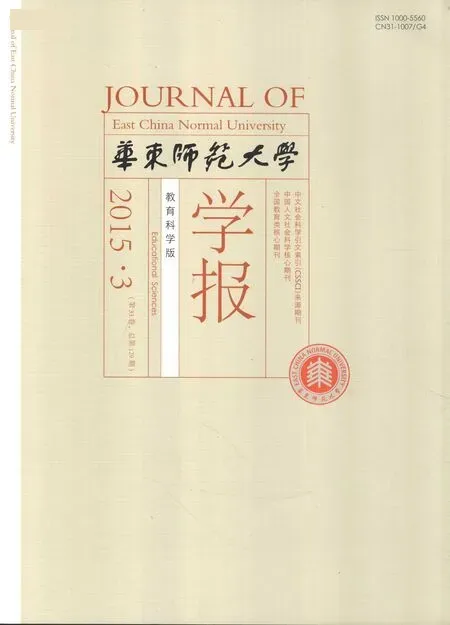片面洞察下的“反学校”生存*
——关于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探讨
2015-03-18史秋霞王毅杰
史秋霞 王毅杰
(1.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江苏徐州221116;2.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8)
片面洞察下的“反学校”生存*
——关于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探讨
史秋霞1王毅杰2
(1.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江苏徐州221116;2.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8)
通过对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边缘且弱势的生活境遇之下,在一些成绩较差、中考无望的农民工子女中形成了娱乐与抵制并存的“反学校”生存逻辑。这些孩子最终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了阶层再生产。然而,要进一步挖掘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关系,则不应将其生存逻辑置于群体层面理解,而应考虑农民工子女具体情境下的策略性选择。当不存在强烈的内群体意识时,这种“反学校”生存逻辑中蕴含的能动性也不具有改变阶层命运的潜能。
农民工子女;片面洞察;“反学校”生存;阶层再生产
一、学校中的阶层再生产
教育是攀爬社会阶梯的有效途径,还是完成阶层再生产的必要工具?这个话题长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再生产理论就是争论中的强大声音之一,当然,在其内部也存有不同观点。以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为代表的经济再生产理论认为,不同阶层未来的道路早已注定,优势阶层的子女会继续沿袭父辈的优势进入上流社会,而劣势地位的子女也会以教育失败者的身份继续底层生活。学校还通过塑造符合各阶层身份的价值和态度来实现再生产,工人阶层的学生会强调规则与服从,管理阶层则强调自治与创造性①,学校教育不过是一个完成社会安排的工具。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布迪厄(Bourdieu)质疑这种观点,他认为虽然教育确实发挥阶层再生产的功能,但它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并非机械执行安排。学校是通过文化再生产来实现社会再生产,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Cultural arbitrary)内化为学生的“惯习”(Hobits),使来自支配阶级的孩子脱颖而出,而被支配阶级的学生惨被淘汰②。然而,当学业成就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生动摇,文化机制的解释力度也受到了挑战,因为它很难解释一些新生现象,例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从事专业职务的人数不多,但美国黑人仍旧对高等教育抱有很高期望③。
对文化再生产的质疑还来自对个体能动性的解释,因为无论是资本转换,还是后期著作中的“场域”(field),布迪厄似乎都赋予支配阶级的孩子更多创造性,而由于资本匮乏,被支配阶级的孩子好像只得被淘汰。因此,这一模式“对于有资本投入的中上层阶级集团无疑是适当的,对于那些没有资本因而不能经由合乎理性地投入来再生自己的下层社会群体来说,是否适用就大成问题”④。威利斯(Willis)认为不应忽视被压迫者及其行为,尤其是那些抵制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过是使其居于边缘化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另一种呈现方式⑤。通过加入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这一维度试图发现被压迫者的行动者特质。他认为,工人阶级孩子因洞察(penetration)到教育的虚假性而建构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旨在获得自由,但最终这些抵制、抗争的行为是以放弃知识获得为代价的,而这(指知识)却可能是一种社会晋升工具或更有效的抵制工具⑥。当然,抵制理论也受到了众多质疑,但威利斯所缔造的“民族志的想象力”(ethnographic imagination)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布迪厄所言的普通人“社会疾苦”的一扇门⑦。
农民工子女是我国探讨教育与阶层再生产关系的重要群体之一,许多学者借鉴威利斯的抵制理论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的作用进行研究。有人认为就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在遭遇“天花板效应”后虽渴望向上流动,但最终还是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民办学校中盛行的“反学校文化”则使农民工子女心甘情愿地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⑧。也有人认为自我放弃式的“反学校”文化与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有关,但由于此观点仅来自于民工学校的调查,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待更多经验支持⑨。还有研究指出正是以“义”为核心的同辈群体文化使农民工子女主动放弃学业,实现社会再生产,“反学校”行为正是依托同辈群体才得以发生⑩。
不难发现,上述研究既有一致也有相悖之处。一方面,对学校教育的作用持一致看法:农民工子女无法实现向上流动,会主动放弃学业而完成阶层再生产。另一方面,对“反学校”文化的理解看似矛盾,或将其视为学校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物,或认为是自我放弃而非洞察后的抗争,似乎农民工子女的行为不过是一场模仿秀,全程没有行动者出场。笔者认为,要理解学校教育究竟对农民工子女意味着什么,他们当中是否真的形成“反学校”生存方式,以及这种生存方式是对外界环境的简单反应,还是行动者能动性的彰显,都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予以证明。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读状况来看,如今农民工子女内部已出现分化,大体分为三类: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进入民工学校就读,不读书而跟随父母打工⑪。随着“两为主”政策的落地,在公办学校就读的人数最多,因此全面了解公办学校中农民工子女的生存方式以及公办教育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借鉴威利斯“民族志的想象力”深入到农民工子女的校园生活,通过“实地展现活生生的日常文化”来“理解和意会社会行动者那不可言说的、身体化的体验和实践”⑫。从2006年读研究生以来,笔者就以义教、课题合作、随班跟读等方式与民工学校、公办学校的教师与学生进行接触。在2009年到2010年间,笔者选择了A市一所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飞翔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并重点关注那些学习成绩欠佳、中考无望的农民工子女,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提前结束学业,步入社会。田野调查结束后,笔者继续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与之前的典型调查对象保持联系。在2014年对仍在A市的对象进行了追踪调查,对他们的初中后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飞翔中学自招收农民工子女以来,先后经历了农民工子女大量涌入、本地生源流失⑬,建立农民工子女品牌教育的过程,是开展本研究非常理想的场所。
二、边缘与弱势的生存境遇
(一)角落中的生活空间
从农村流入城市,将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城市社会的分化程度要远远大于乡土社会,这种分化,表现在收入、居住等多个方面⑭。受经济限制,流动家庭大多蜗居于城郊地带。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曾使用开放题收集了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边的重要事情,发现与城市居民相关的事情多是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偶然接触与摩擦,少有实质交往。飞翔中学本处于城市边缘地带,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衡量,也是城市教育系统底层的学校。消费成为城市阶层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受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农民工子女也无法拥有高品质的生活和娱乐,仍旧要在城市的边缘、角落中寻求低廉、免费的消费以满足需求。然而,流行的装扮、劲爆的音乐和潇洒的舞姿可以暂时掩盖对边缘化生活的无奈,却无法改变当前生存境遇所产生的影响。
(二)颓废的网络非主流
网络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寄托,也为穿梭于城市角落的农民工子女打开了“全面融入”的另一扇窗,这里一切结构性特征均被抹去,个人成为独立、平等的个体。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网络现象,强调个性的张扬、另类,挑战成人权威,弥漫着浓烈的颓废色彩。在实地调查中,这种网络非主流对农民工子女生活的渗透清晰可见。哈韩、哈日的着装,24小时QQ在线,频繁访问网络空间,伤感、绝望的火星文签名与日记,血腥、自残的图片,消极、混乱的歌曲,充斥着农民工子女自主建立的虚拟世界。小雨⑮还告诉笔者网络上的“CK”是非主流的代表。了解后发现,“CK”是网络红人,自创歌曲中大多传达的是家庭、学校的压力使他们无法自由呼吸,是抹杀个性和自我理想的元凶,所有教育会把自己变得更蠢、更颓废,质疑家长的教导、教育和知识的意义。
(三)家庭教育的缺位
从农村到城市,原有乡土网络中的子女看护、情感支持等功能无法在城市网络中延续。农民工繁重、长时间的工作使亲子相处与沟通时间减少,而原有乡土经验的失效,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与能力的下降势必影响到家长权威。大多数家长虽对子女有较高教育期望,但当基本教育权获得后(如能够在公办学校上学),很少有意识主动了解具体的教育政策,而血缘、地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因同质性较高也难提供有效的信息。在家庭教育实践中,或是没有时间与能力,或是认为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家长只看重考试成绩,不仅日常学习辅导明显不足,有时还会占用子女的学习时间。临近毕业,无太多经验的父母对于子女初中后的道路很难给出建议。缺位的家庭教育迫使农民工子女较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种自主性的增长也为其校园生活提供了力量。
(四)凸显户籍身份的品牌教育
学校既承担社会功能也有自身发展诉求,飞翔中学将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学校品牌。在“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城里人”的办学目标下,绘制出农民工子女实现转变的必行之路:
我们的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家里没有钱没有背景,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字,勤!所以我校的校训只有“勤”这一个字,督促领导要勤政,老师要勤教,学生要勤学。——来自新闻报道对郑校长的专访
在此,学校将教育的分层功能直接摆在了农民工子女面前,不断强化一种观念:学习是唯一改变身份的出路。要想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就要“有理想”、“懂感恩”、“守纪律”、“勤学习”。那么,学校对城市人的理解又是什么呢?“一个月好几千钱的工资”的衡量标准透露出的是学校较低的教育期望。在转变身份的办学目标下,飞翔中学开展了系列特色校园活动,获得成功体验的民族舞蹈、解读城市文化的校本课程、体味城市气息的肯德基奖励等,农民工子女的户籍身份成为时刻需要改造、摆脱的对象。
居于边缘、封闭的城市角落,家庭教育缺位并受网络非主流影响的农民工子女又是如何面对飞翔中学的品牌教育的?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这场致力于华丽转身的教育中?
三、“反学校”生存逻辑的搭建
布朗(Brown)通过对威尔士三所学校的调查发现,工人阶级虽然不认可学校的权威,但大多数会按照规定行事(complied with it)而不是“小子”们的反抗⑯。与之相似,农民工子女所搭建的“反学校”生存逻辑也具有表面服从、娱乐为主的特点,不会与学校和教师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
(一)照章办事
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将车间内操作工们努力工作挣得激励性工资的一系列行为称为“赶工游戏”并认为这种超额的赶工游戏为评价从工作组织中引发的生产性活动和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⑰。飞翔中学中,俨然上演着另一场旨在投入最少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学习任务的“赶工游戏”,每个农民工子女都是这场游戏的发明家。他们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时间,飞快赶写作业时不忘观察老师位置,老师走近便佯装认真听课。为完成多遍数的惩罚性作业,有些学生会同时用多支笔书写,即便写得歪歪扭扭也全然不顾。快速完成学习任务的另一条捷径是抄袭,先完成任务学生的作业非常抢手,有时甚至传到别的班中,对错已不是考虑的问题,边聊天边抄袭倒成了一种消遣。比抄袭更便捷的是“偷梁换柱”,很多学生根据课程表到别的班级借课本和资料应付老师检查,下课再完璧归赵。
按照要求完成课堂练习、试卷、家庭作业乃至惩罚练习已与知识获取无关,上下课的铃声也不再能够规范农民工子女的行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赶工的生活。如此快速、高效的完成任务,又为了什么呢?学校本身还是农民工子女重要的娱乐场所,他们在压缩学习时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开辟专属的娱乐空间。
(二)有意违规
他们还会故意违反规定,接受惩罚,在有限空间内让自己脱离无趣的课堂。因此,上课铃声响起有些学生才慢吞吞地站在门口喊报告,因为他们知道迟到会被惩罚到后排站着听课,这种课堂上的“局外人”恰好是他们想要的。教室中的座位次序体现了教师的期望,尤其在初三年级,后排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虽未毕业实则已提前放弃。因此,后排学生的生活更加不受规定作息时间的约束,看小说、折纸、玩手机、睡觉,娱乐需求得到最大释放。
平时的快慢班与中考临近的提优/提合班⑱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种子选手”和“拖油瓶”。因此,有意违规有时还是一种不满的表达:
小华⑲原来是快班的学生,因为一次考试被分到了平行班,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她又考了106分,全年级第一,据说把快班的老师快气疯了,但她并没有选择进快班,在交谈中,她对我说:“那天听到‘老芋头’(快班班主任)说他们一班(快班)‘也就是比平行班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还用手比划着),当时我一听别提多高兴了,当时他们班的高材生就在旁边”。
指标化的评价体系打压着农民工子女的自尊,使得即便再有机会回归精英群体成为“高材生”,也会以主动放弃来报复教师。在小华眼中,教师就是学校的代表,完全为学校及自身利益着想,放弃机会在他们看来也打击了学校,因此会感到“高兴”。
(三)虚拟宣泄
网络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平等自由、调侃甚至反叛的意识影响着学生对教育与教师的看法。传统上的尊师、敬师的意识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旁观、戏谑、反讽、调侃、恶搞甚至反叛⑳。信息社会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也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了更多“反学校”生存的文化选择。
“时尚达人”、“音乐达人”、“爱车达人”,可以使他们在虚拟世界中轻松成为精英。威利斯那里,成人世界,尤其是工人阶级男性世界,成为抵制与排斥的来源㉑,在此,网络世界成为农民工子女武装自己的阵地:
《我们90后就是不一样帅》
上课一排全睡,考试全都不会,成绩基本个位,抽烟打牌都会,
打饭从不排队,逃课成群结队,短信发到欠费,上街花钱干脆,
穿越如痴如醉,地下忘记疲惫,炫舞手骨敲碎,问道闭眼都会,
飞车百战不退,魔兽砍人无罪,垃圾学校万岁。
这则贴子在许多农民工子女的QQ空间里出现,传达出对学校教育和秩序的不屑,对网络世界的迷恋与追捧,“穿越”、“地下”、“旋舞”、“问道”、“飞车”、“魔兽”都是流行网络游戏的名称。在此,没有城乡、学校、成绩上的差别,农民工子女的户籍身份也不再是改造的、转变的对象,不再是学校、班级的拖油瓶,因此他们很可能成为此类网络文化的积极拥护者。
虚拟世界不仅能够满足农民工子女对高自尊的追求,还是现实生活的解压阀。这里,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实现对接,没有无处不在的监视,没有必须遵守的各种规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泄各种不满。
受不了~~小陈了㉒
今天真不爽....
明明不是我的错,冤昂!!
凭啥啊。被叫到办公室被昏天黑地滴批我一顿不说,还罚了偶三块钱,偶滴钱啊,最近本来就金融危机,还...~~不管,偶么钱啦,交了三块钱偶就么钱坐车回家赖!!
呜呜呜呜....
回复1:。
主人回复:真不爽,气死我不偿命昂!!无缘无故被罚,飞来横祸啊…衰
回复2:哈哈
主人回复:唉,…这世上还有比我衰的人么、?
回复3:晕、
主人回复:它个杂种昂,偶家徒四壁咯…
回复4:晕!还罚钱啊!有没有搞错?老子找人砍他去,妈的!
主人回复:好的,妈的,多叫些人来,砍死它!然后让它把吞偶滴三十毛钱
吐出来、
回复5:我们都被小陈、啊不,是老陈、罚习惯了。丫丫的,真不爽
主人回复:妈的,偶滴钢蹦啊
学校中违规被老师惩罚再来到虚拟世界中宣泄不满,寻找安慰,并经他人回复与主人回复形成虚拟互动,通过谩骂达到对教师的虚拟攻击与反抗,现实中受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也使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控制的隐忍更富弹性。
(四)直接挑战
当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时,也会出现一些激烈程度不同的抵制行为以挑战权威。最为隐晦的方式是文本传达,周记是教师监控学生日常行为与态度的重要工具,反之农民工子女也会通过周记以自嘲、调侃的方式向教师传达对学校和教师权威的否定。
“昨天瞌睡过渡,眼皮打架无数,至终扛不住,误入梦境深处。呼噜!呼噜!惊起乘客无数”。以上便是我坐公交车的真实写照。致此我将这首“入梦令”献给广大与我有着相同经历的同学们。最后提点意见上课能不能晚点儿,天冷了早上6点我们便要顶着寒风等车。我容易吗?我。
周记中将完成过程中的各种应付、不屑不加任何掩饰的传达给教师,已经不在乎对日后师生关系和自身处境的影响。反抗程度更加强烈的就是完全生活在自己搭建的生活世界中,与学校建立的有序生活毫无交集。阿水㉓就是这样的学生,让所有任课教师头疼不已,也成为飞翔中学的名人。永远位居旷课、不穿校服、不交作业名单的榜首,面对教师的各种教导总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家长也对他无可奈何。虽然教师在学校中有绝对的控制权,受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约束却没有将违反者“驱逐出境”的终极权力,只能任凭阿水这样的学生“自由”地生活在规范之外。
激烈程度最大的抵制是主动辍学,离开学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师生频繁且紧张的互动往往是抵制方式升级的导火索。笔者在此插入实地调查中发生的“辍学事件”以说明这种抵制:
事件起因:语文老师让学生念课文,小吕㉔不好好坐着,把凳子晃来晃去的,语文老师之前已经说过其他同学了,他们都听话的坐好了,到了小吕这里,老师说:你不要晃了,坐好了,这都是公家的东西,你晃坏了,赔得起啊?老师还很好心地把椅子给他放好了,让他坐下,但是小吕根本就不管老师,继续坐下来使劲晃,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拿书戳了他一下,说他态度不端正,不好好学习语文。语文老师说:“你不好好学习语文,以后上厕所连个男女都分不清楚”。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吵了起来,语文老师很生气让小吕滚,他居然回敬了老师一句,你滚。吓得有的学生去找班主任,有的学生去找德育主任。——事后和其他学生进行的交谈
事件处理:把他的家长也叫来了,让他写检讨,但是写了两句就不写了,说自己就是不想上学,他妈也在。当时让他给语文老师认个错,他死活就是不认,就说自己不上了。这个孩子成绩一直以来都很差,20、30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反应慢,有点傻,上课就那么点成绩,你说他能听进去吗?孩子早就不想上了,但是他妈妈非要他上,其实他这样也是一种解脱,对他自己,对老师都是一种解脱。——事后与班主任访谈
事件最终以小吕辍学收场,也可看到师生现实冲突逐步升级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晃凳子”算是违反规范的行为,也没有服从教师的管教,在教师“赔得起”、“用书戳”、“态度不端正”、“滚”的指责中,小吕回敬“你滚”致使师生关系彻底破裂。事后,小吕继续拒绝认错、写检讨,并执意辍学宣告学校教育的失败与教师控制的失效。同时,“他是一种解脱,对教师都是一种解脱”也能体会到教师在这场战争中的精疲力尽。
四、“虚假性”的片面洞察
威利斯认为,在工人阶级的孩子当中盛行着一种以抵制学校权威为特征的“反学校”文化,他们通过调侃、进攻以及无时不刻的制造课堂问题来中断课堂秩序,通过打架、集会等方式彰显男子气概,欺负女孩、嘲笑少数种族群体,学业失败㉕。麦克比罗(McRobbie)也发现,女孩们会通过彰显女性特质和性特征来反抗学校对于好女孩应该规矩的期望㉖。与国外研究相比,周潇的“子弟”研究认为由于对知识、文凭的认同和肯定,农民工子女不是有意对抗学校规范和教师权威,对教师权威多少有些承认和顺服,抽烟喝酒打架等行为只占少数且具有隐蔽性㉗。如上所述,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也存在一种兼具娱乐型与抵制型的“反学校”生存逻辑。所谓娱乐型,是指不常以激烈冲突、明显挑衅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种表面服从权威,实则自我娱乐的反抗。所谓抵制型,则是与“小子”们相似的调侃、公然违规、对抗教师甚至辍学,而这一般发生在师生关系彻底决裂之时。
“反学校”生存逻辑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意味着什么?在后续跟踪调查中了解到,飞翔中学2007年考入高中的为53人,仅占学生总数的27.0%,08年考入高中的为42人,占总数的28.4%,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进入职校或直接进入社会㉘。无技术无文凭,辍学或初中毕业后都很难获得他们理想中的体面工作,大多跟随父母、亲戚工作,或进入无门槛的销售行业。即使职校毕业也没有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超市收银员、美容美发店学徒、空调修理工、业务员等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岗位是他们的主要去处。
为什么看似充满行动者智慧的“反学校”生存逻辑仍难打破阶层再生产的结局呢?这里,似乎也出现了以发现自主性和能动性为出发点的研究最后恰恰消解了研究对象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怪异现象㉙。威利斯认为,那是因为“小子”们的洞察是有限的(limitation),在看到资本主义教育系统本质的同时,也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中体力和脑力分工以及性别分工的合法性,因此,为显示与那些“文绉绉”的脑力劳动者不同,最终心甘情愿进入厂房工作,刚刚燃起的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火苗也随着“小子”们的主动放弃学业、投入工厂而熄灭。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育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如果说“小子”们的打工经历更加证实了中学文凭的无用和体力劳动市场的空间之大,那么农民工子女的日常生活经历也触发了他们对文凭与知识的思考。在大学毕业都面临失业的就业环境下,农民工子女非常清楚中学文凭不过是一纸空文。同时,学校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片段的碰撞也使他们质疑学校知识的价值:
学校里说的那些都是假的,骗人的,说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上次在菜市场看到有人吵架,明明是买菜的人不讲理,卖菜的打110,让警察过来说说理,但是人家买菜的家里有人,110来了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社会上,要不然你就有钱,要不然你就有权,别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与小朋㉚的访谈
书本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现实生活中的“家里有人”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片段也绝非特例,使农民工子女认为学校知识是“假的”、“骗人”的,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经济与权力。
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也使农民工子女深刻地意识到学校的行动者特质,即活动的本质是学校谋求自身发展。因此,当学校突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为考上某高中的学生奖励每人一台电动车时,在他们看来却是“为了给某高中拉赞助,让学生去那里上学,只有去那里上学的,给奖电动车的。”当学校开展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师生游”时,即便有幸参加游玩的孩子也认为这不过是“老师们想出来玩了,叫上学生就是一个摆设”。
为追求高升学率,飞翔中学还使用非正规方式将中考无望的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正规中考之外,再通过“校内中考”颁发毕业证㉛,而农民工子女对其中的交换关系也深知肚明:
学校做这些也不是白做的,我们不用参加中考,学校的升学率都上去了,对学校也好。不过对我们也是好的,起码我的初中毕业证不用愁了。——与小青㉜的访谈
农民工子女认为自己看透了学校教育的“虚假性”,主要针对的是教育的分层功能与学校的行动者特质。对于前者,他们明白中学文凭毫无竞争力,并非学校所宣扬的能够实现结构性身份的转变;对于后者,他们否认学校品牌教育的价值,认为那不过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深知与学校之间的交换关系。
然而,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育的“洞察”同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小子”把自身置于学校教育和文凭的对立面,而农民工子女虽然在形式上对抗学校制度和知识的传递体系,但他们并非真正反抗知识和文凭的价值㉝。他们知道在不同层次学校接受教育将面临不同的未来,也认可教育水平与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自己在教育系统的底端接受教育感到不公,而是认为“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视为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而自己之所以位于底端原因在于“没有钱也没有权”。其次,否定中学文凭竞争力,但也认为“有(中学文凭)总比没有强”,否定学校知识的实用性,但又以学习成绩评价自身能力。因此,讨论职业学校的专业时,英语成绩不好不会考虑计算机和汽车维修专业㉞,美术成绩不好就算知道汽车美容行业收入不菲也不会选择。正是这种片面性“洞察”使农民工子女所搭建的“反学校”生存逻辑具有温和、隐蔽的特征。
五、“反学校”生存背后的再生产意义
这里仍旧存在疑问:既然“反学校”生存逻辑最终仍旧以阶层再生产落幕,那么,突出来自底层的能动性意义何在?尤其当农民工子女认可教育与职业的对应关系,将自身的底层地位归因于自身,用学习成绩评价自身能力时,是否我们应该再次回归布迪厄的研究范式?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再次从威利斯的抵制理论谈起。如果真正理解威利斯对“小子”们“反学校”行为来源的分析,就必须要看到有限“洞察”的群体性。紧接着,当我们假设“小子”们站在群体层面去理解教育时,也就预示着工人阶级的阶层意识理应萌生。否则,我们又如何将他们的行为与阶层变革相联系呢?
马克思(Karl Marx)认为,“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能转变为“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为共同的阶级利益来集体行动。因此,农民不能算是一个阶级,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更像是“一麻袋土豆”,处境相同但彼此分离㉟。汤普森(Thompson,E.P)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决定性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相互作用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自在阶级”有了共同的经历,并通过文化生产的方式创造出阶级意识,进而转变为“自为阶级”,即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㊲。可见在“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中,阶级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阶层归属是获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却并非唯一要素,有时甚至不发挥决定性作用,譬如种族、社会地位、被压迫程度等也非常重要。
社会行动者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积极的占有者,只有通过斗争、竞争以及对那些结构的部分洞察,他们才将现存结构再生产出来㊳。当我们想用静态的结构性因素去解释动态的行为意义时,还必须考虑一个环节,即阶层意识。在对研究对象的阶层意识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枉然下定论说他们意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小子们的“洞察”是否真是来自群体层面的思考也就有待进一步商榷。同样,农民工子女虽然大多游走于城市角落与教育系统的边缘,但并未形成互为彼此的“我们感”。因此,对于农民工子女“反学校”生存逻辑应该在个体层面上予以理解,而对其能动性的关注则是勾连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的重要纽带。
在群体意识未生成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农民工子女的生存逻辑中挖掘学校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关系呢?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想致力于处理再生产理论家批评的不平等的话,我们就必须更好地理解社会再生产在微观层面的策略,就像我们必须去注意那些没有再生产自己所属阶级的人们的经历和实践一样㊴。因为,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宏观背景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微观制度支持中㊵。另一方面,微观层面上,人们行为的理解应既考虑具体情境也考虑情境之下的多元互动,这一点非常关键。当不仅仅在阶层角度上考虑“洞察”及是否有限时,“小子”们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为特定情境中的经历和实践。只有大多数“小子”们不再以自我、家庭而是以工人阶级群体来思考自己处境时,我们才应该去继续思考其行为所具有的阶层变革性。因此,农民工子女的“反学校”生存逻辑既非主动反抗,也非被动放弃,而是在边缘弱势的生存环境之下,在学校教育的实际互动之中,根据自身对教育、学校、教师的理解而形成的一系列策略性选择。他们懂得服从规范、赶工完成任务以与学校、教师建立良好的关系,懂得同意参加校内中考以换取个人能力无法获得的毕业证。总之,我们应该将文化生产放置在更为宽泛的生存空间中去探讨,看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与互动中,农民工子女通过何种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实践自己的人生。
注释:
①[法]杜里·柏拉:《学校社会学》,汪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②Bourdieu,P.&Passeron,J,C.,Reproduction: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Sage Publications,1990),pp.129-133.
③[美]珍妮·H.巴兰坦:《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朱志勇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④Swartz,D.,Pierre Bourdieu: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Inequality.Harvard Education Review,1977,Vol.47.
⑤[美]迈克尔·W·阿普尔:《被压迫者的声音》,罗燕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⑥㉑㊳[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64-170、24、226页。
⑦Bourdieu,P.TheWeight of the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London:Polity Press,1999).
⑧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⑨㉗㉝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2011年第5期。
⑩㉙熊春文,史晓晰,王毅:《“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
⑪曾坚朋:《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以外来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为例》,《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⑫㊵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⑬这种躲避现象在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并不少见,《现代快报》2008年11月18日B3版就报道了南京宁工学校随着农民工的进入,本地生源的流失现象,标题为《“名校”收不到学区生很郁闷》。
⑭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⑮小雨,女,17岁,父母离异,跟着父亲、奶奶和叔叔一家住,本身很好学,但是成绩总是很差,毕业后在职校学习。
⑯ Brown,P.,Schooling Ordinary Kids:Inequality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Vocationalism(London:Tavistock,1987).
⑰[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7页。
⑱为备战中考,进入初三后,学校会根据初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前30名学生组成提优班,之后的30名组成提合班。晚自习时,被分到提优班、提合班的学生拿着自己的学习资料分别聚集同一个教室里听课,而没有进入这两个班的学生则可放学离校。
⑲小华,女,17岁,学习认真,成绩较好,差班中的“优等生”。
⑳余清臣:《权利关系与师生关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㉒原文中调查资料中错别字均未做修改,以体现真实性。这种表达方式也是网络较为普遍的方式。
㉓阿水,男,16岁,被父母、老师、学生一致认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在学校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看小说、顶撞老师、上课迟到、睡觉。
㉔小吕,男,19岁,学习成绩差,上课和老师顶撞,不肯认错,主动要求退学。
㉕㉖ Collins J.Social Reproduction in Classrooms and School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9,Vol.38.
㉘据学校老师表示,飞翔中学2007年的中考成绩是可喜的,但2008年又是很糟的,在这可喜和很糟之间,我们却能够看到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的大致流向。当然,很多农民工子女虽然考上了高中,但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职校,还有的在职校上学没几天,就选择辍学,尤其是职校的比例,受学校所采取的“后台策略”影响,比例更加失真。因此,笔者在此仅仅参照高中的比例。
㉚小朋,男,19岁,聪明,认为学校知识没用,初中毕业后随家人安装空调。
㉛关于飞翔中学提高升学率的系列措施将在另一篇文章《学校教育中的再生产漩涡——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4期中重点探讨。
㉜小青,女,18岁,人缘差,常说脏话,讨厌老师,初中毕业在超市做收银员。
㉞认为会需要英语和购车客户进行交流。
㉟[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㊱[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页。
㊲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2005年第1期。
㊴ Kaufman,P.,Learning to not Labor:How Working-Class Individuals Construct Middle-class Identitie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3,Vol.44.
(责任编辑 陈振华)
Counter-School Survival under Partial Perception:Discussion on Education and Stratum Reproduction
SHIQiuxia WANG Yijie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Jiangsu,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The authors’field research in a public school for migrant workers’children reveals that among the underachieverchildren with little chance of entering a higher school,a survival logic of counterschool characterized by recreation and resistance is taking shape.This logic is based on the partial perception of education under themarginalized and disadvantaged life situation.The children finally choose to enter the secondary labormarket,hence the stratum reproduction.However,the strategic selection by the children in specific contexts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reproduction.When there is no strong in-group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migrant workers’children,the dynamic in counter-school survival logic does not have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the fate of social stratum.
migrantworkers’children;partial perception;counter-school survival;reproduction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3.00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距离及其弥合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CSH00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项目批准号:12CSH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