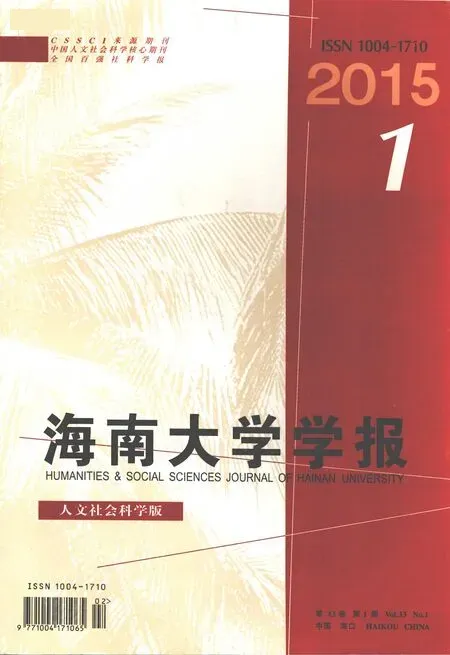论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
2015-03-18程磊
程 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由白居易“中隐”思想指引下所开创的庭园山水,是中国山水审美境界的一大转关。谢灵运的永嘉山水与王维的辋川山水,总体上是表现远离人寰、由凡入圣的山林意趣,白氏则依洪州禅的平常心由圣入凡,将山水游赏移至中隐人生的都市庭园,在凿池叠山的“意中之景”中转物生境、具心自足。宋人更以透脱禅悟凡圣双遣、两边不执,一方面入世从俗普遍于郡斋寓所营构园林小景,不必亲涉险远即得山水之趣,突出追求象外之象的心灵境界;一方面又任道自省挺立精神主体,于山水赏悟中饱含对宇宙人生之理的深刻思考,突出优游自适的理性人生态度。宋人开出的全新的庭园山水境界,是唐宋文化转型和审美理想嬗变背景下审美主体“以哲思对山水”的显著反映[1]。理学的哲学体系构架和心性证悟功夫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的游园观物将体认宇宙之道与塑建理想人格紧密结合起来,追求合道德与审美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构成了宋人山水审美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一、“理一分殊”——重建天人体系
理学家致力于讲道授业以恢复儒家道统、穷理尽性以明天人之际,但也不废山水游赏之乐。“北宋五子”之中,除程颐以“作文害道”的较为保守的文学观而几不作诗外,其余诸人皆不辍吟咏。周敦颐存诗三十三首,大多是行旅寄兴的山水诗;张载以长篇七古作气象雄浑、景象飞动的山水诗如《岳阳书事》、《和薛伸国博漾陂》等,足见其胸中自有无限丘壑;程颢存诗七十余首,绝大部分为游赏山水园林之作,如《陪陆子履游白石万固》:“他时会合重相语,辜负泉石何能忘”[2]8235、《和王安之五首·野轩》:“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2]8238,显出雅好泉石的浓郁诗兴;邵雍更以退居洛阳“安乐窝”和富于吟咏著称,自编《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存诗达一千五百余首,其中有大量累牍连篇的以园林四时风物、闲碎生活情态为内容的咏怀体道之作,被后人称为“邵康节体”[3]。总之,从整体创作情况看,丰富精彩的理学山水诗在宋代山水诗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其美学哲学意义并不在此,理学对传统山水审美及庭园山水境界的影响,应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审视:理学是为挽救传统文化体系的崩毁和解决现实思想危机而应时受命的,它以闳大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传统文化框架内部进行调整强化,吸收禅宗精义,再建孔孟传统,延续文化活力,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艺术等方方面面,理学文艺观和审美旨趣反映了文化肌体内倾精密而日益衰变的总体趋势。在经由宇宙本体的“理”这一核心锁钥所构建起来的天人体系中,诸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哲学理念和艺术思维都包容其中,理学家讲道论学中深邃精微的人心道心,与其观物体道时生意自得的思理证悟,无不具有内在深刻的一致性,即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宇宙观、人格观和审美观达到了理论构建上的致密结合而几乎浑然一体了[4]462。这是本文讨论理学庭园山水境界深层意蕴的基础。
在宇宙观方面,理学主要是自觉吸收佛教的宇宙观和心性论,以及道教的宇宙模式来改造中唐以来趋于坍塌的传统天人体系,以完善和强化“天人之际”的宇宙观来为重建儒学伦理本体服务,以人心对宇宙秩序的悟解和承担来为重建现实政治秩序服务。“中国实用理性是以人可以参预的‘客观’天道为最终法则”[5],战国诸子百家已开始以几乎一致的态度致力于建立庞大浑阔的天人宇宙体系,寻找和设定以无限广大、具有宇宙普遍意义的“天”,来使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升到本体高度以指导具体人事活动,士人的人格境界也只有提升到与天地宇宙同体的高度才能找到终极依据。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结合阴阳五行观念,建立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图式使政治本体化,为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提供了政治哲学的指导,不过这里的“天”仍带有天命意志的人格神的影子,宇宙与人事之间感应、制约的反馈机制仍显得朴拙和粗疏。经过自身理论系统的汰炼调整以及与玄学、佛学思想的碰撞融汇,代表永恒天道的政治本体终于在盛唐达到了极盛状态而创造出辉煌的盛唐文化。中唐以后严重的政治危机造成文化理想的失坠,儒学衰微、佛老炽盛、价值虚空、信仰失落显示着传统天人体系濒于破毁,从韩愈、白居易到欧阳修、王安石,士人对孔颜仁圣的道德偶像、对天经地义的礼乐天道都产生深刻的怀疑和质询,或焦灼紧迫地孜孜补救,或沉沦颓唐地汲汲行乐,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盘根错节的危机症结。
理学家正是从重建天人体系的高度来思考解决这一症结的,只有确立了坚实的宇宙本体论,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才有安放的正大位置。周敦颐《太极图说》借用道教宇宙论由无极而太极,由动静阴阳化生万物,最终落实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通书》云:“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幾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幾微故幽。诚、神、幾曰圣人”(《圣第四》)[6],显示出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内在逻辑。张载继承《易传》“天行健”的精神提出气一元论的宇宙观,来充分肯定感性现实世界的物质运迈迁化,以扞击佛老主于幻化空无的唯心论,“气”的聚散流行是为了推出“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的宇宙万物及人之“性”。《宋史·道学传序》云:“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都是要为伦常人性、“道之大原”树立精微严密的宇宙观来溯源张本。“理一分殊”的话头虽不自张载口中说出,但程、朱一致地以这种宇宙本体论来作为构建自身天人体系的理论支柱,如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云:“《西铭》明理一而分殊”[7]609,朱熹也说:“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8]72。为此,程颐拈出更为抽象、普遍必然的“理”代替张载较为物质性的“气”来作为其天人体系的基石,认为宇宙万物虽至浑至虚,至纤至悉,无论面目如何千差万别,都是宇宙本体的“理”的化生显现:“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周易程氏传》)[7]858、“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7]195,程门弟子杨时亦云:“天地之造化,万物归于一理”[9]。“理”既是永恒的抽象本体,就主宰支配着与人生存相依、不可逃离舍弃的感性现实世界,不仅主宰物理运迈,万物化育(认识论),还贯于心统于性(人性论)而为现实世界的伦常秩序提供本体的依据(伦理学):“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7]204、“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7]292,将“心性”、“性善”尊之为天理之所赋予,这是弥补了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语焉不详的地方,又将《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内在论提升为本体论。朱熹更是屡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10]2、“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流行之妙”[10]1026、“心理流行,脉络贯通,无有不到”[10]2518,这“理”就囊括涵容了天地宇宙间的一切物质经验存在以及心、性、命的伦理道德内容:“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1],此即“理一分殊”、“月映万川”。“理”在涵括时空宇宙之本体的意义最终都要落实到心性层面,为伦理道德提供本体依据,从而在张载那里尚需要从感性的、经验的“气质之性”中去穷极“天地之性”,到程朱这里就只要识此“天理”尽心知性就能直抵伦理本体,也就是人在物质形器与心性境界上都能达到冥合宇宙本体的“天人合一”。“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7]13,20,道器不离,天人为一,身在道中,理学就这样自觉地完成了以“理”贯穿宇宙人心的至大无极、精微无比的“天人”体系。
于是,在此天人系统之中,依据理一分殊之旨,理学家在山水审美中的观物方式和态度就显出不一般的意义来。朱熹曾借譬水月相摄的禅典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10]2409,即天地万物虽万殊不一却又各具一理,即使是至微至细者亦能直接显现着这个精微的本体,那么丘山毫末、太仓稊米就无本质差别,即使是面对亭园中的一木一石也能感受到无穷宇宙运移迁化的律动,故能涵纳万有而与之和谐融一。又在阐释《大学》“格物”、“致知”时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8]7
“格物”就是要以人心之灵去高度自觉地发现和把握此宇宙本体之“理”,以主动的实践行动融摄在“天人之际”的体系当中;且“理”并非是高踞于现象界之上的“超验”理性,而仍是以“仁”、“性善”等感性血肉的心理情感为依据,所以感性的现象界与理性的本体界并不截然分割而是交织渗透在一起,此即所谓天人本无二;依现象而求本体,一面要观物之理(“即物而穷其理”),一面又要不舍感性而体其生意(“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促进天与人在此即感性又超感性之中浑融合一,从而“以明吾心之全体大用”,使极为自律又高度自觉的伦理主体达到一种融入宇宙大化又生意盎然的“本体性”的人生境界,这与审美愉悦中悦志悦神的境界极为相似了。总结来说,理学家的观物而得其生意是以《易传》之“生生”、“天行健”、乾坤推演、阴阳摩荡的宇宙观为大化流行的外在骨架,以《中庸》性命诚明、参赞化育的心性探讨为生机弥满的内在肌理,吸收了庄禅对宇宙本体的邃密思辨以及注重内心超妙灵动的独得悟性以为己用,使理学家眼中的自然宇宙呈现出别样的生机和理趣。理学家亭园山水境界的要义即在于,在观物体道的哲学运思以及审美体验中,主体的自我呈现也显示出与宇宙本体浑融如一,从而自备天地万物之道而达到体验宇宙永恒和谐的“天人乐”。
二、“观造物生意”——由观物而证道
下面结合具体诗例来看,如邵雍《盆池吟》:
因开瓮牖,遂凿盆池。都邑地贵,江湖景奇。能游泽国,不下堂基。帘外青草,轩前黄陂。壶中月落,鉴里云飞。既有荷芰,岂无鳧茨。既有蝌蚪,岂无蛟螭。亦或清浅,亦或渺瀰。亦或渌净,亦或涟漪。风起蘋藻,凉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归。密雪霏霏,轻冰披披。垂柳依依,细雨微微。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物,可以看时。不乐乎我,更乐乎谁?[2]4606
这是典型的依盆池之狭而心生江湖之广的“意”中园林境界,在中唐白居易等人的“壶中”园林中已普遍出现,算不得新鲜。然而进一步从中观止忘机、照物看时,体味化育万物的宇宙本体时,这小小盆池的境界就显得豁然无穷、邃极弥广了,这就并非单纯以禅思转物的直觉想象所能企及。程颢《盆荷》其一:“谁言无远趣,自觉有余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其二:“衡茅岑寂掩柴关,庭下萧疏竹数竿。狭地难容大池沼,浅盆聊作小波澜。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凉风助晓寒。不校蹄涔与沧海,未知清兴有谁安”[2]8240,这些于小盆池得大宇宙的庭园山水境界,展现出理学家独特的理趣和胸怀。邵雍《户牖吟》又云:“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蔾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说的也是同样意思,只不过这种融入无穷宇宙静机的天乐感受比前人要更自觉、更学理化了。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他的“以物观物”说: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观物内篇第十二》)[12]49
所谓观物以目、以心、以理,显然得自庄子的“听之以耳”、“以心”、“以气”,其着眼于以“理”代“气”,就与理学重视把握宇宙本体之理的趋向有关;所谓万物之理、性、命,邵雍解释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观物外篇下》)[12]163,这是事物本质属性和存在根据在不同侧面的表现,故《周易》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沿此以理观物的基点发展下去,就是要“一万物之情”而达万物之理,这与“理一分殊”的宇宙观是一致的。如何才能达到圣人之观物呢?就在于能“反观”:以物观物。达到这一境界有三层内在的逻辑:第一,因为“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主体之“我”与宇宙万物虽彼此分别,界限斩然,但同作为“物”的本质属性的理、性、命则具有深刻的一致性,都是各有禀受又具全如一的“一太极”、“一月”而已,故反观自身得自我之理、性、命,即可以通达万有而知万物之理,此即“万物皆备于我也”。第二,反观自身又并非以身观物。邵雍提出了道、性、心、身、物的向外推衍的系统观照序列:“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这是尚未摆脱主客物我对待关系的观物,犹且牵于利害、“溺于情好”而“相伤”,惟有“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伊川击壤集序》)[12]180,就是要保证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各自独立不受侵伤,不以物累我,亦不以我染物,从而“确立一种超越于主客心物的‘两忘’式认识主体”[13]65,如此一来,“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这里显示出宋人普遍的游弋于物又希求摆脱物累的理性态度。第三,以物观物要确立私情净尽、明澈无染的主体心灵,将主体之我置于客体之物的主位上,以区别于“以我观物”。《观物外篇下》云:“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12]152,可见他是极力强调摒弃主体之情,以“使其禀受于天的理、性、命朗然呈现”,所以“观物”的主体“不是个体化的主体,而是集体化的主体”[14]。这与苏轼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形成了鲜明对照,二者都有转入内心,不滞于物累的一致性,但对于主体精神的提举则指向相反:苏轼恰恰是以“我”观物,任我以情,情感的本体化导向对精神独立自由的个体追求;邵雍则是超越庄子的“心斋”、“物化”而与“那种‘本性清明,周流六虚’、‘广大清明,照乎天地’的本性自觉为一”[13]68,此亦显见理学与苏氏蜀学的分野。
尽管如此,邵雍的“以物观物”仍给弃绝一己之私欲情感的主体带来死生荣辱不入胸中、静观宇宙运迈机趣的“观物之乐”,正如其自序中说:“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观物之乐竟置于“名教”之上了。其诗中亦屡屡表露出观物自得的平和怡悦的心态:“灯前烛下三千日,水畔花间二十年。有主山河难占籍,无争风月任收权”(《安乐窝中吟》其二)、“萧萧微雨竹间霁,嘒嘒翠禽花上飞。好景尽将诗记录,欢情须用酒维持”(其七)、“山川澄净初经雨,草木暄妍正遇春。造化功夫精妙处,都宜分付与闲人”(其十一)、“轻醇酒用小盏饮,豪壮诗将大字书。花木暄妍春雨后,山川澄净九秋余”(其十二)[2]4556-4558,这类安乐窝中吟风弄月、观时照物之诗何止百千计,却的确成就出一种闲适忘情、超然纯净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在大自然中领略宇宙妙机的清朗澄明的心性境界,也是儒家一贯追求的道德理想臻于审美化的人生境界。朱熹曾说:“邵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此言,事物皆有造化”、“渠诗玩侮一世,只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意”[10]2553,邵雍自有诗云:“造物工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依韵和刘职方见赠》),又云:“须识天人理,方知造化权”(《苍苍吟》)[2]4512,4640,“以物观物”构成了“物”与“我”的双向整合关系,既渳沦应接又各持独立,为理学家体察自然宇宙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心性修养功夫遂又进一步开示出一种“诗化的悟道证道方式”[15],此即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观造物生意”的命题。张九成《横浦心传录》载:
明道书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劝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16]
类似“观物生意”的例子还有许多。此种“生意”透显出在天人体系内物我生命接洽融凝于生生大化之中的欣悦自在,“诗化之证道”即是在与现象界浑沦一体中而抉发道心,同时获致一种融入宇宙本体的精神愉悦,这几乎是所有理学家观物悟道所臻极的本体心性境界。如程颢还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纟因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7]120,朱熹亦云:“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10]795,即都是要在天地宇宙间充溢以一种活泼流动的诗性生命存在。正是这种不离现象界的觉入体认,那些青青茂草、袅袅游鱼,以及理学家所常称引的风花流水、鸢飞鱼跃等充满自然生机的感性情景,就构成了山水审美及园林境界中最富审美意趣的根柢之处,此即所谓“见得道体之自然”。如《上蔡语录》载:“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17],朱熹说:“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见之妙处”[10]1534,类似的话程、朱语录中说过许多。理学家诗中也最常见这种生机弥满、充盈流荡的“造物生意”,如邵雍《年老逢春十三首》其六:“池亭正好爱不彻,草木向荣情奈何。便把樽罍通意思,须防风雨害清和”[2]4546、程颢《和尧夫西街之什二首》其一:“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时泰身闲难两得,直须乘兴数追陪”、《郊行即事》:“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2]8237、8239、连绝少作诗的程颐亦在《陆浑乐游》中云:“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2]8374,像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胜日寻芳泗水滨”等悟道之景句就更是脍炙人口了。这些造物生意都直接显出道体化育流行之无限生机,而不至于偏枯奥晦,窈冥难致,又呈托出体道之主体那胸次悠然、襟怀洒落的高明圆满的道德-审美境界。理学家的观物之乐,其外在格局显现的是天人合一的浑融凑泊的宇宙体系,而内蕴生机则源自“大快活”、“天机自完”、仁者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心性本体,这本体已不完全是伦理道德,而是融道德与艺术于一体的审美的人生境界。所以理学家眼中的自然山水,抑或园林中的山石亭树等,既不同于玄意山水的自然机静,也不同于禅意山水的寂淡空灵,而是以儒学“仁”为根基的冲融和畅,饱含深郁醇厚的人间情味而又映现出观者从容洒落的审美胸怀,是儒对庄、禅的吸收与超越;由于理学家在整体上是轻视艺文的,所以它虽并不突出表现在山水诗的创作评论和园艺造景的理论实践上,但同样可以表现为一种应接自然、提举胸臆、美善交汇的审美人生态度而凝聚在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山水审美与园林赏玩中。
三、“天人乐”——审美乐境的形上追求
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又进一步与理学的人格观联系起来,形成了庭园山水境界中突出的人格境界。理学的人格观和宇宙观有着本体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宇宙观的建立还是为塑造道德人格的主体性而服务的,理学的哲学重心始终要从宇宙论落实到伦理学上来;理学家也并非只就“孔颜乐处”、“曾点气象”作重复儒家原典的解释,而是将其提到形上的超越高度,使之成为一种“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18]188;审美主体达到此种超道德的、本体性审美境界,才可能在山水园林审美中体验到悠悠天和的“天人乐”。中唐以来的文化危机导致士人的人格危机,价值信仰的空洞严重销蚀着孔圣颜仁的传统道德人格理想,至北宋则前有柳开、王禹偁,后有欧阳修、王安石等都试图重建士人的理想人格,重举孔、颜偶像来使士人人格超拔出晚唐五代的萎靡孱弱。但根柢的缺失和文化的颓势使这些矫世之举都无济于事,无法树立起新型的、足可倚恃的人格理想。理学关于孔、颜人格建构的突出特点和时代意义即在于,不单纯在社会伦理层面加以纠偏,而是“以高度完善的宇宙理论为基础,把孔、颜人格上升到与宇宙本体浑然为一的境界”[4]401。二程屡屡陈述:孔、颜所乐根本不在自甘箪食瓢饮、安贫守道的生活实践层面,而是“别有乐处”,即是在宇宙观的层次上,“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之用皆为我之用。……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7]17。朱熹亦承接二程观点而阐发得更为详尽:“程子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10]796。此“乐”与“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忧”一样,虽仍不脱离感性心理,但显然高于凡俗物质生活与精神活动之种种,涤去私欲而与天理同流,泰然廓然而无所间杂于心,这样“乐”就由道德而提升到超道德的审美境地(“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曾点气象”的理解也是如此。二程谓:“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又说:“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7]369,366,“涵畅道德”而乐得其所就有了由道德而宗教的安息灵魂的意味。朱熹也说:“问:‘曾点言志如何?是有尧舜气象?’曰:‘明道云:万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尧舜气象。且看莫春时物态舒畅如此,曾点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处。尧舜之心,亦只是要万物皆如此尔’”[10]1034、“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8]130,关于此朱熹还说了许多。“曾点气象”其实正是“孔颜乐处”那种熙然悠然的精神状态的具体显现,它“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是理学家发儒典之未发的人生至高的审美乐境,显示出以此为皈依的宗教式情怀,这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宋明理学确实发掘和发展了儒学宗教性的深度”[19]。这“乐”直观地与春游、浴沂、舞雩、“物态舒畅”这些感性的审美经验联系起来,以“孝悌”、“恻隐之心”的伦常情感为基石依据,尽管理学大讲穷理、尽性、体仁、成圣的超验的理性探询,却仍然要回到生意盎然的现实人生,回归到具体的人际社会和人世情感中,这感性的生活、情感无法舍弃,与理性的融化和积淀就表明着中国文化是以审美来代替宗教的。从而像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深沉博大、卓绝崇高的人生宣言,就不止是道德人格的极致,而是审美人格的“天地境界”,伦理学的下一转演即是美学。以此种理想人格去应人接物,就自然是优游涵泳、顺适康宁,不但乐而恬淡,忧亦从容,亦且能悲欢不动,宠辱不惊,生死不撄,达到与天地万物同流、“天人合一”的“天人乐”;以此种“成于乐”、“乐之者”的审美人生态度去观物、观山水、观宇宙,与庭前草、池中鱼、无私花柳、无边风月相周旋应接,就自然是触处成春,生机流动,一切都呈现着宇宙运迈与心性体认的交流融炼,和谐为一。程颢那两首著名的《秋日偶成》就是理学人格与审美态度的最好体现,也可以为我们分析理学家的亭园山水境界提供观照的窗口和品鉴的佐证: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其一)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其二)[2]8237
这里虽然没有山水形象或亭园风物的具体描绘,但人们无疑感受到,悠悠天地、茫茫万古的“天人之际”的宇宙体系,万物静观皆自得生意的内蕴生命静机的苍浑律动,以及优游自乐、涵泳天理的理学人格已经浑然一体了,构成了这种“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本体人生境界。中唐以来士人那种忧心如焚、若无所倚的价值失落和人格忧惧都在此得以廓清,利名蠛蠓、兴废浮沤这些关于人世空无感的厌倦、惶惑、戚戚不安、踽踽不定也都得以消融在从容悦乐的人生态度中,这是理学给山水审美和亭园观物赏玩带来的全新的主体自我,也由此改变着园林美学的风貌品位。我们知道,中唐以降出现的“壶中”园林境界,反映的是传统宇宙观、天人体系的崩溃和文化生命力的衰弱,士人不可能在外向事功上取得自我价值的确证,才会遁藏退缩到壶中园林中求得形骸托庇与精神寄泊,由此也带来了传统政治人格的失落以及对自足的内心世界的发现。尽管由于禅宗思想的导引,狭小的壶中天地亦能显现无穷广大的峦壑江湖和转物造境的心灵世界,但士人与浩茫寥廓的宇宙之间的生命联系、与“为天地立心”的崇高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联系,却不可否认地日益疏离而缺失了,耽溺诗酒闲乐难掩心中悲凉,寄意佛老慰藉更觉人生空幻。这双重矛盾摆在重续道统的宋人面前,就促使士人通过哲学的、艺术的多种方式来谋求解决,以化遣心灵中百倍噬啮的焦灼与困惑,来重建人格理想与融摄天人宇宙、兼顾社会历史责任的联系。理学重建“天人之际”与“孔、颜人格”的时代意义,正是要在这日渐衰弱的文化肌体上打一针“强心剂”,由于并没有新的精神资源可供利用,亦尚未能开辟新的出路以挽救文化困境,就只好回到传统中,开发、集结和吸收儒释道思想中的有利因素,融聚在理学的“天理流行”的思想体系中,以尽可能多地释放出巨大能量来镇痛遏疾,抗御文化危机,实际上是“为士大夫将退入‘壶中’的理想人格和理想宇宙关系重新充塞整个‘天人之际’宇宙体系找到了切实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支点”、“重新实现其社会、历史、宇宙理想的统一,是士大夫人格内在意义与外在意义的统一,是士大夫内心的和谐、‘壶中’生活环境的和谐,直至整个宇宙和谐的统一”[4]417。这在道学家邵雍据守安乐窝,以及与道学颇有渊源的司马光述志独乐园那里都有极致的体现。甚至不列道学名席而同样沾溉此种人格构建的时代思潮的士人,也常在园境中表现出追求弘道立心、反身穷理、与整个宇宙和谐为一的倾向,如曾鞏《清心亭记》云:
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者,夫岂远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极天下之知,以穷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尽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虚其心者,极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齐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则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国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为是亭,曰不敢以为游观之美,盖所以推本为治之意,而且将清心于此,其所存者,亦可谓能知其要矣。[20]
曾鞏所论在此园林审美中亦能“神明其德,与天地同其变化”,在于“虚其心者,极乎精微”,从而穷理尽性而无累于外物,以此推而为齐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不正是“重新实现其社会、历史、宇宙理想的统一”么?如此“推本为治”的人格塑建和心性内掘的思路,尽管或许尚未能达到理学思想体系的严密精深,却具有多么鲜明的时代一致性。黄庭坚《松菊亭记》亦云:“期于名者入朝,期于利者适市,期于道者何之哉?反诸身而已。……歌舞就闲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于道,岂可以无孟献子之友哉?……贤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于以听隐居之松风,裛渊明之菊霞,可以无愧矣”[21],反身以期于道成为士人人格砥砺的自觉而理性的形上追求。黄庭坚以诗人儒者的身份而最与理学治心养性的宗旨相契合,故朱熹亦赞曰:“吾道千载不传之秘,至周子而后传。当时知其人品者惟山谷焉。谓山谷为不知道不可也”[22]。黄裳《默室后圃记》云:
默室之中,盘踞而独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为天游,寄于貌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与道相会,道与意相适,于是而下焉,开目则欲有所寓,垂膝则欲有所适,乃之圃之中,讽遗编,鸣寒弦,衔素杯,战枯局,联诗篇,点花数,与忘形交,于此为谈笑以寓道,情之至乐。……然则圃虽小,而仁智者寓焉,则圃甚大矣,虽举广圃名苑,绝景盛赏而与之较,彼特有物耳。……惟君子之乐不在物,而物者特其乐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23]
仁人君子乐其所乐的人格理想,无穷天游的广阔宇宙,尽在这“垒拳石为山,钟勺水为池”的小圃中交融无间,尽管身之所处陋隘无比,却不妨士人在其中将自我人格扩展而充塞宇宙之间,此为宋人最为典型的游园乐境和体道之境。随着理学自身的逐步发展,这种反身而诚自备万物,又扩而充溢于无穷宇宙之境的哲学观念和园林美学,就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士人亭园山水境界[24]中,至南宋时已有相当成熟完备的“理学式”的园林出现。
再回到程颢的那两首诗,朱熹曾说过一段话:
“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己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明道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观他此语,须知有极至之理,非册子上所能载者。……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须是自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10]414-415
在朱熹“应然”(“所当然而不容已”)等于“必然”(“所以然而不可易”)的理论体系中,这个“向里入深去”才理会到的“太极”、“极至之理”的本体,成为高于现象界的、个体必须遵循的先验规范和绝对律令,日益显示着高度强化的天人体系与邃密精微的心性境界的统一,无数具体而微的庭园山水其实正是这种哲学观念在园林艺术中的反映。南宋后以至于明清士人园林境界愈见精致深微,有“芥子纳须弥”之说,就是将“壶中天地”进一步内倾收缩而推向心灵境界的极致,实际上也表明,传统文化生命活力经理学的强力撑拄挽救之后,也终于榨尽最后的能量而式微衰落了。我们再看中唐北宋以至明清庭园山水观念的变化,则宋代理学家那一整套宇宙心性系统内的观物方式和人生态度,无疑为宋代甚至是整个传统社会后期的山水美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程磊.山水诗中审美主体自我呈现方式的变迁[J].云南社会科学,2010(6):156-161.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9.
[4]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0.
[6]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
[7]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杨时.周易札记:卷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朱熹.晦庵集:卷七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5.
[15]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08.
[16]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88.
[19]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15.
[20]曾鞏.曾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296.
[2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38.
[22]朱自清.宋五家诗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82.
[23]黄裳.演山集:卷十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程磊.宋代士人吏隐的精神价值与山林境界的转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14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