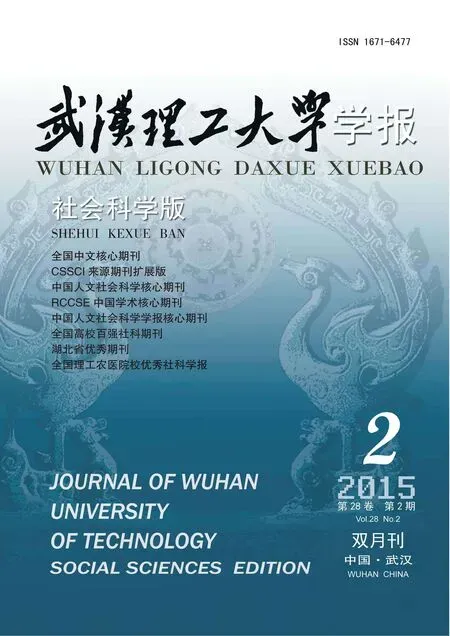论演绎作品的固定性
2015-03-18孙玉芸
孙玉芸
(南昌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论演绎作品的固定性
孙玉芸
(南昌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不同于其他作品,各国版权法对演绎作品的固定性要求有采双重标准之嫌:一方面它要求演绎作品在受版权保护时,必须具备固定性;另一方面,在认定演绎权被侵犯时,它又否定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立法上的这种二重标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法院判决,产生司法实践中的双重标准。对演绎作品固定性的这种双重要求,既不符合版权法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效率。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版权法对演绎作品固定性的态度宜回归单一,在肯定合法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同时,也肯定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
演绎作品;固定性;演绎权
固定性(fixation),是指作品要被实际固定于有形物体之上。所有作品包括演绎作品,要受到版权保护,一般认为都应有固定性,但是,非法演绎作品例外。为了认定侵权目的,非法演绎作品是否应具备固定性?对于此问题,各国立法及司法都较为含糊,未给出明确答案。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演绎作品固定性的认定,常常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一、作品的固定性要求
版权法对作品的保护,一直与作品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在作品与作品载体尚未截然区分时,对作品的保护就等同于对作品载体的保护。那些不能用物质载体固定下来的作品,自然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而当作品与作品载体被逐渐区分开来后,对作品的保护虽然获得了独立意义,但却仍然无法与其载体完全分离。作品是无形的,它必须依赖于有形物(特殊时候也可以是人)的存在才能被感知、被传播。如果不借助于书籍、唱片等有形形式记录下来,那么即使有原创性的作品也将转瞬即逝,既无法传播,也难以保护。如果一个复制没有被保存下来,或者一个证人没有很好的记忆,那么我们将很难证明别人侵权[1]。所以,当版权法被认为保护的是作品本身而非作品的有形载体时,法律所主要保护的,还是那些可以以有形物记载下来的作品。那些没有被有形载体记载下来的作品,多数都只是名义上受到版权法保护,实际上仍处于无法律保护状态。因此,虽然从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出发,著作权体系不要求作品必须被固定于有形载体上,只要求作品能以有形形式复制即可。但事实上,由于没有被固定下来的作品很难被保护,著作权体系的这一无固定性要求意义并不大。对于绝大多数作品而言,固定性是它们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
与著作权体系不同,版权体系从保护作者的财产利益出发,不仅要求作品应被记载于复制品或录音制品之上,而且将这一内在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例如,英国版权法第3条第(2)款就规定:“在以书写或其他方式记载(record)下来之前,任何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都不享有版权;凡本编中的作品创作时间均指该作品被记载下来的时间。”在美国,固定性不仅被认为是一项版权法要求,还被认为是一项宪法性要求,它渊源于美国联邦宪法:由于宪法使用的是writings而非work来指称作品,因此一部作品必须以某种物理形式存在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否则,宪法中writings一词的使用便没有任何意义。1976年的美国版权法首次规定了作品的固定性(fix) 。该法第101条规定:“作品‘固定’在有形表现形式上,是指经作者授权,将作品体现在复制品或录音制品上,其长期性、稳定性足以使作品在不短的时间内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被播送的由声音或图像组成的或由两者所组成的作品,如果是在播送的同时进行录制,视为‘固定’”。在第102条(a)款中,该法又进一步解释了固定性要求:“依据本法,版权保护固定于任何有形表现形式上的作者的原创性作品。通过这种有形表现形式(包括目前已知的或以后出现的),作品可以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播,不论是直接或借助于机器或装置。” 因此,在版权体系,只有当作品记载于一定的有形物上以后,在可以被他人感知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版权保护[2]。英美国家不保护那些没有以有形载体固定的作品,如口头演讲和即兴表演等。
二、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双重标准
按照一般观点,演绎作品也是作品,必须既有原创性又有固定性。无论是作为保护目的还是作为认定侵权目的,演绎作品都应该具备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然而,就现行各国版权法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来看,对其固定性的要求似乎并不同于其他作品,颇为含糊。美国《版权法》即是这一立法态度的代表。首先,该法第101条对演绎作品的定义,就只提到了对已有作品的重作、转换或改编,并未使用复制件、唱片等词和其他与固定有关的词汇。其次,该法第106条第(2)款在界定演绎权时,“根据版权作品创作演绎作品”中的“创作”使用的是“prepare”(准备)一词,而在其他条文中,凡涉及“创作”的地方都使用的是被界定为是固定的“create”(创造)一词。美国《版权法》关于演绎作品的这两大特殊规定,被认为具有特别意义。它意味着,在演绎作品的固定性方面,版权法持双重标准:即,演绎作品如要受到版权保护,则须满足固定性要求;反之,如果是为认定侵犯演绎权,则不需要具备固定性。例如,在解释1976年版权法时,一份议会报告就指出:106条第(2)款的演绎权,在某种程度上和复制权重叠,但它比复制权的范围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复制权要求侵权作品须被固定在复制品和唱片上,但演绎作品,如芭蕾、舞剧或其他即兴表演,即使没有固定在有形载体上,也构成侵权。另外,来自于版权记录处的一份1965年的补充报告也显示:演绎作品只有在要求获得版权保护时才须固定,如果是为认定侵权目的,不必固定[3]。
关于演绎作品固定性双重标准的立法解释,也进一步影响到法院判决,产生司法审判的双重标准。例如,在Galoob案[4]中,法院就一方面否定了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演绎作品应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在该案中,原告美国的任天堂公司Nintendo制作了一款家庭游戏机(NES),在该游戏平台上有很多格斗、赛车、棋牌等电子游戏。被告Galoob设计出一种名为Game Genie的装置,该装置允许玩家修改任天堂游戏人物的三个特征:增加游戏人物的命,加快游戏人物行动的速度,允许人物在障碍物上漂浮。在将Game Genie与原告游戏相连后,玩家只需要手动输入被告提供的作弊码(code),就可以激活Game Genie,拦截由原告游戏发送给NES控制中心的数值,并用新的数值代替原数值,得到自己想要的视听显示。
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的演绎权,主要取决于该新的视觉显示是否属于版权法第106条第(2)款中的演绎作品。为解决这一问题,法院考察了版权法第101条对演绎作品的规定指出:第一,第101条的演绎作品不需要满足第102条第(1)款所规定的固定性。固定只是一部新的作品作为演绎作品受版权保护的要求,而非认定该新作品侵犯他人演绎权的要求。为认定侵权目的,演绎作品不需要满足所有的可版权性条件。法律中使用的“copies”(复制件)一词和演绎作品是不同的。复制品是一定要求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但演绎作品则不必。那种认为演绎作品是作品,作品被创造时必须被首次固定的观点,错误地理解了法律的规定。事实上,法律关于演绎作品的定义并没有明确提及固定这一要求,并且使用的是“prepare”(准备)而非“create”(创造)。第二,第101条中的演绎作品需要以某种“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无论是从第101条所使用的“任何其他对作品的重作、转换或改编”措辞来看,还是从该条对演绎作品的举例来看,都涉及的是以有形形式包含原作的演绎作品。因此,尽管第101条中的演绎作品适用于第102条第(1)款的规定,但是,该条本身仍说明:演绎作品应当以某种“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以此分析为基础,法院进一步指出,第106条第(2)款中的演绎作品应以某种“有形而永久的形式”(concrete and permanent form )包含原作,否则不构成对原作者演绎权的侵犯。
对于Game Genie是否创作了一部演绎作品的问题,法院认为,只是简单地对比原视觉显示和新视觉显示是不充分的,更为重要的是要看该新视觉显示是怎么产生的。法院注意到,尽管二者的视觉效果非常相像,但Game Genie并未改变原游戏的数据,它只有和原游戏相结合才能产生这样的新视觉显示。如果玩家停止使用这一装置,则新视觉显示马上消失。因此,Game Genie只是加强了原游戏的视觉效果,它不能独立产生这些新效果,不影响消费者对原游戏的需求。一旦脱离原游戏,它将什么都不是,成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用处的装置。通过对1976年版权法条文的考察以及对涉案游戏视听效果的分析,法院最后认为,作品包含视听作品,但是视听作品也必须依赖于某种有形形式存在。Game Genie所产生的新视觉效果只是暂时的,既没有形成独立的作品,也没有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视觉显示,所以不是演绎作品,被告不构成侵权。
三、演绎作品固定性的统一
(一)双重标准的否定
首先,关于演绎作品固定性的立法解释,不符合版权法的立法意图。
针对美国1976年版权法中关于演绎作品的用词,不少学者就认为,议会之所以没有在演绎作品上谈及固定,主要是《版权法》想把公共表演纳入到演绎作品范畴,并非故意的不要求演绎作品的固定。没有固定性,那么我们只是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演绎作品的创作,也将构成对原作者演绎权的侵犯。这样的一种非常荒谬的结果,尽管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发生(因为除非你主动公开它,否则你不会被起诉),但即使是这样一种理论上被起诉的可能性,也将使得演绎权的正当性被怀疑[5]。因此,认为版权法在保护演绎作品时,要求它要有固定性;而在认定侵权时,则不要求它有固定性的观点,可能导致演绎权的过度扩张,抑制演绎作品的创作,有违版权法的公益保护目的。 另外,按照这一双重标准,一些演绎作品的创作,如芭蕾、舞剧等公开表演,即使无有形形式固定,也可能构成侵犯原作者的演绎权。显然,这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诉讼成本,带来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和版权法的保护私权目的相悖。
其次,关于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司法解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在Galoob案中,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的演绎权,这取决于一个由Game Genie所引起的新游戏视听显示是否构成演绎作品。与原游戏的视听显示相比,新视听效果作了三处重要改变,明显具有原创性。因此,这一新视听显示是否是演绎作品,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固定性。在此,尽管法院也接受“为认定侵权目的,演绎作品不须固定”的观点,但是根据对版权法中相关条文的理解,法院还是重点探讨了新视听显示与有形载体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判案依据。按照法院的观点,新视听显示只是Game Genie误导原游戏卡片产生的,真正导致游戏图像变化的,仍然是原游戏卡片,Game Genie并没有创作出独立的、有形的新作品。而且,新的视听效果也只是一种短暂现象,Game Genie并没有真正改变原游戏画面,当游戏终止时,原来的游戏画面仍可完整呈现。因此,新的视听效果虽然具有原创性,但没有“有形且永久”的形式,不是演绎作品。第九巡回法院的这一判决,明显自相矛盾。它反映出法院在演绎作品的认定方面,并不愿意接受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双重标准,它更倾向于认为,无论是作为保护目的还是作为侵权目的,演绎作品都须有固定性。其所提出的演绎作品应具有“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标准,与其说是否定了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倒不如说是进一步解释了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要求,即有形就意味着固定,固定才能永久。所谓的“有形而永久的形式”,不过是“将作品固定于有形载体上”的另一表述,这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二)单一标准的确立
非法演绎作品具有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这使得版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6],产生矛盾且不实用的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双重标准,并给法院的案件审理带来麻烦。为保护演绎作品创作,近年来法院逐渐发展出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单一标准,不仅肯定合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也肯定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
例如,在 Micro Star案[7]中,第九法院就重新审视了演绎作品的固定性要求。原告Formgen拥有一款流行电子游戏“Duke Nukem 3D”(D/N-3D)的版权。在该游戏中,玩家将以游戏中的身份去寻找秘密通道,摧毁邪恶力量,逃离各种危险,逐一过关斩将直至获得最后胜利。游戏主要包含三个部分:游戏引擎(game engine),作为游戏控制中心;源图库(the source art library ),包括很多可以显示在屏幕上的图像;MAP 文件(the MAP files),一系列的通过游戏引擎告诉电脑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指令。其中,游戏引擎是整款游戏软件的核心。它告诉电脑什么时候去读取数据、保存和引导游戏,播放声音以及在屏幕上显示图像。当需要创作出某一特别关卡(levels)的视听画面的时候,游戏引擎就会引发符合那一关卡的MAP文件,产生相应的画面效果。随着D/N-3D游戏的日益流行,大量的有关该游戏新关卡的MAP文件被放到网上。被告Micro Star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于是将网上各类新关卡进行了搜集整理,选择了300个他认为最好最新的关卡,刻录成一张名为“Nuke It”(N/I)的光盘出售。Formgen向法院起诉,认为当D/N-3D和N/I 光盘相连时,产生的新视觉显示是原告作品的演绎作品,被告制造和销售N/I的行为侵犯原告演绎权。被告认为,N/I 不是演绎作品。因为正如Galoob案中的Game Genie一样,N/I必须和原告游戏相连才能运转,且主要是依靠源图库来修改屏幕上的画面显示,N/I只是Game Genie的另一更高级的版本,它没有复制任何D/N-3D的受版权保护的表达,由D/N-3D和N/I共同产生的视觉效果也不以任何“有形且永久的形式”包含原游戏画面。
法官Kozinski认为,根据Galoob案,演绎作品应当以“有形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本案很像Galoob案,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首先,一个明显的区别,Galoob案中改变屏幕显示的指令来源于玩家,而本案中新的改变了的视听显示,确切地说是创作这一改变显示的指令,是以MAP文件形式被永远固定在光盘(CD-Rom)上的。通过Game Genie所产生的屏幕显示从未以任何形式记录,但由N/I与D/N-3D所产生的屏幕显示却被包含在MAP文件中。在Galoob案中,屏幕上将产生什么样的视觉显示,这由原游戏卡片设定,不由Game Genie本身决定,没有人可以说是Game Genie的数据描述了这一视觉显示。可是在本案中,当N/I关卡开始运行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声音和画面确实是由N/I的MAP文件来描述的,N/I对屏幕显示的每一细节负责。换言之,Game Genie只是根据原游戏卡片对屏幕显示作出具体改变,它不决定最后的屏幕显示。但N/I事实上决定着最终桌面上会显示什么,它只在图像来源方面依靠原来的游戏。这就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这样一个确定且详细的对视觉显示的描述是否可以满足Galoob案所要求的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我们认为这没什么不可以。举例来说,想象一个粉色过滤器,当你把它放在电视机前,它将使屏幕上的画面呈粉色。如果一个人通过拍摄的方式,将这一粉色过滤器所显示的画面全部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会产生演绎作品。但是人们通过粉色过滤器去看电视上的屏幕显示,这并不构成演绎作品,因为它不存在有形和永久的形式。Game Genie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粉色过滤器,它可以改变玩家能感知到的游戏效果,但这些新的改变效果没有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存在。其次,二者还有另一区别,那就是,Game Genie允许玩家修改在任天堂游戏系统中的任何游戏,但由Micro Star 复制和发布的MAP文件只能和D/N-3D一起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另一游戏可以使用N/I中的MAP文件来讲述一个关于胆小的小伙子穿越迷宫,杀死邪恶敌人的故事,那么该MAP文件将不包含受保护的D/N-3D,因为他讲的不是D/N-3D的故事。” 通过对比二案的不同,法院最后认为,由N/I的MAP文件与D/N-3D共同产生的新的视觉显示被以有形且永久的形式(MAP文件自身)记录,且N/I使用了D/N-3D的故事,这是原告享有版权的。因此, N/I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是演绎作品,被告构成侵权。
在1998年Micro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由被告的NI和原告的D/N-3D所共同产生的视觉画面是否是演绎作品。与Galoob案中Game Genie只能和原游戏卡片相连才能产生新的视觉显示一样,本案中NI的MAP文件也只能和D/N-3D一起使用,且所产生的视觉画面也只是暂时性的,只要玩家停止使用NI,新的视觉显示马上消失。但是,这样的一些相似,并没有使法院马上得出NI不是演绎作品的结论。法院注意到,虽然由NI和D/N-3D所带来的新的视觉画面是暂时的或无形的,但最终决定这一新视觉画面产生的MAP文件却被存储于光盘之上,具有“有形而永久的形式”。通过分析产生新视觉画面的MAP文件具有“有形而永久”形式,法院最后认为NI是演绎作品。第九巡回法院在Micro案中的这一推论,看似延续了Galoob案的“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标准,但实质上却是对这一标准的重大突破。按照Galoob案,新的视觉画面应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才是演绎作品。而在Micro案中,法院则将此扩大解释为,如果新视觉画面本身不具有物理形式,但决定它产生的MAP文件具有“有形而永久”的形式,那么这一新视觉画面也仍然是演绎作品。因此,根据Micro案,在认定他人演绎权是否受到侵犯时,确实需要演绎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但是这种固定性要求并不一定非要新作本身以“有形和永久”形式包含原作不可,事实上,新作只要以“有形而永久的” 形式涉及原作就可以了[5]。法院在Micro案中的这一扩大的解释,使由Galoob案发展而来的对演绎作品的物理要求不再限于演绎作品本身,它降低了演绎作品在认定侵权时的“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标准要求。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几乎是取消了这一标准。按照该解释,即使是Game Genie,如果它能最终决定视觉画面的改变,则由于Game Genie是以计算机软件的有形形式存在,新的视觉画面也具有“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是演绎作品,被告构成侵权。
从Micro Star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从立法来看,演绎作品是否要有固定性仍不明朗,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非法演绎作品的固定性。通过要求非法演绎作品要以“有形而永久的形式”包含原作,Micro Star案变相确立了演绎作品固定性的单一标准,使固定性成为了所有演绎作品,无论是合法演绎作品,还是非法演绎作品的共同要求。当然,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有形而永久的形式”这一标准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很多作品如软件改编,除非它们被终端用户使用,否则并不包含原作材料。因此,考虑到新兴作品的不断出现,未来的“有形而永久的形式”标准将趋于形式化,法院对演绎作品固定性的要求也将不断变化。
[1]Stephen M McJohn.Copyright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M].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6:67.
[2]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0.
[3]Tyler T Ochoa.Copyright.Derivative Works and Fixation:Is Galoob a Mirage, or does the Form(gen) of the Alleged Derivative Work Matter?[J].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L.J,2004(20):978-997.
[4]Carol S Curme.Derivative Works of Video Game Displays:Lewis Galoob Toys,Inc.v.Nintendo of Am.,Inc.,964 F.2d 965 (9th Cir. 1992)[J].U.Cin.L.Rev,1993(61):935-999.
[5]Patrick W Ogilvy.Frozen in Time?New Technologies,Fixation,and the Derivative Work Right[J].Vand.J.Ent. & Tech.L,2006(3):665-692.
[6]孙玉芸.论非法演绎作品的法律保护[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5):79-83.
[7]Emilio B Nicolas.Why the Ninth Circuit Added Too Much to Subtract Add-on Software from the Scope of Derivative Works Under 17 U.S.C.§ 106(2):A Textual Argument[J].Syracuse Sci.& Tech.L.Rep,2004(4):1926-2004.
(责任编辑 江海波)
On the Fixation of Derivative Work
SUN Yu-yun
(SchoolofLaw,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330031,Jiangxi,China)
Unlike other works, copyright acts of many countries treat derivative work with double standards: derivative work is only to be fixed when seeking for legal protection while it's denied fixation for the aim to hold infringement. Influenced by the double standards in copyright acts, the judicial trial also treats it with double standards.The double standards of derivative work's fixation don't conform with the aim of copyright acts, and also handicap the equal justice and efficienc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copyright acts should adjust the attitude about derivative work's fixation, acknowledge the fixation of illegal derivative work.
derivative work; fixation; derivative right
2014-12-26
孙玉芸(1979-),女,江西省樟树市人,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
D923.4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