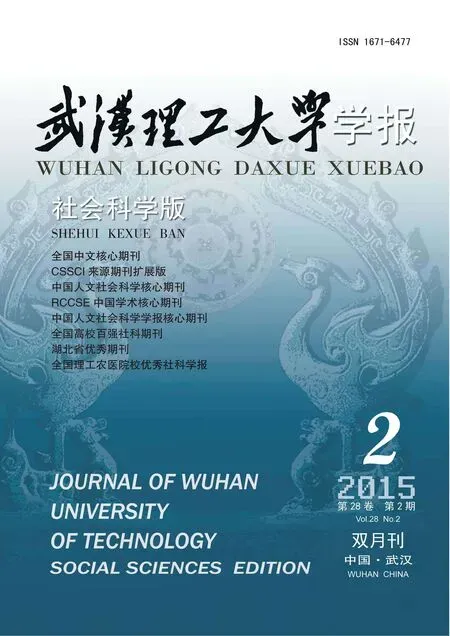从生态美学的“参与审美”看梭罗自然观对爱默生自然观的超越
——以《瓦尔登湖》与《论自然》为文本依据
2015-03-18何山石
何山石
(1.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从生态美学的“参与审美”看梭罗自然观对爱默生自然观的超越
——以《瓦尔登湖》与《论自然》为文本依据
何山石1,2
(1.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梭罗与爱默生均以“自然书写”为世人所熟知,但在长期共同的超验主义理论话语规制下,两者“自然”观的差异混泯不清,因而在生态美学研究日盛的当下,关于两者“自然书写”的生态价值的品量也显得模糊不清。其实,以生态美学的 “参与审美”为切入视角,可以看到梭罗的“自然书写”超越于爱默生之处,梭罗的自然观与爱默生自然观念的巨大差异也彰显无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超越与差异,对当下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启示。
生态美学;参与审美;梭罗;爱默生;自然观念
学界对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与爱默生的研究,如果说前期主要以研究两者的超验主义思想内涵、两人与宗教的关系、各自具体作品风格为主的话,那么,在20世纪后期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类生态危机日益深重的“末世”氛围中,爱默生与梭罗的“自然书写”中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伦理思想便跃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生态美学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学话语中兴起后的今天,以生态美学来审照梭罗与爱默生的精神产品,当会另有新意,更为重要者,这种审照将对当今的“时代病”会有诸多启示。
一、参与自然之“理念”:“零距离”参与与“有距离” 参与
梭罗最为世人所称道之处,就是他对自然的零距离参与方式。在《瓦尔登湖》之“致本书的读者”中,梭罗表明了自己的这种参与姿态:“当我写下本文之后的那些章节,或换句话说,堆砌起为数众多的单词时,我正独居于一处小木屋里。小木屋就在这片森林中,距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之遥,它是我亲手所建,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的湖畔。我全凭着自己的双手劳作来自谋生路,我在此处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1]1梭罗为什么要选择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居住在瓦尔登湖,这之中是有深意的:其一,梭罗是真正离开了那个喧哗嘈杂、伤痕累累的现实“病态”场围,而进入宁静安详、活力四溢的“生态”场围,这既是一种真正的“离弃”,也是一种真正的“参与”。其二,只有在瓦尔登湖这一“生态”场围中,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才能生成。当然,梭罗当时的审美追求不可能是有明确生态美学旨趣的,但他一定能意识到在瓦尔登湖能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健康,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审美愉悦,所以,我们在《瓦尔登湖》里也随时能感受到这份愉悦。其三,只有这种零距离接触,“参与”才会成为一个真实的行为,这样一种去“伪”的举动,是对当时“伪”亲近自然行为的一种嘲讽。
在《瓦尔登湖》这一文本里,密密匝匝都是梭罗“参与”自然的描写:朝阳东升或夕阳西落,镇外的风声,野生动物跃过篱笆,为越橘树和樱桃树洒水浇灌,鹰击长空,红松鼠在自己的脚边跳舞,鱼在湖底流动,春天来临时树木变绿的节奏,湖水怎样结冰、怎样解冻……梭罗仔细地观察着自然中的一切事物,在他眼里,自然的一草一木皆有生命,都是活生生的个体,都可与之对话,亲近相处。
梭罗亦为自己能融入自然而欣喜若狂:“这是一个令人痴迷的黄昏,孤身化为一种感觉,个个毛孔都满溢着愉悦。我在大自然里以飘逸的姿态逍遥来去,已与她化为一体。”[1]83他用逍遥形容自己的感受,这是物我两忘的境界。“我有我的太阳、星星和月亮,这个小世界全属于我。”“人类中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人仿佛就是我。”[1]83这份审美的愉悦,这份独得之乐,如不“参与”自然,便全然无法体会。
梭罗亲近自然的行为,正是“参与美学”所竭力张扬的。生态美学研究者阿诺德·柏林特在《环境美学》一书中对“参与审美”有非常细节化的描述:“所有这些情形给人的审美感受并非无利害的静观,而是身体的全部参与,感官融入到自然界之中并获得一种不平凡的整体体验。敏锐的感官意识的参与,并且随着同化的知识的理解而加强,这些情形就会成为黑暗世界里的曙光,成为被习惯和漠然变得迟钝的生命里的亮点。”[2]曾繁仁教授对阿诺德·柏林特的“参与美学”有切中的评论:“‘参与美学’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无利害静观美学的一种突破,将长期被忽视的自然与环境的审美纳入美学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审美对象上突破了艺术惟一或艺术显现的框框,而且在审美方式上也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3]梭罗这种零距离地融身大自然,正是“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凭借“敏锐的感官意识的参与”,不仅能“获得一种不平凡的整体体验”,而且意义更重大的是,“这些情形就会成为黑暗世界里的曙光,成为被习惯和漠然变得迟钝的生命里的亮点。”正是梭罗的行为,为我们当下的“黑暗”送来温暖的“曙光”,也为我们漠然、迟钝的生命带来一丝令人感动的亮色。
这就是梭罗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他以独特的“参与”方式实现了对自然的独特理解:我们与自然的“和解”,首要的是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漠然”和“迟钝”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工业社会带给人类贻害无穷的观念,即人与自然两极对立,自然是人天经地义的奴隶。人与自然那种诗意的关系被人类的冷漠切断了,人不再是审美地看待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而是功利化地看待外界的一切。梭罗的自然观念,即是审美化的、诗意的“自然”观念——与自然和谐共处,融为一体,恰如中国传统哲学所张扬的“天人合一”观念。
而爱默生“参与”自然的理念,与梭罗大异其趣,爱默生是以与自然有无穷距离的姿态、以局外人的身份对自然冷眼而视,这在他的《论自然》等文本里无数次表露出来。“我们应当彻底相信造化的完美,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那些天设地造的安排激发起我们的何种好奇,事物本身一定会让我们得到满足。”[4]6“造化”即自然,自然就是一种既定的预设,一种人无法改变的秩序,人应该彻底臣服于自然的完美,这无形中颠覆了生态美学所张扬的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将以前的“人类中心主义”置换成“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将自然推至彼岸世界,此岸的人类能如梭罗一样触摸彼岸世界吗?爱默生承认自然的完美,但这是一种远在天边的完美,对这种完美的审美,人不能“参与”,只能彻底且坚定不移地臣服,完全不能取得梭罗与自然肌肤相亲时所获得的那种美感。在《论自然》的第一章《自然》里,爱默生将星星等自然之物视为美的使者,但这些使者有着一个重要使命:“然而,这些美的使者每个晚上都会出现,用它们那带有训诫意味的微笑照亮整个大地。”[4]8所谓“训诫”,同样是一个距离感极强的词,将人与自然的对立感不遗余力地传达出来。
这种与人有无穷距离的自然形象,究其实质是“先知”式的。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里,是存在着多种“先知”形象的,超验主义主张的“超灵”、“超验”,也都是先知式的符号。人类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的能力,也带有浓厚的先知意味。所谓“超验”,似乎更多包含“先验”、“先知”、“先天”的成分。同样,爱默生对自然的设定,也时时将其置于“超验”的先知地位,因而,爱默生的自然观念,不可能如梭罗一样是真正的“参与”,而只是隔岸眺望。
而更为重要的是,爱默生对自然的设定,并非一以贯之便是“自然中心主义”、“自然即先知”,他在不同的场合,要么以人为中心审视自然,要么以自然为中心审视人,对自然何时为中心,何时为配角,完全是一种随意的认定行为,而不是如梭罗那样,视自然为平等对象,贴身参与,并且一直持守这种观念。这种对自然认定的任意性与摇摆性,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文化中一直流行不绝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爱默生正是“功利地”、“实用地”看待自然,而非审美地看待自然,这种参与自然的理念,与梭罗的参与理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细绎出这种差别,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参与”自然的观念。虽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虽然环境保护主义者不断大声疾呼,人类对环境的恶化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在实际“参与”自然时,特别是在自然环境稍有好转之后,人类参与自然的理念立即折转为爱默生式的“有距离的”参与,对环境的破坏行为再度开始。正是因为人类的参与观念没有形成“审美参与”的传统,人类的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审美参与”观念没有内化为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在这里挖掘梭罗文本中的“零距离”式参与就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参与自然之尺度:“约取”自然与“虐取”自然
梭罗主张简朴生活,约取自然,这是梭罗在生态美学意义上的又一重意蕴。
在《瓦尔登湖》最前面的部分,梭罗提到了“生活必需品”:
说到所谓的“生活必需品”,照我看来,是指所有人花费了精力才获取的物品,它或者从最初就是必不可少的,或者经过长久的使用,成了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物品;即便是有人想对它舍之不用,这种人也寥寥无几,他们或出于野蛮,或因为贫穷,或是缘于哲学的意谓,才会将它拒之门外的。
对上帝林林总总的造物来说,具有同样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即是食物。荒野中的野牛,它的食物就是几英寸长、美味可口的青草,还有一些可饮用的生水,除此之外它还需要寻求森林的蔽护或者山野的绿荫。野兽的生存莫过于对食物和隐蔽的需求了。但对人类而言,在目前的天时之中,生活必需品可以确切地分为食品、房舍、服装和燃料,缺少了这些,我们将无法自如地应对人生难题,更别提将来事业有成了。[1]7
接下来,梭罗列出了他的“生活必需品”:一把刀、一把斧子、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已经足够了;对于勤奋好学的人来说,灯光、文具、加上几本书,这已经是第二位的必需品了。梭罗使用“生活必需品”这个语汇,贴切地表明了他的主张:最低限度地索取自然!这种索取是自然能够承受和消化得了的,是自然的再生机制能对这种索取进行补偿的,自然通过自我补偿能维持这种索取与生成的平衡。梭罗希望人们都能安贫乐道,对追求奢侈的行为进行严厉批判:“奢侈的富人不单是追求惬意的温暖,而且还追求自然的温暖,我在前文已提过了,他们是经过烹煮的人,当然是一种很时尚的烹煮。”这种烹煮了的人追求奢侈,“对人类的发展实在是个障碍”。[1]9在20世纪,人类因为“烹煮”自然,为人类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制造了多少障碍!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座障碍的丛林之中,人类已经举步维艰了,修复一处障碍需要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
在《瓦尔登湖》中,还有另外很多有关“简朴”生活的记载。“简朴生活家具”一节中,梭罗用数字告诉读者他的简朴需求:“1张床、1张餐桌、1张书桌、3把坐椅、1面直径3英寸的镜子、1把火钳和壁炉的柴架、1把水壶、1只长柄平底锅、1只煎锅、1只长柄勺、1个洗脸盘、2副刀叉、3只盘子、1只杯子、1把汤匙、1只油壶、1只糖浆罐,还有1只涂了日本油漆的灯。”[1]39在散文创作中如此密集地使用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行为,稍不妥帖便韵味尽失。但梭罗并没有带给读者生硬滞涩之感,相反,读者从这些数字里感受到“简朴”之真美。在“简朴生活收支明细账单”中,梭罗所列举的账单更全面、更细化,而得出的开支结果也更有意思:梭罗两年多的生活费用是25.215美元。如果再加上“简朴生活食谱”这一内容,梭罗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在践行着简朴生活的主张。梭罗想要告诸世人:去掉奢华,返回简朴,人能过上如此具有幸福感的生活!生态美学所倡导的理念,在梭罗的简朴生活里,也表现得如此彻底。梭罗约取自然,上升到生态审美层面,其实质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交往、对话中,人对自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诸多论者都会以梭罗手持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反诘梭罗:如果梭罗是一个真正的生态主义者,他手持斧头的砍伐行为,不也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吗?其实,这是对生态伦理的误解。罗尔斯顿说:“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环境是工具性的和辅助性的,尽管它同时也是根本的必要的。只有当人们不只是提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而是提出对它的恰当的尊重和义务问题时,人们才会接近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型环境伦理学。”[1]175保护环境,并非对环境丝毫不取,而是获取时的适度与过度之别。中国的环境伦理学者也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道德要求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人类向自然界的生物资源进行索取,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取利除害。但是,这一种取利除害的行为必须适度,不能以一己的、少数人的私利的满足来损害人类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取利除害的行为不能危及生态平衡。”[1]57梭罗持斧入林的砍伐行为,只是一种适度的获取,并不会破坏生态平衡,更谈不上损害人类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最值得提及的是,梭罗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主张是以前的研究者较少论及的,那就是梭罗要求人们从自然获取时心怀敬畏:“我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敬畏,就像古罗马人在一个圣林里间疏林木、以使其透光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敬畏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神灵的。”[1]160心存敬畏,使梭罗对自然的适度索取,更具有了生态美学的内涵。
梭罗对动物权利的尊重,也是他平等参与自然的重要表征。梭罗极力反对人类对动物的残暴行为:“我们掠夺它们的羽毛,去精心营造住所中的住所。”[1]46“百灵鸟的寓所已被伐倒,你还能指望她那婉转的歌喉唱出曲调?”[1]122一幕幕残暴的掠夺景象,不知已重演了多少次!人类总是以不同形式的暴力实施对动物的血腥掠取。梭罗的“人与动物关系的主张”是:“到了傍晚,森林远方的地平线上,有几声醇厚牛鸣传来,听起来如此甜蜜、旋律优美。”[1]79“有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和蜘蛛一起住在屋梁上。”[1]156梭罗构织着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动图景,但在今日,这种图景似乎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爱默生不仅没有提及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而且在《论自然》等文本里,大肆张扬人优越于自然,张扬人对自然无责任和无度攫取的合法性。安·罗纳德认为:“爱默生关于荒野的观点不是绝对的,它更倾向于培养人的智力。他对自然的态度更多地是观望和深思,而并非是直接参与。因为,爱默生世界的真正中心依然是人。”[5]这一论断一方面补充说明了上节所述及的爱默生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即说明了爱默生将人置于首位。爱默生希望人类带着自己的优越感,实现对自然的“参与”:“自然界的每个部分都在不停顿地相互协作,以便为人类提供福利。”[4]12“世界因此是为了人的灵魂而存在的。”[4]20“大自然完全是中介物,它天生是为人服务的。它接受人的主宰,驯服得像一头任由救世主跨骑的毛驴。它向人提供它所有的财富,以便他把这些原料改造成有益的东西。”[4]31在人参与自然的尺度上,爱默生完全放弃了观念上的“自然中心主义”,而代之以带有强烈霸权气息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与梭罗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有着天壤之别。
生态美学将生态伦理吸纳到了自己的理论生命中。生态伦理最为强调的一点就是人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人适度向自然索取,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自然对人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人在索取自然的同时,维持生态平衡,不破坏自然的自我补偿机制,这是人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人与自然这两极,在农耕社会,因为人的索取量相对要小得多,所以,这两极牢牢地处于平衡状态。而在工业社会,由于人类力量的相对强大,对自然的索取开始变得过度,人这一极的责任和义务意识被完全抛弃。爱默生的《论自然》这样的精神产品,正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放弃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由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的长期笼罩而被忽略,所以,爱默生的这一面也被人忽略了。
而梭罗是工业化早期少有的清醒者,他看到了人类物欲的极度膨胀会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看到了人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缺失后人类的危险处境,所以,他不仅以在当时看来十分另类的姿态在瓦尔登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而且在《瓦尔登湖》这一文本里多次提及人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只可惜,这个善意的提醒,只有在人类生态危机严重、生态思潮涌起的时候,才被人重拾。
三、参与自然之深度:工业化批判与工业化崇拜
生态美学对现实的批判,有两个维度是最切中时弊的,其一是上面提及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其二则是工业化批判。
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过度性掠取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已多有文字述及,如王诺引英国生态学者贝特的《大地之歌》:“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热量的散发,导致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正在改变,暴风更加凶猛。海洋被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那些物质影响了性激素的正常机能,正在使雄性的鱼和鸟变性。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的农业经济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的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传播给人类。”[6]这里所描绘的图景,我们正在经历,环境的恶化,正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些全球环境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使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问题群。”[7]环境问题已经引发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对人类行为的反思,美学研究也深入其中,以自己的学科背景为依托,吸纳生态学、系统论、环境伦理、存在主义、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生态美育等子类资源,来形成较为特异的研究面貌。这既是美学研究者拓宽本学科研究口径的需要,更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守望共同家园的努力。
梭罗是在工业化早期便关注工业化危害的智者。梭罗对工业化大潮戕害自然生态是有深刻体验的:“现在,湖底的大树,苍老的独木舟,四围墨绿的林子,都消逝了。村夫们连湖在何方都弄不明白,他们没有到湖中游泳或饮水,却想用一根铁管来把湖水引到村中去洗杯盘碗碟!这恒河一样的圣水,他们却想转动一个枢纽,拔起一个塞子就使用瓦尔登的清水!还有那魔王般喷汽吐雾的钢铁之马,那尖厉刺耳的汽笛声嚷得整个地区都听得见,它那肮脏的铁蹄让泡泡泉变得混浊不堪,正是它吞噬了瓦尔登湖边的林木。”[1]122诗意生活的场园消失了——湖底的大树,苍老的独木舟,四围墨绿的林子,都消逝了;诗意生活的方式消失了——村夫们没有到湖中游泳或饮水;技术理性开始支配人类——一根铁管、一个枢纽、一个塞子;破坏环境的恶魔出现——钢铁之马,梭罗用诗意的语言描述工业化对自然的伤害。并且大声质问:“谈什么天堂,你正在践踏大地。”[1]127同时,梭罗对工业化的滔滔巨浪会带给人类怎样的伤害作出了预言:“但尽管人们川流不息地朝火车站蜂拥而来,售票员大声喊着‘请旅客上车’,烟尘渐渐在空气中散去,喷出的蒸气也凝成水滴,这时会看到少数几个人登上了火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辗死在铁轨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惨不忍睹的事故’。”[1]33“人作的恶,死后还在流传。”[1]40梭罗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若是在梭罗的时代里,人们都能如梭罗那样为自然所承受的灾难而疾声呐喊,人类现在的处境可能会美妙得多。
而爱默生崇拜技术,对工业化带给人类环境的戕害漠视无睹。“有用的艺术是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利用同样的自然恩惠再造或重新组合而成的。人不再乞求风向来帮助他的航行。相反,他依赖蒸汽的作用,实现了希腊神话里风神口袋的功能,在他轮船的锅炉里携带了二三十场大风。为了减少摩擦,他用铁轨铺路,在上面安置能容纳满满一船人、牲畜及货物的车厢。就这样,他驾驶火车急速穿越田野,从一座城镇到另一座城镇,就像一只苍鹰或燕子掠过天空。若把人类的这些发明累计起来看,世界的面目从诺亚方舟到拿破仑时代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4]13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技术崇拜,在爱默生的其他文本里,随时都能看到这崇拜。
爱默生对技术的崇拜,对工业化生活的期待,正是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主流期待。人类狂妄地以为自己可以凭着技术进步无所顾忌地征服自然,在工业化进程中巧取豪夺,对自然最起码的敬畏都抛弃了。爱默生在《论自然》的最后部分狂热地预言:“人类战胜自然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凭空到来——目前还远远超出人类有关上帝的梦想。然而人终将迈入那个时代——到那时,他的惊喜之情就如同一个盲人逐步恢复视力,终于重见天地之光明。”[4]59绝大多数人都曾如爱默生一样,以惊喜之情来迎接一个工业化繁荣时代的到来,但事与愿违,工业化之后,恶梦不断,人类将自己推入深重的灾难中。
其实,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本身并不能成为被挞伐的对象。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过度索取自然,完全放弃了对自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完全无视子孙后代的发展也要依赖自然环境,因而不再诗意地审视自然。人类人为地切断了自己与自然的诗意的、审美关联的同时,也放弃了诗意地、审美地栖居于自然中的权利。
因而,在当下重新阅读梭罗与爱默生的意义,体悟梭罗在生态美学维度上对爱默生的超越,正是要借助对经典文本的阅读而反思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疯狂行为,重建审美地参与自然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重塑人栖居于自然中的幸福感,这才是当下之需。
[1]梭罗.瓦尔登湖[M].宗白华,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2]阿诺德·柏林特.环境美学[M].张 敏,周 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54.
[3]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4.
[4]爱默生.爱默生集[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5]程 虹.寻归荒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3.
[6]王 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7]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57.
(责任编辑 文 格)
Thoreau's Nature Idea Transcending over Emerson's from the Angle of “Participation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Taking “Walden” and “Nature” as the Text Bases
HE Shan-sh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ubeiUniversity,Wuhan430062,Hubei,China)
Thoreau and Emerson are well-known for “nature writing”.But within the long-term common transcendental theoretical discourse constraints,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on the “natural”concept are not clear.Thus at present when the study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ecological value of both “nature writing” is also blurry.Actu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participation aesthetics”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Thoreau's “nature writing” transcends over Emerson's with the great differences shown between their ideas of nature.More importantly,this kind of transcendence and difference has a profound inspiration in solv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confronted by mankind today.
ecological aesthetics;participation aesthetics;Thoreau;Emerson;idea of nature
2014-08-10
何山石(1976-),男,湖南省平江县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美学及钱锺书研究。
B83-0;B834.3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