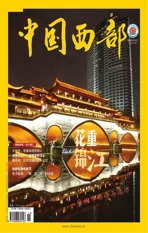老人与鹤
——专访著名鹤类摄影家吴绍同
2015-03-18
文/本刊记者 胡 静
老人与鹤
——专访著名鹤类摄影家吴绍同
文/本刊记者 胡 静

摄影/郑怡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充满悲剧色彩,生动地刻画了一位不屈不挠、坚定顽强地在海上搏斗以保卫战利品的老人的形象。同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吴绍同老先生与鹤共同谱写的却是一个拥有中国式圆满结局的故事,虽然其中也有遗憾。退休以后跑遍全球摄鹤17年的吴老,是当今世界三位拍齐野生鹤类的摄影家之一,与海明威笔下的老人相同的是——不服老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力。

①②③摄影/白显林
金秋时节,著名鹤类摄影家吴绍同现身成都,机缘巧合,吴老在好友公司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我17年跑了15个国家摄鹤,台湾也有鹤,不过在动物园里。要摄鹤的原生态必须到鹤的原生地去,所以我跑的地方比较多。”一落座,吴老就开门见山、侃侃而谈。
“世界上动物这么多,大的、小的,凶猛的、乖巧的都有,您怎么就看上鹤了呢?”
“一个字——缘!”吴老笑着说。
今年已九十一岁高龄的吴老温文尔雅,虽已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几十年间在台湾和大陆的两段画风迥异的拍摄生涯,其间两次捧得台湾最佳纪录片金马奖,退休后又与鹤结缘,从此开始了17年的摄鹤旅程,成为当今世界三位拍齐野生鹤类的摄影家之一,中国鹤类摄影第一人。
跨越海峡两岸的摄影生涯
吴老打开记忆之门,将记者带到上个世纪。1925年,吴绍同出生于广东顺德,两岁时随父母到了上海,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12岁时,吴绍同得到了一部胶壳BABY勃郎尼相机,从此便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以前也是记者。”吴老笑着对记者说,“我1946年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就到《益世报》做了摄影记者。1947年,我从上海到了台湾,从事军中新闻摄影工作。”在13年的军旅生涯中,吴绍同拍摄了很多兵种操典作为新兵训练的教程。退役后,吴绍同任职荣工处摄影组,专业拍摄各种工程纪录片。30年来,硕果累累,于1978年和1983年两次捧得台湾最佳纪录片金马奖,此外,还有30多部程纪录片被台湾各大专院校工程系图书馆收录,作为工程学院辅导教学材料。

作品名称:双双 拍摄时间:1995.12 拍摄地点:贵州草海
几十年来,吴绍同因公去过31个国家,但敬业的他却从没有抽时间去拍拍当地的民俗、风光等等,总是完成工作就匆匆赶回。“我工作的这几十年来,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空白的。”吴老说,“所以,退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关口。退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想,退休以后要做些什么呢?想了很久,终于确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拍摄环中国边境的人文景观,打算以两年为期,骑自行车沿中国边境绕行两圈;第二个目标是拍摄祖国的55个少数民族。”
心中有了目标,就有了期盼。1990年5月1日,吴绍同正式退休。“上午办完退休手续,我下午就已经到上海了。”说起要急切开启自己设想的美好退休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吴老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然而,吴老设定的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第一个目标,当时,我已经兴致勃勃地买了自行车到了漠河,打算从祖国的最北边开始走,但是因为国家对边境管得非常严,环国境线绕行计划没有被批准。”吴老告诉记者,于是,他启动了第二个计划,到55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去拍摄风土人情。但是,在拍摄过程中,吴老发现,有些少数民族风俗保护得不太好,民族特色变淡了,比如,有一次去拍赫哲族的时候,发现赫哲族人居然把最有民族特色的鱼皮服拿去换酒喝,他很失望。于是,第二个拍摄计划也放弃了。
走遍祖国大地与鹤结缘
此时的吴老,从东北到西南,几乎已经走遍了祖国大地。失去目标的他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哪儿了。
就在吴老迷茫、彷徨的时候,他遇到了《哈尔滨日报》摄影部负责人李先生。李先生非常热心,问了吴老的来由和想法,安慰他说,没关系,哈尔滨有很多可以看、可以拍的美景。于是,李先生带着闷闷不乐的吴老去游览了太阳岛等名胜景区。有一天,李先生兴致勃勃地找到吴老说带他去摄鹤。这一去,吴老就对鹤一见倾心,与之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那时,我对鹤感觉很新鲜,一拍就上瘾了。”吴老笑着对记者说,鹤的风采、姿态令他着迷,再加上鹤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以及鹤的美好寓意——清高、清廉、健康、长寿,这些都为鹤加分。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鹤生长在沼泽、浅滩、芦苇塘等湿地,湿地是“地球之肾”,所以,鹤的增减就成为地球生态系统好坏的标志。
于是,吴老将镜头锁定了鹤,最初是偶拍,后来就专程到每一种鹤的故乡去寻鹤、摄鹤。这一拍就是十七年。

作品名称:金蛋 拍摄时间:1993.11 拍摄地点: 黑龙江扎龙

作品名称:全家福(丹顶一家)拍摄时间:2006.7 拍摄地点: 黑龙江扎龙
镜头背后的故事
刚进入东北札龙自然保护区摄鹤,就对札龙这广大平原产生了兴趣。在那里住久了,对日出日落的情形也渐渐熟悉,打好腹稿,心想以《太阳与鹤》为题,拍摄一系列的作品。结果在四年中拍了无数次,耗去了我多少个晨昏,也只能拍到少数一般化的作品,理想的作品难求。直到1993年11月5日的下午,太阳已沉落四分之一,刚有一小鹤步入日影中,左边又有两大鹤陪同。好,想要的有了,按下快门,把它题名为《金蛋》。但在北京,我的九姑母、作家草明女士说:“叫太阳之子更好。”从善如流,改称为《太阳之子》。
2006年,我的右眼视力是0.1,已无法看到什么东西了;左眼视力是0.3,但因为受青光眼的损害,视野仅剩下五分之一,而且中间还有一层雾。当我在拍摄时,用左眼从相机的观景框中望出去真像是在雾里看“鹤”,我仅能看到画面的小部分,就像原来用的广角镜头180度的视野四角清晰,现在变成用1000m/m长焦镜头再加上一个柔光镜。拍摄这张《丹顶一家》的时候,我只能注意到两只大鹤上半部头胸的位置和神态,下面小鹤的动静就要靠友人告诉我,至于对焦则交给相机的自动功能了,在适当时机按下快门。这就是2006年6月3日(在我眼睛病变六个月后),于齐齐哈尔王家营子摄得的这张《丹顶一家》,这是我摄鹤生涯十七年中最后的一张“鹤”影。
沉浸其中,其乐无穷
“作为一位高龄老人去摄鹤,背着很重的摄影器材四处奔波,辛苦吗?”
“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自己喜爱的工作,能够投身其间,感觉乐趣无穷。”
“我花了8年时间,从遇见第一只鹤的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到贵州威宁草海,到云南,到西藏,到四川……把祖国大陆的8种鹤全部拍完。”说起鹤,吴老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扎龙有很大一片芦苇塘,是鹤的大本营,我每年要去好几次,每次在那里待一周到20天。”吴老告诉记者,自己的很多得意之作都是在扎龙拍摄的,其中包括那张著名的《金蛋》和收官之作《丹顶一家》。
“《金蛋》是我在扎龙花了三年时间拍到的。每天黄昏要去守候,等落日,等鹤,等待最佳的时机。”1993年11月5日,这个时机终于来了,夕阳西下,鹤舞翩跹,霞光中,一只小鹤正走入金色的落日中,鹤爸鹤妈在旁边慈爱地注视着它。迅速按动快门,吴老将这绝美的一幕永久定格。
“在贵州的威宁草海拍黑颈鹤、灰鹤,也花了我很多时间。一年有两三个月待在那里,每次去摄鹤都是带点干粮,划着船在湖边晃上一天,把我的长镜头架在船上寻找鹤的踪迹。”
“鹤生蛋很有趣,每次都生两个蛋,如果有人偷走一个或者毁坏掉一个,母鹤就会补生一个。公鹤和母鹤会轮流孵蛋,但公鹤孵蛋时间短,也不太专注,而母鹤很专注,经常卧在蛋上好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说起寻鹤摄鹤以及关于鹤的点点滴滴,吴老兴致盎然,仿佛又回到了那时那地,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然而,高龄野外摄鹤,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西藏阿里的拍摄比较艰苦,到阿里需要渡过雅鲁藏布江,我到的那几天江水比较高,渡船无法靠岸,就在日喀则住了几天,一直等到江水退去才渡过河,然后再由朋友开车送我到阿里,约好三天后来接我。”吴老告诉记者,那里很荒凉,没有旅舍,没有民居,只有一间废弃的养路工人住过的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过路人留下的冰箱等电器的外包装纸箱,压扁了当床铺用。吴老一个人在那里住了三天,拍摄黑颈鹤,但拍得不太成功,地方太空旷,没有驻地可以慢慢等。

作品名称:俪影 拍摄时间:2004 拍摄地点:印度开庆

作品名称:孤拍 拍摄时间:2000.4 拍摄地点:瑞典虹宝湖
“后来我在四川的若尔盖拍到了黑颈鹤,让当地牧民做导游,从花湖骑马过去,穿过一片沼泽地,找到了鹤巢,在离鹤巢200米以外的地方搭了个帐篷,等着小鹤出生,在那儿待了一个月终于拍到了初生的小鹤。可惜的是,这次拍摄的照片在哈尔滨连电脑一起被偷走了。”
吴老告诉记者,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的问题。为了摄鹤,吴老倾尽财力,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在大陆完成8种鹤的拍摄后,为了能去国外继续摄鹤,吴老四处寻求支持。不久,他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台湾电子界的企业家,支持他摄鹤。
得到支持的吴老如鹤般振翅高飞,几年时间里飞遍五大洲,到14个有鹤国家的鹤乡摄鹤,将全球所有15种鹤之美影尽收镜中。
爱到骨髓的摄影
2006年,命运跟吴老开了个玩笑。这一年正值吴老退休后第三个六年计划中期,正在南非拍鹤的吴老,突然感觉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迫不得已,只好飞回台湾治疗眼疾。经医生诊断,吴老的眼疾是视网膜病变,视力骤降为0.1度以下,微弱的视力已经无法承担摄鹤的任务。最终,吴老在哈尔滨拍下收官之作《丹顶一家》,含泪告别心爱的摄鹤工作。
虽然不能再跟拍鹤类,但玩儿了一辈子摄影的吴老并不甘心就此放下手中的相机。经过一番考虑,吴老选择了体型较大、自己也很喜欢的骆驼作为拍摄对象。这一拍又是六七年。“有一次,在内蒙古锡林浩特,零下31度,下的雪都落地结冰了。我追着骆驼跑,但追不上。”吴老回忆起当天的场景,笑着说,于是,只好又换目标。
这一次,吴老选择了恐龙。“我女儿跟我说:‘爸,你这下找对了,恐龙不会动,它等你的。’”说着,乐观的吴老大笑起来。
拍摄了一段时间恐龙之后,受视力和身体状况的影响,吴老终于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心爱的相机。
尽管不能亲自从事摄影工作,吴老仍然没有离开摄影。2008年,吴老和朋友在内蒙古赤峰办起了以摄影专业为主题的图书馆,将自己多年珍藏的摄影书籍捐献出来供大家查阅、研究,促进摄影文化交流。“让世界华文摄影著作、文献有一个温暖的家,使全球华人摄影家的佳作、摄影集聚首一堂。”——吴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这两行文字,这是这位爱了一辈子摄影的摄影文化工作者的心声。
“现在我从事的是保存摄影文化的工作,这是我有生之年一直要做下去的事情。”吴老坚定地说。
保护生态,造福子孙
“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好,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等很多地方都有鹤,但近年来有些环境被破坏了。”吴老告诉记者,比如,贵州威宁草海近20年来变化比较大,原来风光明媚,有水、有沙滩,绵延几十公里,非常漂亮。但后来这片草海被分给了当地的农民,他们在草海上打桩、拉网作为分界线,一眼望去,原来美丽的草海被分隔成一块一块的,已经没有景致可言,鹤类能够栖息的地方也变少了,鹤也少了。
作为当今世界三位拍齐野生鹤类的摄影家之一,吴老的“鹤影专题影展”已经先后在台北、北京、南昌、上海、广州、哈尔滨、齐齐哈尔、赤峰、武汉、昭通,以及美国的旧金山等城市巡回展出。
“遗憾的是还没在成都展出过。”吴老告诉记者,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办一场影展,一来促进摄影文化交流,二来也借此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希望大家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生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有利的环境。”
(责任编辑/凌云 设计/毛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