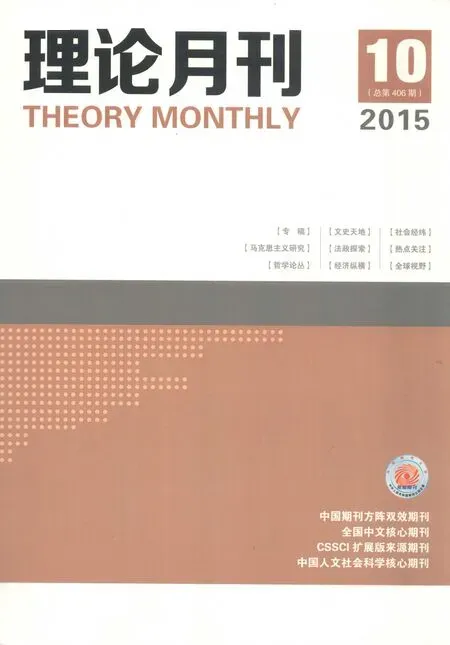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2015-03-17龚柏松广东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龚柏松(广东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龚柏松
(广东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而又最不确定的双边关系。本文在阐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尝试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分析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障碍性因素,即当今“冷战思维”社会事实存在;中美两国不同文化差异;战略互信不足,猜疑有余。最后在建构主义国家关系理论框架内探讨中美两个世界性的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路径。
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主义;认同;互信
在当今全球,中美两国一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第一大经济体,一个是正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一个是对世界领导者角色保持高度热情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之间关系是否健康发展、走向如何,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整个安全格局,而且关联到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走向,牵动着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前途。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际,由于中美两国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大相径庭,历史文化的明显差异,双方在诸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遇到层出不穷的矛盾与问题,而且这些矛盾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并以各种无法预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从局外角度来看,当前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期望和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因此,作为当今世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有巨大影响的中美两国,如何客观理性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岐,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矛盾,尊重彼此间的关切,通过彼此间良性互动实践,换位思考,在重大战略性问题上达到共识,真正走出一条文明的、理性的,兼容性更大的新型的大国合作共赢相处之道,这不仅是两国现实国家利益的基本诉求,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当今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人民对两国关系发展迫切期盼与要求。
1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指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时代主题前提下,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基于对当今世界国家间相互依存客观现实的判断,摒弃传统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理念,政治上平等尊重,文化上包容互鉴,经济上合作共赢。以良性互动为纽带,培育战略信任;以共同利益为契合点,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实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为目标,彻底改变世界历史上国强必霸的传统关系模式。它反映了新的崛起大国和旧的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彼此利益冲突的国家战略新的思维方式。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为了保持中美关系能够在一条健康、理性、稳定轨道上运行,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创造性的提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倡议。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会晤奥巴马总统时,提出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用简洁有力的三句话更进一步地精辟地阐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内涵,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理性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向。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提出加强高层沟通、相互尊重、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包容协作、应对挑战等6个重点方向深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反映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家关系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决非一时冲动,更非是两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存在着坚实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更是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要特点:其一,它不同于以前的中美关系,以前的两国关系是在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展开,很大程度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与从属于超级大国争霸的诉求,而当下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时代的主要特征日益明显,心仪和平,追求发展,向往幸福是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中美两国人民当然也不例外,这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时代前提。其二,它不同于历史上其它大国的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由于自然与科学技术的限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行为体更多把诉诸武力作为维持自身生存之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到来的当下,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交流,经济贸易,人员来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美国日益成为经济命运共同体。有关资料显示,大约70%的美国公司在华赢利,大约42%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平均利润率。这为中美两国确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以合作、包容为核心内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不仅是两国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逻辑发展的需要,也充分反映了两国领导人迫切全面提升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愿望。
2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内容及现代价值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主要流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激发了国际政治理论界学者的思维,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客观环境,也为国际政治理论界新的观点诞生预留了更大空间。冷战的结束又为建构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与时代背景。自从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夫将“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从此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并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兴起,20世纪90年代自成体系并吸引了众多国际政治理论界学者的目光,并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20世纪90后代中后期成长为国际政治理论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理论学派。最具有代表性是1999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言人温特的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它的地位与学理意义随之而来得到普遍的承认与认可,理论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人自己建构的。它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自然事实是不同的,其实质是社会事实,观念、文化、制度、规范等社会事实是由人的长期实践活动建构的。人是建构社会事实的主体,离开人,社会事实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成为无源之水。
第二,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建构在实践中对国家行为体利益与行为的影响,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观念的分配组成的一种文化结构,而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作用中建构的,结构与国家行为体之间是一种互构作用的结构。因此在国际社会系统内,国家安全文化不是一成不变,是随着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实践的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它既可以促成以冲突与战争为主要特征的“霍布斯式文化”,同样也可以促成以和平共处为主要特征的“康德式文化”,这就取决于国际政治结构体系中国家行为体本身如何通过长期实践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行为体完全有可能通过 “良性互动式”的实践路径,消除彼此的敌意,建构一种趋于以和平友好为主要特征合作性的国际政治文化。该理论突出人的主体性建构作用,冲破了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牙还牙”机械的历史循环悲观思想,为当今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族争取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乐观的指向。
第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突出关注规范、文化和认同等社会事实在判定国家利益中的作用。国际规范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约定,包括规则、法律、制度,习俗等。它是通过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国际制度、国际法、世界性的协定等 “共有知识”建构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利益和行为。国家认同是国家行为体对自身在国际政治系统内特定角色的定位和期望,因此认同是国家行为体产生动机和实施行为的主要推动力。国际政治文化是由国家政治系统中不同规范和不同国家认同构成。在国际政治结构中国家行为体通过主体间的长期实践活动促成共有观念,拥有“共有知识”,形成政治文化,文化反过来塑造国家的身份、界定国家利益,影响国家行为,这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主要障碍性因素
第一,当今“冷战思维”的社会事实是影响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因素。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社会事实构成。当下“冷战思维”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事实。它会影响一个国家政策制定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尤其对中国与美国两个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政治行为体表现得更加明显。“冷战思维”,就是在二战胜利后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决策者们根据意识形态为标准处理国际事务特有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或价值理念。突出表现强调自身国家利益极端重要性,突出大国间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性,强调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矛盾不可调和性,主张在全球范围推进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尤其热衷于对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推行“民主扩展”战略,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洪水猛兽,并高调宣扬“社会主义过时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高发展形式。时至今日冷战虽然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但冷战思维阴魂不散,“非友即敌”认识框架仍然存在。这种“冷战思维”社会事实的存在会阻碍中美两国构建以和平共赢为内容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此同时,冷战之后成长起来的西方政要们,他们先辈们积累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思维逻辑常常能对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习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建构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正如美国外交官沃伦·克里斯托弗指出:“只要中国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它就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将永远都是美国的攻击对象。”[1](P48)由此可见“冷战思维”社会事实的存在影响着美国政治界与理论界对中美两国彼此之间国家利益的判断与定位,成为制约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历史习惯性阻力。
第二,中美两国不同文化差异是影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隐性因素。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文化环境在政治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与界定的影响。文化影响认同,文化结构决定了观念结构。霍尔指出“人生没有哪一个方面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改变。”[2]“人们由于在交流中得到信息,从而学会了思考、感受、信仰,而这些信息都打着文化的烙印。”[3](P169)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建构力量,赋予了整个政治架构的意义,它规定了国家行为体行动的主观环境。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独特方式影响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向和内容,引导各种国家行为,影响政治过程的功能。中美作为两个历史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大国,毋庸置疑这对两国政策制定者在对本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对方国家利益的认知上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人坚持认为,美利坚民族具有“上帝的选民”与生俱来的独特身份,怀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情怀,来到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历史未来发展和命运负有不可推辞的责任,即拯救世界于“苦海”。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说,“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移民,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驭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注定人类的希望和伟大的东西来自我们种族,我们感到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东西,其他国家必须步其后尘。”[4](P51)从美国文化历史考察,清教徒的文化在美国政治发展史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不仅促成美利坚民族的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而且深度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历届决策者的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潜移默化作用。小布什曾高调宣称:“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像风中的种子,带给每个民族。在我们的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我们不会独占,而会竭力让大家分享民主,我们将务记于心并且不断传播,225年过去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5]这种文化基因,通过影响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和理论界对其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对其它国家的认知,从而左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超越了意识形态导致的冷战式对抗,但其基本逻辑依然是冲突性的。”[6](P250)可见在历史基础上所延续文化基因是影响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隐性因素。
第三,战略互信不足,猜疑有余是影响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因素。建构主义十分突出认同在国家行为体互动实践中基础性影响。利益是由认同界定的,认同感的高低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之间对彼此的身份认识与角色定位。国际政治体系中如果政治行为体认同感增强,相互利益结构就趋向一致,国家行为体彼此对重大战略问题认识就越接近,互通性的看法就越多,交流互信就更加方便快捷;相反,如果认同感降低,相互利益结构趋向冲突,则对彼此的认识盲点就会增多,交流互信就愈发艰难。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大相径庭。另外由于双方认知与心理因素的影响,这必然导致彼此之间对对方战略意图盲点认识增多,对彼此实力对比与发展水平、两国的发展前景、中美两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认知上存在巨大落差。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国内出现了集体性焦虑和危机感,甚至出现了集体性幻觉。一方面,对中美之间客观的经济实力对比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夸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实际经济规模与竞争能力,甚至以为中国的发展水平已逼近美国;另一方面,以静态的视角看待中美之间的力量变化的趋势,面对经济层面出现新的问题缺少客观的认识,过分渲染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隐藏”自己的科技发展潜力,过高的估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对中美两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认识偏颇。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加加深了美国政治界、思想界对中国崛起后战略意图的误解,更强化了他们所谓的“国强必霸”历史逻辑的自我想象,一相情愿地在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上制造所谓的“潜在对手”和“现实对手”,坚定地认为中美关系一定会沿着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对抗的理论逻辑并遵循“国强必霸”历史模式发展,更有甚者叫嚣中美必有一战。“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两极论”、“中美共治论”各种理论甚嚣尘上,此起彼伏。更加加重了中美两国关系非理性波动,从而损害彼此间的互信,增加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
由此看来,目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等深层次因素导致彼此认同不够、共识太少。另外,中美之间的相互沟通实践远远不能满足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官方沟通多,民间交流少,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薄弱,互信不足促使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上落差巨大,各自为政,自说自话,彼此沟通困难,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向深层次发展,使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呈现出极大的脆弱性特征,也决定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彼此足够的耐心与坚定的意志,更需要在实践中彼此之间建立形式多样交流平台,对阻碍双方关系正常健康发展的深层次因素进行开诚布公、真诚坦率地互动式友好交流实践,力求共识的达成,以减少和消除各种认识误区。
4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主要路径
在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的身份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互动实践中产生的,利益的界定不是先验就存在的。人建构了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在建构人,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作为当今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美两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不仅完全能够而且有必要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自觉地主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共有观念。通过这种共有观念,一方面界定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稳步向前发展。中美双方自建交以来到今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某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而且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政治上在进行广泛性的对话,文化上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更重要的是彼此积累了丰富打交道的经验,培养了两国面临困局时波澜不惊的大国心态,这为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确立良性互动架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两国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提供了稳定因子。其基本路径在于加强良性互动、促进观念重构、培育战略信任、扩大合作共识、构筑长效机制、实现合作共赢。
第一,继续加强经济联系,打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共有观念”形成。随着经济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不断向前拓展,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的关联度也随之加深,这为中美两国培养“共有观念”,破解两国发展关系的难题提供更多的机遇与空间。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互相了解,不断增进互信,双边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和扩大。中美双边贸易额2012年达到4 856亿美元,双方都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而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获取了巨额的利润。通过这种经济实践,中美双方都形成了一个基本“共有观念”:对方的理解与合作对两国不可或缺。因此加强经济往来,保持和发展两国友好经济合作关系,不仅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牢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能为中美两国政治、文化交流,双方战略意图的沟通和政治互信的建立提供更多的机遇。
第二,通过人文交流,培育两国人民之间的“共有知识”,破解政治难题,为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扫除障碍。当前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人文交流在培育国与国人民之间情感,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的作用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可以从人文交流入手去寻找破解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过程中政治难题。应该看到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基本国情不同,对世界重大事务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看法、立场也存在不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两国政治互信方面取得较大突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在美国国度里,国家利益已经深深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需要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打破常规,超越传统思维定式,另起炉灶,通过人文交流的文明形式,培养“合作共赢,互谅体让”和“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共有观念”,从而客观看待与正确处理两国政治上分岐,破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难题。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指出:“美国针对一个国家,从来是一再以对其用心之评估做决策参考,而非以其实力或政策做标准。”[7](P786)可见中美人文交流不仅能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强化政治互信,而且在人文对话过程中“共有观念”的塑造,从而强化彼此间的认同感,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与民意基础。
第三,构建更多的平台,形成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机制和规范,是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机制与规范在国家认同的地位与作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长期性、复杂性因素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客观存在诸多分歧、摩擦、矛盾。但与40多年前相比,当前的国际环境与时代主题都发生巨大改变,要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是世界人民的基本诉求。中美关系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为新时期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很多难得的经验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我们两国通过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和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了各个层面、多种形式的六十多个交流平台;两国签订了多个合作文件和基础关系条约规范;另外还有目前在联合国框架内确立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正发挥着规制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已经存在平台和机制基础上寻找中美关系中更多的切入点,构建更多的平台,确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基本交往行为准则,形成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基本规范,从而保证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稳定健康地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提供保障。
当前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美国是影响我们外部环境的重大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以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审视和处理当下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世界上其他大国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为当今的国际社会贡献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范例,从实践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还在理论上推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走出“历史定律”的怪圈,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引起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人类进步理论一场新的革命,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注入新的活力。
[1][[美]沃伦·克里斯托弗.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2][3]E.T.Hall.The Silent Language.New York:Doubleday,1959.P169.
[4]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5]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7]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友海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30
D822.3(712)
A
1004-0544(2015)10-01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