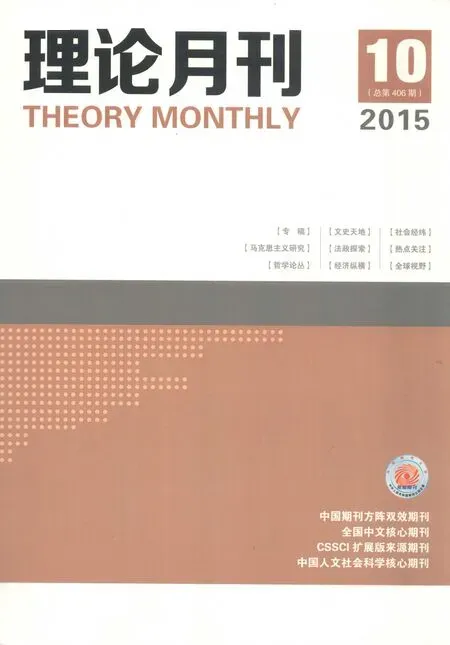性别话语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昭君投江叙事
2015-03-17杨宗红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杨宗红(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性别话语下明清小说戏曲中的昭君投江叙事
□杨宗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昭君和亲是西汉历史上的大事件,然而到了小说戏曲中,昭君却由和亲英雄变成了投江的贞节烈女。“投江”情节的增添,反映了男性话语对贞节的不断加强。在男权视野中,昭君兼有天使与祸水的双重隐喻,这就注定了“投江”的必然。投江叙事,隐藏着男权对女性贞节的规训策略。五四以后,“去投江”叙事经历了从反传统到“情本”,女性本体意识逐渐被强化。
性别;昭君;投江;贞节
昭君和亲,由于史书记载所留下的许多空白,为历代文人吟咏、叙述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昭君怨、帝王恨、画师丑图等在诗文及戏曲小说中被不断渲染,其中又增添了昭君投水之情节。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苏珊·格巴指出,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作为作家在创作中是主体,是基本的一方;而女性作为他的被动的创作物——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常常被加以相互矛盾的含义,却从来没有意义。”[1](P165)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书写,即便不乏对女性的同情,却总会染上深刻的男性意识。昭君和亲故事中被硬加的“投江”情节,更是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意识的外化,是被强化的王权、夫权对女性伦理规范的必然。
1 “投江”情节的定型与男权地位强化之关系
昭君和亲是西汉历史上的大事。《汉书·元帝纪》诏曰“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王昭君至匈奴后,“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前汉书中,昭君对和亲态度不明,后汉书中,昭君则因怨而主动请求和亲。两汉书都揭示了一个重要史实,不论昭君态度如何,她都是汉帝“赐”予匈奴的礼物,是汉匈友好的使者,她留在匈奴、且改嫁,还生有子女。据翦伯赞《王昭君年谱》,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后30年,享年84。所以,昭君投江,是莫须有之事。
文学表述与历史叙述总有差异。昭君至匈奴后的史实被文学改写,始于东汉蔡邕的《琴操》。据《琴操》,昭君到匈奴生一子,因不能接受“父死妻母”的胡俗,乃吞药自杀。其后,晋代石崇、唐代储光曦、王建等人的咏昭君诗,其重心都在昭君之怨。至《王昭君变文》,写单于对昭君甚好,将其立为皇后,然昭君思乡思汉,最终憔悴而亡。上述文学作品对昭君出塞的结局虽然侧重其悲怨,却仍隐含昭君嫁与匈奴王,在匈奴生活的事实。昭君去匈奴后结局的大改写,马致远《汉宫秋》功居至伟。《汉宫秋》写元帝面临强大的匈奴与群臣的无能,只好让昭君和亲。昭君同意和亲,却在行至黑水时,投水自杀。此后,《昭君出塞》、《昭君梦》、《和戎记》、《吊琵琶》、《双凤奇缘》等,一致同构着昭君投江的凄美叙述。《吊琵琶》说王昭君投交河,《和戎记》说昭君投乌江,《双凤奇缘》说昭君投白洋河。小说如此,戏曲也是如此。《风月锦囊·正科入赚》之旧本戏文《王昭君》的剧情梗概中也有投江这一情节,云:“昭君含泪和戎,到边城诒杀毛卿,勒取降书王印。跳入乌江,犬羊不混,[至今]青史留芳,令人堪羡。”[2](P4)“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3](P21)“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考查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4](P334)自宋代开始,“夫为妻纲”被高度推崇,女性的贞节也被理学家提到“天理”的高度。寡妇改嫁被抨击,守节被视为美德,各地方大兴贞节牌坊。到明代,朱元璋发布榜文,鼓励戏剧上演“义夫节妇”。他还下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5](P1254)朝廷通过建牌坊、赐旌门的方式加以宣扬、鼓励殉节的烈女。贞节妇女不仅给家族带来荣耀,还为她们的宗族免除了徭役,解决了经济问题。朱元璋还命儒臣修 《女诫》,作为天下妇女的教科书。明代,女性教科书除《女诫》之外,还有徐皇后的《内训》,章圣皇太后的《女训》,慈圣太后的《女鉴》等。至清代,理学进一步被强化,其间虽然出现鼓吹婚恋自主的论调,但节烈观仍然风靡天下。
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女性贞节观念在明代开始走向登峰造极,于是,“烈女”愈来愈多。据统计,自周代起至清代,节妇烈女的数量总计为 49383人,而明清两代总人数就多达 48152人,占总人数的 97.5%,从人数上看,是历代以来节妇烈女数量最多的时期。《明史·列女传》中记载了265位忠孝、节烈妇女,其中贞妇、贞女占有很大比例。据《古今图书集成》,有明一代节妇烈女多达35829人。[6](P112)
《汉宫秋》的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此时正是理学兴起之时。虽然《汉宫秋》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做理学的传声筒,但仍难免留下理学的痕迹。其他小说和戏曲中的昭君形象,都打上了理学的烙印。虚无的投江“史实”与不断反复言说的 “凿凿可信”的投江情节之间的悖论,显示出男权社会中男性文人不断强化自身地位的努力,以及整个过程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2 投江叙事的天使与祸水隐喻
男性以自身为中心衡量女性,将女性分为两种类型:天使型与祸水型(在更多时候人们更愿意用“妖魔”来表达)。邓尼斯指出,在男性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导致她们“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7](P9)在昭君身上,天使与祸水共存。
昭君是天使。她不仅姿色卓绝,而且还有很多美德:多情、温柔、善解人意,关心民生疾苦,她坚强、勇敢、聪慧、坚贞、果断,勇于自我牺牲。她不贿赂画工以求进;当国家面临危难,她抛却儿女私情前去和亲,以解决两国兵锋。在不令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为贞节保持而投江。《汉宫秋》第三折中,面对匈奴百万雄兵南侵,昭君也赞成和亲。灞桥送别,昭君云:“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诗云:)正是: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8](P314)昭君力图通过和亲免除战争,为丈夫挣得一个安稳的天下。《和戎记》云:“夫妻两分离,奴心欲自尽,与君王相守难抛弃。中原堪叹同胞弟,最苦交锋休怨忆,安定江山封赠你。”[9](P80)又云:“能舍一人之命,保全万载之邦,救万民之难,免吾君之帝褂。与王分忧,妾死无怨。”[9](P104)“第一来难舍父娘恩,第二来难割衾枕,第三来损坏了黎民,第四来百万铁衣郎昼夜辛勤,第五来国家粮草都虚尽。今日昭君输了身,万年羞辱汉元君。宁作南朝黄泉客,不做夷邦掌国人。”[9](P116-117)由此,昭君离开汉宫之不舍,就不仅仅是强烈的故国情怀,还有强烈的夫妻深情。昭君在夫妻情与国家民族大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展示了她的家庭天使形象与民族英雄形象——这正是男权对理想女性的要求。
但昭君也是“祸水”。“红颜祸水”是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甚至是民族的无意识。《新唐书·玄宗本纪赞》:“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欧阳修认为,唐朝从高宗到玄宗,经历了不少女祸,直接影响到唐王朝的国祚。清朝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甚至专列“唐女祸”一条。古代文学中不乏女色害人的故事或议论。徐石麒《浮西施》杂剧借范鑫之口指斥西施“天生尤物,善笑工颦,遇一君则迷一君,在一国则倾一国”。[10]作为“红颜”,昭君不可能脱离人们固有的“祸水”观评价。宋代诗人喜爱反弹琵琶,在为毛延寿辩解时,更不惜将昭君指向红颜祸水,将她与亡周的褒姒、灭吴的西施、引起安史之乱的杨玉环类比。萧澥《昭君词》:“琵琶马上去踌躇,不是丹青偶误渠。会得吴宫西子事,汉家此策未全疏。”陈僴《读明妃引》:“骊山举烬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遣明妃嫁夷狄,画工原是汉功臣。”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云:“伐国曾闻用女戎,忍留妖丽汉宫中?如知褒姒贻周患,须信巫臣为楚忠。青冢不遗芳草恨,白沟那得战尘空?解携尤物柔强虏,延寿当年合议功。”昭君成功使匈奴向汉称臣,有功汉庭。但诗人们却认为,昭君倘若不远嫁匈奴,她在汉宫中的作用,与西施在吴宫中、杨贵妃在唐宫中的作用没有区别——都会魅惑君王,令君王沉溺于美色,最终将令汉王朝落得国破家亡的结果,指控不可谓不严重。尤其是郑清之直接以“妖丽”言昭君,足见其对“红颜”的敌视与恐惧。女色祸国,毛延寿将祸水从汉宫引向匈奴,避免了汉宫重蹈吴宫覆辙,也避免了太真“蜀道蒙尘”的悲剧,当之无愧成为“功臣”。
“传统的文学史是由一个个的‘文学经典’汇成的男性文学的历史,这些经典将男性文本和男性经验作为中心,处处显露出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憎恨。”[11](P 6 9)宋以后的昭君和亲书写,仍然不可避免的受红颜祸水的影响。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都无一例外的写到单于垂涎于昭君的美貌而倚仗强兵索要昭君,否则就发动战争。如此看来,这些作者们都有意无意的将昭君视为引起两国之争的尤物或祸水。在具体叙述中,作者也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阐释女色祸水的观点。《汉宫秋》中,汉元帝初见昭君,说道:“若是越勾践姑苏台上见他,那西施半筹也不纳,更敢早十年败国亡家”。[8](P309-310)汉元帝宠幸昭君后,如痴如醉,久不理朝纲,而且新添了毛病,“一般儿愁花病酒。”[8](P312)当单于索要昭君,尚书在一旁蛊惑汉帝:“他外国说陛下宠昵王嫱,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若不与他,兴兵吊伐。臣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8](P313)“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来,多有因女色败国者。 ”[8](P314)
昭君的自杀与“被自杀”,是作为天使或祸水的必然。天使是圣洁的,善于自我牺牲。她们从身体到心灵都保持着纯洁。一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既然成了汉帝妃子,相对于汉帝,昭君具有了臣子与妻子的双重身份。作为臣子,应辅佐君王解国忧国患,致力于国家大事的解决;作为妻子,应坚守对丈夫的忠贞,忧丈夫之所忧,急丈夫之所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当国家面临战争,和亲可以解国难,这是臣子之职责,也是妻子之责。但妻子和亲,是对丈夫绝对权威的挑战,置丈夫于尴尬之境。“每一个女人都属于某个家庭中的男子,女子的‘失贞’意味着她对‘这一个’男子的利益的彻底背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女性的私人性质的人际关系,破坏了女性自身以‘性的服务’为前提的生存基础,并因此危及到父权社会的基础—父权私有家庭。”[12](P23)天使绝对不会损害夫权,也绝对无法忍受自己被“玷污”而沦于“不洁”。所以,她们采取果敢的行动以避免对丈夫的背叛与被“玷污”的命运。一方面要解危难,一方面要保贞节,昭君在和亲之初就做好了“当效一死”(或自尽)的准备。最后的投江自然破解了国难与贞节的尴尬,于国于夫有利而无害,于己,则达到道德的完满。有论者指出,女性自杀乃是一种道德的完善,“她们的选择不约而同地通向一种道德完满的极致,这固然也是为了免却苟活和失节带给一个妇女的种种不幸,但归根到底,这种完满和不完满,幸福与不幸的所有结局都已经被社会所预定。”[13](P53)昭君投江虽然是莫须有之事,在红颜祸水观以及越来越强化的节烈观主导下,却似乎越来越“真实”了。
天使或祸水的自杀,实际上是男权社会在思想上以女性身体作为牺牲品以祭献传统社会道德。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指出,人们在选择替罪羊时,通常选择那些极端者: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恶习和极端德行,极能诱惑人或极令人讨厌,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极端强大都是众矢之的[14](P23)。当现有各种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代替群体受罚,洗除群体罪孽。选择替罪羊时“不是罪状起首要作用,而是受害者属于特别易受迫害的种族。”[14](P21)当汉匈战争即将爆发,汉王朝陷于极不利境地,昭君的性别、身份、地位、美貌等决定了她的牺牲品或替罪羊命运。
作为天使,昭君主动选择死亡以维护自我价值与国家价值;作为祸水,昭君则“被选择”以死亡维护传统价值。作为祸国的女色,历来贬斥者多,对其结局的安排也是负面的。然而,王昭君虽是“祸水”,她和亲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功绩不可能一概否定。男性作家巧妙地安排昭君投江自杀,以此消解昭君和亲的历史事实与现实节操观之间的悖论,而且此举给昭君披上了忠贞、爱国、爱君、爱夫的美丽纱幔,使之化身为天使,一来消解她“祸水“的沉重背负,二来掩盖了将她作为替罪羊的事实,三来为昭君投江作铺垫。天使也罢,祸水也罢,昭君“被投水”是封建社会大多数男性的共识,不可更改。
3 投江情结与贞节规训
所谓情结,是指人内心的强烈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宋以后的文人在昭君叙事中所具有的投江情结,不是偶然。
中国古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但由于家国同体以及对帝王权威的认同,不可避免的产生臣妾心理。自屈原香草美人的思维方式建立之后,以臣妾自喻成为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现象。屈原投江赋予死亡诗意,投江因此成为男性忠贞爱国的另类表述。屈原“投江”这一情节所代表的悲怨及对节操的坚守,经过历史的沉淀、发酵,越发醇厚浓香。当深受理学浸染的文人审视同为湖北秭归出生的昭君及和番事件,便不自觉地将“投江”移植到昭君身上。《吊琵琶》中,王昭君到了番汉交界之地的交河,昭君涌起强烈的故国之思。“这一条,向南朝;那一条,向北朝。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不是交河,分明是白马胥涛,汨罗江上潮。”[8](P330)在深受理学影响的文人看来,“存天理”,就必然要“灭人欲”,女性又怎么可能离夫另嫁呢?故而,小说戏曲不断描述昭君对君王的不舍,对另嫁他人的抗拒,最终投江。昭君投江实际上是男性文人依照固有的臣妾心理,想象女性对待和亲的态度以及应该采取的行为,代昭君言,代女性言。“所有男人写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15](P10)男性文人的女性代言,不管有多接近女性本来的心理,仍然难免带有他们对女性强加的“当然”。
昭君投江,是文人共同合谋的结果,是对女性贞节的规训策略。
自宋以后,昭君的贞节受到文人的反复咏叹。陶安《昭君图》:“龙沙月照汉宫词,毳锦衣裘换陆离。君命和亲劳敢惮?夫纲定分死难移!”[8](P64)南宋末赵文《昭君词》:“胡俗或妻母,何异豺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纲。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16](P189)小说或戏曲家将昭君由良家子改为深受汉帝宠爱的后宫妃嫔,而且二人之间感情深厚。他们注重昭君作为妻子的身份,不吝笔墨写昭君与汉元帝的难分难舍,突出他们的恩爱之情,以此作为昭君忠贞的前提。《昭君梦》第二折:“如今已是数年,只到俺芙蓉如面柳如腰,那知我冰雪为心玉为骨。所以奴家忠心不死,每日里悬念皇朝,好生伤感人也。”[17]《和戎记》:“我身待学浣纱女,效取当年朱妙音。守节后来全大义,谁想乌江埋我身。……身体发肤难保全,伤风败俗乱纲常。奴家不把清名朽,将身一命丧长江。”[9](P130-131)在太白金星的帮助下,昭君白雁传书给汉王。“一表君臣之义,二全夫妇之情,三显昭君贞节。”[9](P119)这里,作者突出“节义”与“纲常”,突出夫纲难移,冰雪之心与玉之骨,显然伦理观深入昭君灵魂深处。《双凤奇缘》虚构出昭君在胡地生活长达十六年,凭借自己的意志,也凭借九天玄女所赐的一件仙衣保护自己的贞节,最后还是投江自杀。昭君的投江,是为了要保留贞洁,——一个妻子对丈夫的贞节。投江,是对夫纲的维护。
倘若重新审视历代关于昭君和亲的言论,不难发现,不少人甚为鄙视这种“失节”之行。唐传奇《周秦行记》中,牛秀才歇息时,戚夫人、潘妃、绿珠均以各种理由推辞陪宿,最后太后要昭君相陪。理由是:“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索单于妇,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于是,“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予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18](P16)同为女性,昭君却逃脱不了陪宿的命运,与一般妓女无二。昭君和亲及改嫁的经历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洗刷的羞辱,使之成为太后令她陪宿的理由。更甚者,当牛秀才去昭君院,昭君不仅陪宿了,在离别之际,还“垂泣持别”。这个故事中,昭君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简单的叙事中,她水性杨花,毫无节操的形象跃然纸上。唐龙公开说昭君和亲乃“女德之辱也”。明人李有朋《明妃新曲并序》云:“明妃汉宫人也,出嫁呼韩邪君命也。再媵复株累谁所命哉?妃方幸外国,无防可恣,其欲视为乐土,岂复登望乡之台乎?‘黄金何日赎蛾眉’,真浪语也!予病咏明妃者多叙其情,不求其节,节已陨矣,情于何有?为作明妃新曲。”[8](P82)李有朋认为,昭君出塞初嫁单于是因皇命难违,重嫁复株累根本就是出于情欲,更不存在思乡了。有感于咏昭君之作多慨叹其不幸及悲苦却忽视了失节,李有朋作新曲,以“汉家遣色不遣节”为由,斥责昭君失节。《吊琵琶》中,蔡文姬祭奠昭君,其中有一句说道:“后人乃云:先嫁呼韩邪单于,复为株累单于妇。父子聚麀,岂不点污清白乎!”[8](P334)所谓“后人”之语,正是深受理学影响,一味强调女性贞节的道学家的一致看法。谴责昭君失节,在清人那里得到回响。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五中载某生在仙境中看到王昭君在女仙居住的景德楼里,于是质疑道:“景德楼中皆贞女、节妇所聚会,何以诸后妃又往?”祖师回答:“此诸后妃皆贞节之最纯者也。人知贫贱之难葆贞节,而不知位至后妃,苟为事势所迫,其艰难有十倍于平民者。”[19](P161-162)显然,此处昭君能在景德楼居住,应不是她嫁与单于并有改嫁的事实,而应是她在和亲之后“投江”等保持贞节的行为。否则,她只能成为失节之妇,断然成不了仙的。
出于对失节行为的鄙视和对节操的崇拜,在叙述昭君和亲时,文人们自然有两种选择:要么直接写在匈奴“失节”后的生活,要么在失节之前死去。显然,他们更倾向后一种选择,哪怕这样叙事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至少不违背他们心底的意愿,也更符合他们对女性的规训策略。
男性规训女性的策略之一,以“红颜薄命”劝慰女性安于自己的性别,自己的身份及地位,以及遵循与之相应的要求。文学史上昭君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毛延寿的丑图使其不能早得宠于汉帝,怨背井离乡,怨异地的不同于中原的种种。然而宋代以后,昭君之怨减少了,男性声音不断重复“红颜薄命”。欧阳修《再和明妃曲》:“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苏轼《薄命佳人》:“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宋以后,男尊女卑思想被强化,男性以“他者”的声音拙劣地表现女性的思想,想当然地认为这也是女性的真实想法。文徵明《明妃曲》云:“君王顾妾恩何厚,竟按臣工戮延寿。佳人自有命,画工何能为。”“红颜薄命古云然,不恨臣工况天子。”[8](P82)红颜薄命之说为昭君的和亲增添了浓郁的感伤特色,但也为昭君投江打下伏笔。
红颜薄命,也可名垂千古,甚至成神成仙。事实上,昭君的功绩不在她投江确保了民族节气,而在她嫁给匈奴王并生子,避免两国刀兵相见的史实。但在戏曲小说中,昭君最后成仙了,其原因也不是和亲匈奴并生子,而是贞节。“战乱年代,中国传统文人在不堪重负的现实面前,常会生发出‘女性救国’的奇想。战乱中以死御辱的女子为当时所称道,如果能够奋死御敌那就更值得世人崇仰了。”[20](P237)《二度梅全传》第二十二回写杏元到昭君庙,夜梦昭君,昭君说道:“想吾当日,毛延寿害我和番,到此殉节投河。蒙上帝怜悯我贞节,勒掌在此。又蒙国主建立庙宇,受此一方香火。吾只道后世的女子,水性杨花,贪生怕死,岂知还有烈性的佳人,愿其死而不愿其生,实为可敬!……吾神不若显一威灵,将此女送至中原,以全他贞节之名,使后世女子,方肯效节烈,以显我中原之光彩。”[21](P110)小说借昭君之口宣传贞节。所以,昭君投江,是红颜薄命,更是对贞节的维护。将贞节作为成仙的前提条件,对于薄命的红颜来讲,是一种极致诱惑。于是,自杀守贞便不是男权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女性自己主动选择。昭君投江并不妨碍汉匈之间的关系,却确保了汉帝丈夫的权威,成就了她自己的道德理想且能成神、成仙、名垂不朽。男性文人在昭君投江的叙事体现的贞节规训策略,实在高明。
4 “去投江”化:女性平等意识的探索与追寻
1923年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王昭君》与1979年曹禺创作的《王昭君》,依据两汉书的实录与空白,“还原”了昭君和亲的历史事实,完全摈弃了昭君投江情节及其所蕴含的悲怨色彩,摒弃了对于女性“三从四德”约束,将王昭君刻画成和亲英雄。在这两部剧作中,王昭君刚烈、富于反抗精神。她鄙弃汉元帝,斥责他荒淫、丑陋。她深明大义,到匈奴后摈弃民族偏见,和匈奴人打成一片,完成两国和睦的使命。
由此看来,“去投江”看似还原历史真相,实则仍是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王昭君是郭、曹二人的代言人。郭著《王昭君》是《三个叛逆的女人》之一,她的叛逆精神与五四运动中呼吁男女平等的声音一致。诚如郭沫若自己所说:“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离事实怕是不很远的罢。”[22](P74)这种想象的“叛逆”固然成功,但仍是作家的叛逆精神的代言,缺乏女性本位立场的生命关怀。曹著《王昭君》受周恩来总理托付而作,为宣传民族和睦、民族平等而写,政治意识形态明显。郭、曹二著中的昭君看似在为女性争取和男性同样的价值,但是,由于“女性的付出必须得到男性的接纳和确认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整个和亲事件始于父亲的决定或嘱托,成于丈夫的认可,和亲的成功使女性回归了社会的主流秩序。”[23](P62-63)在国家价值层面,“男性对女性的宰制,女性对男性的顺从都有崇高的理由,那就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以国族的名义打破的两性权力结构又在国族的框架内得到了重建,男性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稳固。”[23](P63)
相对于上个世纪的去“投江”叙事,新世纪的去“投江”更在于彰显昭君作为女性本体的情感表述。张平的歌剧《昭君》中,昭君自请出塞主要不是缘于民族大义或爱国之情,而是缘于她与单于的爱情。到匈奴后,因为爱情、亲情的作用,最终完成了和亲重任。与以往的昭君和亲叙事不同,新时期以昭君戏为代表的和亲戏有三大特征:第一,不是通过女性奉献自己来换取和平,主要靠情的力量解决各种矛盾。第二,女性不再是附属于男性的工具,而是独立的存在。她们有表达和决定的权利,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具备相当强的主体性。第三,面对困难,两性合力应对,很难区分他们谁发挥的作用更大,因为他们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23](P64)新世纪的《昭君》突出了女性主体地位,比以往的昭君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夸大了情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导致唯情论,对女性的权利、价值和主体性研究而言,仍有不足。从普通人的情感出发,全方位展示平凡女性的爱恨情仇,不是天使,不是魔鬼,不是高大全,也不是假丑恶,不是男性的对立面,而是凸显女性真实面貌,这种“去投江”化的书写才能成为真正的女性平等意识的表达。
[1]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斯蒂芬·欧文.追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A].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李东阳等敕撰.申时行等逢敕重修.大明会典:第七十九卷[Z].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6]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A].鲍家麟.中国妇女史论集[C].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
[7]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M].徐均尧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8]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9]王昭君出塞和戎记[A].古本戏曲丛刊二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10]徐石麒.浮西施[A].郑振铎编.清人杂剧二集[C].常乐郑氏影印本.
[11]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2]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5]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王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6]可咏雪等编注.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7]薛旦.昭君梦[A].邹式金.杂剧三集(影印本)[C].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18]牛僧儒.周秦行记[A].王弇洲编,孙葆真等校点.艳异编[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19]薛福成.庸庵笔记[M].丁凤麟,张道贵校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20]张永廷.杨家将的历史真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1]惜阴堂主人编辑,天花主人编次.二度梅全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22]郭沫若作品经典:第2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23]杨惠玲,赵晓红.和亲剧的性别文化解读[J].厦门大学学报,2010,(4).
责任编辑段君峰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12
I207.4=48
A
1004-0544(2015)10-0066-06
杨宗红(196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