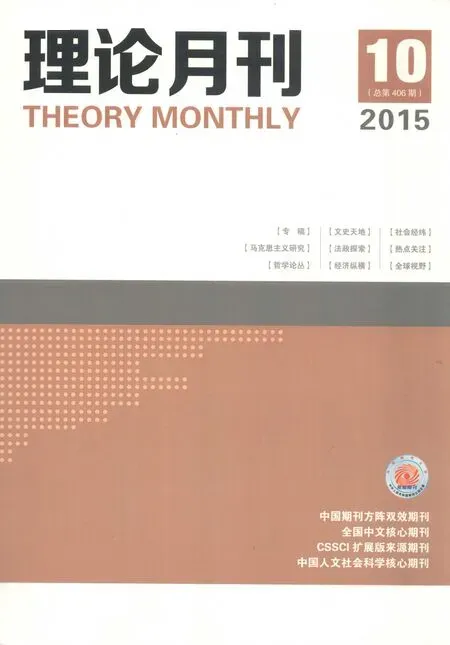制度决定论批判的批判
——驳尹伊文先生的《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2015-03-17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制度决定论批判的批判
——驳尹伊文先生的《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尹伊文先生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重新解释囚徒困境入手,引出人的利益追求不一样、理性程度不一样、行动往往情绪化和人是能动主体这四个观点为理据来否定制度决定论;二是列举四个经验事实来进一步否定制度决定论。但是,经过对这些理据和事证的逐一分析可以得知,它们全都没有在任何方面伤及制度决定论,更不用说整体驳倒。制度决定论是驳不倒的,因为其核心观点“在有制度的地方,制度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是无法否认的。
制度决定论;囚徒困境;理性自利人;理据;事证。
非常奇怪,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界也搜索不到一种自称“制度决定论”的理论或专门著述的时候,竟然就已经有了专门针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尹伊文先生的《制度决定论的神话》(以下简称《神话》),[1]就是率先发难的檄文。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的确是有一些中外解读者将以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说成是 “制度决定论”,但诺思本人从未这样说过,他最多只说过制度“在经济绩效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2]而从《神话》的内容看,它所提到的“制度决定论”的理论基础或来源,也确实不是诺思或其他什么人的新制度经济学,而是由杜尔凯姆所构论的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社会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人的社会行为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然而,“社会结构”与“制度”并不是相互等同的。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含构成社会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而制度只是所有这些要素中的一种。其他的构成要素是人口、家庭、各种社会组织、阶层阶级,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因而当某些结构功能主义者说“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时,并不等于在说“制度对个人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神话》作者将制度决定论溯源于结构功能主义完全是找错了对象。至此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如果世界学界确实已有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对它的指认就不会困难,也不会出错;只有在还没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指认错误。
虽然迄今理论上还没有制度决定论,但这些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在研究方法上,确实逐渐有了一种乐于从制度维度出发去解释人的行为及由行为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制度决定论倾向。而从《神话》全文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批判矛头实际针对的,也正是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制度决定论。
不管是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抑或是方法论的制度决定论,毕竟都是制度决定论。所以,《神话》如果对方法论的制度决定论的批判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应该也可以用来对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理论化的制度决定论。
《神话》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逻辑并不复杂,大致可归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解析囚徒困境引出若干理据来颠覆制度决定论;二是以诸多正、反事证来进一步证明其颠覆的有理和制度决定论的无理。
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层面的批判逻辑都不能成立。
1 对《神话》理据的批驳
基于流行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囚徒困境解释模型隐含有制度决定论的意思,用《神话》作者的说法,是“囚徒困境的分析隐含着结构决定论的思维方法”,《神话》作者选择了以颠覆囚徒困境解释模型为突破口,从中引出若干理据来展开其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
博弈论的囚徒困境解释模型的具体内容,现已在学界广为人知,此处无需再加赘述。它所隐含的制度决定论则还需明示为:外部的制度能对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囚徒困境解释模型证明,在有一套关于如何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及量刑的制度安排之后,两个共同犯罪嫌疑人(囚徒)经过博弈论的分析和算计,最终分别做出的不是进行相互合作并最有利于各自的选择——都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而逃避应有刑罚,而是相互防范对方出卖自己这种最符合制度导向或最有利于制度安排者所想要的选择——老实坦白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得到应有刑罚。
但《神话》作者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警察会告诉我们,审讯员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攻心战术,才能使囚徒坦白。”这就是说,《神话》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在囚徒困境中,攻心术比制度更重要。
“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为什么会有差异呢?”《神话》给出的解释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囚徒困境将人都规定为理性自利人的假设,忽略掉了许多具体条件或具体情况。但“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棋子,而是千差万别的有能动性的主体。”其中,“千差万别”是说,理性自利人所追求或看重的“利”有所不同;理性自利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也不同,并且往往是情绪化的。因此,同样的制度对存在上述差异的理性自利人来说,并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有能动性”是说,每个人都不是只能受动于制度的“棋子”,而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如何选择、如何行动的主体。故制度对这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可能起决定作用。
且不说《神话》用“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这样的假设所得到的假设性回答,来说明“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之间存在实际差异的研究方法是否太不认真,太不靠谱。就算是存在差异,实际情况是警察要在审讯时用到种种攻心术,才能让嫌犯坦白,那还是不能够否证制度决定论。道理不用多说。如果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制度安排(囚徒困境实质上就是一种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么在面对警察或司法官时,嫌犯选择不坦白就永远优于选择坦白,这时又有多少嫌犯会在种种攻心术下坦白自己的罪行?再说,警察种种攻心术的基本内容,岂不就是先向嫌犯交待相关政策即“从宽从严”的制度,再帮助嫌犯分析在此政策框架下,选择坦白和选择抗拒对自己的有利与不利?没有任何人会把制度决定论解释为只要把制度制定出来,就万事大吉,制度就能自动发挥决定作用。所以,有人去解释制度,有人去执行制度之类,都仍然属于制度运作的范畴。
当然,理性自利人所追求的“利”从来都不止一种,并且每个人对不同之利的先后排序也有不同。所以这里可以承认,在囚徒困境中,有嫌犯会出于“哥们义气”或害怕同伙报复等原因而拒不坦白。但从概率上说,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极少数。因为差不多所有不是为了政治诉求而共同犯罪的嫌犯都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而犯事,所以他们中乃至黑道人士中,真正相信哥们义气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偶有真正相信的,也定是少不更事初入其中,一时被蒙骗的人。至于害怕同伙报复,也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的担忧,而只能是个别案例中个别嫌犯的顾虑,即极小概率事件。一来有很多犯罪是个人犯罪而非共同犯罪;二来嫌犯本人是同伙中的强者不存在被报复;三来可能实施报复的同伙也已归案;四来警方可用提供保护或预先警告有报复可能性的嫌犯同伙等方法来打消嫌犯的顾虑。而这最后一点,显然可以成为一个与“从宽从严”制度相配套的制度安排。相反,在没有任何相关制度安排或具体措施的前提下,警察能仅用种种攻心术,就解除掉嫌犯害怕同伙报复的顾虑吗?显然不能。所以,在这里仍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制度而不是攻心术。与上相同,倘若没有“从宽从严”的制度安排,那么对嫌犯来说,采取拒不坦白的策略就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坏处,所以这时仅仅通过警察的种种攻心术就能坦白自己罪行的嫌犯,从概率上讲也只能是极少数。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让嫌犯坦白的问题上,有还是没有“从宽从严”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大不一样,制度在对付嫌犯方面的确是起决定作用。
为什么有多种利益追求且对不同利益有不同先后排序的人竟然都会被同样的一种制度左右?这不奇怪。人有多种需求,因而也追求多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源即利益。由于这些利益都是人生存发展的条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对人的生存发展不利,所以在任何时候,只要存在可能性,就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对任何一种利益的追求,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被剥夺任何一种既有的利益。就嫌犯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嫌犯会因为自己还有其他许多利益追求或更重要的利益追求,而不在乎被刑罚剥夺行动自由这种既有的利益或权利。正因为每一种利益都事关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制度就能通过对任何一种利益的剥夺或给予这样的社会赏罚,来对人们的行为选择进行左右和调控。
当然这里也承认,理性自利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理性化程度也不同。不过,《神话》说人“往往是情绪化的”则不够准确,应该说人“偶尔是情绪化的”。因为若没有特殊的外部刺激,人的情绪是不会凭空起波澜的。而任何人客观地想一下也能知道,自己平生平静的时候要远多于情绪化的时刻,凭理性选择也远多于凭情绪选择。此事且不多说。既然这里也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甚至偶尔是情绪化的,这就导致也要承认,理性自利人在有的时候也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或是不顾制度的率性而为,比如激情犯罪;或是未能选择制度化社会赏罚为人们预设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比如因不知驾车有限速规定而超速受罚。可所有这些仍不能形成对制度决定论的否定。制度不是一次性的命令,而是长期有效的固定指令或正式规则。所以,虽然是有人会率性而为,但只要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赏罚是及时而有效的,那么,他此后至少在这同一种事情上,再不会率性而为,触犯制度,激情犯罪;虽然理性的有限或程度的不同是会使有的人未按制度赏罚的导向行动,但行动之后所遭遇的受罚或未获赏的挫折结果,立刻就会让他获教训,长见识,增理性,并迅速将自己以后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动选择调整到与制度赏罚导向相一致的方式上,比如开车超速受罚后再不超速行驶。这就说明,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情绪化的率性而为和不够理性的行为选择,只可能是他的极少数行为,而不可能是绝大多数行为;若从他对待或处理同一件具体事务来说,基本上只是一次性行为,而不可能是反复发生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和反复出现的行为,只可能是符合制度赏罚导向从而也符合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行为和反复出现的行为,也只可能是符合制度赏罚导向从而也符合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就是说,偶尔出现的率性而为和不够理性的行为,并不意味制度对个人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人也是有能动性的主体。所以,一个人究竟听不听制度的摆布,还是要由他自己决定。这似乎证明了不是制度在决定,而是行动者个人在决定。但是,有能动性的主体也有自己的各种需求,并且他的各种行动追根溯源地讲,也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否则,他就什么都不需要做。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3]既然有能动性的主体最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才“动”,那么他在考虑怎么“动”的时候,就自然会考虑怎样“动”才会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亦即怎么“动”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经过思考发现只有按制度赏罚的导向行动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他就会选择按这样的行动方式行动,并且会在制度赏罚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随之相应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在这里,从外部看,是行动者被制度决定了行动方式;从内部看,也是行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进行选择的结果。这就表明,说人的行为被制度决定,并不等于说人不是有能动性的主体,因为一个人从若干行为选项中选出其中之一这件事本身,就是有能动性的体现,只不过经过理性思考,他最终选择的是对他来说最为有利的行为而已。而这种对他最有利的行为,同时也是制度安排者所希望看到的行为。如同人在洪水、海啸、火山、地震等灾难发生时的快速逃跑,不意味人没有能动性一样,人在制度赏罚的框架下趋利避害,也不意味人没有能动性。当然,人在这里如果选择逆制度赏罚导向而动,也是有能动性的体现。但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行为方式呢?难道舍此就不能彰显自己有能动性?在人的需求与能动性之间,显然需求是目的,能动性只是手段或工具,即人的能动性是为满足人的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否则,人的能动性有还是没有,对人来说都无所谓。所以,最能体现人的能动性的,还是每次自主做出的选择是否最有利于自己。如是,则有能动性,且能动性强;如不是,则缺乏能动性,或能动性不强。据此而论,倘若在制度赏罚灵敏有效的前提下,还是有人经理性思考后逆制度赏罚而动,那就只可能出于这两种情况:一是嗜财如命的利令智昏者心存侥幸地赌一把,他自以为可以凭借其高明的作案手段逃避制度惩罚,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是将“兴天下之大利”(《墨子》)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来追求的革命者,由于他所追求的天下大利为既有社会制度所不容,所以只有采取革命这种逆制度赏罚而动的方式来进行。如是可知,这两种逆制度赏罚而动的情况,仍然符合人的能动性或理性在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追求这一判断。诚然,这两种逆制度赏罚导向而动的情况在整个社会中只能是少数。一来是绝大多数人经理性思考后,不愿在风险极高而成功率极低的情况下 “赌一把”;二来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能将“兴天下之大利”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来追求的境界。因而在制度灵敏有效时,制度对有能动性的主体起决定作用还是普遍情况,而不起作用则是罕见的情况。其实,有能动性的主体能被制度调控,本不应该是一个无法被我们接受的奇特观点。因如果不是这样,社会管理和组织管理就没有任何可能性,管理学和法学也不可能成为一门学问,各种管理理论和法学理论,也都会是一些无用的废话。
《神话》作者为进一步夯实自己的批判理据,还以其囚徒困境分析中警察的攻心术为喻,将直接决定能动主体如何行动的东西,说成是行动者的“心”,并声称“‘心’是能动主体的一个黑箱,是数千年来人们探索的一个谜。人们可以找出无数的能影响‘心’的因素,但至今也没有找到全部因素。”虽然“制度对黑箱有影响,但不能决定黑箱中的运作。”
《神话》喻为的“心”,实际上就是人的动机。虽然影响能动主体动机即“人心”的因素是很多,而制度只是其中之一。但与其他其实并非“无数”的社会因素相比,制度还是对“人心”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撇开非人力可以控制的自然因素不谈,社会中还能影响“人心”的东西,无非就是说教、习俗、道德、宗教、艺术感化(即古人所谓的“乐”)和文化价值观念这些。而这些因素,由于或者不能对人实施赏罚,如习俗、艺术感化和文化价值观念,或者只能对人实施关乎声誉的赏罚,如说教、道德、或者只能对人实施虚构的关乎来世的赏罚,如宗教,所以比之既能对人的声誉实施赏罚,也能对人的其他一切利益进行赏罚的制度来说,它们就显得软弱乏力,只能退居其后,叨陪末座。特别是当制度的导向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导向出现不一致的时候,败下阵来的只会是它们。尽管制度不管来世,似乎难以决定宗教徒的动机,但因宗教往往是统治者的工具,所以宗教徒违反社会制度也会被说成是违反教规,同样影响其来世去向。因此,在所有社会因素中,对人的动机或如何“动”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就是制度。简易言,人心基本由制度决定。而这一观点,其实连《神话》作者自己也已承认。他在文中自问自答道:“什么东西能影响‘心’呢?制度当然能够影响‘心’,但不能完全决定‘心’”。可制度“不能完全决定‘心’”的说法,岂不就等于说“制度能基本决定‘心’”?
2 对《神话》事证的批驳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或微妙考虑,或许是为了使“制度决定论”显得更为荒谬和更容易被批倒吧,《神话》作者在文中经常将其批判对象“制度决定论”偷换成另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命题——“制度决定一切”,并且在其行文至第三部分时,特地举出四个正、反事证来对其进行否证。
“制度决定论”与“制度决定一切”这两个说法,虽然在字面上仅有“论”与“一切”这一两个词的差异,但实质上已有天壤之别。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制度决定论倾向,充其量只是认为,在有制度规定的地方,个人的行为和由个人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是被制度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不认为,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事物也都在制度决定的范围之内。
偷换批判命题的做法,已经彰显出批评者底气的不足,而四个正反事证也奈何不了制度决定论,下面依次来说。
第一个事证是:“当五十年代推行国有化、公社化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一个逻辑:私有财产是私有观念的根源,如果消灭了私有财产,人的私有观念就会逐渐消失,就会变得一心为公;在人民公社中,人没有了私有财产,大家都会大公无私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公有制的企业中,人都变成了公有企业的主人,大家都会一心为公地努力工作。但是二三十年的实践却告诉我们,公有制的结构并没有消灭所有人的私有观念,并没有使人人都变得一心为公。”
关于这个例证,首先要说,如果严格按照《神话》的叙事逻辑推论,根据后来“公有制的结构并没有消灭所有人的私有观念”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消灭了私有财产,人的私有观念就会逐渐消失”的预期就是错误的,因为其时的国有化和公社化只是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即生产方面的私有财产,而没有消灭生活资料的私有,即生活方面的私有财产。既然这时还有私有财产,不仅有生活方面的大量私产,也还有一定的生产方面的私产,如农村的自留地或菜地和家禽生猪之类,那么这时人们还有私心也是正常的。所以用这个例证来否证制度决定论是没有用的。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在消灭了生产和生活中的全部私有财产之后人们还有私心,也不能由此否证制度决定论是不对的。因为私有财产根本就不是利己心的根源,以为消除私有财产就能消除私有观念的想法本身是极其幼稚和错误的。利己心是人的本性,生而有之,无法消除也不能消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如果自己都不操心自己的生存发展,他就根本不可能生存发展,其结果不是死亡,就是像婴幼儿一样依然完全依赖他人,成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而要能生存发展,就必须操心自己的生存发展,必须为自己谋取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或利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否认人性自利的人,是把“自利”、“为己”等同于恶,以为承认人性自利就等于承认人性恶,承认恶的必然性,承认恶永远无法消除。但实际上,人为己或有利己心本身并不是恶,并且将其变成为自己谋利的现实行为也不都必然是恶。只有在谋利时选择了损人利己的行为方式才是 “恶”,才导致“恶”的发生。但如果他采用的是利己不损人或既利己也利人的行为方式,那就完全是正当的,毫无“恶”可言。
第二个事证是:“公有制使人吃大锅饭使企业效率低下,私有制会使人努力工作,会提高效率。这个逻辑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时的强力话语、主导说教。私有制真的使人都努力工作了吗?私有制真的使企业都提高效率了吗?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有人努力工作,有人耍滑偷懒。有的私有企业高效成功,有的私有企业低效破产。”
在这个事证中,《神话》作者仅用“有人努力工作,有人耍滑偷懒。有的私有企业高效成功,有的私有企业低效破产”这一句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统计数据的话来否证“私有制会使人努力工作,会提高效率”的制度决定论观点的逻辑是非常草率的。私有制可明确产权,使企业有明确的所有人或业主,而业主对企业经营的好坏又直接决定其收益,因而私有企业相比产权不清,企业没有实际业主或企业所有人无法在场的公有制企业来说,一般都会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这既是世界范围的经验事实,也是得到公认的产权理论的基本常识。此其一。其二,有私有企业的社会,一般都是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通过市场竞争进行利益分配和优化资源的社会配置,因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所谓“有的私有企业低效破产”,不过意味着破产企业的资源已被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去,这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实际上是得到提高。由于这种优胜劣汰式竞争持续存在,各个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相对以往也就越来越高。因此,“有的私有企业低效破产”的事实,不仅不等于说私有制在总体上没有效率,反而意味私有制在总体上有日益增进的效率。何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那些“低效破产的私有企业”之所谓“低效”,也只是相对效率更高的私有企业而言,若是相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则很可能仍然是算高的。其三,“私有制会使人努力工作”这句话意味:只要实行私有制,就能使所有的人努力工作。但《神话》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谁曾这样低能地如此说过?且不管有没有人这样说。事实上,说“私有制必然会使私企业主努力工作”是对的,说“私有制也必然会使企业雇员努力工作”则不够严谨。因为如果私企业主不能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有效的奖勤罚懒制度,企业雇员就不会全都努力地工作。因之即便某些私企确实存在“有人耍滑偷懒”的现象,那也与私有制无关,而是与企业内的激励制度有关——还是取决于制度!
第三个事证是:“根据制度决定论的逻辑,制度可以决定谁给出乌纱帽,因此也可以决定接受乌纱帽的人会对谁负责。但当我们观察现实和历史,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有无数的皇帝委任的贪官,他们并没有对皇帝负责。现实中也有无数上级委任的恶吏,他们并没有对上级负责。在选举制度中产生的官员,也不是人人都对选民负责。”
戴乌纱帽的人贪污,不等于他没对给乌纱帽的人负责。事情很简单,给乌纱帽的人,不管他是皇帝、上级还是人民,都不会是傻子,如果戴乌纱帽的人没按自己的意志做事,完成指派给他的工作任务,给乌纱帽的人就会立刻摘去他的乌纱帽。另换他人来干。比如和珅,虽是特大贪官,但若没有不俗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能办好皇帝交代的各种差事,他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官越做越大。因而制度的确“也可以决定接受乌纱帽的人会对谁负责”。既然戴乌纱帽的人会对给乌纱帽的人负责,那其中为什么还会有人贪污?这是因为官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利人,而凡贪污者都认为其贪污行为不会被发现,贪污符合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为给自己乌纱帽的人负责和为自己贪污,在一个官员身上,并不是不能兼做或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事情。诚然,给乌纱帽的人是不仅希望戴乌纱帽的人为自己做事,也希望戴乌纱帽的人不搞贪污,在后一件事情上也为自己负责。但凡有点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他要想做到后一点,光靠给乌纱帽是不行的,而是还要另行设计防范贪污的制度。因此,官员是否贪污还是由制度决定的,只不过不是由给乌纱帽的制度,而是由反腐败制度:反腐败制度有效,官员就不敢贪污;反腐败制度无效,就没有不敢贪污的官员。所以,以官员贪污之事来解构制度决定论也是不成立的。
第四个事证是:“笔者有一位朋友是‘制度决定论’的坚定信仰者,……他和他的太太在美国经营一个小店,两人从不同时回中国探亲,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们看店。他似乎并不相信他可以在他的小店中建立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能决定一切。相反,他还是要用‘人治’,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看管他的店。这位朋友的所为并不罕见,笔者见到许多 ‘制度决定论’的坚定信仰者在雇用家庭保姆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保姆人品是否可靠,而不是去想法建立制度来决定保姆的行为。”
这个事证似乎很有说服力,其实仍然威胁不到制度决定论。在小店或家中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制度来决定雇工的行为的,只不过这样做的成本太大,既要花时间精力设计制定制度,也要安排专人来监督雇工是否遵守制度,甚至还得再设专人来预防监督者与雇工的串通合谋,这就远远超过雇一个人看店或做家务的收益。因此,在这类事务中,并不是不能由制度来决定,而是由制度决定实在划不来。确切说,是为雇一个人做以上制度安排实在划不来。所有具有制度决定论倾向的人,都没说过“制度决定一切”,也没认为制度覆盖了所有的人类事务,任何事务或问题都需要通过建立制度来解决。所以制度决定论是这样的观点,在有制度的地方是制度起决定作用,在没有制度的地方也没有制度的任何作用。没有制度的地方,一般都是不需要制定制度或制定制度的收益超过成本而不值得制定制度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起作用的通常是习俗、道德或说教,它们都是成本低廉的社会管理工具。因此,好人品是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甚至达到免设制度的程度。而且如果人人都是圣人,那就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建立制度。但问题是只要世界上还不断有新的人口降生,本性使然的理性自利人就不可能都在某一天同时修炼成圣人并再不会沉沦。既然如此,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不需要任何制度的时候,也永远不会有仅凭道德或“人治”就能平天下的时代。
3 总结性批驳
经过以上分析和反批可知,《神话》对制度决定论的批判逻辑,不论在理据方面还是事证方面都站不住脚,因而它也就没有在任何方面伤及制度决定论,更不用说是整个驳倒。
制度决定论是驳不倒的,不仅《神话》的作者驳不倒,换了其他任何人也驳不倒。因为制度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在有制度的地方,制度起决定作用”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这个核心观点,既不意味着在没有制度的地方制度也起决定作用,也不意味在有制度的地方其他相关因素不起任何作用。其他相关因素这时起的是次要作用,其次要性可以从其他因素与制度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看出.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其他因素的价值导向与制度是一律的,那么这时所有人的行事方式都是一样的,既符合制度的愿望,也符合其他因素的愿望。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其他相关因素的价值导向与制度是不一律的,则会有少数人按其他因素的导向行事而未按制度的价值导向行事,从而出现个体间行事的差异。但无论何时,由于制度是强导向,绝大多数人还是都会按制度的价值导向行事,正如“大锅饭”时代,虽然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人们热爱劳动,也教育出一些如王进喜、张秉贵那样的劳动模范,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越变越懒,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也是越来越低。这就是说,其他社会因素在第一种情况下,起的作用是辅助制度导向,提高制度导向整体效率;在第二种情况下,起的作用是干扰制度导向,小幅降低制度导向整体效率。
制度决定论是驳不倒的,甚至由《神话》自己说出的两个事实也隐喻了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是《神话》作者在介绍社会学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方法时写道:“在‘结构’和‘个人能动主体’的框架中,杜尔凯姆的传统强调结构决定;韦伯的传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能动主体。其后的各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往往在这两个传统中徘徊,在徘徊中有时从一个传统衍生出来的理论会最终滑到另一个传统中去。譬如,二十世纪中叶的行动理论的重要代表帕森斯(Parsons),他的理论本是从韦伯传统衍生出来,但他在解释个人行动的时候,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对个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使其理论最终落入结构决定的框架中。博弈理论也是韦伯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它的囚徒困境分析却也在设置假设条件的时候埋下了结构决定的种子。”
为什么后来源自韦伯“个人能动主体”传统的个人行动理论和博弈理论,最终都滑到了被《神话》作者视同制度决定论的结构决定论的传统那里?相反,却没有某种社会学理论从结构决定论滑到能动主体论的例子?这些事实岂不已经隐喻了在解释个人行动和社会现象时,制度决定论的不可抗拒?
第二个事实是《神话》作者在论述“能动主体”的“心”这个不可捉摸的“黑箱”时写道:“能动主体的黑箱最终决定人的行动。能动主体处在社会结构中,制度是结构的重要部分,结构和制度对黑箱有影响,但不能决定黑箱中的运作。建立制度比深入黑箱容易得多,浮躁懒惰的政治家往往相信‘制度决定论’,企图建立制度就万事大吉。务实负责任的政治家会小心地探索黑箱,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影响黑箱。虽然他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控制黑箱,但是他们会对能动主体的行为有更准确的预测,有更多的影响。当然,有些影响黑箱的方法也可以视作为某种小制度。制定这些具体、微观、渐进的小制度要比盲目空洞地改变大制度往往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讲了半天,所谓“务实负责任的政治家”想出的影响黑箱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原来主要就是制定小制度。可“小制度”还不是制度?!又有哪个相信制度决定论的人说过“小制度不是制度”,“只要有大制度就万事大吉了”?!退一步讲,如果现实中确实有人只定大制度,不定小制度,那也只是他个人学艺不精的问题,而与制度决定论无关。既然用小制度解决问题的观点也还是制度决定论,那就证明,《神话》的作者也和上述哪些试图抗拒制度决定论的理论家的宿命一样,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滑到了制度决定论的一边。
[1]尹伊文.制度决定论的神话[J].读书,2008,(7).
[2]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9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6.
责任编辑文嵘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08
D0-02
A
1004-0544(2015)10-0043-07
国家教育部2014年度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4YJA72002)。
韩东屏(1954-),男,湖北钟祥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