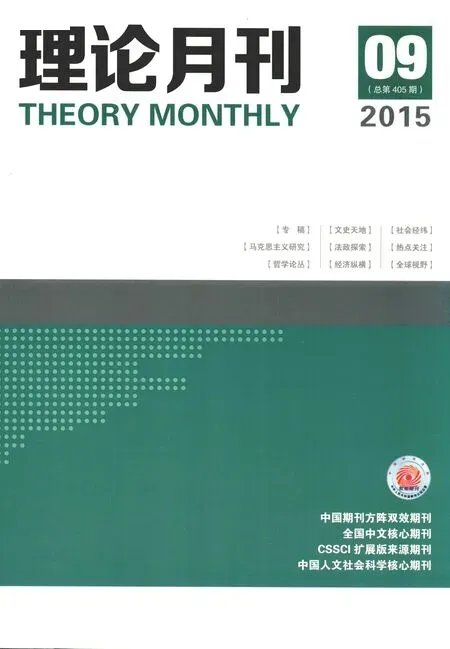“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定性的类型化研究
2015-03-17高维俭李晓磊
□高维俭 ,李晓磊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0)
“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定性的类型化研究
□高维俭 ,李晓磊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0)
“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以强奸论处。在特殊情形下,该一概而论式的定性模式会出现显著的不合理:即,既不利于保护精神病妇女权益初衷,又有悖于人们基本的价值观念。故而有必要对“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形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在理论上予以澄清、立法上予以跟进。具体而言:一是将“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类型化为强奸故意型、同居意愿型和婚恋意愿型三种形态;二是司法上应根据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及个案的具体情态,予以合理的区别对待;三是在理论上推定同意可以成为破解相关困境的关键点;四是立法上相应的特别规定应当得以确立。
精神病妇女;性关系;类型化;推定同意
据报道我国精神病患者数量庞大,有1亿之多,其中重症患者约1600万。①参见 《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http://www.chinanews.com/jk/news/2010/05-29/2311755. shtml(新闻中心-中国网),2012年5月10日访问。此外,我国精神病患者的监管和治疗问题十分突出,即一方面家庭往往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和社会救济又相当匮乏。②精神病患者被害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与精神病妇女③发生性关系案引起颇多关注。为了体现对精神病妇女性权益特别保护,我国司法实践中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严重痴呆者)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情形以强奸论处(以下统称“一概而论处理模式”)。此种处理模式的直接依据可以追溯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简称《解答》)(最高人民法院[84]法研字第7号文)。虽然《解答》已被废止,但并未有新的合理规定予以填补有关空白,这种“一概而论处理模式”实际上并未随之废止,而是仍为司法实务界所遵循。因此,深入系统地对这种处理模式予以反思,探求合理的处理模式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案例引起的思考
案例1:在2004年11月份,黄某(男,未婚)在农贸市场买完菜回家的路上,看到余某(女,系精神病患者)对其微笑。黄某见余某衣着单薄,十分可怜,于是将余某领回家并给予照顾,后与其共同生活。黄某视余某为妻,在黄某精心关照爱护下,余某对黄某 “言听计从”,十分“依恋”,且其在两人发生性关系时也积极配合。后,余某的父母找到黄某并表示,如果黄某愿意照顾余某,在余某病好以后同意二人结婚。公安机关闻讯,以黄某涉嫌强奸罪将其逮捕。经鉴定,余某患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
案例2:刘某因家庭贫穷,年至42岁仍未娶妻。冯某系邻村冯老汉之女,25岁,未婚,面容姣好,患有严重精神病。冯老汉夫妻打算将女儿嫁出去,以为其找到安生立命之所。故托人做媒将其女介绍给刘某。刘某最终答应这门亲事,并把冯某娶回家,给予应有照顾。公安机关得知后,查明刘某已与冯某多次发生性关系,于是将刘某抓获,并提请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后经鉴定,冯某患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
案例3:犯罪嫌疑人凌某,男,江苏南通人,未婚。王某,女,上海人,未婚。2004年7月,在上海打工的凌某将恋爱不久的王某带回江苏南通,并与其同居。后,邻居发现王某不太正常并告知凌某母子,凌某母子遂带王某到村医吴某处检查,吴某告知凌某母子王某脑子有病。在同居的两年时间里,凌某多次与王某发生性关系。后公安机关介入,经鉴定王某系精神病患者,无性防卫能力。与之类似的案件还有王老汉“娶妻”案、①佚名:《娶精神病患者为妻是否构成强奸罪》,http://homelife.scol.com.cn/2004/02/03/1051 32048.html(源于《家庭与生活报》),于2012年5月10日访问。杨宝桂强奸“老婆”案、②王某某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③等。
上述案例有共同之处在于:其一,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均以涉嫌强奸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二,犯罪嫌疑人在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均未采取强迫、威胁、迷药等强制手段,且精神病妇女亦无反抗情形。其三,犯罪嫌疑人均明知或推定应当知道被害人患有精神病。其四,犯罪嫌疑人均出于婚恋等共同生活目的而发生性关系。其五,同居期间,犯罪嫌疑人并未有虐待精神病妇女的行为,且两人的共同生活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其六,被害人系精神病妇女,经司法鉴定均无性防卫能力。
如果采用“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上述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均会以强奸罪论处。然而,如上述三个案例所显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在与精神病妇女共同生活期间,均对其给予应有的呵护和关照,并未对“被害人”造成实质危害,很难得出上述行为具有实质违法性的结论。故而如果不区分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的具体形态,采用“一概而论处理模式”,将明知是精神病妇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均定性为强奸,显属不妥。那么,为什么“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还被司法实践所广为遵循?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采用何种处理模式处理“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问题更加妥当?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又如何具体实现?
2 “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的理据分析
“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在一般情况下是合宜的,其理论基础如下。
第一,刑事政策基础,即特殊群体的特别保护。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对精神病妇女等特殊群体的特别保护显然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国家刑法个别化政策的具体体现,即通过对特定群体的人格发展进行保护以期实现实质平等。从生物学上讲性是人的一种本能;从法理上讲,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自主表达自己的性意愿和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性行为和以何种方式实施性行为来实现性之需求,不受他人强迫和干涉。[1]精神病妇女虽然存在表达障碍,但亦不例外。精神病妇女心理、精神等方面存在障碍导致其缺乏正常的自我保护能力,较之常人更易遭受性侵害。因此,“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更能对罪犯(或潜在罪犯)造成威慑,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有利于保障精神病妇女的性权益。
第二,刑法理论基础,即被害人同意理论。被害人同意作为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是指基于被害人同意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而实施的阻却犯罪的损害行为。[2]通常认为因精神病妇女欠缺同意能力,故其承诺无效。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患有精神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其承诺无效。[3]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奸淫精神病妇女构成强奸罪的条件是,精神病妇女必须是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缺乏性承诺能力。[4]也有学者认为,精神病妇女与精神正常的妇女有所不同,这里以一种司法解释的方式限定了他们的性同意能力,是出于刑法对其予以特殊保护的目的。[5]这种“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正是遵循这一思路。
第三,域外经验。为了对精神病妇女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对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做了特别规定,严惩侵害精神病妇女的犯罪分子。例如,英国1956年颁布的《性犯罪法》第7条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6]德国刑法第179条将“利用他人因病理性精神错乱、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或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而无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规定为犯罪。[7]日本刑法第22章第178条将“乘女子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规定为犯罪。[8]意大利刑法第609条将“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接受性关系”规定为犯罪,等等。[9]综上,虽然不同国家对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行为构成犯罪的具体要求不同,但都对其作出了与普通强奸罪不同的规定,体现出国际上对精神病妇女进行相似(或相同)的特殊保护原则。在特殊保护的目的上,我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基本一致。但比较而言,我国“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更加绝对。
3 对“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的检讨
虽然该处理模式看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处理模式,因其过于绝对而罔顾特殊情形,实际上造成诸多流弊,致使其正当性存疑。
第一,是否真正有利于精神病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概而论的处理模式”希冀通过严惩侵犯精神病妇女性自主权的犯罪分子,进而实现对其特殊保护的目的。但司法实践中,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处理模式非但没有达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初衷,反而极有可能使这些精神病妇女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以案例1为例,余某在外到处流浪,衣食艰难,不止性自主权、甚至生命权亦无法得到保障。黄某出于怜悯等原因收留她后,该流浪女亦对黄某产生了感情并就此告别流浪的苦难历程,过上比较稳定和幸福的生活。在当前国家和社会无法给予其基本生活、医疗保障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对余某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然而若采用“一概而论的处理模式”,不但刘某面临入罪(且为重罪)的危险,余某也面临再次被迫流浪的危险。
第二,是否真正符合人们的一般价值观念?在特定情形下,“一概而论的处理模式”亦不符合人们的一般价值观念。所谓一般价值观念,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是非、善恶观念,即 “良知”(或法的内在精神)。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形式上当然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实质上必须侵害到被害人的重大生活利益,即法益。同时,相关规定本身亦需不违背人们一般的价值观念,即贯彻“恶法非法”的基本精神。①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审判中确立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即恶法非法。符合人们一般价值观念的法律,强调法律的合道德性。诚如美国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所言,真正的法律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参见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记(八)——恶法非法:纽伦堡大审判》,《法律与生活》,2010年8月。上述三个案例中,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均出于恋爱、结婚等共同生活的目的与精神病妇女同居,且同居期间均未虐待过被害人,而是给予悉心照顾,使被害人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相对和谐的环境。上述“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是乃其共同生活的组成部分,且上述行为亦能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在共同生活过程中照顾关爱精神病妇女的行为,是国家和社会相关监管保障严重不足 (甚或缺位)的有益补充。从人们一般的价值观来看,行为人的行为非但未危害被害人,亦未危害社会,反而使被害人受益,其行为可谓善举。因此,在某些情形下,“一概而论”的处理模式实际上既不利于精神病妇女合法利益的保护,也有悖于人们长期持守的基本价值观念。
第三,是否真正符合刑法谦抑性(不得已)原则?英国法学家边沁曾深刻指出,刑法中有两种恶,一为代表罪行之恶,另一为代表刑罚之恶。[10]刑法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的重要思想理念,其目的之一即为限制第二种恶。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刑法适用应当秉持谦谨、克制的理念。即,谨守刑法作为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性;谨守刑法的不完整性,不过分介入国民生活;谨守刑法的宽容性,对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或虽然侵害(或威胁)法益尚未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不适用刑法规制。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件中,确实存在犯罪分子利用精神病妇女心智缺陷,以强迫、欺骗等手段对精神病妇女实施奸淫的情形,对这类犯罪分子当然应给予刑法惩罚。但是,与上述犯罪分子不同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有人出于婚恋的目的与精神病妇女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案例1、案例2和案例3中,这些所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不具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也能为大多数人所容忍、理解。若不区分案件的具体形态,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方式、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害人切身利益,一概而论地适用1984年“司法解释”,将上述行为定性为强奸罪,乃是对尚未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给予刑法规制,不但有过分介入国民私密空间之嫌,且明显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悖。
第四,是否与“奸淫幼女行为”的定性理念相混同?根据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等规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明知其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幼女是否同意,均构成强奸罪。申言之,即从刑法理论上讲,对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不能适用推定同意理论,即使其明确表示 “同意”或“未表示反抗”,也应当推定其不同意。不难发现“一概而论的处理模式”在内在逻辑脉络上与“奸淫幼女”的相关规定惊人一致。即在两个问题上都排除了推定同意理论适用的空间。然而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对前者,我们当然可以“基于相关科学常识和社会一般价值判断”认定,幼女身体和心理尚未发育成熟,均属稚嫩,与其发生性关系显然有害其身心健康。但对后者,却不能基于相同的理由认定,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必然或显然有害其身心健康,也不宜想当然地作出精神病妇女必然不同意的推论。因为,从生理学角度分析,多数精神病妇女的生理发育与正常妇女几无差异,其当然具有正常妇女或类似正常妇女的性需求。所不同之处只是其性需求的表达存在障碍而已。因此,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完全有可能符合其基本利益,具有推定同意的基础。
4 “类型化处理模式”的提出及证成
4.1“类型化处理模式”的提出
目前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对“一概而论式处理模式”的偏误予以纠正。我们认为,当下比较妥当的方法是:以“类型化处理模式”代替“一概而论处理模式”。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后者对行为人的罪过心态进行了细分,而前者则一概而论。具体而言: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关键在于他是否利用妇女的精神缺陷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从而达到“奸淫”的目的,即是否具有罪过心态。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不能机械地沿用“一概而论处理模式”,应全面考察案件情节,结合强奸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及个案的具体形态,予以合理的区别对待。根据行为人罪过心态的不同,有必要将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件类型化为以下形态。
形态一:强奸故意型。顾名思义,该类型罪犯有奸淫(强奸)的故意。其既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也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契合。概言之,行为人以奸淫的故意,明知其为精神病妇女,而以威胁、暴力、引诱、欺骗或其它手段与之发生性关系,对其可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以强奸罪论处。
形态二:同居意愿型。同居意愿是概括的意愿,既包含与精神病妇女“共同生活”的目的,也有诸如奸淫、贩卖人口等其他的目的而与之共同生活。如果同居的目的单是为了“共同生活”,且并未伤害“被害人”,则不宜机械地以强奸罪论处。即需要考虑具体案件的全部情节,譬如行为人因家庭贫困没有能力娶妻,单单找个人“结伴”生活,且在结伴生活中对精神病妇女的生活予以合理的照顾,在此情况下很难认定其出于奸淫的故意,亦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实质违法性。如果同居的目的是利用精神病妇女的缺陷意图长期奸淫等目的,则应以强奸罪论处。
形态三:结婚意愿型。该类型中,行为人是以与精神病妇女恋爱、结婚为目的而发生性关系的。如案例1、案例2和案例3中,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均出于婚恋的意愿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且在共同生活期间,基本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显然不宜以强奸论处。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类似前述三个案例的“犯罪嫌疑人”并无强奸的罪过心态,该类案件实际无受害人,亦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不宜以强奸罪论处。至于婚内与精神病妻子发生性关系的形态,更不应以强奸罪论处。
4.2类型化处理模式的学理基础:推定同意理论之引入
何谓推定同意?理论上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推定同意(又称为推定承诺),是一种违法性阻却事由,是被害人同意理论的特殊方面。大冢仁教授认为,推定承诺的行为,是指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被害人自己作出的承诺,但是可以认为被害人知道情形时就当然会给予承诺,从而推定其意思所实施的行为。[11]德国的耶塞克教授指出,推定同意(mutmassliche Einwilligung)是指,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根据情形可能赋予有效性的同意。鉴于无法与法益享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取得联系,或者某个需要紧急治疗的病人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可能表示同意,但若对整个事情进行事前的客观评价,应当肯定能够得到该病人的同意。[12]木村龟二博士也在其《刑法总论》中指出,所谓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是指根据客观的判断,从理性人的见地,能预期被害人承诺的行为。[13]鉴上,不难发现,推定同意相关界说中隐含着判断“推定同意”的两种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者多数情况下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只是主观标准更强调对被害人主观心理的推测,客观标准更强调站在理性人角度的客观判断。
笔者基本赞同耶塞克教授和木村龟二博士的观点。因为人们难以测透隐秘之事,法律更关注外在形态,以推定内在表达。客观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合乎法律的内在旨趣。具体而言,推定同意可界定为:在被害人因故“不能表达”或相对行为人临时无法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相对行为人站在“理性人”的视角,基于社会一般价值标准考量,若相对行为人的行为及结果有利于被害人,从而推定被害人“如能表示”则应当同意。申言之,推定同意的构成要素有:(1)情景要素,即前提条件。特定情形下被害人不能做出合法有效的同意表示。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主观不能”,即被害人自身具备同意表达能力,但由于特殊情形不能表达。所谓“客观不能”,是指被害人因为生理年龄或精神障碍等原因而暂时不具备相应法律意义上的同意表示能力,如幼女、无性防卫能力的智障患者等。(2)客观要素,即拟制要素。所谓有利,即被害人“拟制意志”下的有利:其不是有关被害人主观的推定,而是相对行为人站在“理性人”的立场,在特定情形下依据客观的判断可以期待被害人应当做出同意表达。(3)价值要素,即限度条件。具体而言,推定同意的判定应当符合社会相当性标准,亦即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符合公序良俗和正当有序的法律精神。[14]
我国有学者认为,推定同意的成立需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前提条件(情势紧急)、实质条件(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补充条件(行为的社会相当性)。①在我国,有学者认为推定同意行为与紧急避险性质相同,但特征有别,并且把“推定是否存在同意的可能性”(即同意能力的有无),以及是否存在现实的、需要立即处理的紧急事由(即情势是否紧急)作为推定同意的必备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其将导致我国推定同意理论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从而将精神病人等亟待法律保护的人排除在外。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田国宝:《论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但是,将情事紧急、被害人须有承诺可能性等纳入推定同意的构成要素,无疑使该理论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难以实现其应有的现实价值,且如此界定有与紧急避险有混淆之嫌。推定同意与紧急避险在许多情形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并非同质,更不宜混同。众所周知,推定同意与被害人同意虽然相似,但区别明显:前者的同意是“拟制意志”,后者的同意则是真实意志。而推定同意与紧急避险关键区别在于二者正当化的基础不同,前者正当化基础取决于被害人 (即法益主体)的 “拟制意志”,后者基于一种客观利益的权衡。需要澄清的是,推定同意的正当化基础虽然基于“拟制意志”,但并不意味着客观的利益权衡在推定同意中无地位,只是该利益权衡处于辅助地位,为“拟制意志”服务而已。此外,笔者同意推定同意理论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但是将情势紧急作为推定同意前提要件,显然不当限缩了推定同意适用范围。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前述案例,我们不难得出:在特定情形下,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完全可以适用推定同意理论。具而言之,在下列要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推定精神病妇女的性同意,相对行为人的行为可以正当化。其一,适用对象须为不能表达性同意的精神病妇女;其二,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应当有利于该女子的利益;②其三,推定应符合人们一般价值观念;其四,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相对人的初衷是善意的。
5 结论:“类型化处理模式”的立法前瞻
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立法不足造成的。虽然可以通过制定新的“司法解释”等方式解决,但为了使该问题得到系统和根本解决,笔者建议相关部门③对该课题进行充分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具体方式上可以立项资助专家学者、科研机构来完成,亦可以通过司法系统内部立项调研的形式展开研究。关键是要通过真实地实证考察,以详实准确数据分析为支撑,研究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案的司法运行现状,以及推定同意理论引入的可行性分析,等等。依笔者的见解,将来在修改刑法中,具体可在刑法分则第二百三十六条后增加关于与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推定同意的特殊规定。大致内容如下:与性防卫能力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论。但行为人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在对精神病妇女予以合理照顾过程中与其发生性关系,且对精神病妇女没有采取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手段造成伤害的,推定精神病妇女同意,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1]郭卫华:性自主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8.
[2]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339.
[3]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55.
[4]陈兴良: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91.
[5]车浩:论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6).
[6]张旭主编:英美刑法论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54
[7]德国刑法典[M].许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95.
[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M].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5.
[9]最新意大利刑法典[M].黄风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83.
[10]〔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67.
[11]〔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59.
[12]〔德〕汉斯·海 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66.
[13]马克昌.比较刑法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415-416.
[14]高维俭,李晓磊.奸淫精神病妇女案中的推定同意问题[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1,(4).
责任编辑赵继棠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9.020
D924.34
A
1004-0544(2015)09-0106-05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3YJA82003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课题项目(GJ2013D20)。
高维俭(1972-),男,湖南怀化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磊(1983-),男,河南襄城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