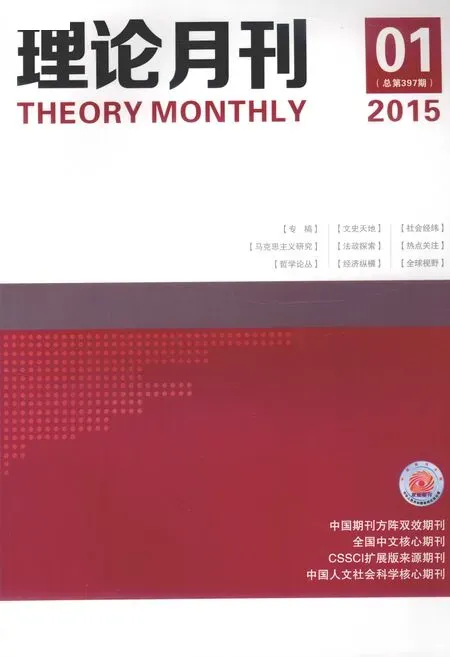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及其行动者研究
——基于越南、印度以及中国的比较研究
2015-03-17陆海燕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及其行动者研究
——基于越南、印度以及中国的比较研究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不同的轨迹和特点。这里基于政体和发展状况考虑选取越南、印度以及中国这三个国家为例对劳资关系的演进及各自行动者进行探讨,指出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中政党和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在劳资关系中注重追求工业和平,与此同时工会职能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自由化,劳资关系越来越追求灵活性,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劳资关系也日益关注,因此,国家也在追求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以维持稳定。从这些国家劳资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工会职能存在一定问题,应当加快改革,与世界接轨,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劳资关系体制。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行动者
劳资关系是一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反过来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里之所以选取越南、印度及中国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基于政体和国情以及劳资关系模型考虑:第一,中国和越南都属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并且都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第二,印度与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第三,这三个国家劳资关系表现了不同的模式。越南和中国属于劳动关系保护和工会自治欠缺型,印度属于劳动关系保护过度和工会多元化型。
1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的演进
1.1 越南劳资关系的演进
历史上越南一直是传统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例。据《2011年越南GDP和社会经济统计报告》,越南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48.0%,第二产业占22.4%,第三产业占29.6%,可见大量的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上。
1990 年越南通过的工会法赋予了越南工人罢工权,然而,行使罢工权有以下前提:工人在采取任何罢工行动前必须提前两周通知以提供时间进行协商;罢工权在有可能阻碍关键商业、影响公共生活和国家安全和防卫时不能行使,这些领域包括医疗、公共交通、公共用水和能源;公务员、军人和警察也不能罢工。[1]自允许罢工以来越南工人罢工现象越来越频繁,从1995年至2010年共发生3402件劳工罢工案,平均每年有213件,其中从1995年至1999年仅有307件,而从2000年至2005年已窜升至3095件,2006年后各年劳工罢工案件数亦不断剧增,参与罢工的劳工人数亦随之增加,同时劳工罢工的时间亦较长,且有漫延至其他企业的趋势。[2]罢工次数的高涨反映了越南劳工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实现,而法定的利益诉求渠道几乎不发挥作用。越南劳动法典规定,越南劳工总会附属的工会组织是集体谈判的代表。事实上,越南的工人罢工没有一次罢工是由工会组织和领导的,都是由工人自发发动,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罢工程序,属于非法罢工。所幸的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解决“非法罢工”,进而没有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在越南劳工的普遍的意识里,工会是行政机关,最多不过是作为调解人居中调解劳资纠纷,解决劳资冲突,没有人把工会看做是自己的靠山。[3](P179-180)在越南劳动者也没有真正的结社权利,越南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工人只能参加由越南劳工总会组织的工会。普通的工会会员没有积极参与工会活动,这意味着工作条件很少通过集体协议来谈判达成,工作条件多半是由管理部门通过一系列公司规则来单方规定的。在企业的层面没有工人的代表人,以及盛行未经工会批准的工人自发罢工,这些表明了越南关于集体协商的法律制度未能很好适应其经济的成熟期,制度结构未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不断变化的技术构成和人力资本。制定劳动标准和解决争端的过时做法,对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4]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越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稳定和进步”的劳动关系,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也在协助越南修改完善劳动法和工会法。越南劳资关系的发展仍然需要不断的革新改进。
1.2 印度劳资关系演进
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后,传统的最主要的纺织工业遭到打击,印度沦为典型的向宗主国出口初级产品的附属国经济。劳资关系上采用由英国移植过来的带有保护性的劳动法,这超出了印度生产力水平及工人生活水平,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投资发展,致使印度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难以发挥。
独立后的政府保留了殖民地时期带有保护性的劳资关系政策,寻求通过充分的劳动立法来控制工业冲突,这主要是受同政党密切联系以及在独立斗争中形成的劳工影响。在这一政体下,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许多方面受到了法律的规制,法律规定范围事无巨细,包括安全与健康、假期、解雇、临时裁员等,以避免潜在的冲突。劳资关系争议法案强制雇主只能在得到政府许可的前提下解雇工人,在解雇后180天内支付雇员一定薪水,在精简人员及工厂关闭时更需得到政府许可。争议处理办法也反映了这一行为暗含的逻辑:确保争议不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虽然罢工权存在,但它只有提前给出通知才能实施,而且当任何一方要求通过政府协商官员要求第三方干预时,罢工必须停止。如果协商失败,依据争议的性质,政府有权将争议移交到劳动法庭或工业法庭进行强制仲裁以作出最终的决策。关于劳动标准、保护雇员防止不公平解雇,人员精简以及工厂关闭的法律在理论上可以减少潜在的冲突。当有冲突发生时,争议解决机制能够抑制并解决。此外,考虑到社会安全立法的缺失以及政府保护雇佣的目标,一些社会政策如退休、医疗照顾以及一定程度的儿童照顾由雇主来承担。[5](P200)
这种以工人为中心的工业关系政策得到维持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家的进口替代(ISI)策略,这种策略强调高技术含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实行工业许可证制度、进口控制以及对外资企业施加限制以保护国有和私营企业免于国际竞争。因此,只要ISI策略存在,高成本和相对来说缺乏灵活性的工业关系规制并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印度的制造商不需要同国际市场竞争。对于制造商的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企业低效的增加。就劳资关系而言,这些低效率反映在国有企业劳动力过多以及私营领域不能够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或采用劳动成本控制的策略,因为这会涉及到劳动力减少,同时会带来罢工。而且,缺乏单一的谈判中介的立法造成了每个工作场所工会的多重性;工会彼此之间为了成员而展开竞争,使得雇主和工会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存在,从而导致了高度冲突的工业关系。因此,在这一阶段,虽然劳动争议的初始目标是为了给工人提供高程度的劳动保护并确保在雇佣上提供一定的稳定性并且避免冲突,但合作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产生。
1991 年印度的经济政策见证了巨大的转变,持续40年的ISI政策开始瓦解,采用了自由化的开放经济。这一经济政策转变的影响是剧烈的,一夜之间,印度的经济受到了国际竞争的威胁,但印度企业并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压力导致了对劳资关系政策的巨大争议,也对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进行了转移。考虑到来自雇主和世界银行要求允许“退出政策”(允许雇主减少雇员或关闭工厂)的压力,劳资关系立法改革提上日程,成立了三方委员会,以建立一个安全网为被解雇工人提供再培训和解雇赔偿金。总的来说,随着印度融入全球经济,印度的劳资关系从维护劳工和平转向了通过增加灵活性来提升企业竞争力。
1.3 中国劳资关系演进
改革开放前,中国劳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处于稳定平和期。劳资关系稳定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以及为了便于对城市工人的控制,实行的是单位制。当时的国有企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企业组织形式的独特的组织形式,是集政治、经济与行政于一体的组织,不可能存在倒闭破产。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来说,企业雇佣是终身的,而且企业也为职工提供了包括教育和住房在内的福利,职工以单位人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全国总工会早在1925年就成立,但它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会法明确地对工会作用进行了规定:“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是组织群众和政党之间的传送带”。因此,虽然工会扮演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传送带的角色是最核心的。
中国的劳资关系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开始有自主权经营企业以赚取利润,政府减少了集中化的工资决定以及工作分配,允许以短期合同雇佣工人,允许企业追求同其竞争地位一致的人力资源策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合资企业数量增加,特别经济区遍布全国。随着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倒闭以及转制浪潮,下岗工人急剧增多。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各地政府极力打造廉价的、驯服的、稳定的劳动大军来吸引外商投资,外资尤其是港澳台企业以低成本为其竞争优势从而剥削工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急剧上升,劳动争议的发生率快速上升。
为了解决劳资冲突以保证工业和平,中国政府逐渐增强劳动领域的立法,1994颁布了新《劳动法》、2001年对《工会法》进行了修正、2003年通过了《集体合同规定》、2008年出台了《劳动合同法》、2013年对劳动合同法又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加快官方工会的普及率,要求每个企业建立工会,尤其是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建立工会以及农民工工会,目前工会普及率已达90%以上。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制度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采取了法团主义策略,在制度上克隆了三方主义,即提倡工资集体协商。赋予工会同雇主就一系列议题包括工资和工作条件等进行集体谈判,同时也要求雇主支持工会活动。[6]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劳资关系进入了良性轨道。应然上来说,三方机制若想发挥制度上的作用,必须存在能够表达其代表团体利益和观点的集体行动者。然而,这一条件在工会和雇主组织两个层面上都是欠缺的。这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工会与上一级工会的脱离,企业工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仍有待提升。
2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演进中的行动者
2.1 越南劳资关系中的行动者
越南的政治状况决定了越南政府在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中的全能型角色,在越共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劳资关系,而且很容易形成对工会的控制。为有效监控这种工会体制,政党一般会委任一些成员积极参与工会。但另一方面,越南政府对工人和工人运动较为包容。当野猫式罢工发生时,地方劳动部门常常派遣协调员去对罢工进行调查并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以解决罢工。政府的干预倾向于通过指出工人的合法权利受到雇主的侵害使工人的行动合法化,并劝说雇主接受罢工者的合法要求。[7](P418)
越南的工会由于特殊的殖民抗争历史,在成立之初就带有某种政治性,其组织功能和目标均发生偏离。当下越南工会在国内的主要活动是:教育和动员会员及工人执行并完成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和任务,维护职工队伍政治上的稳定;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和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完成生产计划;同国家机关和企业领导一起努力保障职工的工作岗位,尽力减少下岗人员,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困难。[8]可以看出越南工会实际上充当的是政党意志通过国家得以执行的辅助性组织,工会组织职能缺失和功能失效与执政党和政府对工会的严厉管控有直接关系。越南宪法和工会法都规定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社会组织,是劳动者和劳动者集体的唯一代表组织,自由工会被禁止。这样,当现任工会领导工作不力时,工人没有办法另行成立工会取而代之。[3](P180-181)但随着工人罢工的增加,工会也意识到其代表性危机,从而在罢工中越来越站在工人一方。地方工会干部在罢工中一般陪同政府协调员进行调查,对工人抱有同情,并对管理层施压以接受罢工的合理要求,同时说服工人回去工作。国家以及地方层面的工会在罢工中有时也会公开站在罢工者一边,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并要求改进。[7](P418)
越南普通工人展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自发的团结性,在法定的框架外通过组织良好的罢工行动保护及提升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从罢工都是由工人自发发动而非由工会带领上显现出来,这表明越南工人有着更大的组织能力通过集体行动来动员和团结。究其原因,虽然越南的罢工权受一系列繁杂程序的限制,但法律对罢工权的认可有助于使工人集体行动合法化,消除政治上的敏感和恐惧。[7](P419)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来自国际层面的力量也对越南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影响,尤其是来自西方购买者“行为守则”的影响。遵守行为守则的趋势来自西方国家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6年的顾客和工会发起的抵制耐克工厂以批评越南分包商工厂里的劳动实践。作为对顾客和劳工团体抗议的回应,西方采购者开始要求他们的分包商严格遵守行为守则。为了确保这些守则的实施,许多大型的采购者雇用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承包商工厂里的劳动实践。
2.2 印度劳资关系演进中的行动者
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过度保护工人的劳资关系政策被独立后的政府继承下来,印度本来希望建立一种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劳资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尝试非但没有起到帮助工人的作用,还阻碍了经济增长并增加了贫困,这种阻碍对穷人的影响更为显著,导致城市的贫困率上升。[9]印度复杂的民族、宗教以及种姓制度要求强有力的政府维持社会稳定运行,但政府的高度管制也致使印度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市场成二元状态,即保护政策只有在国有经济部门和大企业强制实施,而小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劳动者则成为保护性政策的“漏网之鱼”,面对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的状况,这些企业部门的劳动者只能接受低工资和缺少劳动保障的劳动待遇。自由化改革之后,政府角色做出了转变,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开始与企业合作,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这使得管理者和雇主对解雇工人的控制权力越来越大,而且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政府一再修改劳工立法,反对罢工权,允许雇主随意解雇工人,还要修改工会法,阻挠工人参加工会,这使工会活动更加困难。[10]
在印度,工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且附属于政党,这使得工会不仅能通过政党在国家层面对与劳工相关的议题进行输入,而且能促使有利于工人的保护性立法的出台。工会的成立、认可和功能都受到法律的良好保护,谈判高度分权。[11]这源于印度工会最初的成立是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非出于维护工人利益,因而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但这在给有组织的工人以相当程度保护同时,对于效率和工作场所灵活性的发展不利。例如,允许工作场所存在多个工会导致了工会内部强烈的竞争,从而阻碍了工人和管理层之间长期合作的发展。此外,雇主没有政府许可下无权解雇、裁减员工以及关闭工厂导致了低效。更为显著的是,工会的政治化以及派遣外部人员作为企业工会领导的做法给工作场所工会活动带来了政治考量。因此,这是以牺牲效率和灵活性为代价保证平等和保护。[11](P17)1990年经济自由化后,劳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雇主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竞争,在劳资关系上变得更具侵略性。在一些关键产业和公司,由于雇主通过自愿退休和外包减少了正式人员数量,从而使工会成员数量下降。另一方面,工会与其传统联盟——政党——之间也产生了分裂。工会反对经济自由化,然而所有政党都支持经济自由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在地方层面对劳动法进行修改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导致了新的雇主——政府联盟,政府逐步站在雇主这一边。明显地,竞争逻辑在印度不断增强,而且制度环境对工会越来越不利。[5](P201)
2.3 中国劳资关系演进中的行动者
对中国劳资关系的观察脱离不了工会与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社会组织,工会如想获得影响力,同政党和政府发生联系是符合逻辑的和自然的。在中国,同党和政府保持联系也有利于采取统一行动,增强工会的力量,开展工会活动。但问题在于工会同政党和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很难将工会脱离出来作为一个自治的社会组织来看。从财政上,工会在经费上也依赖政府拨款。没有政府的拨款,工会能否正常运作是值得怀疑的。人事和经费上的依赖性,致使工会定位上更像政府的一个部门。
早在革命时期,工会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就结成了联盟,共同合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全国总工会也得以成立,其职能由1950年所颁布的工会法所规定。事实上,1966年之后,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团体已经消失了,直到1978年才开始得以重建。一方面,党对工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政党和政府给予了工会更多的政策制定的权限,但后者必须支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政党和政府也意识到工会在快速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官方工会的地位也得到提升。而企业工会在获取工人忠诚和合法性存在困难,被看作企业的“次级伙伴”,对于工资、雇佣条件或帮助工人解决诸如失业、住房和寻找工作等问题上作用不大。[12]
工人和雇主随着经济的转型也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工人用其政治合作换取相对有利的待遇,而且当时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从而没有所谓的劳资关系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改制,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引入,工人丧失了原先的地位和待遇。工人的自我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慢慢被激发。当工人权利受损时,不再象以前一样默默承受,要么采取弱者的反抗,即怠工、暗中破坏等,要么直接走上街头,集体表达抗议和不满。同工会组织一样,雇主组织在中国主要以企业家协会的形式存在,在三方谈判中作为雇主一方的代表。但企业家协会作为雇主的法定代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试图以一个组织来代表中国所有企业是不现实的,因此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其它的雇主组织,如全国工商联、中国外资企业投资企业协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等。虽然企业家协会试图成为所有企业的保护伞,但每个组织都享受其在自身领域内的垄断地位。[7](P420)
3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演进的特点
3.1 政党和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从这三个国家劳资关系的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三个国家的工会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工会附属于政党,工会的成立、地位以及职能都是由政党通过法律认可的,在政党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能够影响国家政策议程。这一点在越南和中国尤为明显,工会都处于执政党的领导之下,是党的助手。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在劳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2 劳资关系追求稳定性和灵活性
在这三个国家中,劳资关系最初的目标是维护劳工和平,即工业稳定。对这些政府来说,稳定是引进外资从而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立法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当然,这三个国家追求稳定性的策略不同。印度最初主要是以保护工人权益来维系工业稳定,越南和中国则是对工会尤其是企业工会功能发挥进行制约来实现。越南政府在表面上虽然支持罢工,但本质上政府是不希望劳工运动过于强大以至于吓跑外资的。
虽然稳定是这些国家劳资关系首要的关注点,但随着全球化以及经济自由化的推进,劳资关系越来越体现灵活性。国家赋予了企业和雇主越来越多的裁员、下岗以及解雇等灵活用工的权力,非正规雇佣和劳动外包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3.3 国家在劳资关系中追求保护劳工合法权益
尽管在劳资关系中追求灵活性,这些国家同时也追求对劳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在越南,政府对于工人的野猫式罢工持中立态度,并不断加强工会改革以提升。在印度,为了减轻企业重构对员工就业负面影响,政府于1997年建立了国家更新基金委员会对工会提供咨询和培训。虽然政府在2001年宣布改变劳动立法以倡导工作场所灵活性,但这并没有在议会进行讨论和得到批准。相反,政府通过了增加额外福利的政策,以维护劳资关系稳定。[5](P202)在中国,1994年通过的的劳动法赋予了工会集体谈判权,并对工会提供财务支持(每个企业必须将员工工资总额的2%划拨给工会作为经费),制定了工作场所的相关劳动标准。2008年顶住各方压力通过了《劳动合同法》,2014年又通过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以对劳务派遣用工进行规范。总之,政府近二十年来的立法都表明了政府希望能保证劳工合法权益的目标。
3.4 工会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
在这三个国家里,工会功能未得到发挥而且碎片化。在越南和中国,工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隶属和依附于政党。工会客观上来说是政府部门而不是社会组织,代表缺陷是两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在印度,情况有所不同,工会在独立前就存在,许多工会领导人同英国斗争争取独立。在独立后,这些领导人成为印度政坛的重要人物。因此,工会有政党的支持,他们财政上独立,而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它们。但印度允许多元工会的存在,一个企业常常存在多个工会,因而是碎片化的,这是不利于劳工团结和工会发挥作用的。
3.5 全球范围内对于跨国劳工议题的关注日益涌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同时,劳工议题也日益跨出一国范围内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反血汗工厂运动和生产行为守则运动的兴起,在传统的包括国家、雇主和劳工的三方结构的劳资关系中引入了新的一方。许多发达国家也日益对后发国家的劳权表示关注,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状况进行评判和干预。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的发展除了立足本国国情之外,还须接受来自国际层面力量的冲击。
4 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的启示
4.1 加速工会改革,加强工会认同
上述三个国家工会在现实运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当然三个国家问题不同。中国和越南工会问题在于其对政党和政府的依附性,印度工会虽较独立,但过于碎片化。针对这些问题,工会应加快改革,以提升其认同度。中国和越南工会应回归其社会性,与政党保持联系虽然正常,但不应过度依赖。工会在人、财、物上都应摆脱对政党和政府的依附,走向独立。当然,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印度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制度过于超前反而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尤其对中国来说,工会的发展路径可以采取三步走的策略,首先是加强工会职能,即在获得政党支持和认可下,扩大工会职能,增加工会提供工人福利和保障方面的职能,以加强工会的社会认同;第二步则是加强工会的自治性建设,即在同政党保持联系的情况下,注重工会同党和政府相对分离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建设;第三步则是工会回归社会组织的本质,回归其自治独立的地位,作为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社会组织而存在。
4.2 劳资关系的发展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
自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世界发展报告》涉及劳工和雇佣议题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会在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已成为国际议题,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劳资关系与工人状况关注也越来越密切。因此,在劳资关系的发展中,一方面要注重本国劳工标准与世界劳工标准的接轨,从而避免受到他国的指责和抵制。另一方面,工会也应加强国际交流,政府也应乐于就劳工标准进行国际对话。来自国际层面的影响力量,对劳资关系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4.3 劳资关系的确立要注重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随着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劳资关系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取得一个稳定和灵活的工业关系体系,以满足双重目标:效率和公平。纯效率模型会长期镇压劳权从而导致工业关系的冲突和不稳定,弱工会也不能参与工作场所决策。纯公平模型颁布过多的劳动规章制度从而阻碍了工作场所灵活地根据环境变化。印度劳资关系发展初期保护过度,过于注重公平从而损害了灵活性和效率,中国和越南在劳资关系发展初期过于注重效率从而牺牲了劳工的权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条件下,新的竞争环境要求更为灵活劳资关系的支撑。劳资双方不能维持在此消彼长的一方压倒一方的状态,而是要发展出兼具公平和效率的劳资关系模式和解决劳资争议有效途径。
[1]ZhuYing,StephanieFahey.TheImpactof Economic Reform in Industrial Labour Relations inChinaandVietnam.Post-Communist Economies.Vol.11,1999,No.2,P183.
[2]经济部驻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商务组.越南从1995年至2010年共发生3,402件劳工罢工案[N].越南经济时报,2011-06-06(5).
[3]吴远富.越南企业劳资关系状况及工会法的修改[J].河北法学,2011,(8).
[4]Christ Manning.Glob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s inBoomandCrisis—theCaseof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27,No.1,2010,P136-38.
[5]Sarosh Kuruvilla and Christopher L.Erickson.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Asian Industrial Relations.Industrial Relations.Vol.41,No.2,2002.
[6]Sarosh Kuruvilla,Subesh Das,Hyunji Kwon and Soonwon Kwon.Trade Un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Asia.British Journal of Indusrial Relations,Vol.40,No.3,2002,P446.
[7]Chang-HeeLee.RecentIndustrialRelations DevelopmentsinChinaandVietNam: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East Asian Transition Economies.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48,No.3,2006.
[8]张国峰.越南工会工作掠闻[J].工会理论研究,2009,(6):42.
[9]〔英〕提莫西·贝斯利.劳动力市场监管对经济发展的阻挠——来自印度的证据[J].比较,2006,(26).
[10]张淑兰.全球化背景下的印度工会[J].南亚研究,2011,(1):54.
[11]Saroh Kuruvilla and C.S.Venkataratnam.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the Case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Industrial Relations Jounal.Vol.27,No.1,1996.
[12]GordonWhite,ChineseTradeUnionsin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owards Corporatism or Civi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34,No.3,1996,P437.
责任编辑 王友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35
F246
A
1004-0544(2015)01-0183-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CZZ014)。
陆海燕(1979-),女,湖北咸宁人,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