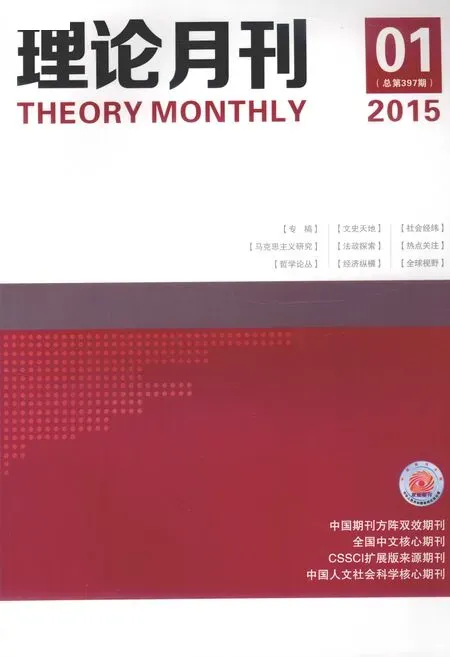什么是有效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
——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2015-03-17邱少春崔兵
□邱少春,崔兵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管理系,湖北武汉 430068)
什么是有效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
——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邱少春,崔兵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管理系,湖北武汉 430068)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作为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的政府分权体系中的制度子集,其选择服从于实现激励相容的目标,有效的金融分权具有与制度环境和互补性制度安排相容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安排,而是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中国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转化是政府对激励目标和激励制度调整的制度因应,而不是对“分权至上”的盲崇。
金融分权;有效分权;中国式分权
1 引言
“中国式分权”,即经济分权与集中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相结合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原因(Blanchard,Shleifer,2001;付勇,张晏,2007),钱颖一(Qian and Rolan,1998)认为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结合的“中国体制”硬化了地方政府的约束,因为“做对了激励”(getting incentive right)而演绎了迄今完美的“中国故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央地”关系无疑在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做对激励”尤其是“做对政府激励”便具有了极端重要性,“中国式分权”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安排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激励。[1]进一步打开“中国式分权”这个“黑箱”,我们发现“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涉事甚广的系统问题(cross-cutting issues),是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bundles of inventive),是一个包含多项激励装置的“工具箱”。金融集权或分权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安排进入“工具箱”,并服从于政府实现激励相容的目标,由此可见,对金融集权或金融分权有效性的判定不能脱离金融制度所在的“激励束”,对单独“切割”出来的金融制度进行“孰优孰劣”的判断可能会误读真实世界的金融现象。
本文将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界定为一种激励制度安排,基于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评判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并将其置身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分析金融集分权与“激励束”中互补性制度安排相互融合实现政府激励相容的“中国故事”。
2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无非是要确定有效性的判别标准。由于将金融集分权界定为政府间的一种激励制度安排,便会顺乎逻辑的运用经典激励理论确定的激励相容标准判断其有效性。然而,下文的分析表明经典激励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其难以对“真实世界”中金融集分权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进行合理评判,对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有效性的评价必须结合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以作为制度安排集合“激励束”的制度结构的相容性为标准。
2.1 经典激励理论分析的局限
经典激励理论基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考虑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环境以及代理人面临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设计激励合同以通过代理人的行为满足委托人的目标追求。具体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激励问题的分析,往往运用多任务或多代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相应激励机制设计,以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其难以对作为一种激励制度安排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进行客观分析。
首先,经典激励理论委托人的目标函数是既定的,是在给定委托人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分析委托代理问题。但是“真实世界”中金融制度的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会依据其需要实现的金融功能设计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基于默顿和博迪(Merton and Bodie,2005)的金融功能和结构观(Function and Structure Finance,FSF),金融功能是金融分析的“基点”(anchor),多样化的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制度变迁的目的不过于有效地实现金融功能。虽然金融的核心功能可以高度概括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跨越时空配置金融资源,但这一核心功能中的储蓄动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清算和支付结算、企业监控及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Merton and Bodie,1995;Levine,1997)[2]并不总会进入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而且在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基本功能中各种功能的重要性也会存在差别。言下之意,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会根据政府在金融功能中的担当发生变化,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选择必须致力于政府金融功能的实现。
其次,经典激励理论并不考虑激励机制的成本。任何激励机制在实现激励目标(获得激励收益)的同时必然付出激励成本,满足激励相容标准的激励合同即使是完全契约(现实中所有契约都是不完全契约),也仍然存在交易费用。[3]一项激励契约涉及的交易费用存在于签约、执行及监督的各个环节,包括信息搜寻费用、签约费用、谈判费用、公证费用、再谈判费用等多项费用。特别是政府内部激励机制的实施会由于目标函数中的多任务和异质性的多代理人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委托代理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可能需要付出高额的制度成本。因此,综合考虑激励机制的激励成本后,原本“最优”的激励方案可能成为收益成本对比后无效率的方案。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选择同样要考虑制度成本,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激励收益和激励成本综合比较的基础上。
最后,经典激励理论未考虑激励制度的“不可分性”。经典激励理论习惯于将某种激励机制“割裂”出来,单独考察其激励效果。但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提供给代理人的激励契约并不是由单一的契约或激励工具构成的,往往是多个契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或多种激励工具集合成的“激励束”。“激励束”中各项激励制度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并依靠制度“合力”实现激励目标,因而对单一激励契约有效性的判定不能无视激励制度的“不可分性”。如此意味着在一种激励制度组合中,不能只看单个的激励契约或激励工具是否有效,而要看它们组合起来是否整体有效。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束”中的制度子集,对其有效性的判定不是基于金融集分权自身的效率,而是基于其所在的“激励束”的整体效率。
2.2 制度金融学的分析
制度金融学认为“金融制度非常重要”,金融制度的创新和竞争能够最大限度增进实现金融功能的效率(Merton and Bodie,2005)。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的激励功能,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激励制度安排。给定金融功能,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依赖于金融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决定的金融制度“激励束”的整体有效性。因而,制度金融学对金融集分权有效性的判定标准是金融制度结构的相容性而不是单一激励机制的激励相容标准。
金融集分权有效性的判定不能脱离金融功能。设计金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执行金融功能的效率,给定一定时空条件下政府需要实现的金融功能,金融功能就会进入政府的目标函数并成为金融制度选择的依据。[4]任何金融制度在实现金融功能的过程中都存在制度成本,因此并不存在“绝对占优”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选择体现在二者实现不同金融功能时具备的“比较优势”,只有与金融功能相“匹配”的金融制度才是有效的。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集权的金融体制更有利储蓄动员和长期项目的投资,而分权的金融体制则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短期项目投资上具有优势。纵然金融功能相对金融制度具有稳定性(Merton and Bodie, 2005),但是政府执行的金融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还必须具有与金融功能演进相适应的适应性效率。由此可见,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不仅表现为实现既定金融功能的静态效率,还表现为适应金融功能变化的动态效率。
金融集分权有效性的判定不能脱离制度环境。金融制度安排固然要与金融功能相适应才能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由金融功能派生的金融制度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还受制于金融制度供给,当制度供给的成本超过满足制度需求产生的收益时,与金融功能并不相适应的“次优”的金融制度同样成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金融制度是由制度集合构成的政府分权体系“激励束”中的制度子集,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选择毫无疑问受制于“激励束”的束缚,而“激励束”的构成则取决于比制度安排层级更高的制度环境。由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形成的制度环境会决定“激励束”中各种激励制度和激励工具的组合,并划定组合的制度可能性边界,金融制度的选择难以逾越组合的范围和边界。由此可见,制度环境决定的“激励束”构成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制度选择的约束条件,与制度环境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的制度安排。
金融集分权有效性的判定不能脱离关联性的制度安排。激励制度的“不可分性”意味着“激励束”中所有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受制于关联性制度安排的牵制。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集分权本身,而在于其能否与关联性制度安排形成制度“合力”,实现“激励束”整体有效。“局部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如果不能与关联性制度安排形成有效互补,反而会损害“激励束”的整体效率;反之,“局部无效”的金融制度安排也许是为增进“激励束”的整体效率而付出的激励成本。“激励束”中制度安排的互补性,意味着某一单项激励制度或激励工具与其他关联性制度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孤立改变单项激励制度的做法都是“无效率”的。构成政府间激励制度安排的“激励束”往往是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精巧的制度集合,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体现为与关联性制度安排塑造的制度结构的相容性。
3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有效性:“中国式分权”的经验分析
认可“中国式分权”演绎了成功的“中国故事”的理论结论,便不应该忽略该进程中金融制度扮演的角色。基于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本节结合“中国式分权”过程中金融集分权演变的特征事实,对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进行经验分析并对实施有效的金融分权提供建议。
3.1 “中国式分权”中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国有金融企业为主体的金融制度安排,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一直广受主流经济学的诟病。无论是研究发达经济体还是研究欠发达经济体金融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揭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icks,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 Shaw,1973)。虽然Allen(Allen,2005)和Rajan and Zingales(Rajan and Zingales,2004)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系统并不发达但却获得快速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但仍然没能纠正其对中国金融制度“滞后无效”的片面判断。研究“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将中国式分权简单定义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以财政分权代替经济分权,没有发现经济权力分割内部至为重要的财政、金融等要素配置权力的集权、分权的组合和演化。钱颖一(Qian and Rolan,1998),丁骋骋、傅勇(2012)注意到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结合的“中国体制”因为硬化了地方政府的约束而成就了“中国故事”,但并没有对金融集分权制度的有效性进行直观判断。[5]无论是对中国金融制度的固有偏见还是对“中国式分权”中金融制度作用的忽视,都源于现有文献只是孤立研究金融制度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背景下金融制度与整个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的互补性和互动性,没有从制度关联的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的“中国故事”,也难以对金融集分权制度的有效性做出合理评判。
“中国式分权”中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表现为金融制度与金融功能的融合。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制度选择是政府实现金融功能的制度设计,金融功能是中央政府确定激励机制目标函数的依据,中国金融集分权制度的安排体现了有效实现政府金融功能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大都奉行追赶发达国家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国家稀缺的金融资本服务于赶超目的,由此决定该战略下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资源动员而不是资源配置。为此,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或者隶属于财政部,形成了“大财政、小金融”的格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的金融结构,并在银行内部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中央政府通过金融集权和对垄断性国有金融企业的控制,确保金融制度动员储蓄功能的实现。即使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由于政府的赶超战略并没有遗弃,因此储蓄动员仍然是金融制度的首要功能。而且集权垄断的金融制度相对纯粹市场金融制度在控制存单提供成本与扩展储蓄规模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张杰,1998),选择集权的金融体制显然有利于金融功能的实现。[6]
“中国式分权”中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表现为金融制度与制度环境的融合。威权的政治体制和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是金融制度设计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该制度环境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组织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授权”(delegation)关系。威权政治体制普遍存在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父爱主义”极易形成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因而无论是有效的分权体制(Weingast,2006)还是地方政府有效竞争的制度条件(Litvak,1998)都离不开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的制度设置,金融制度的选择也必须有利于克制软约束导致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7]金融制度作为社会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深刻地体现着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金融制度必然是一种高度集权、计划配置资金、组织结构单一和高度行政依附型的金融制度。以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的计划金融制度集各种金融功能于国家银行制度,大而统的国家银行制度构成传统金融制度结构的全部。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带来金融制度的变革,与转型经济体制相适应以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为特征的金融集权因为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金融剩余”并防范“日益自利”的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攫取”,因而是“暂时”有效率的或至少具有效率增进的意义。
“中国式分权”中金融集分权的有效性表现为金融制度与关联性制度安排的融合。“中国式分权”能够成为演绎成功的“中国故事”的制度因素,关键在于其“激励束”中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造就了激励相容的制度结构。一方面,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形成互补性制度安排,通过建立“锦标赛”式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有利于中央政府意志的贯彻。另一方面,在经济分权内部,至为重要的财政权力和金融权力实现有效互补硬化了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政府整体财政支出的比例日益扩大,财政支出分权化趋势明显;同时,从财政收入角度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日益提高,财政收入集权化趋势明显。为防范地方政府通过金融方式举债填补财政能力不足,中央政府设计了与财政分权互补的金融集权制度安排。孤立评价金融集权制度很容易发现其“无效率”,但是将其置于“激励束”中我们发现尽管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金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自己(金融压抑)来承担着某些财政功能(周立,2003),正是金融的“牺牲”换来了“激励束”的整体效率,金融本身垫付“激励成本”有效降低了“中国式分权”的整体制度成本,满足了制度结构的相容性标准。[8]
3.2 实施有效的金融分权
认识到“中国式分权”产生的“为增长而竞争”的负面效应,当下理论界开始反思“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伴随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及金融对民间资本的开放,政府间金融分权化改革似乎势在必行。“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实现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分权已经作为改革政策进入政府决策者的视野。但由上文对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制度有效性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可知,对金融集分权的改革不能局限于金融视角,必须将金融制度置于整个政府激励制度的“激励束”中进行考量和评价。有效的金融分权必须与政府金融功能相调适,并与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相适应。
实施有效的金融分权是适应政府金融功能调整的需要。基于转型后期“中国式分权”目标由效率性分权向公平性分权的转化,政府金融功能也相应从动员性金融向效率性金融和普惠性金融转变。与传统集权金融制度共存的金融管制、国有金融垄断及政府隐性担保制度正在逐渐向金融市场化、多元化和显性担保制度改变。政府要实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普惠的金融功能,需要实现金融集权到金融分权的制度变迁,因为分权的金融制度相对集权的金融制度在实现上述金融功能时具有“比较优势”。金融市场化和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改革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体多样化、差异化金融需求的出现,需要更具信息优势和更能了解金融需求偏好的地方政府担当金融功能。此时,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实现金融功能的制度成本,提升实现金融功能的效率。
实施有效的金融分权必须注重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的整体协调性。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式分权”激励制度集合的子集,金融集权到金融分权的制度变迁需要“一揽子”制度安排的协同推进,“单兵突进”的金融分权改革不仅无助于金融功能的实现,甚至有损于“激励束”的整体效率。“文化渊源决定着一国交易成本的‘禀赋'或者初始结构,或者说,一国的交易成本(以及组织成本)结构具有某种程度的‘先天性'和外生性”。(张杰,2012)如果一国的制度禀赋中“先天性”的具有对政府的偏好,无疑有利于选择集权的金融制度;反之,如果一国制度禀赋中“先天性”的具有对市场的偏好,则会有利于分权金融制度的建立。[9]中国长期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金融集权到金融分权的改革需要意识形态和非正式制度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金融分权为地方政府利用金融资源提供了“合法通道”,如果目前整个金融体系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信用制度不作调整,金融分权就会进一步软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导致中央政府设计的激励制度失效。因此,金融分权改革必须与关联性制度安排互补联动,形成有利于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激励束”。金融分权改革只有满足与关联性制度安排构成的制度结构的相容性标准,才是有效的金融分权。
4 结论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制度的选择体现了金融制度服务于金融功能的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制度安排是由诸多激励工具构成的“激励束”,金融制度安排作为“激励束”中的制度子集,其有效性表现为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效率以及与关联性制度安排形成的制度“合力”。“中国式分权”中金融集分权制度的选择有助于转型期政府金融功能的实现,并满足“激励束”中制度结构的相容性标准,因为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演绎了成功的“中国故事”。伴随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引致的政府金融功能转变,要求金融制度安排随之调整。目前,实施有效的金融分权需要对金融集权制度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和关联性制度安排进行整体变革,孤立推进金融分权化改革不仅面临高昂的改革成本,而且会损害“激励束”的整体效率,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
[1]钱颖一,GérardRoland,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1998,88(5),P1143-1162.
[2]RobertC.MertonandZviBodie,Designof FinancialSystems:TowardsaSynthesisof Function and Structure[J].Journal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Vol.3,No.1,(2005),P1-23.
[3]吴军,何自云.金融制度激励功能与激励相容度标准[J].金融研究,2005,(6).
[4]〔美〕兹维·博迪,罗伯特·默顿.2000:金融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丁骋骋,傅勇.地方政府行为、财政—金融关联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6).
[6]张杰.何种金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转轨中的储蓄动员与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1998,(12).
[7]Jennie Litvack,Junaid Ahmad and Richard Bir,RethinkingDecentralizationinDeveloping Countries[R].The World Bank,1998.
[8]周立.改革期间中国财政能力与金融能力的变化[J].财贸经济,2003,(6).
[9]张杰.交易成本、法律传统与金融制度边界的决定[J].财贸经济,2012,(2).
责任编辑 梅瑞祥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22
F830.2
A
1004-0544(2015)01-0112-0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YCJ790021);湖北工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BSQD12083)。
邱少春(1977-),女,湖北恩施人,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管理系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崔兵(1974-),男,湖北恩施人,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博士后创新基地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