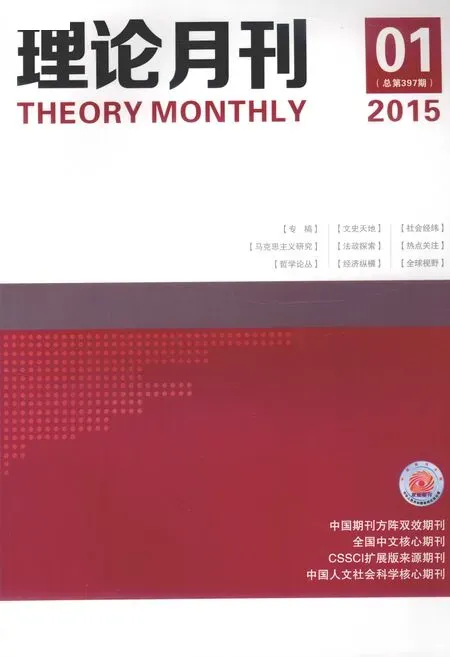试论荀子的诚信思想
2015-03-17刘乾阳
□刘乾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试论荀子的诚信思想
□刘乾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之一,这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得益于儒学在中国长期的主导地位。儒家学者非常重视诚信道德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以性恶论为基础,荀子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屡次强调诚信之于统治的重要性。荀子的诚信思想还与他特别重视礼义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礼义是诚信的前提,没有君臣之分,也就不会有君主作为诚实守信的楷模去构筑起社会整体诚信的良好风气。可见,荀子的诚信思想具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荀子;性恶;诚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之一,它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从个人内心诚意的修养到与朋友、乡党交往言而有信,从统治者好信而民众信服到国家间盟誓与用兵的戒欺守信,从学以忠信为本到经商童叟无欺。可以说,诚信这个德目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它规范着中华儿女的个人化和社会性的行为,力图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维护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
1 诚、信与诚信
根据现有的出土资料,“诚”、“信”二字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但在商周时代的金文中已经出现了“信”字。相对于“信”字来说,“诚”字出现得更晚。并且,春秋以前的文献中信字较多见,而“诚”字相对偏少。在后世学者对于先秦典籍的训解中,他们往往用互训的方式来解释“诚”与“信”。班固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说文解字·卷三·言部》)“诚,信也。从言成声。”(同上)这种训诂的方式虽然有利于我们理解“诚”、“信”的含义,但也容易导致对二者之间差别的忽视。实际上,“诚”、“信”二字的含义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
“诚”应当是一个较为晚出的概念。在已经可以识别的甲骨文、金文中,并没有“诚”字出现。在《尚书·太甲下》中“诚”字已经出现,但《太甲》篇一般认为是后人伪作。另外,在今本《尚书》中“诚”字只出现一次,属于孤证。因此,这一条不应成为“诚”这一观念已出现在商周时期的证据。
在金文中,“信”是一个会意字,由“言”和“身”构成,这表明在创造此字之时,先民们赋予了它“以言立身”的隐含语义,它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左传·桓公六年》载隋国大夫季梁语:“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旧有的朴素和谐的社会氛围被打破,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经过儒家学者的提倡,信开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概括来说,“信”的主要含义是指人在社会交往中要恪守自己的诺言,要努力做到言行一致,诚实不欺。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诚”与“信”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两者是互相贯通,互为表里的。二者追求的都是实,即真实、实在、真心实意,这也正是有些学者将二者进行互训的原因。但是,二者又存在着区别,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点:(1)“诚”主要从内心上说,侧重的是内心的修养;“信”则侧重于与人交往时言而有信,遵守信用。(2)“诚”是实质,“信”是表象;“诚”是“信”的内在根基,“信”则是“诚”的外在表现。(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诚”可以被看作是对道德主体的单向要求,而“信”具有普遍的规约性。(4)很显然,“诚”的哲学化、形上学化色彩更为丰富,并且在儒家哲学中它的位阶更高。
现在回到我们所主要讨论的“诚信”一词。既然“诚”、“信”两种观念互相贯通,所以二者合称从而作为一个复合词来使用、作为一种德目来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现代意义的“诚信”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我们还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但从先秦时期开始,“诚”与“信”就开始连用,例如《管子·枢言》云:“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荀子·不苟》有“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之说,《礼记·祭统》有云“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商君书·靳令》则把诚信看作是祸国殃民的“六虱”之一,《盐铁论·世物》里多次出现“诚信”一词。其中,《管子》、《礼记》较为晚出且经过后人大量加工,那么在现有材料中,《荀子·不苟》篇似乎是“诚信”最早出现的篇章。对此,下文论述荀子的诚信思想时,我们将进一步地说明。
2 性恶论前提下的荀子诚信思想
古代的圣哲贤人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并将诚信规约为一种政治之道、交友之道与处世之道。虽然中国古代各家各派都很重视诚信之道,但归根结底使诚信思想开始成为一种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还是要数先秦的儒者们。孔子对于诚信的论述散见于整篇文献之中而无完整的体系,但他的诚信思想涉及到从个人修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诚信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将之前诚信思想的潜流开掘出来并使之显性化。从此,儒家的诚信思想基本就在这样一个有些不太完整的体系之中发展演化。可以说,孔子的诚信思想“不仅是我国儒家诚信思想的源头,也是我国伦理哲学的重要内容,它的精神己经嬗变成中华文明的内核之一,永远奔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之中”。[2]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孟子的诚信思想凸显了由内心而发的“诚”的重要性,而将“信”作为五伦之一的定位则进一步提升了信在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孟子的仁政思想所体现出的取信于民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座丰碑,而“惟义所在”的原则为人们践行诚信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正当之路。荀子的诚信思想则是建立在他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学说之上,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如果说孟子主要倾向于从人的内在性上讲“诚”的话,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则由天道以言人事,倾向于从外在政事上强调“诚”的重要性。荀子认为,“诚”是天地四时最为重要的本性,“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不苟》)进而,“诚”对于天地化育万物,对于圣人之化万民,对于处理父子关系,对于树立君上的权威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同上)所以“诚”是君子应该坚守的道德品质,也是国家政事之本,“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同上)可以说,“诚”连接了内圣与外王,是由内而外的逻辑进程。就君子的道德修养而言,君子以仁义为本,“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同上),但仁义必须以“诚”行之,“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同上)仁是内心之守,义是外在之行,内有仁之为守,外有义之为行,便可以达到至诚的境界。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就能神明而又有理智,就能感化别人,进而改变别人。能变能化则与天德相合,“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同上)故诚是君子修身之本,“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同上)这无疑与《中庸》“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是同一思路。
在《荀子》中出现了“诚信”合称的情形,《荀子·不苟》中说:“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致士》中也说:“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我们发现,在《荀子》中,“诚”往往与“神”密切关联,“神”是“诚”之效用的一个特有的表达,指的是奇妙莫测的变化。《易·系辞上》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易·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晋韩康伯注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也。故曰阴阳不测”。《荀子·天论》中对“神”也有表述:“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北宋周敦颐《通书·顺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我们就不难发现,诚信之“神”神就神在其自然而然却有变化莫测的状态,人们说不清楚其中的道理,却享受着它生化万物的特殊功用。
第二,在人性论上,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荀子主张“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同上),即所谓“化性而起伪”。什么是“性”与“伪”呢?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同上)在荀子看来,人性生来是恶的,所谓的善只是人经过可学、可事的后天努力而达到的成果。因此,“辞让”、“忠信”、“礼义”等致善的思想与行为,都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而完全是人为的。既然忠信也是经过后天人为才能达到,那么能不能达到也就被看作是区别人之等级的一项重要指标:“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是,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日常的言论必定诚实可信,行为必定小心谨慎,不去效法流俗的做派,也不敢自以为是,如果能做到这样便可以称作是忠厚之士。言语经常没有信用,行为常常不忠贞坚定,唯利是图,无所不为,如果像这样做的话便可以叫做小人。这里,荀子是从言行的角度来讨论诚信问题的,其实,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荀子·大略》中说:“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这段话是说,不能踏踏实实去做的人,言论一定是言过其实;不坚守信用的人,说话时一定会装出十分诚恳的样子。所以,《春秋》赞美胥命,《诗经》反对屡次盟约,它们所讲的道理都是一致的。精通《诗经》的人不去解说,精通《周易》的人不会为人占卦,精通《礼经》的人不去替人行相礼,他们的用心相同的。这里的“胥命”指古代诸侯相会时只是重申约言,并不举行歃血而盟的仪式。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正是要告诫人们言必信,行必慎,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做到诚信的人,而能够言行一致的人被荀子看作是国家的宝贝。《荀子·大略》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一个人对不仅嘴上能说会道,而且能身体力行去践行的,这是国家的宝物;嘴上虽不能言善说,但能身体力行去实践的,这是国家的重器;嘴上能说但不能身体力行的,这样的人是国家的用具;嘴上说得好听,而行动上做得很差的,这样的人是国家的妖孽。治理国家的人要敬重那些国家的宝贝,爱护那些国家的重器,任用那些国家的用具,清除那些国家的妖孽。对于君子而言,他们“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欲人之亲己也”。(《荀子·荣辱》)但是,荀子也知道,君子可以做到诚信为人、诚信处事,但能不能被当作国宝、重器甚或用具则是另一层面的事情了,但君子一定要坚持他们的操守。《荀子·非十二子》云:“士君子之所能为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这段话告诉我们,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尊重自己;能够做到诚实守信,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信任自己;能具备可被任用的才能,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任用自己。君子只对自己品德不好感到羞耻,而不对无故被人污辱感到羞耻;对自己不讲信用感到羞耻,而不对不被人所任用而感到羞耻。所以,君子从不被赞誉所引诱,也不会被诽谤所吓倒,他遵循正道而行,时刻端正自己,意志坚定,决不为外物所动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君子。我们看中国古代有无数的志士仁人不被统治者们所赏识,有些人可能选择了沉沦,有些人可能选择了暴戾,也许最可贵的还是那些坚守道德底线的真君子们。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式的“大丈夫”和荀子所言的“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式的“诚君子”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第三,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强调诚信政治的重要性。荀子的诚信思想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他非常重视对历史上诚信事例的总结,借以发挥自己对于诚信的看法。《荀子·强国》在总结桀纣失国而汤武成功时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桀、纣之所以身亡国灭原因在于他们的污漫、争夺和贪利的本性以不行礼义、不务忠信的作为;相反,正是因为汤、武遵循礼义、谦让、忠诚守信之道,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喜爱。他们拥有四五万人以上的国家,能够强大常胜,不是靠人多的力量,而在于崇尚信用;地域在数百里以上的国家,能够安定坚固,靠的不是地大物博的力量,而在于注重整顿政事。
荀子在总结春秋五霸的历史时,也指出了诚信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荀子·王霸》中荀子把治国之道分为“王”、“霸”和“亡”三个等级,《荀子·天论》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在荀子的心目中,“隆礼重贤而王”是最高理想,“重法爱民而霸”次之,“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则根本不足语于治道。“隆礼尊贤”则“义”立,“重法爱民”则“信”立。故荀子又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所立不同,结果迥异,所以对于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需要谨慎选择,仁德之人一定要弄明白。在论述霸道时,他认为霸主们虽然没有把政教作为根本,没有追求完备的礼义,没有完善礼法制度,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意方针策略,强调劳逸结合,谨慎积蓄力量,加强战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像牙齿一样契合,于是天下没有人敢同他们对抗。五霸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能从一个偏僻落后的国家而成为威震天下的霸主。一句话,是取信于天下让他们称霸。那么如何才能取信于天下呢?荀子指出要靠“信法”与“信士”。所谓“信士”,指的是千年不渝地信守礼法的士人。关于“信法”,荀子主要指的是政令和赏罚要符合信的标准。荀子说:“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同上)这两句分别指出政令和赏罚要以信为标准。《荀子·成相》有云:“听之经,明其情,参伍明谨施赏刑。显者必得,隐者复显民反诚。”这句话是说,处理政事的要领在于弄清实情,反复调查清楚之后而谨慎地施以赏罚。明显的要弄清,隐藏的弄明白之后人民才能回归真诚。总之,荀子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人的生命很有限,而诚信的道德以及信法、信士却是长久的、永恒的。国家讲诚信,使用信法,任用信士,就会强盛;不讲诚信,不用信法,弃用信士,则不免危削。这是荀子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的道理。
第四,在信与义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提出“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强国》)的观点。上文已经提到,荀子是非常重视礼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的。《荀子·议兵》里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他认为礼义不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而且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在。“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荀子·修身》)因此,“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一言以蔽之,“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的表现形式是“分”,“礼也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程以立数,礼以定伦。”(《荀子·致士》)。他认为礼的作用,在于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于分辨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角色,并使各等级之人都能养其欲,给其求。只有明确规定个人的职守和地位,才能有群居的生活,否则,“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荀子·富国》)这里“明分”的内容,除指不同的职业和分工外,最根本的内容是指等级制度。在荀子看来,如果社会成员的地位都相等,欲求也就都一样,那么物质生活资料就不能充分供给,势必发生争夺和混乱的现象。所以,先王制定礼义,对人的等级名分加以区别,使有贫富、贵贱之等级。在他看来,不同人的不同道德水准和素质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就此,他在《荣辱》中将“蒸民”分为天子、诸侯、士大夫、官人百吏、庶人、奸人等六类。我们说“义者宜也”,结合荀子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荀子论“义”是和礼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礼之分的功能才会造就“义”的存在。所以,在《荀子》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礼义合称的现象。质言之,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指“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荀子·荣辱》);“义”谓分而“各得其宜”,各当其称,使贵贱长幼皆有所节,是对礼制正当性的规定。当然,义还是“宜于等级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使等级之分(礼)得以实行的道德力量。[3]“义以分则和”(《荀子·王制》),行义以等级之分为据则能和谐等级关系,“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同上)。因此,礼义相须,密不可分。荀子还强调“礼义”由圣人所作,“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
“义”可以说是一种总的规范,是对一种能够使各阶级各有分属、各得其宜的社会关系的描述性概念。当然,这种能分能群的能力只有人类才能具备,所以,荀子讲“义”作为人与草木禽兽的重要区别之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如果君主不顾这礼义之分,那么就会产生混乱,因为“义”本身就有限制奸恶的作用。君主是臣民的表率,臣民与君主的关系就如同回声响应声音,影子与形体相似一样。所以,作为君主,不能不慎重行义。义对内可以节制人,对外可以节制万事万物,对上可以安定君主,对下可以协和百姓。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十分恰当,这就是“义”的实际内容。既然如此,那么,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要以义为根本,其次就是要守信用。夏禹、商汤以义为本,务求守信,因而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抛弃义,不守信,因而天下大乱。因此,作为君主,一定要慎重地对待礼义,致力于诚实守信,然后才能成功。这就是作为君主的根本原则。这里的“义”与其说是“信”的原则,不如说是“信”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义为本而信次之”和孔、孟所论述的信与义的关系有所不同,这里强调的是在有礼有分、各个等级各守其职的前提之下,才有讲信用的必要。那么在这样一个有礼义的社会里,如何讲信用呢?荀子认为,这其实和君主贵义、敬义的作用机制一样,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荀子·君道》里提到,如果君主喜好玩弄权术,那么臣下百官中那些好搞欺诈的人,就会乘机进行欺骗。相反,如果君主喜欢礼义,崇尚贤德之人,任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私利之心,那么臣下也将非常谦让、非常忠诚守信,严格遵守做臣子的本分了。如果能做到这样,即使是在老百姓中,不用验证符节、辨认契券,也会互相讲信用。可见,在塑造诚信的社会风气上,君主要起着绝对的引领作用,“君主端正诚实,臣民就老实忠厚;君主公正无私,臣民就坦荡正直;君主如果信誉卓著,民众就会欢呼响应”。[4]当然不要忘了,这一切的前提是有君与民的区分,也就是先有“义”的存在了。
3 小结
总之,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荀子诚信思想更加注重人为的成分,也就意味着荀子倾向于从外在政事上强调诚信的重要性;荀子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他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屡次强调诚信之于统治的重要性;荀子的诚信思想还与他特别重视礼义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礼义是诚信的前提,没有君臣之分,也就不会有君主作为诚实守信的楷模去构筑起社会整体诚信的良好风气。可见,荀子的诚信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此外,荀子还明确提出了“诚信”的命题,认为讲诚信是对社会上所有人提出的要求,还把“信”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尺度。可见,荀子的诚信思想极为系统和丰富。因此,可以说:“荀子综合百家之学,把先秦儒家的诚信思想发扬光大,并使得先秦儒家诚信思想更加系统和完善。因此,荀子的诚信思想之形成标志着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趋于成熟。”[5]
[1]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382.
[2]王公山.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5.
[3]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11.
[4]傅礼白.中华伦理范畴·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2.
[5]唐贤秋.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0.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07
B222.6
A
1004-0544(2015)01-0035-04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D082);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思想史基本概念研究”项目。作者简介:刘乾阳(1987-),男,山东邹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