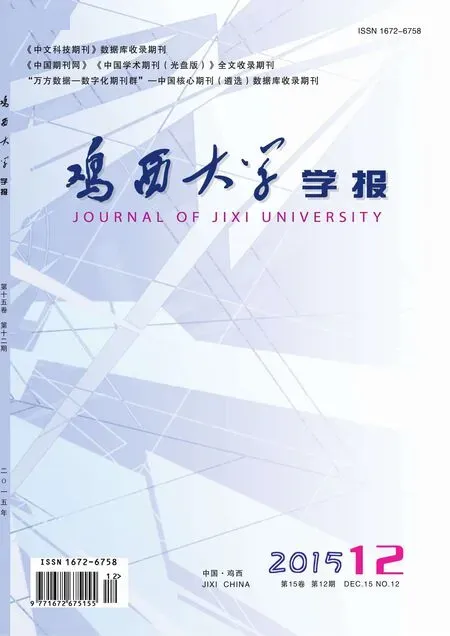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与朱熹批判管窥——以几十篇与朱熹密切相关的提要为切入点
2015-03-17彭纬璇
彭纬璇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四库全书总目》与朱熹批判管窥
——以几十篇与朱熹密切相关的提要为切入点
彭纬璇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摘要:朱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且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乾隆朝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涉及朱熹的地方很多,对朱熹及其著作进行评判时往往抱着十分矛盾的心态,亦褒亦贬,时褒时贬,而且一种力求宽厚博大、公正平允的力量贯穿于这种矛盾心态的始终。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朱熹;批判;矛盾心态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儒学家,他的学说在南宋以后被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众多经典著作得到了广泛流传,《四书章句集注》以及部分其他的经学著作还被列为官学课本,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乾隆朝在结集前人遗书,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1]就成了《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如不特殊说明,均指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在古典文献的保存、分类、评介、文字考订等众多方面均具有独特成就,是中国古典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基于朱熹与《总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研究《总目》对朱熹及其著述的态度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有意义了。近几十年来,《总目》研究的成果颇丰,最卓著的当属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但是在《总目》与朱熹批判研究方面,目前学术界涉及尚少。笔者不揣固陋,搜集了几十篇与朱熹密切相关的《总目》提要,①又翻阅参考了《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中的部分相关提要,对《总目》与朱熹批判问题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最终撰成此篇,希望为《总目》与朱熹批判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清代乾隆、嘉庆两朝,以考据为主的朴学之风盛行,乾嘉学派蔚为大观。《总目》的总纂官纪昀便是乾嘉学者。“由于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大,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的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1]纪昀作为朴学大盛时期的乾嘉学者,其崇尚汉学的学术立场必然广泛深刻地影响到《总目》的编撰。因此,虽然《总目》在经部总叙及其各小序中一再提及要消除汉宋门户之见,其实际的“尊汉抑宋”倾向却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朱熹作为“宋明理学儒学的集大成者”,[2]其学说在宋以后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崇高的地位在 “尊汉抑宋”的《总目》里就有些水火不容了。依笔者之见,《总目》对朱熹持有的是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得不肯定他的非凡学识以及在封建王朝中的崇高地位,并为他的种种“离经叛道”行为“开脱”;另一方面,又屡次以或避而不谈,或不置褒贬,或委婉含蓄的方式对他进行质疑与批判。当然,基于馆臣总体博大宽厚、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态度,《总目》在很多地方对朱熹的批判还是不盲从古人旧说,力求公允的。
一承认其重要地位,赞扬其学识,开脱其“罪责”
《总目》的史学观念较强,在各部总叙及其各类小序中,往往能用简练的语言勾勒出该类著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目·经部总叙》在谈到宋代程朱理学时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其后又对经学历史总结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总目》在经学史“大纲”中认为宋学最大的特点是疑古,并且拿它与汉学相提并论,肯定了其“精微”的优点。宋学的代表是洛闽,即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因此,实际上总叙在此充分肯定了朱熹及其学说在经学史上的重要甚至崇高的地位。《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经学著作之一,宋末、元、明、清,此书逐渐成为官学课本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结合经部四书类小序中的“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等句与《四书章句集注》的提要“特其(《四书》)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等句可见,馆臣虽未对朱子予以极力赞扬,但对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之长久以及其为《四书》定名的草创之功还是予以承认的。
中国历来重视“知人论世”,在众多著述朱子生平事迹的年谱中,清朝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是最为精善的一种。此本《朱子年谱》的提要说:“然(此书)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异审同之辨,元元本本,条理分明。无程瞳、陈建之浮嚣,而金谿紫阳之门径,开卷了然。”虽是赞扬此书,但也可得出馆臣对朱子生平的总体概括,即“求端致力”“考异审同”,是勤奋严谨之人。《四书章句集注》提要中的“ 镕铸群言”,“剖析疑似,辨别毫釐”等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朱子年谱》后面著有此小类(属史部传记类名人小类)的案语,开头便是:“此门所录,大抵名世之英,与文章道德之士也。”充分肯定了包括朱子在内的这类人物卓越超群的人品学识。②清康熙皇帝十分崇尚朱子,曾命大学士李光地编纂《御纂朱子全书》,其《总目》提要云:“然则读朱子之书者不问其真赝是非,随声附和,又岂朱子之意乎哉!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乃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分为十有九门。金受炼而质纯,玉经琢而瑕去。读朱子之书者,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于多岐矣。”大意是读朱子之人,不能明辨是非真伪,蒙蔽了朱子的光辉,有鉴于此,圣祖仁皇帝以其睿智高深的学识“炼金琢玉”,编成此书,以指导学者后生走向朱子之学的正轨。“明清君主敕纂理学著作的私意之一,在于自我标榜,为臣民树立圣贤形象”,[3]康熙皇帝编纂此书也不例外。但是,其“自我标榜”与“树立圣贤形象”所借用的人物——朱子又反映出清皇帝以及撰写提要的馆臣对于朱子之学识的肯定与褒扬。
宋代“疑经”之风较为盛行,疑经的参与人数多,涉及的经书范围广,影响广泛深远。“朱熹是疑经的代表之一。”[4]《总目·经部总叙》里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指的就是程朱的“疑经”行为。但应指出的是,此处馆臣对于程朱的疑经行为有歪曲和夸大的成分。清代朴学之风较盛,四库馆臣也大都是尊经崇圣的乾嘉派学者,他们对于朱熹的疑经行为实际上是很不满的。但大概是基于朱熹在宋以后官方的崇高地位以及他不可否认的杰出学识,馆臣在提要中多次回护朱熹,为其“离经叛道”的行为开脱。朱熹怀疑的经学著作主要有《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孝经》等。朱熹怀疑《诗序》,是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影响巨大。然而,《总目》经部诗类小序对朱熹却避而不提,而对其三传弟子王柏加大批判,说:“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这实际就是一种回避、回护的行为,当然,我们也可将之理解为一种无言的、旁敲侧击的批评。在《诗集传》的提要中,馆臣为朱子“攻《序》”的“行径”寻找托词:“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意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作为杰出的经学家、思想家,朱子当然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怎么会因为吕祖谦“太尊《小序》”而“尽变其说”?馆臣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还是引杨慎之说为朱子开脱,真是用心良苦。[5]朱熹也怀疑《尚书》。《总目》经部书类小序采取了与诗类小序同样的回避,或者说旁敲侧击的方法,说:“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又是对朱子避而不谈,而直言不讳地批评朱子的弟子(以及三传弟子)。《总目》中这种手法还不少,兹不一一赘述。除此之外,“对于朱熹引领的水火争诟,《总目》认为是后学混淆未达其意”[5](即使《总目》对“门户”“朋党”很反感),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开脱办法。
二以避而不谈、不置褒贬及委婉曲折的方式进行质疑与批判
据《总目·凡例》,提要的作用是简介“作者之爵里”,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本书之得失”,并辨订“文字增删,卷帙分合”等。然而据笔者观察,《总目》中部分朱熹的著作(或与朱熹相关的著作)的提要并不符合这些撰写要求。这些提要往往详于辨订“文字增删,卷帙分合”,而对于“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本书之得失”部分却较为简略,有时甚至完全不提。这并非馆臣的疏忽,实在是他们刻意而为。言多必失,因此避而不谈;考察得失,便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不置褒贬。馆臣在撰写这些提要时大概着实费了些心思。
前面已经论及《诗集传》的问题,此处再谈一些。此书的提要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朱子“注《诗》,亦两易稿”,前“宗《序》”,后“攻《序》”的问题,之后则用大量的篇幅辨订“文字增删”。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朱熹与“横删圣籍”的王柏之间的师承关系,也难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馆臣对于朱熹疑经的褒贬态度,但仔细阅读,会发现褒贬自在其中。提要在“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后,笔锋一转,开始介绍“钦定《诗经汇纂》”,说它“虽以《集传》居先,而《序》说则亦皆附录,允为持千古之平矣”。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朱熹的疑经攻《序》的做法是有失偏颇,不足取的。又如《朱子语类》,它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对于研究朱熹的思想具有必不可少的价值。而其提要主要论述此书的源流版本及卷帙分合,对于此书特有的全面记录朱子在各领域之言论、思想的文献学价值却少有提及。这也是刻意而为的。又如《晦庵集》的提要,通篇在考订版本源流,而对此书(别集)及其作者的得失不置一词,实在是“避”得有些明显了。又如朱子后人朱玉为其编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的提要,主要记载此书的卷帙门目,对此书收入的朱子之著作未加丝毫评论,也是馆臣避而不谈,暗含褒贬的。
另外,朱子最经典的著作——《四库章句集注》的提要也多少能证明这一论点。如前所述,馆臣对其并未大加称赞,最正面的评价也不过是“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主要讲朱子对于《四书》用力之勤、《四书》之精微以及《四书》高于他的其它著述的特点。这种评价着实与其在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崇高地位不符。也与《荟要》提要的“朱子融洽众说,著为《集注》,心得之妙,超出前儒”,[6]“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以毕生之力为之,至精至密。数百年来,一字一句,儒者皆奉为指归”,[6]“《章句》多出新意,《集注》熔铸群书”[6]的高度评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三总体宽厚博大、力求公允的批判态度
乾隆朝秉承康乾盛世的强大国力和恢弘气象,又加之纪昀、陆锡熊、王念孙、邵晋涵、戴震等四库名馆臣的渊博学识,《总目》在总体上形成了兼收并蓄、力求公允、宽厚博大的学术批评态度。馆臣对于朱熹的批判虽含有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但总体还是客观、公允的。
朱熹对《四书》研究用力颇勤,他倾注毕生心血,撰成《四书章句集注》,还在人生不同阶段撰成《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等书。由于朱子在世时间较长,思想前后变化较大,且多次删改著作内容等等原因,这些书籍的内容往往有前后矛盾之处。《总目》评价朱子的《四书》相关著述涉及这点时,态度是公正、客观的。《四书或问》的提要中说:“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又引用朱子自己的话说明朱子对于这些矛盾之处“亦不讳言”。然后说:“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於《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这是在提醒后人朱熹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要以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评价其矛盾之处,不可以于一书中“偶摘数语”,指责攻击另外的书编撰有问题。
《孝经刊误》一书的提要甚是有趣。如前所述,朱子对于古文《孝经》是加以怀疑的,还进行了删改。然而朱子怕自己背上妄改经典的骂名,在此书的《自记》中拿胡宏和汪应辰当挡箭牌,说自己是受了他们的启发才悟到“《孝经》之可疑”。然而这些没能逃过馆臣的火眼金睛,提要列出了几条《朱子语类》中朱子怀疑《孝经》的言论,然后说:“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令人惊讶的是,反感质疑先圣的馆臣对“阴用是(指删改经文)例”的朱子,居然又评价道:“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这是引用陈振孙的话承认了朱熹的远见卓识、非凡勇气。大概馆臣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最后还是宽厚博大、力求公允之心战胜了“尊汉抑宋”的门户之见。朱熹作《楚辞集注》,往往运用改读字音的叶音法使看似不押韵的《楚辞》诗句押韵。这实际上是由于朱熹不懂音韵学而产生的不科学的解释法。馆臣对此并不讳言,较为委婉地说:“然则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也是一种宽厚的论人态度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综上所述,《总目》对于朱熹及其著述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朱熹在封建王朝中的崇高地位及其非凡的学识,并为其种种“疑经辨伪”开脱;另一方面,又对他的“空疏”的理学思想、“狂妄”的“离经叛道”行为暗中不满,并予以曲折的表达。而贯穿此矛盾心理的,又是总体宽厚博大、力求公允的学术批判态度。
注释
①据笔者粗步统计,殿本《总目》中,“朱子”这一词条共出现一千七百余次,此外“程朱”“晦庵”“紫阳”等词条也分别多达几十甚至上百次;《总目》共两百卷,有一百五十七卷涉及“朱子”一词。由此可见朱子与《总目》的密切关系。由于时间、精力的关系,笔者只以几十篇与朱熹密切相关的提要为切入点来撰写此文。所谓“密切相关”,首先是指朱熹的著述,其次是指《朱子年谱》《朱子语类》这类影响巨大的传著朱子的书,此外,还包括清朝黄帝、朱子后人、朱子弟子这些特殊人群传著朱子的一些书。
②传记类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小类。朱子未列入“圣贤”一类,是因为馆臣为“圣贤”这一类设置的门槛很高,只记孔、孟以及孔、孟在世时判定为“圣贤”的人。见“圣贤”类及其存目的案语。
参考文献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1.
[2]张立文.朱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3]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67.
[4]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
[5]张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朱熹《诗集传》叙录中态度笔法平议[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2):94-96.
[6]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97-198.
Class No.:I206.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and Zhu Xi's Criticism
Peng Weixu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China)
Abstract:Zhu Xi is a master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had written a lot books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 the master work 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has been compiled which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The character Zhu Xi is often mentioned in this book. There are both praise and criticism for Zhu Xi . General speaking, A fair and equitable criticism is mad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Key words:Catalogue of Imperial Collection; Zhu Xi; criticism; ambivalence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758(2015)12-0115-4
作者简介:彭纬璇,在读硕士,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