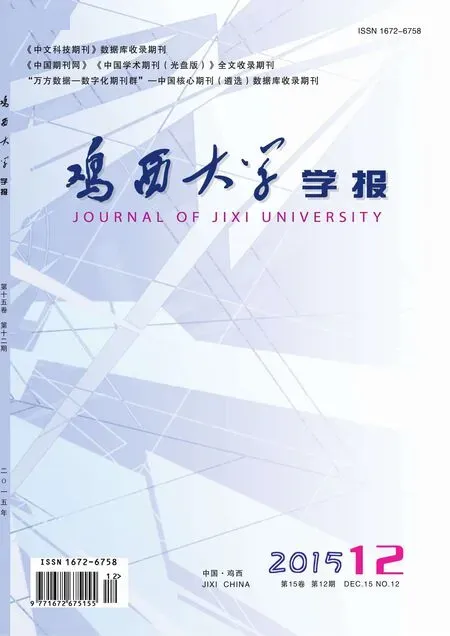陆贾民本思想探微
2015-03-17孙珊珊
孙珊珊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陆贾民本思想探微
孙珊珊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摘要:由于连年战争,在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陷入“大饥馑”的困乏局面。鉴于对民心与政权关系的深刻认知,陆贾在向刘邦总结秦亡教训和“古成败之国”经验的同时,适时提出“轻徭薄赋”“崇俭黜奢”“重农轻商”“约法省刑”的民本主张,从而为汉初采取“与民休息”的统治方针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西汉经济的恢复和政权的稳定。
关键词:陆贾;民本;轻徭薄赋;崇俭黜奢;重农轻商;约法省刑
在西汉建立初期,因秦末连年战争,特别是楚汉之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1]社会财富极度贫乏,不但“民无盖藏”“鬻子孙”,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加之严重的灾荒疾疫,田野荒芜,粮价飞涨,“米石五千”,社会陷入“大饥馑”的困乏状态,甚至出现“人相食,死者过半”[2]的惨象。百姓的生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社会动荡不安。陆贾亲身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和政权递嬗的过程,他从中看到了人民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性,民心的向背是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所在。所以,在汉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陆贾基于“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3]适时提出“轻徭薄赋”“崇俭黜奢”“重农轻商”“约法省刑”的民本主张。
一轻徭薄赋
秦王朝赋役繁重,当时全国约有2000万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各自约用人役70万,北伐匈奴调兵30万,加上修长城、戍五岭、修驰道等工程动用的人数,总共约达3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5%。[4]无论是兴建土木工程还是戍边征伐,其所需的劳动力和财力都不可小觑。秦朝政权为了能够得到这些人力和物资,就不得不进行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于“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2]而赋役的繁苛也严重限制了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给农业经济造成极大危害,以致于“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糜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2],百姓连基本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
陆贾身受秦朝赋役繁苛之苦,也深深地意识到秦朝的赋役制度乃是激起农民起义,进而导致秦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他向高祖刘邦进言西汉政权理应采取“轻徭薄赋”的恤民政策——“国不兴不事之功”“稀力役而贡献”。[3]“国不兴不事之功”,即国家不随意兴建无利于国计民生的土木工程,这样就可以相对地减少物资的消耗以及赋税的征收,而“稀力役”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对减轻了劳动力的徭役负担,保证劳动力优先使用于农业生产,从而鼓励和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显而易见,陆贾这一民本主张,对汉初的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汉高祖刘邦因亲身经历而对民心所向与政权存亡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对陆贾“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也比较容易接受,故在其称帝后便积极推行“轻田租,十五税一”的田赋制度,同时采取“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2]的税收政策,量出为入,意在防止无节制地向人民加税。惠帝、高后时期“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因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文帝即位后“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因而“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2]他多次颁发诏书,要求“务省徭费以便民”;[2]在其统治时期,曾多次下诏减少田租,甚至在公元前167年,全免天下田赋。景帝统治时期也曾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2]汉初所采取的这些“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是在秦末战争后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的历史背景下,统治者对民心力量的认识与肯定的结果,对于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新兴的西汉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二崇俭黜奢
陆贾在主张“轻徭薄赋”的同时,积极呼吁“崇俭黜奢”。在他看来,崇俭和轻徭薄赋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君主崇俭,才有可能实现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他赞赏伊尹“修达德于草庐之下”[3]、颜回“一箪食,一瓢饮”[3]的节俭精神,并谴责骄奢靡丽的行为,在陈述“古今成败之国”经验教训的同时,把君主过度奢侈看作是其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以秦始皇为例,认为其“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3]其实,在秦都咸阳和故都雍,本就有不少奢华宏丽的宫殿,但始皇仍不满足,在兼并六国时,就每灭一国便仿建“其宫室,坐之咸阳北阪上”,以致于“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统一六国后,更是大肆扩修,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1]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又“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1]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据《史记》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1]无论史料中关于阿房宫的描述是否夸张,但秦始皇穷奢极欲之面目却表露无遗。在陆贾看来,君主如果过于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如秦始皇,为了一己之私而广建宫室、大兴土木工程,向人民大肆征发徭役和赋税,从而影响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长此以往,必然会激发民怨,导致民心尽失乃至国破身亡。因此,君主必须崇俭才能使“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3]
君主作为一国之君,是百姓效仿的重要对象,为民之表率,“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3]正如荀子所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则水圆。”[5]因此,陆贾认为君主应格外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远荧荧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3]努力约束自己的行为,崇俭黜奢,使自己的行为更能合乎君道。另一方面,君主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崇俭”行为来教育和感化民众,行“无言之教”,从而使“璧玉珠玑,不御于上,则玩好之物弃于下;琱琢刻画之类,不纳于君,则淫伎曲巧绝于下”。[3]而汉初的几位统治者,也确实受到陆贾“崇俭黜奢”思想的影响。他们一改秦朝君主的奢华作风,带头躬修节俭,其中尤以文帝为甚。汉文帝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2]他曾想造一“露台”,却因需耗资百金而作罢。即便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2]
三重农轻商
西汉是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专制国家,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西汉初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2]非但没有实现“仓廪实”的基本需求,相反,社会还呈现出“大饥馑”“人相食”的困乏局面。因此,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讲,他们有浓厚的重农思想不难理解,而心系天下、以天下之忧为忧的陆贾,自然也不例外。
陆贾在《新语》一书中,虽然没有专篇论述其“重农”主张,但却在多处对弃本逐末的行为进行谴责。他认为世人“释农桑”转而“入山海,采珠玑,捕豹翠,消筋力,散布泉,以极耳目之好”[3]是“快淫侈之心”的荒谬行为;而“五谷养性,弃之于地,珠玉无用,宝之于身”[3]的做法,也不利于自身道德的修养。他以古代圣人贤主为例,认为“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3]杜绝了“淫邪之欲”“琦玮之情”,因而天下能够大治。所以,只有“匹夫行之于田,治末者调其本”,才能“养其根者而枝叶茂”,[3]实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陆贾的重农抑商主张意在恢复汉初的农业生产,虽然不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尤其还处于刚脱离战乱不久,亟需恢复农业生产以解决百姓温饱问题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是必须的、无可避免的。而在西汉建立初期,汉廷也的确采取过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进行限制。但惠帝以后,随着黄老政治的盛行,政府对商人的限制大为降低,甚至在汉文帝统治时期除“盗铸钱令”和弛山泽之禁。除“盗铸钱令”和驰山泽之禁政策的施行,虽然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背本趋末”和“淫侈之俗”等不良风气,也导致政府可以直接掌管的编户急剧减少,不利于国家赋税的征收、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初统治者没有将陆贾的这一“重农轻商”主张贯彻执行,是对于汉初应“劝农务本”以安民心而做出的错误判断。为缓解这一局面,文景帝时期继续采取减轻田租的办法,期望把百姓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农业生产上来。[6]由此可见,陆贾“重农抑商”的主张符合汉初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其“因世而权行”的正确选择。
四约法省刑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人民统治的严酷性,集中反映在法网的严密上,尤以秦代法律最为突出,这也是其处于封建法律创建初期所致。秦法内容细碎,刑罚种类繁苛,林剑鸣先生就曾对秦法的种类做过统计,在他看来,秦朝实行过的刑罚应不少于二十种,仅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就有“隶臣妾”“斩左止”“劓”“宫”“笞”“车裂”“黥”“弃市”“腰斩”“戳”“枭首”“剖腹”“囊扑”“烹”“绞”,除此之外,还有“蒺藜”“鬼薪”“白粲”“从死”“三族”“诛九族”“参夷”“籍没”“连坐”“阬”等。[7]同时,秦代的刑罚也十分严酷,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比如说,对死刑之外的徒刑就未曾设定期限,像“隶臣妾”“鬼薪”“白粲”等刑徒,一经判定则为终身。这种情况一直到汉文帝颁发减刑诏令才得以转变,徒刑有了具体的服刑年限。总之,秦法法网之严密、条目之繁苛、刑罚之严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最为突出的。百姓轻易间就会触犯法律,从而导致秦末社会刑徒众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2]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对此,陆贾明确地指出,“秦非不欲治也”,[3]而是错误地选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只知以法治国,“以刑罚为巢”以致于“举措太重、刑罚太极”,[3]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3]法律刑罚若使用不当,只会激化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因此,陆贾谏言治国者应“以仁义为政”,以德治民,而不是片面依仗严刑酷法,“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3]当然,陆贾不赞成治国仅靠严刑酷法并不意味着他轻视法治。法律刑罚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但用法需适度,“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3]他劝诫统治者“虐刑则怨积,德布则功兴”,[3]“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3]也就是说,治国要以法为辅,法律只是起辅助作用,其最主要的还是要依仗统治者施行仁政;法治只能作为仁政的调剂和补充。这种融合了法治思想的德治思想,陆贾称之为“中和”——“行中和以统远,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渐渍于道德,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3]
陆贾的这一主张对汉初统治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也与汉初统治者的身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汉初的统治集团,如刘邦、萧何、曹参、张苍等人都曾是秦王朝的中下层官吏,是秦朝严刑酷法的执行者,因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秦法的影响;但同时秦法繁苛,刻薄寡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秦法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深知黎民百姓对秦法的厌恶和排斥。为收揽民心,刘邦在入关之初就曾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余悉除去秦法。”[2]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元前202年,刘邦命萧何依秦法作律九章,秦法中的族诛法、连坐法、诽谤法等苛法均得到了恢复。汉十一年以后,受陆贾“约法省刑”思想的影响,汉统治政策发生转变,虽未明文废除挟书、诽谤、夷族诸酷法,但在诛杀黥布时就没有实施族诛法。此后直到武帝即位约六十年间,多有轻刑政策,如公元前191年(惠帝四年)“除挟书律”;[2]公元前187年(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2]公元前179年(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2]法令显然趋于宽松,但汉初之法,毕竟其性质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百姓的,因此,其镇压剥削百姓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所谓的“除”“减”之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因此,对于汉初的除秦苛法,我们也不能估价过高。随着汉初约法省刑的推进,民间的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变化,“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奸之俗易”,使“吏安其官,民乐其业”,[2]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作为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的民本理念可以说是对秦亡教训的一种反思——秦朝统治者片面注重法治,“举措太重、刑罚太极”,以致错失民心,二世而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陆贾希冀可以建立一个老少怀安的“至德之世”:“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3]当然,在当时那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背景之下,陆贾的这一理想政治明显是一种空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所希冀的“至德之世”意在强调君子治国,应行“自然无为”之政,不能肆意实施扰民的政策。这是他对汉初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也是其民本思想的充分体现。他将先秦流传下来的民本理念纳入到汉朝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治国方略之中,[8]为汉初统治者制定和实施“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而为维护西汉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877,412,239,241,256,256.
[2]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7,1127,1137,2800,1127,1097,1097,116,1135,134,134,1127,1096,23, 90,96,110,1097.
[3]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30,167,101,104,77,111,77,63,167,167,45,45,55,71,71,71,29,172,35,131,74,132.
[4]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52.
[5]安继民,注译.荀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93.
[6]中国秦汉史研究.秦汉史论丛(第2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50-151.
[7]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9-130.
[8]王云涛.两汉民本思想述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17.
Class No.:K234.1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On Lu Jia’s People-based Thought
Sun Shansh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Due to years of war, the economy remained deep in recession and all the society was fallen into the great food shortag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ecause of this and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 feeling and the regime, Lu Jia put forward some people-based policies of reducing the burden of taxation and cost, praising frugality and objecting extravagance, valuing?agriculture above commerce and reducing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penalty. What’s more, these people-based policie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direction for the policy of “taking rest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ed th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Lu Jia; people-based; reducing the burden of taxation; praising frugality and objecting extravagance; valuing agriculture above commerce; reducing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penalty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758(2015)12-0036-4
作者简介:孙珊珊,在读硕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